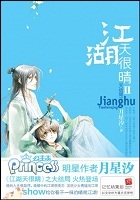
第12章
天,终于完全黑了。
看见那盏灯之前,朱灰灰肋下挟着一只大公鸡,正在树林里飞奔,心情很愉快。
一头花溜溜的大肥猪跟在她的后面,挪动着四条小肥腿,跑得哼哼唧唧,一条小尾巴快乐地甩啊甩。
朱灰灰和朱花花兄弟俩没法子不愉快!
虽然刚才摸进村子偷鸡的时候,被五六条大狗狂追,可是她和它仗着长期配合出来的机灵劲儿,最终安全逃脱了!
眼见已逃得足够远,再也不怕别人追上,朱灰灰终于停住脚步。
摸摸空空的肚子,看看手中的肥鸡,她感叹道:“大侠勿怪!虽然小的答应你不再偷东西,可是实在迫不得已,失节是小,饿死是大。”
这句话好像是从前某一天,她靠在一家书馆的墙根晒太阳睡午觉的时候,听教书先生讲的。
她东张西望地想要找一个地方,将鸡洗剥干净,生火烤了,可是看清楚周围的环境后,不禁皱起了眉。
稀疏的树林,阴森森的野外,刚才她只顾逃跑,没注意看路,这是哪里?
正在疑惑的时候,前面远远的地方,倏然亮起一盏灯。
昏黄的灯火摇曳着,在黑暗里,就像一只浑浊的眼,忽明忽灭,不住地眨动。
朱灰灰呆了一呆,心中升起诡异的感觉。
这盏突然亮起在旷野中的微弱灯火,让她想起很久以前,一个同样无星无月的晚上。
那天夜已经很深了,她没有找到食物,空着肚子抱着花花,走在一个长长的暗巷里,又冷又饿。
身后,突然传来脚步声!
孤寂无人的巷子,那声音异常沉重,一步一步,仿佛踏在她的心上。
一种没来由的恐惧让她拔腿飞逃,甚至不敢回头瞧一瞧身后是什么!惟恐脚步一慢,会有一张白森森的利口咬在自己的颈子上!
这盏骤然亮起在荒野中的灯火,便像那天晚上的脚步声一样,点亮了她心底莫名其妙的恐惧。
她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哆嗦,缩缩脖子,悄悄地自言自语:“算了,老子最近倒霉,还是离那种地方远一点为好!”
拎着公鸡的翅膀,往花花的屁股上踢了踢:“花花,我们走另一条路吧!”
花花只是哼了两声,没有发表其他意见。
寂静如死的林子里,便是这几声“哼哼”,也令朱灰灰的心温暖了一些——她毕竟不是一个人,虽然娘不要她了,大侠不要她了,先生和夫人也不要她了,至少她还有花花作伴呢!
林中其实并没有路,她只是随便找了个方向,胡乱地走,可是没走出二里,又停下了脚步。
前方不远处,也亮着一盏灯。
不用多话,立刻掉头,再换一个方向。
这次还没走出半里路,眼前,又飘起微弱的灯光。
那是一间小小的屋子,房子已经很破,窗户开着,遥遥可见窗前的木桌上放着一盏油灯。
幽火飘摇,一灯如豆。
再远些,是一些影影绰绰的土馒头。
有的前面立着石碑,有的没有;有的长着长长的荒草簌簌作响,有的则光溜溜的寸草不生;有的上面飘着冷绿的磷火,有的裂开露出白森森的骨头……
“不是吧!”转来转来,转到个乱葬岗子!
朱灰灰打量着前面,大叫晦气。自己只不过想找一个地方把鸡烤熟了,跟花花饱餐一顿,然后守着火堆睡一觉而已!
这个地方怎么就这么难找呢!
她转身刚要走。
头顶突然传来一阵怪笑声,她吓得一抖,手中的鸡掉在地上。随即听到空中有扑翅的声音,抬头一看,有一只夜猫子拍着翅膀掠过,飞到另一棵树上。
她将手按在胸口,感觉心脏怦怦乱跳,不禁在肚子里大骂,贼猫头鹰,死猫头鹰,睡觉在一棵树上睡就不行?半夜三更的瞎换什么啊,吓得老子半死!
算了,这个地方鬼比人多,不能久待——就算有人,估计比鬼还可怕呢!
能在鬼堆里待着,那个小破屋里的,能是普通人么?
所以,咱还是走得越快越好、越远越好!
朱灰灰越想越觉得没前途,好不容易偷来的鸡也不要了,转身就跑。跑了十几步,不见花花跟来,纳闷地回头一望,顿时大惊失色。
自古以来,猪爱拱地,兔子爱盗洞,老鼠爱咬东西,都是生理需要,天性使然。
朱花花虽然是一头比较聪明的猪,但天性方面,和它的同类也没什么区别。
此时,它正在林边一个土包上,用鼻子又拱又顶,拱得泥土乱飞。
朱灰灰仔细一看,那哪是什么土包,分明是一座坟,石碑断成两截歪在一边,坟包上新土盖旧土。
令她感到惊悚的是,被花花拱开的地方,正露着一条白白的大腿。
“花花!你干什么!”朱灰灰怕惊动了鬼,不敢大声训斥,捡起一个东西,向朱花花屁股上砸去。脱手之后,才发现那不是石头,而是一枚幼儿拳头大的珠子。
她心里一寒,那不是眼珠子吧?
不对!眼珠没有这样硬!顺手一划拉,又在地上摸到几枚同样大小的珠子,入手沉甸甸的,也不知道是铁的还是其他什么,扁圆形,中间有个洞。
她感觉这玩意儿有点熟悉,仔细想了半天才恍然大悟,这不是算盘珠子嘛!
奇怪!坟地里的鬼还会玩算盘?
她这里一分神,朱花花的工作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三拱两拱之下,竟然刨出一具尸体来!
朱灰灰简直要疯了,上去照着花花屁股踢了一脚,这死猪是饿疯了还是怎么的?想吃人啊!
“哼~~~”声音极微弱。
朱灰灰大怒,用力揪住花花的耳朵:“你还敢顶嘴!”
花花拼命摇头,一是耳朵被拉疼了,二也是在极力表示:“我没有顶嘴,你别欺负我不会说话,便什么都赖在我头上……”
“不是你是谁?还学会撒谎了你!”朱灰灰将它另一只耳朵也揪住。过去都是直接拎着耳朵提起来的,可是现在,花花实在太胖,她拎不动它了!
“哼~~~~”
又是一声低弱的呻吟!
朱灰灰在花花的屁股上拍了一巴掌:“你还叫!再叫我宰了你!”
忽然,朱灰灰撒腿就跑!
她再粗心也听得出来,她们家朱花花是哼不出这么悲惨、瘆人的声音的。
有鬼!
要不是拼命咬着嘴唇,朱灰灰恨不能叫得比鬼还凄惨!
“别……别走……”
不走才怪!
朱灰灰只恨走得不够快!一发力,窜出去一里多地,听得身后没动静,刚要松口气,回头一看,一颗心却提得更高!
花花没有跟上来!
朱灰灰好生气!这头笨猪!明明她已经暗示它了,都不知道跑!在心里把花花煎炒烹炸了好几遍,虽然害怕至极,终是担心这唯一的伙伴,于是硬着头皮原路返回去。
她转过身,刚要迈步,忽然觉得脖子后面一凉,似乎有一只冰冷的大手在自己的颈子上摸了摸。
“刷”的一下,朱灰灰的头发和汗毛一起站起来。说实话,她常年四处流浪,见过的尸体死人也不少,平日里其实并不很怕鬼啊怪的,可是当这鬼在自己脖子上找下嘴的地方的时候,胆子再大也觉得恐惧了。
一声尖叫已经冲到嘴边,她紧紧闭住唇,硬生生憋了回去。
不……不能叫!老娘说过,碰到比咱恶的,不论是装横还是装熊,心都不能怯,心一怯,就被吃定了!
再说了,就自己这样的,一个鬼都对付不了,万一喊出声再招来更多的鬼聚餐,那不是更惨……
拼命控制着心中的恐惧,为了麻痹那只鬼,朱灰灰假装迟钝地转了几个圈子,壮着胆子喊了两声“花花”,只是声音颤抖得像风中之烛,连自己听着都觉得可怜。
那只鬼可能真的被她搞糊涂了,半天没有动静。
朱灰灰提着的心,终于慢慢地放下一些,虽然很想就此逃跑,可是笨花花没有踪影,它的肉比自己的多,鬼啃起来更过瘾……
她硬着头皮,向来时的路走去,可是走了几步,心里却叫了一声“苦也”——这荒山老林,本来就没有路,自己适才又是慌不择路乱窜出来的,根本不辨方向,刚才转了那几个圈子之后,只觉身边都是树,她已经分不清自己是从哪个地方出来的。
林子里很黑,虽有淡淡的星光,却根本无法穿过头顶密密的枝叶照进来,朦朦胧胧间,只见那些树一模一样,棵棵张牙舞爪,看上去甚是诡异。
朱灰灰皱起眉,踌躇片刻,手伸进袋子里,掏出火镰、火石和火折子。虽然杂货铺子里卖的普通千里火并不贵,可是她实在穷得很,连买千里火的钱都没有,这一套取火的工具,还是被悲空谷晨先生和晚夫人赶走之后,去清风桠村长家里接花花的时候顺手偷的呢!
想起先生和夫人,立刻又想起他们的女儿暮姑娘,然后很自然地想到枫雪色,顿时一股苦涩滋味涌上心头,突然便有点自暴自弃。算了!被鬼咬死好了,反正这世界上,也没有人想念自己!
想归想,她摸摸自己的脖子,还是没舍得!
“嗒!嗒!嗒!”
用火镰和火石对敲了几下,火折引燃了,亮起一小簇微弱的火苗,刚举高一点想要照着找找自己走过的地方,眼睛突然看到身边树下的一道人影。
那人似乎一直就待在那儿,全身从头到脚包在黑布里,与树干合为一体,像隐形人一样。虽然与朱灰灰仅仅三尺之遥,但她却一直都没有察觉,甚至连人家的呼吸都听不到。若非他那双空洞而凶残的眼睛,她只怕跟人家鼻尖对鼻尖,都不会知道那是一个人。
朱灰灰手一哆嗦,火折掉了,额头上全是冷汗。
黑衣人!
对于朱灰灰来说,黑衣人远比鬼可怕!此时她三魂七魄飞走了一半,两手将火石等物一丢,抱着脑袋,掉头就逃。可是还没跑出十几步,脖子忽然被一条绳索套住,不等她惊呼出声,绳圈一紧,扯着她向树上飞去。
朱灰灰只觉得颈骨欲断,一丝气都吸不进去,血液上涌。她勉强用两只手抓住绳子,双腿乱踢,徒劳地挣扎,可是根本于事无补,很快便觉四肢无力,脑中晕眩,耳朵嗡嗡作响。迷迷糊糊间,似觉身子一轻,自己竟然飞到半空,冷冷俯视着被吊在树上的人影——完了,魂魄出窍,自己以后就是吊死鬼了……
眼看再过片刻,自己这条小命便要归位,“嘣”的一声,头顶的绳索不知怎么搞的,竟突然断了。
朱灰灰重重地摔到地上,腰还硌在一块凸起的树根上,疼得她眼前发黑,险些昏过去。拼命忍着不呻吟出声,在地上躺了半天,眩晕耳鸣渐渐止了,她的心里浮上一丝喜悦,呵呵,幸亏那绳索不结实,老子没死!
又一转念,现在就庆幸太早了,那些黑衣爷爷在,自己会不会死,还不一定哪!
她不敢乱动,躺在地上装死,一双耳朵竖着,倾听周围动静。
周围没有动静。
连风声、枝叶摇动声、夜虫的嘶鸣声,都听不见!
朱灰灰如果不是还能感觉到心跳,几乎怀疑刚才那一下子,把自己摔进地狱里去了。
“滴嗒!”
一滴液体落在朱灰灰的额头,刚想也许是滴落的夜露,鼻端便闻到一股血腥气,她心里一寒,血!
“嘀嗒”、“滴嗒”、“滴嗒”。
血滴的速度加快,全掉在朱灰灰的脑门上,腥气扑鼻,非常不舒服。虽然在“装死”状态,她也忍不住偷偷地往旁边挪了一下。脚无意中踢到了什么东西,还没等她反应过来,一个黑乎乎的影子倒了下来,“扑通”一声,将她砸个正着。
这东西跟一座小山似的,虽然软乎乎的,但极重,朱灰灰被砸得半天没喘上气来,直翻白眼。忍住到了嘴边的一连串咒骂,伸手去推,却摸了一手的血,然后便听得“骨碌”一声,从那人脖子上掉下一颗肉乎乎的大脑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