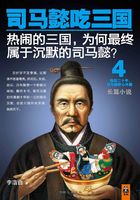
第11章 退吴之战(3)
但是,这些暗暗高兴的情绪只是在他心底疾掠而过:孟达此人反复无常、唯利是图,自己此刻表面上看似乎是暂时稳住他了,但倘若自己亲率大军东攻夏口城之后,他觑破襄阳城守备空虚,再在自己背后乘机作乱,又该当如何应付?把求稳求安的希望寄托在他这样一个根本就靠不住的小人身上,也实在是悬得很……
然而,司马懿不愧是司马懿,他内心深处虽是暗暗焦灼,表面上却不动声色、安之若素。他转过脸来,把幽幽目光深深投向了裴潜,道:“裴君哪,你此番前去援守江陵城,肩上压力实在是不小啊!”
“是啊!”裴潜双眉紧锁,脸上忧色浓浓,“陆逊这厮用兵如神,连西蜀伪帝刘备当年都败殁在了他手下……裴某和他交手,只怕是凶多吉少啊……”
司马懿微微一笑,耐心劝道:“裴君,外敌固然强大,但我们亦自有应对之方。兵诀有云,‘两军相交,不能战则和,不能和则守,不能守则避。’你和夏侯儒到了江陵,切莫出城与他陆逊争锋,只需把他在城池外给本督耐心拖住二三十天的时间,则万事无忧矣!”
“什么?要拖住他二三十天的时间?”裴潜仍是一副忧心忡忡的模样,“大都督,裴某只有在此保证拼了死命尽力而为了……”
“裴君,本督相信你一定会拖得住的。”司马懿郑重言道,“依本督之见:一来江陵城原有士卒二万人,且又墙坚门厚、粮械完备、易守难攻;二来陆逊虽有三万五千精兵而远离根本,不宜久拖虚耗。所以,你一定能撑到最后关头的……”
裴潜脸上的神情仍然振奋不起来:“裴某最忧虑的是万一孙权派兵前来增援陆逊……”
“这一点,你倒不必过于担忧。本督可以指着城外汉水为誓,向你保证:孙权是绝对不会调兵前来增援陆逊的。”司马懿将手一挥,喊他近前,起身俯过去向他侃侃而道,“本督为何将你单独留下?便是要给你细细解析一番。你可能没有看出来,其实孙权这一次实施‘东西交击、两面齐攻’之计,在兵力调配部署上从一开始就存有明显的私心杂念——自五年前夷陵之战后,陆逊挟火烧蜀军八百里连营、一举逼殁西蜀伪帝刘备之大功,在江东朝野之际誉望极隆。孙权只怕早已对他怀有功高震主之暗忌了……所以,他此番才故意让诸葛瑾所掌的兵力远远多于陆逊,逼得陆逊只有以较少的兵力来啃江陵城这块‘硬骨头’,塞给了他一个进退两难的窘境。若是此仗胜了,不消说陆逊也一定会胜得相当艰难,其战果也不会十分耀眼;若是此仗败了,则陆逊威名遭损、声望暴跌,其实正是孙权心底暗暗称快之事。孙权既存着这样的心思,你说他还会派兵增援陆逊,为陆逊的累累战绩再度‘锦上添花’吗?”
司马懿一边在口里这么细细讲着,一边在心底却暗暗想道:这全天下的帝王君主几乎都是一路货色,曹丕也罢、孙权也罢——个个都是嫉人之功而抑之以权,对有才有能的属下往往是明防暗制、掣肘有加!倘若那孙权以刚健中正之度而决断大计,放手任用陆逊,如当年夷陵之战时一般倾心待他,大胆拨给他五六万精兵,令诸葛瑾自东面仅以二万步骑进攻沔阳而策应陆逊,则陆逊兵强势锐定能一举拿下江陵而长驱北上,那才是我大魏最为可虑的严重危局!可喜可贺的是,孙权因己一念之私而弃此大计不用,实乃大魏之万幸也!就凭这一点,司马懿已然洞察出孙权虽为一代枭雄而终究难成帝业的“症结”之所在了——他和曹操当年忌惮我司马懿一样,也深深地忌惮着他那帐下第一儒将陆逊哪!
听罢司马懿这一番话,裴潜这才暗暗放下心来,紧锁着的眉头也渐渐舒展开了。他心情松弛之下,便向司马懿抱拳而道:“裴某在此多谢司马大都督的这一番指教释惑了!这样吧,江陵城如今形势危急,裴某不敢再作滞留,不如就此告辞,与夏侯儒将军一道火速赶赴那里善加驻守!”
司马懿郑重地一点头,右手一摆,道:“裴君行事果断迅捷、毫不拖泥带水!本督甚是佩服!好吧!你且去吧!本督在此预祝你旗开得胜、一举驱敌于坚城之下!”
当裴潜疾步退出厅门之后,司马懿才向榻床的锦绫靠背上缓缓倚了上去。他粗粗地喘了一口气,脸庞上那一派刚毅沉稳的表情犹如层层轻潮一般渐渐消退了下去,代之而来的是一种深深的焦虑和疲惫之色。
“大都督,如今大计已定,您还有何事如此焦灼?”牛恒瞅了司马懿一眼,有些小心翼翼地问道。
司马懿微微眯着双眼,森森然反问道:“古语有云,‘祸患常生于所怠忽。’牛君,你猜本督此刻在为何事而焦灼?”
牛恒双眸滴溜溜一转,轻声答道:“大都督莫非还在为孟达一事而焦灼?”
“不错。”司马懿双目一睁,向他直盯而来,“这孟达为人反复无常、倏东倏西、难以捉摸,倘若他在本督东攻夏口城,与吴寇斗得难分难解之际而狂性大发、狼奔豕突,外结神农山东面的伪蜀江州都督李严为援,而向内则直捣襄阳而下——我等又该如何应付呢?”
“大都督,您已虚悬出荆州牧一职为‘香饵’,向他施放了‘烟幕之阵’,他这个人贪权嗜利,两眼直盯着顶上官帽,只怕不会轻易就与我大魏决裂吧?”梁机沉吟着在旁边讲道,眸光如水游移不定。
司马懿没有接他的话,仍是自顾自缓缓而道:“这些都是本督用以暂时稳住他的权宜之计罢了,拖不得太久的。说直一点儿,它们只是本督‘软的一手’。要想让这个孟达彻底不生侥幸渔利之念,本督还须得再有‘硬的一手’来监控和防备他才行。”
“司马大都督实在是过虑了。孟达应该不会选择在这个关头来‘浑水摸鱼’的。”一直沉默着的牛金蓦然开腔了,“您可以假设一下:就算孟达铤而走险,一咬牙迈出了这一步,从我军背后狙击襄阳城——这样的后果是,我军可能会溃散,但孟达也未必讨得了什么便宜去啊!因为我军败后,陆逊、诸葛瑾必会挟虎狼之威北上侵吞而来,其势已是易客为主,孟达在他们面前又有何利可图?李严尚还远在神农山东面,于孟达而言,亦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孟达乃是何等精于算计之徒,像偷袭襄阳这种损人而不利己的事儿,他怎会去做?他应该还是一味游移观望而待时局之变……”
司马懿一听,心下暗自称奇:没想到数年不见,牛金从一介赳赳武夫竟已成长为今日这般通明时事的大将之才了!他的目光之犀利、见解之练达,当真是迥非昔日“吴下阿蒙”了!他在心底暗暗高兴了一会儿,慢慢说道:“牛金此言甚是。不过,本督行事一向务求严谨周密,还是不能让孟达这么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游离于咱们的掌控之外……这个人诡计多端,谁知道他将来会捣出什么乱子来呢?”
牛恒听了,微垂着头慢慢沉吟了起来。过了半晌,他眼中忽地灵光一闪,双掌一拍,喜道:“对了!大都督,牛某险些忘了,属下此番从新城郡带回了一个人,他十分熟悉新城郡、魏兴郡等西南一域的诸多内情,或许对大都督您以‘硬的一手’监控和防备孟达有所裨益。”
“谁?他是什么来历?”司马懿目光亮亮地一跳。
“他是咱们在荆州境内多年蓄养的一个死士,是寒门孤儿出身,拜了牛某为义父,名叫州泰,今年二十八岁。此人年纪虽小,但聪敏好学、有勇有谋、行事干练,是个可造之材。牛某三年前听从大都督您的指令,为了及时监视孟达,就让州泰一直以一介售铁商贩的低微身份潜伏于新城郡、魏兴郡等西南一域暗暗刺探孟达的内情。”
“周泰?荆州沔阳一带的周氏家庭颇有盛誉,他莫非是出自那里的周家后人?”司马懿对荆各姓各族都了如指掌,随口便问了一句。
“启禀大都督,这个州泰的姓是‘荆州’的‘州’,而不是太史令周宣大人的那个‘周’。州泰自己给自己取了这个姓,声称自己是以名寓志:‘州泰者,可保一州之泰也。’”
“哦?州泰?‘可保一州之泰’?”司马懿微微而笑,“听起来这小子还蛮有志气的嘛!身为售铁贩货的杂流之士,他居然亦有‘可保一州之泰’的大志?有趣!有趣!难得!难得!本督倒是很想见他一见了——行!你去传他进来答话吧!”
牛恒应声出门而去之后,司马懿伸手端起案几上那盏绿玉双耳杯,慢慢啜了一口朱枣碧荷茶,眼角斜光一扫,瞧着牛金、梁机在自己案侧仍是恭恭敬敬地肃立着,便向他俩招了招手,笑道:“你俩这时怕也早就站乏了——就在那坐枰上坐下休息了吧!”
牛金和梁机口里嗫嗫地应着,却并不挪步。司马懿知道他俩怕是失了礼数,就也不好多劝,平和了语气,开言道:“牛金哪,本督到这荆襄之域来,也幸得当初安插了你们两兄弟,还有裴潜等几员得力干将在下面撑持着——不然,本督一到这荆州地面上落个‘两眼一抹黑’,成得了什么大事?你们也须得体谅本督的一些难处:说起来荆襄行营人才济济,但一个夏侯儒是夏侯尚的堂弟,一个曹肇是曹休的儿子,扯起来都是来头不小的皇亲国戚,本督怎好轻易使唤得他俩?而你们兄弟和裴潜,都是我司马家贴心贴肺的知交,关起门来不是外人,本督的训话有时说得重点儿或轻点儿,你们也莫往心底里去——你们只要明白闯过眼下这道难关之后,大家前边的路也都必将豁然开朗了!”
牛金听得热泪盈眶,双拳一抱,躬身而道:“大都督,属下兄弟等誓死为您效忠!您若有差遣,一切尽管直言!”
司马懿深深点头,满眼皆是赞许之意。他正欲讲话,却见厅堂木门一开,牛恒领着一个身着劲服的高大青年疾步趋上前来:那青年一眼见过司马懿,竟忽地停下了脚步,远远地向司马懿迎面拜倒,扬声呼道:“小人州泰拜见司马大都督!”
“免礼吧!”司马懿放下手中双耳杯,容色一敛,缓缓答了一声。
州泰抬起头来,在地下直直地仰视着司马懿。司马懿仔细瞧去,只见他二十七八岁的年纪,戴着青帻巾,方方的国字脸,一对黑珍珠般的眼睛不停地一眨一闪的,淡黄的茸须之下,两撇八字胡髭微微上翘,透着一股说不出的精悍伶俐之气!司马懿一看,便辨出了这个人是从三教九流的纷纭场合之中摸爬滚打出来的机灵角色,只要调教得当,倒真是一块难得的“社稷之材”!他定了定神,目光一亮,正视着他徐徐问道:“州泰,本督听闻你曾在新城、魏兴等郡县多方游走,应该对我大魏西南之域的一些地理人情有所了解——你且详细禀来,让本督倾听一番。”
“启禀大都督,那新城、魏兴、房陵、上庸等西南一域所有郡县的内外形胜、地理人情几乎都藏在小人的胸中,几乎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州泰那对黑亮的眼珠滴溜溜转了几下,“却不知您究竟想倾听哪一方面的详情?您若不明问,小人又从哪里开始细说呢?”
“好个州泰!当着大都督的面,你居然还是这般油嘴滑舌!大都督乃是何等睿智明达之士,岂是你能出言冒犯的?你还不快快向大都督逊辞谢罪!”梁机一听,不禁变了脸色,当场就向他劈头盖脸叱了下来。
那州泰把头一歪,满不在乎地斜了梁机一眼:“这位大人言重了!小人刚才这话并无失礼之处——若要讲起新城、魏兴、房陵、上庸等西南一域所有郡县的内外形胜、地理人情来,小人若是不分轻重、不论虚实,只怕在这里滔滔不绝地讲上个三天三夜也未必讲得完!大都督您想问什么就直说,小人也好有的放矢。”
司马懿也晓得自己刚才那话问得有些唐突了,便摆手止住了梁机,敛容问道:“州泰,你这话讲得不错。本督便单刀直入问你:倘若新城郡太守孟达心怀异志而起兵作乱,本督须得在他出兵之前先行占据西南一域的哪个要塞方能扼其来路?”
“这孟达一向鬼头鬼脑、变化无常的,朝廷老早也该调走他了!先前的那个夏侯镇南手太软,纵容得他愈发狂放了!”州泰两眼精光流动,先是咕哝了几句,然后朗声答道,“不过,大都督您别担心,正所谓‘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依小人之见,孟达那厮真要起兵袭往襄阳而来,您便可速速派出一支劲旅,抢先占据汉水上游的华阳津口,在那水陆交汇的衢道要冲之处,给他一个‘关门打狗’之势,则孟达非但难以东下,而且进退失据、必败无疑!”
“‘关门打狗’!怎么个‘关门打狗’之势?还有,倘若到了那时,本督还来得及调兵把守住华阳津口吗?”司马懿听到后来,不禁悚然变色,探身过来直盯着他继续追问。
“当然来得及。因为孟达若要起兵作乱,他首先要做的第一步并不会是顺流东下进取襄阳,而是调过头来挥戈向西直夺魏兴郡!大都督您想——到了那时,咱们东有华阳津口,西有魏兴郡城,就像两扇大门那么紧紧一关,岂不正是将孟达这条‘疯狗’关在里面打得他无处可逃了?”州泰两手一边左右比画着,一边眉飞色舞地讲解着。
梁机听他讲得有些粗鄙,立时便觉得他果然未脱市井商贩的流俗之气,不禁冷冷皱眉斜睨着他。而那司马懿却似毫不在意,对州泰的话,听得煞是认真,嘴里还喃喃道:“魏兴郡?对啊!申仪就在那里值守啊!本督怎么把它一时给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