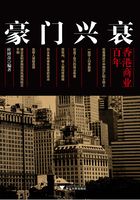
第6章 船王和他们的时代(1)
很不幸,关于大多数富有船主的事业生涯,只有笼统的而且是歌功颂德的记述。
——古斯塔夫斯·迈尔斯
1949:来自大陆的年轻人
1949年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道分水岭,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难以数计的中国人的命运之河猝然改道。生与死、去与留,时代汪洋中的人们无暇思索,一个不经意的决定便可能改变余生。
国民党军队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丢掉大半河山,也让国民政府的有产阶级感到惶恐无限。富商巨贾犹如惊弓之鸟,拖家带口逃离大陆。香港自然成了移民汇集之地,从1948年开始,移民潮一浪接一浪涌来,香港人口剧增。这些大陆客中,有四名从上海远道而来的年轻人,日后在香港航运业后来居上,崛起为名噪一时的“四大船王”,创下不朽的财富传奇。
这四人分别是宁波籍的董浩云和包玉刚,江苏无锡人赵从衍和上海本地人曹文锦。
董浩云名头最响,他已是两家航运公司的总经理,手中掌控数十艘货轮。和董浩云同龄的赵从衍只有一艘运煤的旧轮船,而且还是与他人合资,仅持有一半股权。30出头的包玉刚还是航运界的门外汉,他之前的身份是上海市银行副总经理。生于航运世家的曹文锦则是家族劝业银行的实习生。
赵从衍一家最先到来。1948年冬天,他们乘着自家的“国兴号”货轮,从黄浦江收锚起航。望着被甩在身后的上海外滩,赵从衍心想,“我出去避避风头,当然还是要回来的”。
那时候,赵从衍经商不到10年,却已小有所成。赵父是国民政府官员,家境富裕。从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后,赵从衍在上海当过几年职业律师。日本人占领上海期间,汪精卫政府对律师执照进行重新注册,赵从衍不愿沆瀣一气,放弃注册,成了一名香烟贸易商。上海孤岛时期,物资紧缺,赵从衍盯上船运生意,买不起船,只能开展中介服务,从中赚取佣金,稍有积蓄后才与人合伙,买下这艘二手轮船“国兴号”,从事煤炭运输,没过几年居然成为沪上富豪。
据说当时赵从衍身价在千万级别,官宦子弟出身,专业律师背景,在上海商界正值春风得意,若非迫不得已,不会轻易离开上海,因此带一家老小到香港“避一避风头”。
与赵从衍的情况类似,曹文锦一家也是“来港避风”。
曹家原是黄埔江畔的一个清贫读书人家,曹文锦祖父曹华章从一艘小木船起步,摇橹载客创下家族基业。1925年曹文锦出生时,祖父曹华章经营的“曹宝记”运输公司业务已遍及长江沿岸,其父曹隐云开办了中国劝业银行并从事进出口贸易,其母吴娱萱则主持南京路的“天成宝银楼”。作为家中长子,曹文锦从上海圣约翰大学一毕业,就开始接受“强迫性”的商业训练,上午去银行实习,下午去达昌洋行学习进出口贸易,晚上去祖父的运输公司帮忙。
曹氏家大业大,1949年这趟出走起意匆忙,上海的公司、地产、珠宝和股票没有来得及出售或带走。幸好一年前蒋经国“上海打虎”时曹文锦不甘心家产被掠夺,冒险把“天成宝银楼”的金银首饰转移到广州,兑换成港币存入香港的银行,价值10万余美金。这成为曹氏“逃难时唯一的活命钱”。【引自《华人时刊》杂志2002年第6期P30-P32,节选曹文锦回忆录《我的经历与航运五十载》一书《我的五洲四海航运生涯》,作者曹文锦】
后来曹文锦回忆说,“只随身带了10万美元的现金和一些珠宝,希望局势稳定之后再回上海。”【引自祝春亭著《香港商战风云录(中)》第二十九章“赵氏曹氏初衷不改不同航”,广州出版社1996年版P11】有香港媒体推测,曹家带出的资产仅占家产1%,《资本家》杂志估算“大致只有当时曹家财产的5%至10%”。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曹家在上海富甲一方,而此番赴港财产大多留在了上海。
未曾料想,从此一别,剩下的资产就再也没有机会带走。这对曹文锦的商业生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即便局势稳定之后,他也没有考虑“再回上海”,甚至对香港前景也始终忧心忡忡。
相比赵从衍、曹文锦,董浩云则决绝得多,早已不再对“重回上海”存任何幻想。
董浩云祖籍福建,祖父这代迁居浙江定海,以裁缝为业,清末移居上海闸北,董浩云之父董瑞昌在上海南市大东门经营“源森玻璃五金店”。董浩云自幼对海洋感兴趣,16岁进入日商在上海开办的“国际运输株式会社”做学徒,不久转入民国“金融巨子”周作民的金城银行旗下“通成公司”,19岁时被派往金城银行另一附属公司“天津航业公司”任秘书。【引自《民国档案》杂志2002年第4期P87,《董浩云年表》一文,作者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郑会欣】
所谓天助自助者,董浩云出身低微,但聪敏勤奋,所以运气总是特别照顾他。
来天津第一年,董浩云便得到船运大亨顾宗瑞赏识。顾氏独资拥有两家轮船公司,旗下轮船数十艘,经营天津、上海间的煤炭运输业务,与董浩云供职的“天津行业公司”有业务往来。顾宗瑞有意栽培董浩云,还把女儿顾丽真许配给他。可惜,顾宗瑞不久便去世,这个后台倒塌了。
好在董浩云能力过人,几经交涉,帮助金城银行收回被英国领事馆租借的物业,用作“天津航业公司”的总部。此事令董浩云名声大噪,23岁就被选为轮船同业公会副会长。1936年开春,天津大沽口被冰雪封冻,140艘中外轮船被困,董浩云沉重指挥救灾,展现出行业领袖的潜质,此后平步青云,不到30岁便成为民族航运业旗帜性人物,与民生公司创始人卢作孚一北一南,遥相呼应。
与卢作孚拥有自己的民生公司不同,董浩云身份上属于职业经理人。直到1940年在美国特拉华州注册成立“金山轮船公司”,他才算拥有了自己的航运公司,第二年又在香港创建“中国航运信托公司”,悬挂英国或巴拿马国旗,往来于中国沿海及东南亚。不过,随后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董氏旗下船只被日军作为“敌产”接管。抗战胜利后,董浩云申请复业却被国民政府财政部以在香港注册为由驳回。1947年,董浩云重起炉灶,从美国购入三艘战时生产的7600吨胜利型散装货轮,先后在香港创建“复兴航业公司”与“中国航运公司”,开展沿海及远洋运输。董浩云对国民政府忠心不二,1948年底举家迁往香港。那一年他36岁。
刚跨过而立之年的包玉刚已是四个孩子的父亲。1949年开春,上海解放前夕,包玉刚乘坐中华航空公司的班机去香港与家人团聚。其父包兆龙一年前已把家人、资产转移到了香港。
尽管是上海吴淞船舶学校船舶专业科班出身,包玉刚最大的心愿是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银行家。这个丝绸商人的儿子确有成为银行家的潜质,22岁投身金融业,进入国民政府中央信托局,在衡阳办事处做职员,后来得到银行家陈敦甫赏识,进入中国工矿银行衡阳分行做副经理,在战时的衡阳金融界崭露头角。抗战胜利后,包玉刚被派往上海,接管日本帝国银行资产,参与组建上海市银行,并担任副总经理。可惜,他的职业生涯被战争打断了。
在上海时,包玉刚是官办银行经理,深受当权者器重。由于权力斗争,上海市银行总经理不停更换,但副总经理一直是包玉刚,还兼任业务经理,上海市银行离不开他,少了谁也不能没有包玉刚。法币贬值后,银行挤兑空前,上海市长吴国桢说:“有包玉刚在,银行就能正常运转”。
但包玉刚似乎对留在上海有某种不详的预兆。早早将家族财产转移到香港,1949年向吴国桢成功请辞后,飞赴香港,决心重操旧业。不过,包玉刚的英语、粤语都不过关,在英国人和广东帮把持的香港银行界混不开。最后,他只能和朋友开了一家小公司,经营大陆的土特产。
这一时期,大陆难民不断涌入,致使香港人口激增,从1945年的50万暴涨至1950年的200余万,包兆龙认为房地产前景可嘉,但包玉刚认为房屋地产都是死的,靠不住,不如做船运生意。“行船跑马三分险”,包兆龙不愿冒这个风险。不过,最后还是被包玉刚说服了。
1955年,包玉刚斥资70余万美元,从英国购入一艘28年船龄的蒸汽旧船“仁川号”,更名为“金安号”,开始了他的航运事业。这时候,董浩云、赵从衍、曹文锦三人早已在香港航运界立定脚跟。但他们尚未取得什么骄人成绩。香港航运界的领军者还是一个名叫许爱周的广东人。
“老船王”许爱周
大约50岁时,许爱周才购入生平第一艘货船“宝石号”,经营不到10年就成为名震华南的航运大亨。这固然得益于他本人出类拔萃的商业才干,但更离不开特殊的时空机运。
许爱周1881年出生在广东湛江农家,长大后与父亲在家乡开办了一家“福泰号”,专营粮油杂货。18岁那年,法国迫使满清政府签订《中法互订广州湾租界条约》,湛江地区从此变相沦为法国殖民地,荒凉萧条的城镇忽然涌入大量西洋人,许爱周的命运也因此发生改变。
法国看中了雷州半岛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将广州湾辟建为自由港,大肆投资,修建码头、船坞,拓建公路,联通西南各省。短短20多年,广州湾在贸易拉动下成为华南重要的运输中心。
许爱周从中发现了商业机会。他先人一步,在湛江各地开设分号,以“周泰号”经销水产品,以“广泰号”、“天泰号”收购当地优质花生,制成“湾牌”花生油,经香港销往沿海各地,甚至一度远销美国西海岸;同时,许爱周在香港开设“广泰号”,批发洋货及大陆土特产,经湛江销往广西、贵州、云南等省份。资本扩大后,他与人合资,在广州湾开发商业地产和酒店,并取得美国“德士古”石油公司在广州湾的代理权。由于竞争匮乏,这些生意无不利润巨大,因此,许爱周身价急剧抬升,30岁出头就成为湛江地区首屈一指的富商。【参见香港《资本》杂志1989年12月刊,第86页,所载《许爱周家族发迹史》一文】
春风得意的许爱周却有一件心腹大患,忧虑已久。进出口贸易严重依赖航运业,但民族航运业却长期掌控在洋人之手,所谓“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成为许爱周事业进一步发展的最大障碍。
清末,伴随列强入侵,英美日三国轮船公司不断扩张在华势力,逐渐垄断远洋运输和内河航运,几乎摧毁清朝漕运。北洋运动开始后,“官办”、“民办”之风渐起,轮船招商局、民生轮船公司、中华气船公司、粤航公司等大批本土公司应运而生,可惜资本薄弱、装备落后,根本无力与外资竞争。加上各级官吏搜刮勒索,民族航运业委实虚弱。曹文锦祖父曹华章就经常叹息:“中国人搞航运真是太辛苦了。几十年来战争不断,船常常被拉走,从没好好地做过生意。只有外国人的船,他们才不敢去拉,并且有特霸权住在中国内河及沿江、沿海的航运。”
直至1920年代,这一状况有增无减。英资怡和、太古洋行,日本邮船会社、日清汽船会社等几大巨头联手制定游戏规则、打压中国对手,国内贸易商无不受制于此。许爱周为此头痛不已。他逐渐意识到,摆脱他人操控的唯一途径,就是创办自己的航运公司。
幸运的是,许爱周并没有等待太久。
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决意振兴民族航运业,在全国设立五个航政局,分管内河及沿海航线,华南航政局设在香港,统辖福建、广州、广西等华南诸省【参见《银行周报》第15卷第4号第6页】。在此前后,香港至广州湾航线开通。许爱周的机会终于来临。他以广州湾为基地,创建“顺昌航业公司”投身航运业,斥资购入一艘“宝石号”货船,往来香港、湛江之间,打通贸易业与航运业。
抗日战争爆发前,许爱周旗下已拥有十余艘船只,航线拓展至上海、广州等地,初具规模。1938年广州沦陷,因是法租界,广州湾暂时免受日军侵袭,成为华南仅剩的几条交通要冲,许爱周趁机扩大规模,合资组建四家航运公司,购买或租赁船只,将大批物资经湛江运往西南各省。当时,国民政府已迁都重庆,大西南物资匮乏,严重依赖外部救援,广州湾成为最重要的运输枢纽之一。在日军攻陷湛江前,许爱周发挥了重要作用,奠定了他在民族航运业的地位。
日军投降后,香港人口暴增,物资紧缺,许爱周遂将事业中心移至香港。为顺应融资的需要,许爱周将顺昌航业注册为有限公司,购入大批货轮,开辟远洋航线,依托香港、广州湾及东南亚各埠贸易网络,到1950年代顺昌航业发展为香港最大的航运集团,许爱周也被尊为香港“第一代船王”。
将盈余资金投入实体生意之外,许爱周还是地产投资的一面好手。早在1920年代,他便涉足地产业,在广州湾参与填海造陆而掌握大宗物业单位。移居香港后,许爱周与嘉华地产主席彭国珍等好友合资组建中建企业有限公司,是香港最先涉足地产开发的华商。许爱周长期看好香港经济,奉行“逢低买入”的投资策略,在皇后大道、中环等重要地段购入大量物业单位和黄金地块,大多数开发为商业大厦,只租不售,坐享地皮升值之利。
许爱周身上展示出一个老道商人的远见卓识。他以航运业为盈利之源,地产投资为后续保障,两者互为犄角:航运业现金流动频繁,经营难度随规模升级递增,地产业资金流动性较差,管理难度低,充当“资本蓄水池”,彼此取长补短,家族财富获得飞速增长。
如果说财富是衡量一个商人事业成功与否的直观标尺,那么有操守的行商则可以极大提升一个商人的威信。许爱周所以成为香港航运界的领军人物,固然与其在航运业取得的卓然成就有关,更为关键的因素在于,他以一而终的操守与品行赢服众人,使之成为华商的表率。
民国初年,许多华商靠着捞偏门,办烟馆、赌摊成为巨富,也有人奉劝许爱周从中取一杯羹,他却正言厉色地拒绝,不仅生平从不参与鸦片贩卖,更绝禁家人赌博吸烟。
香港被日军占领后,两艘货轮来不及撤走,许爱周宁可将它们凿沉,也不允许落于日本人之手。国难当头,许家三公子许世勋迎娶夫人简剑勋,各界名流纷纷拜贺,许爱周大手一挥,将贺礼全部捐作抗战军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许爱周家族在战后崛起为香港新贵绝非偶然。
赵从衍、曹文锦重新起家
多年后,赵从衍回忆来香港的初衷:“当时形势十分混乱,我最初只把香港当做庇护所,逗留半年便返回内地,但内战结束后,反观香港却有作为,所以便索性以香港为根据地”。【引自祝春亭著《香港商战风云录(中)》第二十九章“赵氏曹氏初衷不改不同航”,广州出版社1996年版P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