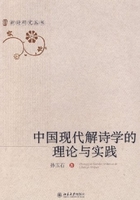
第3章 朱自清对现代解诗学的倡导
中国现代解诗学的诞生,标志新诗批评由对现代主义诗歌潮流总体发展态势的观照,转入对这一潮流的作品本体微观世界的解析。克罗齐进:“要了解但丁,我们就必须把自己提升到但丁的水准。”华兹华斯又说过:“一个诗人不仅要创造作品,还要创造能欣赏那种作品的趣味。”理解和欣赏虽然不是一回事,但却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理解是进入欣赏的准备,欣赏是实现理解的成果。中国现代解诗学,以理解作品为前提,在理解中实现对作品本体的欣赏和审美判断。
现代解诗学的萌芽始于《现代》杂志对西方和中国象征派作品的一些简略剖析。该杂志创刊伊始,就刊登了现代英国象征派大诗人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的七首现代诗。译者同时对这些作品进行了简要的解释,有些地方不仅释析了象征的内涵,而且对文字的特殊用法也作了点化说明。最后译者申明:“诗本来是不能解释的,尤其是别人的诗。但终于写了这些,其动机实在也像译她们一样,由于深嗜之而已,读者倘不憎厌,便看作是一段鉴赏,否则,当作丰干饶舌也罢。”另一期杂志中,编者以解析的方法阐明了现代诗联想和构句的特征,“替代”诗人“逐一解释”,并回答了读者对一些“朦胧诗”的指责,使“不易索解”的“比较朦胧的诗”变得“明白畅晓”了。作者显然在解释诗的象征意蕴和独特的修辞法的同时,包含了对于作品本身最初步的艺术鉴赏和审美判断。
朱自清先生是中国现代解诗学最早的倡导者。新诗领域中开展的“明了”与“晦涩”的讨论,实质是现代派诗歌与传统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诗歌美学原则的分歧和论争。历来以宽宏的观念看待新诗的发展并认为象征派的“突起”是新诗发展一个“进步”的朱自清,十分关注这场争论。他随着时代与艺术的发展而更新自身的诗歌观念,提出了多元化的新诗审美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尺度,从宏观上来审视新诗发展的思潮流派、趋向和规律。与此同时,他比别的批评家更早地注意对诗的本体进行微观的解析,并以现代人的诗的自觉意识,把这种实践加以理论化,名之为“解诗”。这种理论与实践,我称之为中国现代解诗学。
在《解诗》一文里,朱自清先生说明了他在诗的传达问题讨论中意识的凝聚点。他说:“我所注意的是他们举过的传达的例子。诗的传达,和比喻及组织关系甚大。诗人的譬喻要创新,至少变故为新,组织也总要新,要变。因此就觉得不习惯,难懂了。其实大部分的诗,细心看几遍,也便可明白的。”接着,朱自清先生在文章中就讨论中举到的难懂的例子,如林徽音的《别丢掉》和卞之琳的《距离的组织》,“试为解说”,进行“解诗”主张的实践。此文发表于1936年,可以视为朱自清先生提出解诗学理论的开始。以后他还连续写过几篇短文贯彻这一批评的思路和方法。1944年10月,当他将这些以《新诗杂话》为总题的文章汇集成书的时候写了一篇《序》。解诗的理论在这篇《序》中由零散的实践而走向了自觉的形态。我们在作者认为“片片断断”的非“系统的著作”里看到了一种中国现代批评诗学理论形态的诞生。作者在对自身批评实践的回顾与反思中,更加自觉地概括了自己的诗歌批评意识:这本书里所收的15篇文章“多半在‘解诗’,因为作者相信意义的分析是欣赏的基础”。文章具体阐发这一思想说:
作者相信文艺的欣赏和了解是分不开的,了解几分,也就欣赏几分,或不欣赏几分;而了解得从分析意义下手。意义是很复杂的。朱子说“晓得文义是一重,识得意思好处是一重”;他将意义分出“文义”和“意思”两层来,很有用处,但也只得说个大概,其实还可细分。朱子的话原就解诗而论;诗是最经济的语言,“晓得文义”有时也不易,“识得意思好处”再要难些。分析一首诗的意义,得一层层挨着剥起去,一个不留心便逗不拢来,甚至于驴头不对马嘴。书中各篇解诗,虽然都经过一番思索和玩味,却免不了出错。有三处经原作者指出,又一处经一位朋友指出,都已改过了。别处也许还有,希望读者指教。
这段话里包含了朱自清倡导的现代解诗学的主要精义。它阐明了现代诗歌审美的欣赏对作品本体了解的依赖性;诗歌意象和语言组织的“本文分析”是了解一首复杂作品的主要切入口;解诗就是依从作品的意象和语言一层层挨着剥开去,即遵从作品自身内部的逻辑性进行细读、思索和玩味;解诗本身是一个读者、作家、批评者不断的审美创造过程,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接近审美的客观性。现代解诗学的诞生,开辟了缩短现代主义诗歌领域中作者的审美追求和读者审美心理差距的途径。对作品本体的“思索和玩味”的结果,是产生了一种以作品本体为中心的批评诗学。
一种新的诗歌潮流推动一种新的诗学批评的产生,而这种理论的产生不是一个人孤立完成的,往往要依靠更多人的探索和实践。当时的诗人或批评家李广田、废名、卞之琳、朱光潜、李健吾、闻一多、施蛰存、戴望舒、杜衡、金克木、林庚、邵洵美等人,都曾以他们多种形式的理论探索和批评的文字,为构建中国现代解诗学作出了自觉或不自觉的努力。这种情况决定了现代解诗学以非系统理论的形态出现,缺乏完整的深刻的理论阐述和论证,因而在诗学批评领域中未能形成有影响的思潮和派别,还未能独立地引起新诗批评方法论的巨大变革,像西方新批评派那样;但是这种新的批评诗学的诞生,毕竟表现了批评家对现代主义诗歌自身艺术特征的尊重,并在作者、作品和读者之间架起了一座智性的桥梁。众口一声简单地认为现代派诗“晦涩朦胧”、“不好懂”而加以否定的时代,由于现代解诗学的出现便告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