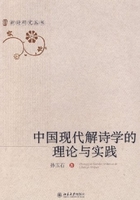
第5章 现代解诗学的公共原则
现代解诗学表现了批评家对诗歌本体自觉意识的强化。在纵的坐标上,它不同于只注重社会内容和外部艺术特点的社会历史批评诗学,开始进入对作品内在的意象和语言结构的分析,达到了由形式而走向内容。在横的坐标上,它区别于西方新批评派完全杜绝了解作者创作意图而将作品进行封闭式的细读和注释的形式主义,也区别于中国传统解诗学过分追求字义的考据疏证从而陷入穿凿和烦琐的附庸主义,达到了为了内容而进入形式的境界。协调作者、作品与读者三者之间的公共关系,理解趋向的创造性和本文内容的客观性相结合,注意形式和内容的统一,始终是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特征。
要重建协调作者、作品、读者的公共关系的解诗学,应该注意以下几个原则:
第一,正确理解作品的复义性应以本文内涵的客观包容性为前提。象征派诗、现代派诗的朦胧和多义性,允许理解者的创造产生多元的释义。但是无限的多元就变成无元,也就取消诗本身的意义了。卞之琳有一首诗《雨同我》,李广田认为此诗蕴蓄了诗人为天下忧的情感与怀抱。一二句写两个朋友在埋怨雨,第三句由自己一口承当责任,然后由两个朋友又想到第三点:“第三处没消息,寄一把伞去?”这就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个人应当为多少人担心呢?于是“我的忧愁随草绿天涯”、“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我”所关心的岂止人,一切有生“我”都担心它在“雨”中的情况,“雨”,自然就是雨,但也可以说是那“不已”的“风雨”,世界上不尽的苦难都是的,故曰:“鸟安于巢吗?人安于客枕?”真是,一草一木,一角一落,都分得“我”的忧愁,“我”只好把一只杯子放在天井里,明朝看普天下的雨落了几寸。“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从我的小杯子里我可以看见普天下淋成了什么样子。”同一首诗废名却说“第三处没消息”,是指情人。因为没消息,究竟那里下雨了没有呢?无奈只能想到寄一把伞去。诗人在外客旅或寄居友人家里,故曰“客枕”。玻璃杯盛“天下雨”的多少是一种思念之情的象征。我以为这两种理解,都没有超出作品意象的涵盖面积,又是合乎语言意象逻辑的分析,它们符合诗的多义性的特性,因而是应该允许同时存在的。即使作者说明一种本意,也不能抹煞读者经验和想象“小径通幽”的创造果实。
第二,理解作品的内涵必须正确把握作者传达语言的逻辑性。诗人并非以逻辑思维写诗,但是富于艺术创造性的诗在意象组织和语言传达上却自有它严密的逻辑性。如果不注意每一句、每个字,甚至一个标点符号的安排,差之毫厘就会谬之千里。还是卞之琳的一首诗《尺八》,有的研究者把这首“表达怀乡思旧”的诗视为抒情主体复杂变换的典型进行解析是对的,而分析本身由于弄错了复杂主体的内指性和语言组织的逻辑性,就产生了不应有的谬误。他说:角色“海西客”、叙述者和诗人,虽然我们知道这三者都是卞之琳这个主体的一部分,他们在诗中的声音却是不同的。“海西客”沿尺八东传的老路来到东京,夜半时孤馆寄居,听到尺八的吹奏,既“动了乡愁”,又“得了慰藉”,第二天他到东京市上想买支尺八留作纪念,却在霓虹灯耀眼的现代城市闻到“一缕古香”。研究者这里的错误在于:第一,注意了诗的三重主体复合,却把第四行的“海西客”和第六行的“孤馆寄居的番客”这两个分别为真实的现时的主体和想象的古代的主体混成一个了,实际上“海西客”是指诗人自己,“孤馆寄居的番客”应是诗人想象中唐朝时来到长安的日本人。第二,第九行“次朝在长安市的繁华里”,原发表期刊和作者自编的《雕虫纪历》均没有标点符号,与下面第十行诗“独访取一支凄凉的竹管”构成一句话,而这位研究者却将第九行后边加了句号,与第十行分开。这样,就把在长安市上访取“凄凉的竹管”的“孤馆寄居的番客”误解为在东京市上买支尺八的“海西客”,把想象中的唐代的日本人误解为现实中旅日的诗人自己了,说明了主体复杂性却弄错了诗中的主体内涵,不应有的断句背离了作者时空交错的用意和感慨祖国衰微的深层表现方法。诗人卞之琳在为这首诗写的散文《尺八夜》中明明白白写道:这首短诗是“设想一个中土人在三岛夜听尺八,而想象多少年前一个三岛客在长安市夜闻尺八而动乡思,像自鉴于历史风尘的满面的镜子”。在长安买尺八的是“三岛客”,而在霓虹灯中闻到“一缕古香”的又是诗人自己。研究者提到这篇优美的散文且多有引述,恰恰忽略了这一句最要害的话。这就不能说是“创造性的理解”,而只能是背离作品原义的“迷误性理解”。由此我们即可引出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独具特色的另一项原则。
第三,理解或批评者主体的创造性不能完全脱离作者意图的制约性。前面说过,中国现代解诗学可以视为是由作者、作品、读者三者构成的公共关系的诗学批评。批评对象审美创造的特殊性决定了理解者视界与想象的创造性;机械地以作者本意为理解和阐释的唯一准绳是对理解者创造性的扼杀。诗歌本体意象丰富的内涵也必然被引入狭窄。但是,解诗毕竟不等于纯然的鉴赏。理解者的创造不能变为随心所欲的臆造。李健吾先生讲的“一首美丽的诗永久在读者心头重生”,“它所唤起的经验是多方面的”,这主要就欣赏者而言才是真理,解诗仍要有限制。批评家或读者的解诗不能不受作者和作品客观性的制约。西方新批评派和后结构主义的批评诗学把作者与批评者完全隔绝开来,甚至完全否定作品和作者这个创造本体的相互联系,宣布“读者的诞生必须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这只能导致批评者自身的迷误。李健吾、朱自清在建构解诗学的理论和实践的过程中,不断与作者、读者相互磋商,力图使“小径通幽”达到多义性和客观性的统一,这正是我们在今天重建中国现代解诗学的时候应该汲取和坚持的理论精髓。
§§第二章 现代诗人的玄想思维与文化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