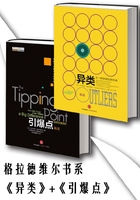
第1章 引言
罗塞托之谜
“生活在这里的人都是自然死亡,事实的确如此。”
异类(outlier),名词
1.离开主体或者相关本体的东西;
2.一个在价值上能与其他样本显著区别开的统计观察值。
健康的罗塞托人
罗塞托瓦尔福尔托雷坐落在亚平宁山山脚,它是意大利福贾省的一个小城,位于首都罗马城的东南方向,距离罗马约100英里。小城环绕一个中心广场展开,这里有着典型的中世纪村庄风格。正对广场的是马切斯宫,这是当时这片土地的大地主萨吉斯家族的宅邸。旁边一座拱门通向卡米尼圣母堂。顺着山边狭窄石梯拾级而上,就能看到一排排有着红瓦屋顶的两层石头房屋。
几百年来,罗塞托的居民不是在附近山上的采石场劳作,就是在山下的梯田耕种。他们每天早晨要走四五英里下山干活,傍晚再花相同的时间回家。那时村里的生活着实不易,大多数人不识字,他们很难想出什么办法改变贫穷的生活状态。直到19世纪末,第一批罗塞托人离开家园,在大洋彼岸找到新的机遇,这个消息才给罗塞托小城带来一丝新的希望。
1882年1月,11名罗塞托人——包括10个成年男子和1个小孩儿——驾船向美国纽约进发。初到美国,他们在曼哈顿小意大利区桑树街一家小旅馆的地板上睡了一夜。随后他们向西行进,最终在纽约市以西90英里,宾夕法尼亚班戈城附近的一处采石场找到工作。第二年,又有15个罗塞托人离开意大利来到美洲,他们中的一些人与先到的同胞会合,一起在采石场谋生。这一批新移民不断向故乡发出讯息,描述这个充满机遇的新环境,于是,一批又一批罗塞托人背起行囊向宾夕法尼亚进发。不久,移民的人群就从涓涓细流汇聚成移民潮汹涌而来。仅1894年那一年,就有约1200名罗塞托人办理护照前往美国,而他们的老家罗塞托逐渐变得冷冷清清。
渐渐地这些罗塞托移民开始购置土地。通往班戈城的道路崎岖不平,地面上全是四轮马车轧过的痕迹,而他们所购置的土地就遍布在道路两旁的石山之上。他们沿着山坡建满了有着石板屋顶的两层石头房子,这些狭长的街道也慢慢变得热闹起来。他们在此处修建了一座教堂,将其命名为圣母圣衣堂,并把教堂所在的主街道命名为加里波第大道(加里波第是意大利统一运动的著名领袖)。一开始,人们给小镇起名“新意大利”,但很快又改称“罗塞托”。因为他们几乎都来自同一个村庄,这个名字让移民们备感亲切。
1896年,一位年轻力壮的神父帕斯夸里·德·尼斯科接管了圣母圣衣堂。他着手举办节日活动,在当地组织宗教生活。尼斯科鼓励居民们清扫街道,他还发放种子和树苗,让他们在自家后院种植洋葱、大豆、马铃薯、甜瓜和水果。渐渐地,小镇开始焕发生机。村民们有的养猪,有的种葡萄酿酒。小镇建起了学校、公园、修女院和墓园。一些小商店、面包房,甚至饭店、酒吧也开始在加里波第大道两旁出现。随后,10多家制衣厂也纷纷开张,从事服装贸易活动。离罗塞托最近的镇子是班戈城,在班戈城周边聚居着大量的威尔士人和英格兰人,而另一边的镇子则以德国移民为主。那时候,这些国家的移民聚居的村镇关系紧张,这就意味着居住在罗塞托的也只能是从意大利罗塞托来的移民。在20世纪初的几十年间,走在宾夕法尼亚的罗塞托,你就会发现这里的人们只说意大利语,确切来说是意大利福贾省南部小城罗塞托的方言。总之,宾夕法尼亚的这个罗塞托是个自给自足、外界知之甚少的小地方。直到斯图尔特·沃尔夫(Stewart Wolf)的出现,人们才逐渐揭开小镇神秘的面纱。
沃尔夫是名内科大夫,主要研究肠胃以及消化系统,他当时在俄克拉荷马大学医学院任教。他曾多次在宾夕法尼亚离罗塞托不远的一个农场度过暑假——当然,即便如此,他对罗塞托也鲜有耳闻。因为罗塞托是个封闭的小世界,所以就连相邻的几个城镇对它也知之甚少。“大约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某一年夏天,我们又到了那个地方。我受邀在当地的一个医学研讨会上发言,”多年以后沃尔夫在一个访谈节目中这样说道,“演讲完毕,一个同行请我吃饭。席间他对我说:‘你知道么,我在这里行医17年了,收治的病人遍布整个地区,但我几乎从来没见过65岁以下的罗塞托人来看过心脏病。’”
沃尔夫相当吃惊。在20世纪50年代,预防心脏病的降胆固醇药物以及侵入性治疗方式还未出现,心脏病是当时美国的流行病,已成为65岁以下男性病人的头号杀手。一般而言,那个时代的医生在工作中肯定都接触过心脏病病人。
于是,沃尔夫打算就此课题进行调研。他召集了他在俄克拉荷马的一些学生和同事来帮忙。他们收集了罗塞托地区大量的病患死亡报告,包括许多年前的病患资料,他们分析病患的诊疗记录,并研究用药记录以及病人家谱。“当时我们忙坏了,”沃尔夫说,“我们决定先进行初步研究,就从1961年的记录着手。镇长告诉我:‘我的四个姐姐都能来帮忙。你们还可以用镇上议会的会议室。’我说:‘那你们怎么开会?’然后他说:‘我想办法推迟会议吧。’于是来帮忙的女士们为我们做午餐,而我们就把会议室隔成了小隔间,在那里采血,测心电图。初步研究用了4个星期,随后我与当地一些有威望的人士进行了交谈。我们打算借当地小学用一个夏天,因为我想把研究范围扩大到所有的罗塞托人。”
研究结果令人称奇。在罗塞托,55岁以下的居民当中,没有一例死于心脏病发作,甚至连一例显示出心脏病症状的病人都没有。该地区65岁以上男性的心脏病死亡率只有全美国心脏病死亡率的一半左右。而该地区各种原因造成的死亡概率也比预期低30%至35%。
沃尔夫请来了他在俄克拉荷马的好友——社会学家约翰·布鲁恩来协助调研。“我雇来医学系和社会学系的学生,在罗塞托挨家挨户登门拜访,对所有年龄超过21岁的成年人做问卷调查。”布鲁恩回忆道。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50多年,但提到调研的发现,布鲁恩还是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这里没人自杀,没人酗酒,没人吸毒,犯罪率也很低。他们没有人领救济金。我们甚至没有发现任何人患上胃溃疡。生活在这里的人大多都是自然死亡,就这么简单。”
可以用沃尔夫的专业术语来形容罗塞托这样的地方——它超出了我们的日常经验,惯例已不再适用于此——罗塞托是一个“异类”(Outlier)。
超越个体寻找原因
一开始,沃尔夫以为,罗塞托人保留了旧时代的健康食谱,这使得他们比美国其他地区的居民都更健康。但很快他就发现这个假设不正确。在美国的罗塞托人做菜时喜欢用猪油,而不是像从前在意大利的罗塞托人那样,食用更有利于健康的橄榄油。意大利人做比萨时,他们会在薄薄的表面酥皮上抹油、撒盐,再加上西红柿、凤尾鱼或洋葱。而宾夕法尼亚的罗塞托人则用香肠、辣香肠、腊肠、火腿和鸡蛋来制作比萨;意大利脆饼和塔拉利饼干一般是为圣诞节和复活节准备的,而在美国的罗塞托,人们一整年都这么吃。沃尔夫请来营养师对典型的罗塞托人的饮食习惯进行分析,竟然发现当地人身体热量的41%来自饮食中的脂肪成分。在这里,人们并没有早起做瑜伽或者小跑锻炼的习惯。恰恰相反,这里的人们喜欢吸烟,而且很多人过度肥胖。
既然饮食与锻炼都无法揭开罗塞托之谜,研究人员很容易就想到遗传基因因素。在美国的罗塞托移民和意大利的罗塞托人有着紧密的亲缘关系,所以沃尔夫设想,是不是他们有特殊的耐受基因保护他们远离疾病。为此,沃尔夫开始调查生活在美国其他地区的罗塞托人的情况,看看他们是不是和宾夕法尼亚的亲戚一样百毒不侵。但结果并非如此。
于是,沃尔夫又开始考虑罗塞托人所处的地理位置,是不是宾夕法尼亚东部的山麓环境给人们带来了健康?班戈城是离罗塞托最近的镇子,就在山脚下,另一个比较近的镇子是几英里外的拿撒勒。两个镇子与罗塞托面积相当,人口结构也差不多,都是从事重体力劳动的欧洲移民。然而,沃尔夫将3个镇子的医疗报告相比较后发现,班戈和拿撒勒65岁以上男性心脏病死亡率,是罗塞托的3倍。这一条线索也断了。
慢慢地,沃尔夫开始意识到,罗塞托的秘密不在于饮食,不在于运动,也不在于遗传基因和地理位置,而在于罗塞托社会自身。当沃尔夫和布鲁恩漫步在这个小镇的时候,他们终于明白了其中的奥秘。他们看到这里的人们如何走访亲友,如何在半路上停下来用意大利语拉家常,如何在院子里为家人做饭;他们了解到这里的不同姓氏如何拓展家族规模。这里有许多三代同堂的大家庭,长辈在家族中享有绝对权威。居民们都参加圣母圣衣堂的弥撒,教会在团结社会和安抚伤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这个人口不到两千的小镇上,竟然存在22个相互独立的社会团体。这里的人们崇尚平等理念,富人不会浮夸炫耀,整个社会都愿意帮助失败者走出困境。
在罗塞托人将意大利南部的本土文化移植到宾夕法尼亚州山区的过程中,他们建立起一种强大的社会结构,这使得他们免受现代社会的压力。罗塞托人之所以健康,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山区小镇。
“我记得第一次去罗塞托,看到祖孙三代共进晚餐,看到街边许多惬意的小面包店。那里的人们经常在街上散步,有空就会坐在门廊聊天。妇女们在制衣厂工作,而男人们则在采石场里劳动。”布鲁恩说,“这真是一幅和谐的图景。”
可以想象,当布鲁恩和沃尔夫带着这种观点第一次步入医学研讨会时,他们会受到多少人的质疑。同行们当时正用冗长的数据分析遗传因素,或用复杂的图表分析生理原因,他们压根就没想到当街驻足聊天,或者三代同堂的生活方式是揭开罗塞托之谜的关键。当年主流的观点是长寿与否取决于我们是谁——也就是个体的基因,还仰赖个体做出的选择——选择吃什么,选择锻炼多长时间,以及我们受到医疗体系照顾的程度。在此之前,还从来没人从“社区”的角度研究人体健康问题。
沃尔夫和布鲁恩的研究结果使医学界最终认识到,孤立地考虑个人选择和个人行为,根本无法解释罗塞托的人们如何保持健康。这为医学界研究心脏疾病和健康问题提供了一条全新道路:那就是超越个人的范围寻找原因——要理解人们所处的文化背景,要考虑他们的家庭和朋友状况,要追踪其家族渊源。人们必须认识到,人类栖身其中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对人的发展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斯图尔特·沃尔夫所做的工作是努力揭开健康的奥秘;而在这本书中,我所做的工作则是揭开成功的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