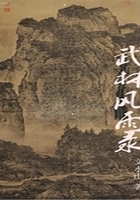
第67章 风陵野渡
“这本刀谱……”独孤胜眼带几许憾意,摇了摇头道:“虽说其中言辞古奥,颇有几分玄妙,但这些招式么……当真没有甚么称道之处!远哥儿就当是留念之物,留在身边便好了,待你伤愈,我传你一路刀法便是……”说罢拿起那刀谱来,又是微微摇了摇头。
“你看仔细了?”癞和尚神情一紧问到,他虽也看过几眼这刀谱,甚觉着刀谱中武功,并无甚么称道之处,其实还多少存着一丝侥幸之意,或许自己武学修为不够,不足以通晓这刀谱上武功,但这独孤胜他却是深知,此人博览天下武学典籍,兼之学识渊博,实为武林中不世奇才,因此才让独孤胜将这刀谱一观,哪知此刻连独孤胜都说这刀谱中武学毫无可称道之处,那么这本刀谱看来果然乃是一本废书,当真是武林中好事之人杜撰而来……
“看仔细了”独孤胜长叹一声点头道:“若有一招奇妙之处,老夫自信也能看的出来,但这其中招式,不过是故作玄妙,炫人耳目罢了,如远哥儿方才所练,莫说江湖中寻常刀客,便是乡野村夫,凭着一身蛮力,也不过一两招便能破了……”癞和尚原本还要再说几句甚么,见独孤胜说的如此笃定,也只是张了张口,到底还是摇摇头,什么也没说出来
宇文远闻言如受雷震,呆立不动,先是一副不信之意,双眼紧盯着孤独胜,想要从独孤胜脸上看出些甚么来一般,过了半晌,见独孤胜眼光落寞,神色萧然说出那番话来。猛地退后几步,脸上神情极为怪异,似是想哭,又是想笑,面容扭曲,看着如同要挤出一丝笑容来一般,却又嘴唇抖动,双眼迷离。抬头向天,双手在空中漫抓来去,所触之处空无一物,喉头咯咯有声,显见是听闻独孤胜此说,心中悲伤已极,一时不得释放而已。
独孤胜与癞和尚见宇文远如此,都是神情默然,心知这番打击,只怕比他身上所受内伤来的还重,均都叹了一口气,独孤胜食指伸出,嗤的一声点在宇文远后颈风府穴上,他知道宇文远此刻内心大乱,不论是哭是笑,必要让他出声才可,否则积郁不发,牵动心脉伤势,将来只怕更难医治,宇文远被这一指之力一点,顿时全身一震,双腿一软跪倒在地,满脸是泪,却哈哈大笑道:“为了这一本毫不足道的刀谱,蓬莱三友反目成仇……为了一本毫不足道的刀谱,你苦心孤诣珍藏了二十多年,到底没躲过这一场劫难……为了这一本毫不足道的刀谱,你们三人都是死于非命……爹呀,爹呀,你将这刀谱藏了这么许多年,倒不如当日拱手相送,何至于让儿子我流落到今天地步……若是那一晚你将这刀谱送于他二人,今日咱们父子仍在临安城外忙忙碌碌……爹啊,你……你……你好痴啊……。”。
癞和尚心中也是一片颓然,想要劝宇文远几句,却又不知从何劝起。只是在宇文远东走几步,西走几步,也不知道自己要作甚,突然哈哈一声苦笑,坐在地上叹道:“痴,果真是痴啊……想不到一本废书,夺去这许多高手性命,可笑,可叹,可悲……”独孤胜也是摇摇头,一脸苦笑,不言不语。
癞和尚呆坐良久,此时一轮夕阳渐渐西沉,天色一片深蓝,远处村庄正是晚饭时节,整个村子被一层氤氲的烟雾罩住,一群归林倦鸟,带着一阵嘈杂从天上飞过,直朝远处一片树林而去,,忽然看看一旁早已无声,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双目无神看着天上的宇文远,心中一阵无限悲凉,又看着独孤胜狐疑道:“那书中果真一无是处么?”他心中至此,虽然知道独孤胜所言定然不虚,但仍是不甘,必要求个究竟。
“一无是处!”独孤胜原已打坐入定,听得癞和尚一问,遽然睁开双目,他自然知道癞和尚心中所想,这和尚若不十分确认,绝不轻易死心,拿起那本书来道:“从这书页上颜色来看,多有水浸火烤过模样,想必是有人怕这书页上隐写字迹,因此试过,看来是无功而返,再看这书中所言,多有不可理喻之处。”说着拿起那本书来,翻开一页,手指点点道:“他书中这一路四切法所言,刀走四方,以春为引,夏则盛之,遇秋则凝,至冬而定。若照这样讲,远哥儿现在还练不成这路功夫,现在正是夏秋之交,那是练夏还是练秋?就算从春始之时练起,若是春日将尽而春刀未成,那又该如何?”
独孤胜见癞和尚一语不发,眼珠却仍在左右乱转,知道这和尚心中心思急动,想要给这几句找出一个说法来,摇着头微微一笑,将那刀谱又翻了几页道:“这几句也颇为奇怪,所谓触天地,倚风雷,如履山泽,踦行水火,周而复始,转圜相生,或风起而天地昏,或雷动而山泽变,起于行,动于势,奇妙自在其心也,这其中这个触字,前文从未提过,忽然至此冒出一句,以何触?如何触?都不可解。”
说着又翻几页道:“再看这其中所谓刺法,只有一势,所谓刀缺则刃缓,刀足则刃速,当提刀而尽其势,刃发疾逾奔雷,疾逾电闪,依我来看,这一招若真的使出奔雷之势,电光之速,只怕要选大刀,譬如河南王家金背砍山刀或是关二爷青龙偃月刀才可,只是刀势越重,破绽未免更多,一招若不能得手,岂不是受制于人?还有这刀有清浊,则刃分上下之句也不可解,何为清刀,何为浊刀?”
“天地风雷……”癞和尚口中反反复复念叨这几个字,手中指头也不住掐来掐去,好似在算甚么一般,独孤胜见这和尚到此地步还不肯甘心,将那刀谱翻到第一页道:“再看这其中总纲,开篇第一句说;刃之所依刀也,合而为不世利器,故隐而不发,善而藏之。此句勉强可解,只是这世间多有无刃之刀,锋利之处,未必就在那世间利器之下,这一句也就罢了,其下又言;论其用,运乎刀,御乎刃,无坚不摧,无往不利,刀可无刃,刀至则锋自生,刃不可无刀,虽利不能断一发。刀与刃合,乃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其功自成。这句话看似神妙,实则不值一驳,试问世间哪里会有无刀之刃?从来刀为刃体,刃为刀魂,体之不存,魂将焉附?这语句之中,为之四顾,踌躇满志八字,乃是庄子《养生主》里的原文,却放在这总纲里故弄玄虚。”
“那不是总纲……”
癞和尚正被独孤胜这一句又一句说的一阵气馁,心中那一点不甘,到底在独孤胜这解说之下消失殆尽,万般无奈看了一眼侃侃而言的独孤胜,两人都是无声苦笑,忽然躺在地上的宇文远声音微弱发出一声,倒让癞和尚一惊,唯怕这一番刺激,又激起他心中烦乱,便如在卢家庄一般发痴作癫。
“远哥儿你说甚么?”独孤胜听见这一声,眼波一动,看着宇文远,见他眼神虽空,眼光却仍是一片清澈,面容平静,并不是神智混乱之像,合起刀谱问到。
“独孤前辈,师父,你们方才所说的那个,不是总纲!”宇文远忽然翻身坐起,擦了擦脸,神色坚毅道:“这书中总纲,乃是一首解牛歌,被我义父撕去了。”
“解牛歌?”独孤胜闻言一愣,看着一旁也是目光呆滞的癞和尚道:“何为解牛歌?秃驴你可晓得?”癞和尚也是木然摇头道:“我若知道,我便告诉你了,我徒儿既然说有,那自然是有,就看他还记得不记得了!”
“记得!”宇文远掷地有声道:“当日我义父撕去这总纲,命我死记在心,切不可忘,因此宇文远从不敢将这解牛歌忘却!”
“不知远哥儿可否背出来,或许有些端倪也未可知?”独孤胜当即将那《解牛刀谱》放在膝上,端身凝坐,看着宇文远到。癞和尚也道:“你若是能背,且背出来看看,如何叫做解牛歌!”
宇文远忽的坐起,撩起衣襟在脸上擦擦,这才盘膝而坐,收敛心神,略略回忆一番,缓缓朗声道:
刺割切解隐玄机
水火锻炼始成金
灵台一点阴阳现
春夏秋冬窥四夷
天地清浊分双势
五声东西又两分
触倚履踦灵台会
桑林经首自在心
这解牛歌并不甚长,宇文远一气背完,心中也是忐忑一片,其实这解牛歌中所说,倒比那刀谱上的还玄妙难解,方才独孤胜只是将那刀谱大略一翻,便找出许多不是之处,这歌诀不过短短八句,只怕自己背完,独孤胜便要说这歌诀更是不足道。
“这……这。。这甚么意思?”独孤胜还未说话,癞和尚倒是一脸茫然道:“这歌诀念起来倒是顺口,只是这其中甚么水火,又是春夏秋冬……这是甚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