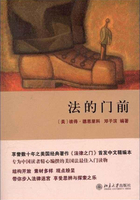
第5章 遵循先例(2)
我们认为,合法与非法必须完全取决于实施管教的意图。在权限范围内,教师就是法官,他有权判断何时需要管教和必要的管教强度,并且,像其他所有被授予自由裁量权的人一样,他不应为自己的判断错误而只应为其邪恶目的承担刑事责任。最优秀、最聪慧的凡人,也是有弱点、易犯错的动物,他在实现自己作用的过程中,其判断受到这种作用的引导,因而不应当超越其诚实的目的和勤勉的努力来要求其判断的正确性。他的判断必须被推定是正确的,这不仅因为他在此就是法官,而且因为难于证明存在需要管教的不当行为及其积累,难于展现被管教者特殊的脾气、禀性和习惯,也难于在诉诸管教前展示各种更温和的但却曾经徒劳的手段。
但是,如果教师严重滥用被授予的权力,即使没有超越它们,也是可受刑事处罚的。如果他用手中的权威遮盖恶意,在管教权的伪装下满足自己邪恶的激情,那么,他的法官面具应被剥去,将作为一个没有被授予司法权的人接受正义的审判。
我们相信这些规则适于裁决我们面前的案件。对陪审团的指导本应是这样的:除非陪审团从证据之中清晰地推断出,所实施的管教已经造成或者本质上是有意造成对孩子的永久伤害,否则,被告就没有超越被授予的权限。无论施加的皮肉之苦多么严重,无论依陪审团的判断,这种痛苦对年幼而柔弱的孩子的过失或不当行为而言是多么不相称,只要没有造成永久伤害,也不具有这样的危险,陪审团就有义务判定被告无罪,除非质证的事实在他们心中引起这样一种确信:即使依照被告自己的正义感,她也不是在诚实地履行义务,而是在履行义务的掩护下正在满足其恶意。
我们认为,尽管这些规则使教师们有机会在用权时实施草率的严厉行为,并且还能获得法律上的豁免,家长的情感、公众的舆论还是足以制约或矫正这些不够审慎的行为。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就必须将其作为瑕疵与不便的一部分而加以容忍,而瑕疵与不便是人的法律无法完全消除或彻底纠正的。
本庭推翻原判。
★“潘德格拉丝案”遵循了所有法庭意见的写作模式:讨论事实,提出法律问题,并适用一项或一组规则。通常,法庭要对规则适用做一些说明,以使人们确信案件的结论是适当的。通过朴素的实践,任何人都能掌握这一技巧并且看到案例分析法的要点。法庭拒绝承担维护学校纪律的责任,授予了教师管控孩子日常生活的权力。家长的影响或公众的舆论对于教师权力制约的效果如何?如果法院选择介入本案,会不会削弱家长的行动或减少公众的义愤?法庭判决的主要理由似乎是保护已经建立的权威或者维持等级关系。无等级制的教育是可想象的吗?也许正是基于家庭等级制的思想,本案才成为后续的殴妻案不断引证的先例。
本案至今已经许多年了,这期间我们不断遇到儿童遭受心理、身体和性侵犯的案件,在判决本案的年代,法院可以听凭其他权威体系支配本案,而现在,人们期待法院、社会机构、警察等介入这类案件。然而,孩子们易受侵犯的一些场所,也是被认为最隐私和神圣的场所。即使所有的人都承认隐私必须让位于孩子的利益,但谁应介入?在何种情况下介入呢?这些都是不容回避的现实质问。
二、乔伊纳诉乔伊纳案[Joyner v.Joyer,59 N.C.332(1862)]
陪审团查明:原告人请求离婚,她生长于体面的家庭,本人有良好教养;丈夫与她也算般配;她丈夫有一次用马鞭打她,还有一次用树条抽她,在她身上留下了几处青肿的伤痕;有几次,他曾用侮辱性的语言骂她。
首席法官皮尔森(Pearson):
立法机关认为扩充离婚的理由是有益的,但是,作为对离婚申请的限制和制约,防止离婚理由的滥用,离婚理由必须在离婚请求中“详尽而特别”列明。
根据普通法的诉讼规则,对每一事实的主张,都必须辅之以具体的“时间和地点”。这一规则的采用是为了确保诉求的适当性和确定性,但是,在诉求中没有成功证明确切的时间和地点并不总是致命的,除非时间和地点涉及本质问题并构成事实的实质部分。
从表面判断,本诉求中没有什么表明时间是实质性的或者是离婚原因的本质部分,譬如,抽打是在妻子怀孕状态下实施的,意图在于引发流产,并置她的生命于危险之中;也没有什么表明地点是离婚原因的本质部分,譬如,抽打是在公共场合实施的,意图在于羞辱她,使她的生活不堪忍受。因此,我们倾向于这样的意见:叙明时间和地点在此不是绝对必要的。
但是,我们的意见是,必须叙明用马鞭和树条抽打的情境,比如,离婚请求人的举止怎样,她都做了什么或者说了什么,以致引出丈夫的如此暴力?我们从离婚申请人那里得知,她是一个“生长于体面家庭,本人有良好教养”的妇女,丈夫与她也算般配;没有说他喝醉了酒,也没有任何一方有不忠的行为(这是请求离婚的最常见的原因)。因此,显然需要一些解释,如果不叙明产生不幸的具体情境,离婚的理由就没有被“详尽而特别”列明。
据说有这样的论点:既然丈夫有一次“用马鞭打她,还有一次用树条抽她,在她身上留下了几处青肿的伤痕”,这一事实本身也就构成离婚的充分原因,不必列明伴随这些伤害实施的具体情境。这正是本案要面对的问题。
妻子必须服从丈夫。每个男人都必须统治他的家庭,如果妻子因其不羁的性情和放肆的言辞而不断辱没丈夫,而他竟然容忍屈服,那么他不仅失去了所有的自尊感,而且丧失了家庭其他成员的尊敬;没有这种尊敬,他就不可能统治他们,并且会在邻里中名誉扫地。从人类的原初开始,这种状态就一直是婚姻关系的应有之义。上帝对女人说:“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因而,法律授权丈夫使用必要的强力使妻子安分守己。为什么妻子辱骂或袭击、殴打一位邻居,依据普通法的原则,丈夫要负责赔偿?或者,妻子当着丈夫的面实施了重罪以外的不法行为,她并不承担责任?这是因为,法律赋予丈夫对妻子的人身管辖权,因而要采取适当的措施以防这一权力的滥用。
我们不再深入讨论了,这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话题,我们也不愿招致不必要的、缺乏对弱性适当尊重的指责。就我们的目的而言,这样的阐明已经足够:可能存在这样的具体情境,它将减轻、宽宥丈夫,乃至认为丈夫“用马鞭打她,还有一次用树条抽她,在她身上留下了几处青肿的伤痕”是正当的,因而不给她声请离婚、丢弃丈夫的权利。举例来说,假如丈夫回家后妻子对他恶言相向,叫他流氓,不如死了算了。他因这种挑衅刺激而暴怒,举起恰好在手中的鞭子打了她。依我们的意见,这就是附随于丈夫行为的具体情境,并且也是他行为的诱因,它使丈夫的行为正当化,以至于法庭不仅驳回她的请求,还要奉以劝诫:“如果你改善自己的一言一行,你就能指望更好的待遇。”
★皮尔森法官对夫妻关系的一本正经的叙述,可能使当代的读者感到震惊。除了《圣经》,皮尔森还可以引证一些令人尊敬的权威,以支持某些关系是“传统的”和“自然的”思想。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说:
第一个家庭是从妇人和奴隶这两种人的联合中脱胎而来的,诗人赫西俄德(Hesiod)说得好:“首先得到一座房子、一个妻子和一头牵犁的耕牛。”(牛是穷人的奴隶。)这种按照自然法建立而又日复一日延续下来的人的联合就是家庭。
三、北卡罗来纳州诉布莱克案[State v.Black,60 N.C.262(1864)]
首席法官皮尔森:
丈夫要为妻子的行为负责,为统治家庭之目的,法律许可他对妻子施用必要的强力,以克制她的暴躁脾气,使她安分守己。除非造成了永久的伤害,或者有过分的暴力,其残忍程度说明了暴力的实施是为了满足丈夫自己邪恶的激情,否则法律将不会介入家庭或者走入幕后。法律更愿意让夫妻双方自行解决,这是引导他们重修旧好的最佳方式。
像本案这样暴露家庭内幕,肯定是毫无益处的。对当事双方而言,在法庭上将夫妻间的争吵和打斗公之于众,扩大了感情裂痕,使和好几无可能,并且鼓励了桀骜不驯。对公众而言,这是个危险的趋势。因此,为了公众利益,这类事情应被排除法庭,除非造成了永久的伤害,或者存在过分的暴力,其残忍程度昭示恶意与报复。
本案中,妻子挑起了争端。在极端的羞辱导致的激情支配下,丈夫拽着她的头发,把她拖倒在地,但他克制住自己,没有动手打她。她承认,他并没有卡她的脖子,而她在站起来以后继续辱骂他。在这种状态下,陪审团应当作有利于被告的裁决,像“潘德格拉丝案”和“乔伊纳案”所作的那样。
有人坚持认为,本案夫妻分居,不适用上述原则。我们认为,对正式离婚者可以不适用,但法律可以不理会私下的分居协议。在此,丈夫仍然为她的行为负责,婚姻关系及其附属内容都未受影响。
★法庭援引“潘德格拉丝案”与“乔伊纳案”作为先例。这两案和“布莱克案”的事实有何相似与不同?作为“布莱克案”指导的两个先例,其明确程度如何?“布莱克案”的结果是否已由两个先例所注定?法庭在“布莱克案”中指出:不必承认夫妻双方私下的分居协议。为什么维护这一协议没有维护家庭隐私重要?这些案例反映出,家庭中的权力失衡问题被回避了。法庭避重就轻,径行过渡到“责打如何发生,何时何地发生”这类问题上,不过这类问题的确能够在“较少感情用事”的情况下加以处理。像法律这样的职业,能够以感情为基础吗?感情用事的法治会是什么样子?“闭嘴”、“住口”之类能是法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