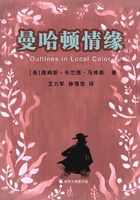
第2章 告别信
早上飘起的零星小雪快到中午时却变成了温和的阵雨,随着夜幕的降临又变成了久久不散的雾。一月最后一周的暴风雪使得街道两侧筑起了两道雪墙,每当太阳再次出来的时候,积雪就快速融化,雪水流进宽阔的排水沟,在夜间席卷城市的冷风吹拂下又变得铁硬。此时,闷热的一天已经过去,夜幕将至,一滩令人生厌的雪泥化开了,在十字路口四周流淌开来。女店员们回家时择路而行,在高架铁路车站的支柱下小心翼翼地从一角拐到另一角。头顶上方的火车一辆紧随一辆,接踵而至;火车在刺耳的刹车声中急停下来时,一团团蒸汽也随之盘旋落下。高架铁轨上的雪水滴落到下方的缆车车厢上,缆车轰隆隆地行驶,靠近十字路口时,车铃便叮当作响。空气潮湿,薄雾弥漫;路口的四个拐角上都是酒吧,酒吧窗户里的黄色灯泡周围都笼着一圈光晕。阴沉沉的一天就要结束,东河里的渡船那嘶哑而悲伤的喇叭声也越来越频繁。
一个意大利小贩已经把手推车推到通往上方车站的台阶下面,开始叫卖车上摆着的香蕉、苹果和坚果。摊位的一端摆放着一个烤花生的圆筒,小贩一丝不苟地摇动烤箱的手柄,就像在演奏手摇风琴。将近六点一刻的时候,他打开火箱,往里放了一两根柴火,顺便就着火苗暖和一下冻僵的手指。这乍现的红光透过毛毛细雨,吸引了一个正在过马路的中年男人的目光。他立足未稳,一瞬间的分心足以使他踏错步子。他脚下一滑,仰面躺到地上,右肩胛骨正好撞在一块结实的雪团上,雪团被冷风吹得很硬,但毕竟比石头人行道要软一些。
这次碰撞让他受到了严重的惊吓;他在地上躺了差不多一分钟,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根本站不起来。在他努力想站起身并再次正常呼吸的时候,他听见一个女店员大喊:“哦,莉斯,你看见他摔倒了吗?摔得可真惨。”然后,他听见女孩的同伴回应道:“我说,马姆,你去问问他伤得厉不厉害。”随后,两个男人走下人行道来扶他站起身,还有个男孩捡起他的帽子递给他。
“起来就好,”其中一个人说,“没有碰坏哪根骨头吧?”
跌倒的那个人慢慢缓过气来。“没有,”他呼哧带喘地说,“骨头没断。”说着,他小心翼翼地活动一下四肢,好确认这一点。
“这一跤摔得够呛,”另一个人说,“不过一会儿就能缓过来了。进帕特·麦卡恩的店里喝上一杯吧;会让你恢复活力的。”
“说得对,”被扶起来的那人说,“说得对;扶我进帕特·麦卡恩的店吧那儿的人认识我我能歇一下过一会儿就没事了。”他把长话拆短了说,即便如此,说起话来还是很费劲。
他滑倒的地方离酒馆门口很近,两个男孩一人搀一只胳膊,把他搀进了酒馆,径直向吧台走去。
“晚上好,马隆先生,”酒保招呼道,“老板一直在找你呢。”看到刚进门的这个人面如土灰,他又说:“你气色不太好。想来点什么吗?”
这个叫马隆的人穿着普通;衣服虽整洁但已磨得发亮;外套很薄,由于刚才跌进雪泥里,背部已弄得很脏。破旧外套的扣洞里是共和国大军[1]的青铜扣子。
马隆抓住吧台前的栏杆使自己站稳。“给我来点威士忌吧,汤姆,”他说,依然气喘吁吁,“再问一问这两个好人他们想来点什么。”
这两位先生和他一样要了威士忌。然后,他们再次安慰他,说他一会儿就没事了;说完,他们把他留在吧台前,分头离开了。
这时,酒吧里碰巧没有别的客人;酒保汤姆得以把全部注意放在马隆先生身上。
“你在老板的店门口跌倒,而他碰巧不在,没能扶你起来,听了这事他会伤心的,”汤姆说,“但你最好待到他回来再走。你要缓过劲儿来也不太容易呢我自己也摔过跤,我知道虽然我不是在冰上摔的。”
“帕特·麦卡恩想见我,是吗?”马隆问。他想深吸一口气,却发现办不到,因为他撞伤的背部肌肉不听使唤。“哦,好吧,我就坐在这儿等吧。”
“去那边角落,你的老地方坐着吧,”汤姆回应。
“我要抽上一锅子烟,”马隆边说边挪动步子,“只要刚才那一跤没摔坏我的烟斗就行。没坏,还好着呢。”说着,他从外衣胸前的暗袋里掏出一个欧石南木的烟斗。
马隆拖着脚慢吞吞地朝酒吧角落里的一张桌子走去时,临街的门被推开,酒吧老板走了进来他个子很高,戴着高顶礼帽,穿着毛边大衣。麦卡恩径直向吧台走去。
“汤姆,”麦卡恩问,“我那玻璃杯里现在还有几张记工签?”
汤姆看了看放在身后靠墙的架子顶上的一只平底玻璃杯。“还剩五张。”他回答。
“巴里·麦科马克在我们关门前会来,他会管你要记工签,你给他三张,”酒吧老板说,“告诉他就剩这几张了。如果杰里·奥康纳又来找我保释他那个犯事的弟弟,你必须把他支走。我不想保释他,你知道,但我又不想跟他直说我不愿意。”
“那我该跟他说什么呢?”酒保问,“我是不是说你去华盛顿见参议员去了比较好?”
“随你怎么说,”麦卡恩回答,“但是别让他难堪。”
“我会尽力的,”汤姆应承,“你出门之前说过要找丹尼·马隆。他现在就在角落里坐着。他在门外的冰上狠狠地摔了一跤,摔得够呛不过骨头一根没断。”
“我要告诉他的消息不会让他更好受,”麦卡恩答道,“但我会尽快说完的。”说着他穿过酒吧,走向远处的角落,来到马隆落座的小桌前。
麦卡恩向这边走来时,马隆抬起头,认出了酒吧老板,就试着站起身来;可这突然的举动被他背上拉伤的肌肉迅速制止,他随即跌坐在椅子上,脸疼得直抽搐,又喘不上气了。
“哦,丹,老伙计,”麦卡恩说,“你摔得可真够惨的。我为你难过。千万别站起来!坐那儿歇一会儿,打起精神。”
身材高大的老板僵硬地站在摔了一跤腰也挺不直的马隆身旁,好像一座铁塔,这时马隆抬起头看着店主的脸,希望上面写着好消息。
“好的,帕特,”他又缓过气来,开口说道,“我是摔了一跤但不要紧再过个把小时我就没事了。我还强壮得很哪你给我找什么活儿我都能干”
他眼巴巴地盯着对方的眼睛,急切地等着一句充满希望的话。
酒吧老板垂下目光,清了清嗓子。他的外衣扣子已经解开,衬衣前襟上的那块大宝石露了出来。
不等店主作答,马隆老汉又忧心忡忡地开口了。
“你见到他了吗?”他问。
“是的,”店主回答,“我见到他了。”
“他会给你办吗?”老汉接着问。
“他要是能办的话会为我办的,可是他不能。”麦卡恩回答。
“他不能?”马隆问,“为什么不能?”
“他说,因为那个岗位不由他指派,”酒吧老板解释,“他跟我说,如果可以的话,他很愿意把这个位置给我的朋友但那是政府文职部门。他必须照章办事,他说,主要是因为上次他打算破例,结果他们大发雷霆。”
“但我是个老兵,”马隆恳求,“我服了三年役。文职部门也得算上这个呀,不是吗?”
“此时此刻你也许就在名单上,但是根本没用,”店主回应道,“名单上的老兵现在多得是!”
“老兵协会会推荐我的,只要我开口这总该有用吧?”
“什么都没用,他是这样说的,”麦卡恩解释道,“不是一支烟、一口酒就能帮上忙,否则我自己就能给你找着工作了,对不对?”
“那么,我是谁都指望不上了?”老汉又问。
“我跟你说,我已经尽力了,而且我相信在这一片儿没有人能比我做得更好了,”酒吧老板回答,“他说他倒是愿意给把这个职位给你,可是他不能这么做。他必须录用文职人员。”
“那你就没有别的办法了?”马隆绝望地问。
“能办我就办了,”麦卡恩回答,“可我真想不到还能有什么其它办法。人家就是不肯帮忙,就是这样。一切都完了,没有别的办法。当然,我要是听到什么信儿,我会告诉你要是能行,我会为你争取的。不过现在看来,今冬找工作着实不易啊;这你很清楚。”
马隆老汉没做声;他耷拉着脑袋,茫然地盯着酒吧另一头的沙箱。
面谈终于结束了,酒吧老板松了一口气。
“好吧,”他说着转过身去,“我得走了。我得去见个新人,他刚签了合同,在哈莱姆[2]那边顶缺。”
“别觉得我不知感恩,帕特。”马隆又抬起头,说道,“你知道我很感谢你,我也知道你已经为我尽力了。”
“我确实尽力了,”麦卡恩承认,握住对方伸出的手,“我希望下次能做得更好,但愿吧。”
说着他轻轻握了握马隆的手,离开了酒吧,走的时候对酒保喊道:“如果有人找我,跟他说我一小时后就回来。好好照顾丹尼·马隆。他受的打击可不小。”
老板刚走,三位顾客就进来了,酒上来后,他们站着一口气喝光,随即离去;他们打开外门时,阴冷潮湿的夜风吹了进来。
酒保走到马隆坐的角落,马隆手里拿着没有点燃的空烟斗,正瞪着眼睛发愣。
“马隆先生,”酒保说,“现在感觉好点了吗?缓过气来了吗?”
“好,好。”马隆应道,回过神来,“现在感觉好多了。”他又试着往起站;然后又腾地跌坐在椅子上,被肌肉的剧痛所困。“我好点了但是我想我最好再歇一会儿。”
“就是嘛,”汤姆高兴地回应,“在这儿歇着。我来给你装烟斗。我想,没什么比抽口烟更让人舒坦的了。我估计,来口陈年麦芽酒应该伤不着你吧?”
五分钟后,丹尼·马隆嘴上叼着点燃的烟斗,面前的桌上摆上了一杯麦芽酒。他慢慢地喝着酒,一次只抿一小口;烟也是有一口没一口地抽着,烟斗都快灭了。他独自坐在那儿,瘫软在椅子上,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
半小时后,酒吧里又没有别的客人了,看见酒保得空儿,马隆就向他要来一个墨水瓶和一支钢笔,又要了一张纸和一个信封。汤姆把桌子清理干净,把这些东西都摆在他面前,然后他又要了一杯麦芽酒,并再次装上烟斗。
抿了一两口酒,抽了四五口烟之后,马隆忍痛坐正,开始写信。
首先,他在信封上写明收信人:奥尔巴尼[3],州议会,特伦斯·奥唐奈敬启;然后他把信封推到一边去晾干,开始写信。他的字迹比平时更不工整;他的字一贯歪歪扭扭,难以辨认,何况今天手还有点抖。
“好友特里:我在帕特·麦卡恩的酒吧里给你写这封信,这也将是你从我这儿收到的最后一封信。我在这儿的街角摔了一跤,肩膀着地,伤得很重,气都喘不过来了,现在的我就像一只闭合的风箱。我还没有缓过劲来。我再也不会有力气了。我才五十岁,但我在联邦政府的军队里服役了三年;你带着腿伤在沼泽地里摸爬滚打、日夜拼命你迟早得为寻求这种欢乐付出代价。我现在就在为我的乐子付出代价。今晚我感到十分衰老,老了就没用了。如果我再年轻点,我不相信玛丽会甩掉我跟了杰克。特里,你还年轻,又娶了一个好媳妇,上帝保佑她,你们会兴旺发达的,因为你为人正直,够朋友。但你永远不会知道被你爱的女人甩掉是什么滋味。这很伤人心,就算她嫁的是你亲弟弟也一样很伤人心。你知道,杰克只是我同父异母的弟弟,但还是一样伤人心。玛丽嫁给了他,他伤害了我,还一直不肯放过我。玛丽也站在他那边。我想这是自然他是孩子的父亲嘛但那也很伤人。这个冬天他一直对我恶语中伤。我都知道,但是我绝不会说出去。现在我发现他又在纵容孩子们和我作对。他们一直很友好,玛丽的两个孩子都是。随我名字的那个是一个好小子,特里,如果你哪天能帮他一把,那你就看在我的份上,帮帮他吧。我离开这儿后,就去当铺把手表当了,然后买把手枪。不过我会把当票和这封信一起放在信封里,有一天你发达了,我希望你把表赎出来给小丹尼。我一直想让他拥有这只表。
“我之所以现在求你,是因为这是我写给你的最后一封信,我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我正在抽我的最后一锅烟,最后的一杯啤酒也已经喝完一半了。我会在干掉剩下半杯的时候想着你,祝你健康,祝玛吉健康,也祝你们即将诞生的宝贝儿子。
“我要退场了。我累了,而且一小时前摔了那一跤之后,我体会到了从未感到过的衰老。这一跤不止让我喘不上气来,它着实把我摔惨了。我以为这儿的帕特·麦卡恩能帮我找份工作,但是他因为对文职部门有顾虑也帮不上忙。我是到了永久退场的时候了。我打算把我的表当了,买把枪。然后我就上杰克家去。玛丽不会不给我一口吃的。我要的不多,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向她伸手了。孩子们要出去聚会主日学校组织的聚会。我将最后见他们一次,向他们说再见。晚饭后,等孩子们都走了,我就掏出手枪,把子弹射向它最该去的地方。也许杰克会悔之晚矣,也许玛丽也会。我不知道。当初他们要是对我好点儿,我如今就不会需要买枪了。
别了,特里,上帝保佑你们全家。我还想见见孩子们,现在是去玛丽家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