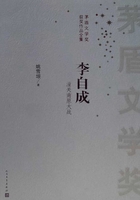
第3章 北京在戒严中(2)
当杨嗣昌同皇帝在文华殿谈话的时候,从昌平往北京德胜门的大道上奔驰着一队骑兵,大约有一百多人。他们所骑的全是口外骏马,时而加鞭飞奔,时而缓奔,以便使冒着汗水的马匹稍得休息。马蹄声在霜冻的、寂静的、夜色沉沉的旷野里像一阵凶猛的暴雨,时常从附近十分残破的村庄里引起来汪汪犬吠。一些惊魂不定的守夜人躲在黑影中向大道上张望。
挂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衔,宣、大、山西总督卢象升,骑着他的最心爱的骏马五明骥走在中间,心头上非常沉重。从五月间他的父亲在回宜兴原籍的路上病故以后,他曾经连上十疏,哀恳皇上准许他请假奔丧,在家乡守孝三年。他说他希望将父亲埋葬之后,就在父亲的坟墓旁盖三间草房,住在里边,谢绝交游,借着“庐墓”的机会安心地读三年书,然后再出来为皇帝“效犬马之劳”。但是崇祯皇帝心中明白:儒臣们在父母死后都喜欢拿庐墓三年的话妄自标榜,实际上没有看见一个做大臣的曾经那样做过。他认为卢象升请求回籍奔丧是真,庐墓三年只是说说罢了。倘在平常时候,他会立刻批准卢象升回籍奔丧,在家守孝,过一段时候如果需要他出来做事,就下诏叫他“夺情起复”[1],重新做官。然而目前国事艰难,军情紧急,崇祯不但没有准许他请假奔丧,反而根据杨嗣昌的推荐,调他做兵部尚书,加重了他的责任,另外派陈新甲接替他的总督职务。陈新甲尚在四川,因路远还没有赶来接任。清兵入塞,廷臣交章推荐,皇帝派人赐卢象升一把尚方剑,叫他星夜来京,总督天下援军。
卢象升是文进士出身,自幼脑瓜里灌满了儒家的孝道思想。在上月清兵入犯以前,京畿一带和他的宣、大防区并无战事,他每次想到不能奔丧这件事就痛哭流涕,同时对杨嗣昌很不满意。目前既然是清兵入犯,京师危急,他只好暂时放下了奔丧的念头,带兵勤王。从阳和出发以后,他只让步兵按站稍作休息,而自己同一万多骑兵日夜赶路,实在困倦时就在马鞍上合合眼皮,或在喂马时和衣躺下去矇眬一阵。今天午后,他带着骑兵到了昌平,步兵须要在三天后才能赶到。在进昌平城之前,他率领几位亲信幕僚,携带在路上准备的祭品,走进大红门,一直走到长陵前边,向武功赫赫的永乐皇帝致祭,跪在地上哽咽地祝告说:
“但愿仰仗二祖列宗[2]之灵,歼灭鞑虏,固我边疆,以尽微臣之职。臣即肝脑涂地,亦所甘心!”
申时刚过,他进到昌平城里,一看各路援师都没来到,只有他自己带的骑兵扎在城里城外。他把千总以上的军官召集到辕门外,对天酹酒,大声说:
“国难如此,援军不多,只好仰仗诸将之力,先摧折东虏气焰。倘有不奋勇杀敌的,军法不赦!”
他原以为派他总督天下勤王兵马,他可以在京畿一带同清兵决一死战,使敌人不敢再轻易入犯。不料刚到昌平就听到一个消息,说杨嗣昌和太监高起潜主张同满洲议和,不惜订城下之盟,满京城都在纷纷地议论着这件事,这使他十分生气。他把军队部署停当后,就把亲信幕僚和重要将领们召集到总督行辕的大厅里,商议如何使部队稍作休息,准备寻敌作战。有一位幕僚知道皇帝将要召见他,问道:“大人,如果杨阁老和皇上问到大人对和战有何意见,大人将如何回答?”他从桌边站起来,紧握着佩刀柄说:
“我卢某深受国恩,恨不得为国而死。今日敌兵压境,只能言战,岂能言和!”
幕僚散去,已是二更天气。仆人顾显和李奇来照料他上床安歇。他想起李奇这个人跟着他快两年了,小心服侍,没有出过错误,虽不是家生孩子[3],却同顾显差不多一样地对主人忠心耿耿。他问道:
“李奇,你的家里人都住在北京东城?”
“是的,老爷。”李奇低声回答说,一面替他整理床铺。
“到京以后,你可以回家去看看父母。恐怕你的父母也很想你啦。”
卢象升又转向顾显说:“顾显,到京后你取二十两银子给李奇,让他拿回去孝敬父母。”
“谢谢老爷!”李奇躬身说,赶快跪下去叩了个头。
卢象升正要上床,忽然门官进来禀报,说杨阁老派一位官员来见。卢象升立刻传见,原来是杨嗣昌催他连夜进京,说是皇上明日一早就要召见。他决定立刻动身,感情十分激动,吩咐左右:
“快去备马!”
在奔往德胜门的路上,他一面计划着如何同敌人作战,一面想着明天见皇上如何说话。当他驰过那被称做蓟门烟树的大都城遗址[4]时,听见从几间茅屋中传出来一家人的嚎啕哭声,使他蓦地又想起来自己的亡父,心头上十分酸楚,几乎要滚出泪来。
进了北京,回到了自己的公馆时,已经是将近四更天气。有许多京中朋友都在公馆里等候着他,希望在他还没有去觐见皇上的时候能够把自己的心里话和京中士民的舆论告诉他。他们都愤恨杨嗣昌和高起潜的“卖国求和”阴谋,要求他在皇上的面前坚决主战。有一位在督察院做御史的朋友、江南清江人杨廷麟,非常激动地说:
“九老[5],请恕小弟直言。目前阁下一身系天下臣民之望,如阁下对此事不以死力相争,京城士民将如何看待阁下?千秋后世将如何评论阁下?请勿负天下忠臣义士之心!”
“请放心,”他回答说,声音有些哽咽,“象升以不祥之身[6],来京勤王,能够战死沙场,于愿已足,决不会贪生怕死,不敢力争,致负京师士民之望,为千秋万世所不齿!”
众人一则知道卢象升几天来日夜奔波,极其辛苦,二则怕谈得太久会被东厂[7]侦事人知道,对主人和客人都很不好,只好稍谈一阵,纷纷辞去。卢象升正要休息,忽然那位跟随他两年的仆人李奇走来,恭敬地站在面前,含笑说:
“老爷,你明天去见皇上,我今夜也要走了。”
卢象升莫名其妙地说:“你要走了?你是说要回家去看看父母?为什么不等天明?”
“不是,老爷。小人的父母早亡故了,有一个哥哥住在家乡河间府,只有小人的女人在京城住。小人不再侍候老爷了,如今是向老爷请长假的。”
“为什么要请假了?害怕打仗?”卢象升用眼光逼着李奇的眼睛问,心中恼火。
“不是,不是,”李奇赶快笑着说,向后退了半步,“小人两年来在老爷身边服侍,看见老爷还没有什么大错,小人用不着再留在老爷身边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疯了?你胡说什么?”卢象升继续瞪着眼睛问。
“小人不是胡说。小人是东厂派来的。”
卢象升大吃一惊,愣了半天,才又问:“你不是户部王老爷荐来的?怎么是东厂派来的?”
“是东厂曹爷[8]托王老爷荐小人到老爷这里,为的怕老爷你多疑。要不是因为老爷待我好,我不会临走前对老爷说明身份。请老爷放心,我决不会说老爷一句坏话。”
李奇走后,卢象升感慨地叹息一声。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多年来出生入死,赤胆忠心地为皇上办事,而东厂竟然派人跟随在他的身边,把他的一言一动都随时报告皇帝!
去杨嗣昌那里报到的人已经回来,并且杨府里也派人跟着过来,告诉他杨阁老在五更时要亲自前来看他,陪他进宫。
如今已经有四更多天,公鸡早已开始叫鸣。刚才李奇的事情在他的心上所引起的不快,已经被快要陛见的大事冲淡了。仆人顾显劝他躺到床上矇眬片刻。他不肯,立刻洗脸,梳头,准备着进宫陛见。当顾显替他梳头的时候,这位忠实的仆人看见左右没有别人,忍不住喃喃地说:
“老爷,没想到李奇在老爷面前那么好,他竟是东厂的侦事人!”
“呃,天下的事情我们想不到的还多着哩。”
“我很担心,”顾显又说,“老爷今晚说了许多主战的话,他会不会一古脑儿都禀告东厂,报进宫里?”
“恐怕东厂来不及报进里边,”卢象升笑着说,“要是能报进里边就好啦。我的这些话迟早要在皇上面前说出来,早一点让皇上知道我的主张岂不更好?”
“可是杨阁老和高太监他们……”
“他们?”卢象升轻蔑地哼了一声,“主张订城下之盟的只有他们两个人,顶多不过是几个人,可是满京城百万士民都反对议和。我说的话也正是大家要说的话。再说,皇上是英明之主,我敢信他也不会同意订城下之盟!”
顾显看见他很激动,不敢再做声了。
吃了早点,稍微休息片刻,卢象升就开始穿戴。当顾显捧出二品文官朝服,侍候他更换身上的便装时,看见他不肯脱掉麻衣,胆怯地小声问:
“老爷,今天去见皇上,还穿这身孝衣在里边么?”
“穿!”
“白麻网巾[9]也不换?”
“不换!”
“网巾会露在纱帽外边,陛见时万一被皇上看见,不是有些不好么?”
“国家以孝治天下,岂有父死不戴孝之理?别噜苏!”
穿戴齐备,天才麻麻亮。杨嗣昌来了,对他说了些慰劳的话,陪着他一起骑马往皇城走去。路上常看见成群难民睡在街两旁的屋檐下,不住地呻吟悲哭。卢象升不忍看,不忍听,心中打阵儿刺疼,愤愤地想:“看国家成了什么情形,还有人想对敌人委曲求全,妄想苟安一时!”他向杨嗣昌狠狠地看了一眼,忍不住问道:
“虏兵已临城下,听说朝廷和战决策不定。皇上的意见到底如何?”
“皇上今天召见老先生[10],正要问一问老先生有何高见。”
“我公位居枢辅[11],皇上倚信甚深,不知阁老大人的意见如何?”
“九翁,你知道皇上英明天纵,许多事宸衷独断……”
“可是公系本兵,又系辅臣,常在天子左右,对和战大计应有明确主张。”
“学生也主战。”
“这就好了!”卢象升高兴地说。
“不过虏势甚锐,战亦无必胜把握。”
“只要朝廷坚决主战,激励将士,各路勤王之兵尚可一用。”
“这个……”
“阁老大人,大敌当前,难道还可以举棋不定?”
“等老先生见过皇上之后,我们再仔细商议。”
卢象升心中疑惑:“难道皇上也会主和?”但是他不敢直问,对杨嗣昌说:
“在学生看来,今日只有死战退敌,以报皇上!”
杨嗣昌没有做声,心中很不高兴。他觉得卢象升这个人秉性太强,很难马上同他的意见取得一致,只好让他碰一碰钉子再说。卢象升看透了杨嗣昌的主和心思,他不再同他争辩,心里想,等我见了皇上再说吧。
他们在承天门西边的长安右门以外下了马,步入皇城。在明代,内阁在午门内的东边,为着保密,非阁臣不得入内,所以杨嗣昌不能把卢象升请到内阁去坐。到兵部衙门休息虽然方便,过了东千步廊和宗人府就是,但太监出来宣诏和象升进宫陛见又太远,所以杨嗣昌就陪他坐在冷清的朝房中(今天不是常朝的日子)闲谈,等候着太监传旨。
大约过了一顿饭时候,从里边走出来一位太监,传卢象升速到平台见驾。象升慌忙别了嗣昌,随着太监进宫。当他从皇极殿西边走过去,穿过右顺门,走到平台前边时,皇帝已经坐在盘龙宝座上等候。御座背后有太监执着伞、扇,御座两旁站立着许多太监。两尊一人高的古铜仙鹤香炉袅袅地冒着细烟,满殿里飘着异香。殿外肃立着两行锦衣仪卫,手里的仪仗在早晨初升的阳光下闪着金光。卢象升在丹墀上行了常朝礼,手捧象牙朝笏,低着头跪在用汉白玉铺的地上,等候问话。听见太监传旨叫他进殿,他赶快起来,躬着腰从左边登上台阶,走进殿里,重新行礼,更不敢抬起头来。
虽然五年前卢象升就担任了重要军职,替崇祯立下了不少功劳,但崇祯还是第一次单独召见他,希望自己同杨嗣昌秘密决定的国策能够从这一位孚重望的总督身上得到支持。有片刻工夫,崇祯没有说话,把卢象升通身上下打量一眼。这位文进士出身而又精通武艺、熟悉韬略的人,今天给他的印象特别好。卢象升才三十九岁,面皮白皙,带有风尘色,下颏有点尖,显得清瘦,配着疏疏朗朗的胡子,完全像一个书生,不像是一个娴于骑射,能够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的人。但是他的一双剑眉和高耸的颧骨,宽阔的前额,却带着沉着而刚毅的神气。把低着头跪在面前的卢象升打量过后,皇帝开口说:
“虏骑入犯,京师戒严。卿不辞辛苦,千里勤王,又为朕总督天下援兵,抵御东虏,忠勤可嘉。朕心甚为喜慰。”
这两句慰勉的话使卢象升深深感动,觉得即令自己粉身碎骨,也没法报答皇上的“知遇之恩”。
“臣本无带兵才能,”他回答说,“平日只是愚心任事,不避任何艰难。但自臣父下世以后,臣心悲痛万分,精神混乱,远非往日可比。况以不祥之身,统帅三军,不惟在将士前观瞻不足以服人,恐怕连金鼓敲起来也会不灵。所以常恐辜负圣恩,益增臣罪。”
崇祯又安慰他说:“尽忠即是尽孝。大臣为国夺情,历朝常有。目前国步艰难,卿务须专心任事,不要过于悲伤,有负朕意。”
说到这里,崇祯就叫太监拿出花银、蟒缎,赐给象升。象升叩头谢恩毕,崇祯问道:
“东虏兵势甚强,外廷诸臣意见纷纷,莫衷一是。以卿看来,应该如何决策?”
一听见皇上提出来这个问题,似有游移口气,卢象升突然忘记害怕,也忘记注意礼节,抬起头来,双目炯炯地望着皇上,声如洪钟地说:
“陛下命臣督师,臣意主战!”
太监们都吃了一惊,偷偷地向皇上的脸上瞟了一眼,以为他必会动怒。他们看见皇上的脸色刷地红了,一直红到耳根。卢象升也意识到自己的态度有点鲁莽,赶快低下头去。但是性情暴躁的皇帝并没有动怒,反而被他这简短的一句话弄得瞠目结舌,没有话说。过了很久,他才说:
“说要招抚,是外廷诸臣如此商议,不是朕的主张。此事关系重大,卿出去后可以同杨嗣昌、高起潜他们商量。倘不用抚,那么或战或守,何者为上?”
“臣以为自古对敌,有战法,无守法。能战方能言守。如不能战,处处言守,则愈守愈受制于敌。”
“战与守,须要兼顾。”
“战即是守。今日必须以战为主,守为辅,方能制敌而不制于敌。”
“卿言战为上策,但我兵力单薄,如何战法?”
卢象升慷慨回答:“臣以为目前所患者不是我兵力单薄,是朝廷尚无决心!关宁、宣、大、山西援军不下五万,三大营兵除守城外也有数万列阵城郊。只要朝廷决心言战,鼓励将士,即不用三大营兵,五万勤王兵也堪一战。况敌轻骑来犯,深入畿辅,必须就地取粮。恳陛下明降谕旨:严令畿辅州县,坚壁清野,使敌无从得食;守土之官,与城共存亡,弃城而逃者杀无赦。洪承畴、孙传庭所统率之强兵劲旅,可抽调部分入援。畿辅士民,屡遭虏骑蹂躏,莫不义愤填胸,恨之切骨,只要朝廷稍加激劝,十万之众不难指日集合。”
“粮饷困难。”
“京城与畿辅州县,官绅富户甚多,可以倡导捐输,以救国家燃眉之急。”
崇祯苦笑一下,停了片刻,说:“洪承畴、孙传庭正在剿贼,不宜抽调。”
“即令洪承畴、孙传庭的人马不能抽调,臣虽驽钝,仍愿率关宁、宣、大、山西诸军,与虏决战。”
崇祯心思沉重,默默无语,毫无表情地凝视着卢象升的乌纱帽顶。
卢象升不敢抬头,又说:“目今国危主忧,微臣敢不肝脑涂地,以报陛下?但兵饷须要接济。”
崇祯说:“但得卿肯受任,替朕分忧,至于兵饷一节,即命杨嗣昌与户部臣设法接济。”
“谢万岁!”卢象升叩头说。
崇祯又问了些关于昌平军中和宣、大、山西防务情形,心中又十分犹豫起来。一方面,他觉得卢象升的忠心是可嘉的,坚决主战也不无道理,另一方面,他又怕万一一战而败,大局更难支撑。沉吟片刻,他说:
“卿往年剿办流贼,迭奏肤功[12]。但东虏非流贼可比,卿宜慎重。”
“用兵作战,自宜慎重。但以愚臣看来,流贼中若高迎祥与李自成一股,坚甲铁骑,部伍严整,其手下强兵悍将,不让安、史[13],只是诸臣讳言,朝廷未之深知。今日如有人在皇上前夸张虏骑精锐,只不过为议和找地步耳。”
“我军新集,远道疲累。敌势方锐,总以持重为上,不可浪战。”
卢象升听到“不可浪战”四个字不觉一惊,好像一瓢冷水浇在头顶。他正要不顾一切地继续向皇上披肝沥胆地痛切陈词,忽然皇帝用冷淡的声调说:“卿鞍马劳顿,休息去吧。至于战守事宜,可与杨嗣昌、高起潜等仔细商议,看如何进行方好。”
卢象升不敢再说什么,只得叩头辞出。他刚走到右顺门外,一个太监出来,说皇上在左顺门赐他酒饭,他就随着太监往东走去。皇上赐酒饭照例是个形式,菜只有四样,不能认真吃;酒也不能认真喝,只能把杯中的酒浇在地上,还得重新叩头谢恩。但是在封建时代,这件事被认为是皇帝的特别恩宠,也是难得的光荣。卢象升感动得噙着热泪,向北叩头,山呼万岁,同时认为皇上又倾向主战了。跟着,崇祯又派秉笔太监王承恩出来,问他此刻日旁抱珥,下有云气一股,其曲如弓,弓背朝上,是什么征兆。正如古代别的统帅一样,卢象升除精通兵法之外,也留心占候之学,而且迷信。他抬头看了一阵,记不清是在汉人《星经》还是唐人《望气经》上说过,这种现象主奸臣当道,蒙蔽主上,不觉心中叹息。但是他对王承恩说:
“请你代学生回奏陛下,此克敌之兆也。”
王承恩进去以后,卢象升怕皇上再有什么询问,不敢离开。过了一顿饭时,王承恩又走了出来,传皇上的口谕:
“上天虽有克敌之兆,但也要万分持重。军事究应如何料理,卢象升要速与杨嗣昌、高起潜详议而行。”
卢象升从左顺门出来,心中异常沉重。他找着杨嗣昌同到朝房,恰巧高起潜也在这里候他,三个人便谈了关于下午如何遵旨会议的事。因为一则这个会议必须关防十分严密,二则高起潜驻兵东直门内,杨嗣昌也住家朝阳门大街附近,所以决定午饭后在安定门上举行会议。尽管在朝房不能多谈机密大事,但是卢象升也听出来高起潜果然同杨嗣昌一个腔调,害怕同满洲兵打仗。离开朝房,他的勤王的一腔热血差不多冷了一半,只剩下惟一的希望是在下午的会议上说服他们。当他步出端门以后,回头来望一眼,在心里感慨地说:
“他们如此惧敌,热中议和,这仗叫我如何打?万不得已,我只好不顾死活,独力奋战,以谢国人!”
从大明门到西单一带的大街上,他看见了不少难民,使他的心中更加烦恼。回到公馆,听家人回禀,有许多客人前来拜候并打听朝廷和战大计。卢象升推说连日不曾睡眠,身体不适,一概不见。
“老爷,”顾显一面替他脱下朝服一面说,“刚才翰林院杨老爷来过一趟,等不着就回去了。他叫小人告诉老爷一声,他有重要话要同老爷面谈。”
“啊,知道了。”
虽然论官职他比杨廷麟大得多,但是他一向对杨廷麟怀着敬意,认为他有见识,有胆量,有骨头,有真学问。“他有什么重要话要跟我谈呢?”卢象升在心中盘算,“莫不是有可以助我一臂之力的地方?”沉吟一阵,他吩咐顾显说:
“你去回禀杨老爷,就说我稍事休息就要去安定门同杨阁老、高监军议事。请他在府上等候,我回来时一定前去领教。”
卢象升在北京的公馆里并没有亲人。他的夫人和如夫人都在五月间带着孩子们和一部分仆婢回宜兴奔丧去了。因此,卢象升从朝中回来,谢绝了宾客,躲在书房里倒也清静。随便吃一点饭,他本想稍睡一阵,但想着和战问题,十分苦闷,没法入睡。假寐片刻,他就猛然坐起,呼唤仆人顾显来帮他穿戴齐备,动身往安定门去。刚走到大门口,一个人不顾门官拦阻,从门房抢步出来,向他施礼说:
“老公祖[14],东照特来叩谒,望赐一谈!”
卢象升定睛一看,又惊又喜,上前一把拉住客人袍袖,说道:
“啊呀,姚先生从何而来?真想不到!”
“东照因事来京,适遇东虏入犯,本拟星夜返里,因闻老公祖来京勤王,故留京恭候叩谒。”
“好,好。请到里边叙话。”
这位来访的姚东照表字暾初,年在六十上下,身材魁梧,精力健旺,胸前垂着斑白长须,眉阔额广,双目有紫棱,开阖闪闪如电。他是巨鹿县的一个穷秀才,为人慷慨好义,颇重气节,在乡里很有威望。崇祯二年秋天,清兵入犯京畿,直薄朝阳门外。卢象升当时任大名知府,拔刀砍案大呼:“大丈夫岂能坐视胡马纵横!”遂募乡勇万人,星夜勤王。路过巨鹿,姚东照也率领了一千多子弟参加,很受象升嘉奖,从此他们就成了熟人。象升在大名做了几年知府,后来升任大名兵备道,管辖大名、广平和顺德三府,几次想要东照做官,都被拒绝,因而对东照更加敬重。后来他离开大名,有几年不通音讯,但听说在一次清兵深入畿辅的时候,姚东照率领乡里子弟与敌周旋,有一个儿子战死。现在这老头突然来访,卢象升又觉诧异,又觉欣喜,所以纵然有要事在身也愿意同故人一谈。到客厅中坐下以后,略作寒暄,姚东照开门见山地说:
“老公祖,你马上要去安定门商议大计,而且军务倥偬,非暇可比。东照本不应前来多渎,但国家事糜烂至此,南宋之祸迫在眉睫,东照实不能不来一见大人。大人今去会议,可知朝廷准备暗向满鞑子输银求和之事么?”
“求和之事已有所闻,输银之事尚不知道。”
“听说朝廷愿每年给东虏白银六十万两,并割弃辽东大片国土,以求朝夕之安,此不是步宋室之覆辙么?”
卢象升猛然跳起,两手按着桌子,胡须颤抖,两眼瞪着客人问:“这话可真?”
“都下有此传闻,据说可信。”
“虏方同意了么?”
“虏方只因周元忠是一卖卜盲人,不肯答应,必得朝廷派大臣前去议和,方肯允诺。目今倘不一战却敌,张我国威,恐怕订城下之盟,割土地,输岁币,接踵而至。老大人今日身系国家安危,万望在会议时痛陈利害,使一二权臣、贵珰[15]不敢再提和议。然后鼓舞三军,与虏决一死战,予以重创,使逆虏知我尚有人在,不敢再存蚕食鲸吞之心。如此则朝廷幸甚,百姓幸甚,老公祖亦不朽矣!”
“先生不用多言,学生早已筹之熟矣。有象升在,必不使大明为南宋之续!”
“东照就知道大人是当今的岳少保,得此一言,更觉安心。就此告辞了。”
卢象升又一把拉住客人,说:“暾初先生!目前正国家用人之际,学生有一言相恳,未知可否惠允?”
“老公祖有何赐教?”
“请台端屈驾至昌平军中,帮学生赞画[16]军务,俾得朝夕请教。叨在相知,敢以相请,肯俯允么?”
“东照久蒙恩顾,岂敢不听驱策。但以目前情形看来,虏骑恐将长驱深入,畿南危在旦夕,故东照已决定叩谒大人之后即便出京,星夜返里。倘果然不出所料,虏骑深入畿南,东照誓率乡里子弟与敌周旋。过蒙厚爱,只好报于异日,还恳老公祖见谅为幸。”
“好!既然如此,学生不敢强留。明日动身么?”
“不,马上动身,今夜还可以赶到长辛店。”
卢象升想着姚东照是一位穷秀才,川资可能不宽裕,便叫顾显取出来十两银子,送给东照。但这位老头子坚决不受。象升深知他秉性耿介,不好勉强,便叫顾显取来他常佩在身上的宝刀,捧到老人面前,说:
“先生此番回里,号召畿南子弟执干戈以卫桑梓,学生特赠所佩宝刀一柄,以壮行色。”
姚东照并不推辞,双手接住宝刀,慷慨地大声说:“多谢大人!倘若虏骑南下,东照誓用胡虏鲜血洗此宝刀,万一不胜,亦以此刀自裁!”
象升叹息说:“也许我们还会相见的。”
把姚东照送走以后,卢象升就带着随从骑马往安定门去。在路上,他一方面为姚东照的这次见访和慷慨还乡所感动,一方面心头上总是摆脱不掉一种不好的预感:姚东照把他比做岳少保,他平日也常以岳少保自期,可是岳少保饮恨而死,并未能挽既倒之狂澜!他抬眼望天,虽然天空只有淡淡浮云,但是他觉得似有无边愁云笼罩着北京上空,日色也昏昏无光。他还看见,凡他经过的大街上,街两旁的士民都肃静地用眼睛望他,有的眼睛里充满忧愁,有的却流露着对他的信任和希望。这些眼神和平日多么不同!
参加安定门会议的除卢象升、杨嗣昌、高起潜之外,还有两位兵部侍郎,一位勋臣,崇祯的亲信太监、提督东厂的曹化淳,以及率领京营的几员大将。平日杨嗣昌见了王德化或曹化淳,总是自居下位,让太监坐首席。卢象升一向瞧不起这班太监,认为自己是朝廷大臣,不应该巴结他们,有失士大夫气节,所以他略作谦让就拉着杨嗣昌坐在上席。高起潜等心中很不高兴,但也无可奈何。象升首先发言,坚决主战,说得慷慨激昂,但在座诸人却相顾默然。卢象升大为生气,厉声问:
“敌人兵临城下,诸公尚如此游移,难道就眼看着虏骑纵横,如入无人之境不成?”
分明是被他的正气所慑服,杨嗣昌和高起潜都没生气,劝他不要操之过急,对作战方略需要慢慢详议。他们丝毫不说他们不主张同清兵作战,但又不肯提出任何积极意见。倒是曹化淳因不满高起潜近两三年爬得太快,如今做了天下勤王兵马总监军,淡淡地说了句:
“毕竟卢老先生说的是正论。”
会议开到半夜,没有结果。当时是否对清兵作战问题,有一定的复杂性,不可能在一次会议上解决。卢象升只强调一部分勤王兵的士气可用,而杨嗣昌和高起潜等却明白军队普遍的士气不振和将领畏敌怯战。卢象升所说的号召京畿百姓从军而责令京师官绅大户出饷,根本办不到。筹饷会遭到官绅大户的强烈反对,没有饷便不能招募新兵。何况临时招募的新兵也将经不起清兵一击。所以会议进行到半夜不得结果,徒然增加了卢象升心中的苦恼和忧闷。
从东郊传过隆隆炮声,声声震撼着卢象升的心,使他如坐针毡,很想立刻奔回昌平军中,布置作战,免得在这里浪费时间。他皱着眉头,站起来走到门口,掀开帘子,侧首向东,望望城外的通天火光,回头来向大家拱拱手说:
“今夜郊外战火通天,城上争议不休,象升实感痛心。请诸位原谅。学生军务在身,须要料理,改日再议吧。”
高起潜乐得今天的会议草草结束,赶快说:“对,改日再议。”
大家下了安定门,拱手相别。卢象升不胜愤慨,跳上五明骥飞奔而去,既不谦让,也不回头招呼。杨嗣昌摇摇头,与高起潜交换了一个眼色,请高起潜和曹化淳先上马。高起潜没有立即上马,继续望着卢象升和五明骥的背影,连声称赞说:
“好马!好马!少见的好马!”
那几位京营大将,有人对今天的会议心中不平,但不敢说话;也有人畏敌如虎,看见杨嗣昌和高起潜坚主持重,放下了心。大家各怀心事,上马分头而去。
卢象升回到公馆已是三更过后,知道许多朋友来看他,打听和战决策,有些人直等到将近三更才陆续散去。第二天早晨,一吃过早饭他就进宫陛辞。这事在昨天就已经同司礼监掌印太监王德化联系好了,所以他一到朝房,等候不久,就有一名小太监走出来把他引进宫去,来到金碧辉煌的左顺门前。像一般大臣陛辞的情形一样,皇帝并没有出来,只有几个太监分两行站立殿前。卢象升在汉白玉雕龙台阶下恭敬地跪下去,向着庄严而空虚的御座叩了三个头,高声唱道:“臣卢象升向皇上叩辞,愿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看起来这句话只是一般的朝廷仪节,但当卢象升说出口时,他的心里却充满痛楚和激情,声音微颤,几乎忍不住流出眼泪,因为他有一个不好的预感:这次陛辞以后,恐怕不会再看见皇上了。
一位太监走到台阶下,口传圣旨赐给他一把尚方剑。卢象升双手捧接尚方剑,叩头谢恩,热泪突然间夺眶而出。
离开左顺门,他到内阁去向杨嗣昌辞行。限于制度,杨嗣昌没让到内阁去坐,把他送出午门。临别时候,他很想对卢象升说几句什么私话,但是嘴唇动了几动,没有说出。过了一阵,他终于小声嘱咐说:
“九翁,皇上的意思你现在也很明白。国家之患不在外而在内,未能安内,何以攘外?山西、宣大之兵,皆国家精锐。流贼未平,务必为皇上留此一点家当。”
卢象升没有做声,向他作了一个揖,回身就走。刚出承天门,他就接到从昌平来的报告,说是清兵虽然大部分向东便门和广渠门一带移动,但是也有游骑到安定门和昌平之间的地区骚扰。他决定立刻回昌平军中,对一个家丁说:
“你去告诉杨老爷,就说我因军情吃紧不能去看他,请他一二日内移驾至昌平一叙。”
吩咐毕,他连公馆也不回,赶快换了衣服,在长安右门外上了马向昌平奔去。
注释:
[1]夺情起复——在封建礼教盛行时代,做官的人遇到父母死亡,必须辞去官职,回家守三年之孝。倘若在守孝期间由于皇帝的旨意出来供职,叫做夺情,意思是为国家夺去了孝亲之情,又叫夺情起复。
[2]二祖列宗——二祖指明太祖和成祖,列宗指成祖以下至熹宗的历代皇帝。虽然明太祖不葬在昌平,但“二祖列宗”是明朝士大夫们的习惯说法。
[3]家生孩子——明朝士大夫家庭养有家奴,特别以江南为盛。家奴生的子孙仍为家奴,称为家生孩子,和临时投靠来的或收买的不同。
[4]大都城遗址——元朝时北京称做大都。德胜门外几里远有大都城蓟门(北门之一)的遗址,树木茂密,明清两朝都作为北京八景之一,称做“蓟门烟树”。
[5]九老——卢象升字建斗,别号九台,所以称他九老。明代士大夫习惯,中年人也可以被尊称为“老”。
[6]不祥之身——因为身戴重孝,所以自称是不祥之身。
[7]东厂——明代由皇帝的亲信太监掌管的特务机关,地址在如今北京的东厂胡同。
[8]曹爷——指崇祯的一位亲信大太监曹化淳,曾掌管东厂几年。
[9]网巾——明朝人束发的网子。平日用黑丝网巾,守孝时用白麻网巾。
[10]老先生——当时官场中有种习惯,如果谈话的对方是自己的同辈,或者比自己的职位稍低而不是直接下属,不管对方年老或年轻,都可以尊称对方为老先生,自称学生。
[11]枢辅——中央政府称为中枢,六部尚书都是中枢大臣。杨嗣昌以兵部尚书入阁,所以称为枢辅。
[12]肤功——大功。
[13]安、史——安禄山和史思明。
[14]老公祖——在明代,知府、巡抚和总督都可以被尊称为老公祖。
[15]珰——本是汉代阉宦帽子上的装饰物,后来就作为太监的代称。此处权臣指杨嗣昌,贵珰指高起潜。
[16]赞画——是明代督、抚幕中的一种文职官员,取赞襄谋划之意。具体职责和品级无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