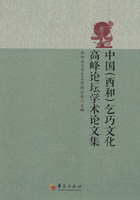
第13章 浅谈西和乞巧节的原初性及其地域性特征
兰州大学教授 柯杨
有人在传统的乞巧节与牛郎织女传说之间画上了等号,说什么“乞巧节,也称七夕节,在每年的七月七日,是由纪念牛郎与织女相爱的故事而形成的。”[1]也有人想把乞巧节人为地改变为“中国的情人节”,这都是欠妥当的。已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中的乞巧节和牛郎织女传说被区分得非常清楚。它们各有三处,即甘肃西和县、浙江温岭西塘镇和广州天河区珠村,它们被命名为七夕节(乞巧节)文化保护地;而山东沂源县燕崖乡(有唐代织女洞、牛郎庙遗址及传说)、山西和顺县松烟镇(有牛郎峪、南天池、天河梁等与牛女传说有关的遗址)及西安市长安区斗门镇(是汉代昆明池畔牛女石雕像的出土地,有石婆、石爷庙及传说),则被命名为牛郎织女传说保护地。前者的性质属于传统节日文化,后者的性质属于民间口头文学;前者是中华民族传统的女儿节,后者是一个凄婉的爱情传说,属于我国著名的四大传说之一。无论从历史文献记载、各地活动内容,还是从学术研究层面来看,这两者都是有着明显差别的。尽管乞巧节与牛女传说最初都与先民的星辰崇拜有关,但在我国民俗文化史上,它们却有着各自的发展趋向和演变轨迹,其文化内涵与核心价值观念也各不相同。
最早的关于乞巧节的文字记载,当属东晋葛洪《西京杂记》中“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人俱习之”这句话。它说明,早在汉代就有了妇女于七月七日穿针的习俗。较晚的,则有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中的记载:“七月七日,为牵牛织女聚会之夜,……是夕,妇人结彩缕,穿七孔针,或以金、银、鍮(tou黄铜)、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至于唐宋以后的文字记载和诗人们对乞巧节的描述就更多了。明人朱日藩在其《滇南七夕歌忆升庵杨公因寄》一诗的小序中写道:“予少日游滇南,见其土风每岁七夕前半月,人家女郎年十二三以上者,各分曹相聚,以香水花果为供,连臂踏歌,乞巧于天孙,词甚哀婉。”[2]这段描述中的每个细节,与如今甘肃西和县乞巧节的活动极其相似、甚至相同,不知滇南的乞巧节盛况现在尚存续否。很有必要在对这两地深入调查的基础上进行比较研究。
在甘肃东南部陇南市的西和县与礼县相交界的一大片地方,长期流传着极具地方特色的乞巧节日风俗。其文化空间之广(二十多个乡镇),延续时间之长(七天八夜),参与人数之多(约四十万人),活动内容之丰(有“制巧”、“请巧”、“迎巧”、“坐巧”、“祭巧”、“唱巧”、“相互拜巧”、“娱巧”、“跳麻姐姐”、“祈求神水”、“照瓣卜巧”、“转饭”、“巧饭会餐”、“送巧”等不同阶段的活动),在全国可能是绝无仅有的,称得上是“华夏第一”!在这篇短文里,我主要谈谈西和乞巧节作为传统女儿节的原初性质及其地域性特征。
一、巧娘娘这个神话人物是秦人祖先崇拜与星辰崇拜的合二而一
“河鼓”(牛郎星)、“织女”二星的命名始于何时虽难以考证,但到了周代,就已经是家喻户晓、一致认可的了。我认为“织女”星的命名,最初极有可能是古秦人的创造。甘肃陇南地区是秦人的发祥地。礼县永兴乡、永坪乡交界处的大堡子山一带,1994年考古发掘出秦人先公先王墓及大量高品位的青铜祭器就是明证。《史记·秦本纪》中说:“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大业。”大业乃秦人之祖先,是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时期的关键人物,而天上织女星的原型,正是历史上善织的女修,是被神化了的秦人的祖先。西和、礼县人在乞巧歌中唱到“巧娘娘”三个字时,发音为“qiaoniania”。niania者,母亲也。“巧娘娘”即“巧妈妈”,人们是以高度尊敬、虔诚的语气来称呼“巧娘娘”的,认为天上的织女星就是她们的老妈妈、老祖宗。她们一代又一代向善织的织女星祈求心灵手巧、才智双全的本领,希望在巧娘娘的佑护和传授下获得更多的生活本领、生产技艺与生存能力。正因为“巧娘娘”这个神化了的人物形象,在当地人心目中具有相当高的神圣性,因此在当地乞巧节上成为唯一被供奉的神灵。把祖先崇拜与星辰崇拜合二而一,正是西和乞巧节在民间信仰方面的显著特点之一。
二、把天上的银河叫“汉”,也与秦人崇拜织女星有密切关系
《诗经·小雅·大东》中有“维天有汉,监亦有光”的句子,《古诗十九首》之十中有“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的说法。班固《西都赋》曰:“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六朝《三辅黄图》中说,秦统一天下后,“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这些把银河称“河汉”、“云汉”、“天汉”、“银汉”等,都有一个“汉”字,为什么呢?这都来源于秦人的想象与创造,是东迁秦人对故土汉水的记忆与怀念。在古代秦人心目中,既然他们的祖先女修成了神——天上的织女星,那么,她面对的银河也应当像她生前所处的故土河流——汉水一样,叫做“汉”,这样,她就会少一点寂寞,多一点慰藉。汉水发源于甘肃,《书·禹贡》称:“嶓冢导漾,东流为汉”[3]。《山海经·西山经第二》:“太华之山……又西三百二十里曰嶓冢之山,汉水出焉,面东南流注于沔。”现在被称为西汉水的这条河,历史上长期被称为汉水,直到1933年,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所编纂的《中国分省新图》中,仍然被标为“汉水”。在汉水流域(包括它的支流漾水河)长期流传的巧娘娘节,正是古老秦文化的活态遗存,反映了我国传统岁时节日与民间信仰(自然崇拜与祖先崇拜)的密切关系。
三、西和的乞巧节从来没有牛郎的位置
虽然包括西和县在内的陇东南地区,民间也有牛郎织女的悲剧性爱情传说长期流传,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地乞巧节上,织女(巧娘娘)受到了普遍的尊崇,却恰恰没有牛郎的位置。如果说在全国其他一些地方的乞巧节上,牛郎、织女像之所以被并列在一起,受到同等的重视,主要是表达了几千年来人们对农业社会男耕女织、自给自足这一理想化了的性别角色的期望和对他们爱情悲剧的同情,那么,西和的乞巧节则从一开始就把思绪完全集中在了织女身上,女孩子们对她的期望值极高,希望通过对巧娘娘的膜拜和祈求,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在西和的乞巧节期间,几乎村村都要供奉巧娘娘的纸扎像,却从来没有出现过牛郎的纸扎像,而男孩子们也从不参与乞巧节的活动,这正是西和乞巧节最突出的地域性特征。于是,我联想到了古文献中一条有趣的记载。《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引《苏州府志》云:“织女庙在太仓州南七里黄姑塘。宋咸谆五年,嘉定知县朱象祖重修。……旧立牛、女二像。建炎时,士大夫避难东冈,有经庙中,壁间题云:商飚初起月埋轮,鸟鹊桥边绰约身。闻道佳期唯一夕,因何朝暮对斯人?乡人见此诗,因去牵牛,独留织女像。”这条资料说明,到了宋代,牛女会少离多的悲剧已深入人心,那种硬把牛女同塑一庙、令其日日同享人间供奉的做法,不论当初主持重修织女庙的县太爷用心多么善良,也被后来的人认为违背传统情理而加以改变。这个故事还从另一个侧面启示我们,全国各地的乞巧节如果仔细加以考察,其发展脉络不尽相同,在内涵和形式上也是有差别的,也就是说,它们都有其各自的地域性特征,应当让它们百花齐放,不必将其统一化,更不能在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影响下,将其改造成什么“中国的情人节”。
四、从乞巧歌看西和巧娘娘节的原初性质
我们从流传在当地的大量乞巧歌中,丝毫看不出有关男女爱情的词语和表述,有的,只是少女们学习技艺的强烈愿望和对巧娘娘的崇拜之情。虽然歌词中也偶尔出现“天上的牛郎配织女”这样的句子,但主要还是歌咏巧娘娘。比如,“一根香,两根香,把我的巧娘娘接进庄。一根线,两根线,把我的巧娘娘接进院。一根绳,两根绳,把我的巧娘娘接进门。巧娘娘,驾云端,把我的巧娘娘请下凡。”[4]在这类迎巧歌中,总是只迎巧娘娘,从来不迎牛郎。我们再来看另一首乞巧歌:“我给巧娘娘点黄蜡,巧娘娘你把善心发。巧娘娘给我赐花瓣,照着花瓣许心愿。巧了赐个花瓣儿,不巧了给个烂扇儿。巧了赐个扎花针,不巧了给个钉匣钉。巧了赐个扎花线,不巧了给个背篼襻。巧了赐个铰花剪,不巧了给个剜草铲。巧了赐个擀面杖,不巧了给个吆猪棒。巧了赐个切肉刀,不巧了给个朽心桃。巧了赐个写字笔,不巧了给个没毛鸡。巧了赐个磨墨砚,不巧了给个提水罐。巧娘娘给我赐吉祥,我给巧娘娘烧长香。巧娘娘给我赐花瓣,照着花瓣了心愿。”[5]这首有点幽默的照花瓣歌,充分表达了姑娘们乞巧时的良好愿望和紧张情绪。“巧了赐个”是她们所最希望的,而“不巧了赐个”则是她们退而求其次的要求,像“背篼襻”、“剜草铲”、“吆猪棒”、“提水罐”等都是农村里最常用也最简易的室外劳动工具,它们象征着最基本的生存手段。西和县还流传着这样一首乞巧歌:“大姐成(成:出嫁的意思)到南门下,生意算账难不住她(嫁给了商人)。二姐成到东门下,跟上提锤拉风匣(嫁给了铁匠)。三姐成到水沟下,礤洋芋来把粉挂(制作粉条)。四姐成到老庄里,学做大小炮仗哩。五姐叶家大路上,挂的挂面细如香。六姐王家磨下里,做的豆腐大着呢。七姐成到姜席川,会捻毛线会擀毡。八姐成到晚家峡,织的箩儿也不帕(网眼紧密)。九姐成到将军山,编个窠箩子装针线。十姐成到晒经寺,划篾条来编席子。当年乞巧的全散了,眼泪流成长线了。巧娘娘下云端,我把巧娘娘请下凡!”[6]这首歌反映出当年乞巧的少女都已出嫁,并在婆家学会了各自不同的生产技能,既有掌握了某种手艺的自豪感的流露,也有向巧娘娘“汇报”成果,感谢巧娘娘的意思。最值得注意的是巧娘娘不但是智慧和技艺化身,成为姑娘们崇拜和祈求的对象,甚至成为妇女们重要的精神支柱。比如,张家川县的一首乞巧歌中,就有“我给巧娘娘鞠个躬,巧娘娘教我打阿公。我给巧娘娘献花花,巧娘娘教我打阿家(婆婆)。我给巧娘娘献李子,巧娘娘教我打女婿”[7]这样的句子出现。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在三从四德旧礼教的束缚下,农村妇女所受的压迫与欺凌是众所周知的。这类乞巧歌只不过是受压迫的小媳妇们一时的气话,她们绝不敢对公公、婆婆和丈夫下手,只是利用乞巧节这个特殊的环境和氛围,向巧娘娘诉说自己的痛苦与不幸,与在场的姊妹们发泄共同的愤懑而已。巧娘娘是当地妇女内心深处的亲人,七天八夜的巧娘娘节,使女孩子们在情感上大大拉近了与巧娘娘的距离。请看这首《送巧歌》:“七月七,节满了,巧娘娘把我不管了。巧娘娘身影出了门,石头压心沉又沉。有心把巧娘娘留一天,害怕天河没渡船。有心把巧娘娘留两天,害怕走迟了天门关。有心把巧娘娘留三天,害怕老天爷寻麻烦。白肚子手巾写黑字,巧娘娘走了我没治。巧娘娘走了我心酸,眼泪流着擦不干。野鹊哥,野鹊哥,你把我巧娘娘送过河。巧娘娘,上云端,我把我巧娘娘送上天!”[8]当你身临其境,目睹姑娘们流着泪唱这类乞巧歌时,你才能体会到巧娘娘在她们生活中的重要性。
五、三点初步的结论
如果我们对西和有关乞巧节的材料进行详细的分析,就会认识到当地巧娘娘节在许多方面,的确保持着乞巧节古老的原初性质。首先,它是古老的秦文化的延续与活态遗存。巧娘娘是祖先崇拜(善织的女修)与星辰崇拜(被神化了的织女星)的合二而一,反映了我国传统岁时节日与民间信仰的密切关系。其次,它是一个以未婚少女为主体的真正的“女儿节”。祈求心灵手巧、才智双全,希望获得更多的生存本领,过上幸福的生活,是它价值观念的核心,它很少受到汉、唐以后牛郎织女凄婉爱情故事情节的影响。牛郎在当地巧娘娘节上毫无地位可言,当地人从未制作过与巧娘娘平起平坐的牛郎纸扎像,在大量的乞巧歌中,姑娘们也很少提到他。第三,西和乞巧节在历史上当然也在发展变化,但它不是朝着牛女爱情传说的方向延伸,而是朝着为受压迫的农村妇女争取社会地位和话语权的方向发展,成为女孩子们从自然人向社会人过渡的重要载体,为她们的成长、成熟提供了广阔的社交空间。这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就这一点而言,说西和巧娘娘节是当地传统的“妇女解放日”或“妇女狂欢节”也不为过。由此可见,我国各地的乞巧节也是百花齐放、各有千秋的,不必人为地予以划一,更没有必要改变它们各自的传统内涵,叫什么“中国的情人节”!那种处处事事奉西方文化为圭臬的思维,不但是受欧洲文化中心论影响太深的表现,也是对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缺乏自觉、自尊、自爱、自信的表现,是我们所不赞成的。
注释:
[1]杨景震:《中国传统岁时节日风俗》第189页,西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第1版。
[2]朱日藩,字子价,江苏宝应人,嘉靖23年(公元1544年)进士,其《滇南七夕歌忆升庵杨公因寄》一诗,见《明诗记事》己签卷八。
[3]嶓冢(bozhong),山名,汉水发源地,在今甘肃省天水市与礼县之间,现名齐寿山。
[4]见《中国歌谣集成·甘肃卷》第354页。
[5]见杨克栋搜集《西和乞巧歌》(自印本)。
[6]见赵子贤编《西和乞巧歌》,第21页,线装本,香港银河出版社,2012年7月第3次印刷。
[7]见《中国民间歌谣集成·甘肃卷》,第355页。
[8]见《西和乞巧歌》,第1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