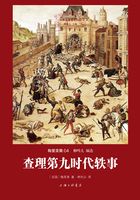
第2章 作者序
我刚读完不少关于十六世纪末叶的回忆录和小品文。我想把我所读过的写成一篇概要,这儿就是这个概要。
在历史中我只喜欢轶事,而在轶事中我偏爱的是那些我认为可以从里边找到某一个时代的风气和特征的真实画图的轶事。这种口味不大高贵;但是我很惭愧地承认,我却宁愿拿修昔底德[1]的作品来换取真正阿斯巴西[2]的回忆录或伯里克利[3]手下的某一奴隶的回忆录;因为回忆录是作者和他的读者之间的亲切闲谈,只有它才能够把那个引起我的兴趣和关心的人物形象供给我。绝不是在梅捷黎[4]的作品里,而是在蒙鲁克[5]、勃兰多姆[6]、德·窝比臬[7]、达瓦涅[8]、拉·怒[9]等的作品里,人们才能够对十六世纪的法兰西人得出一个概念。当时的这几个作者的笔调也和他们的记述一样,告诉了我这个概念。例如,在埃都亚勒[10]的作品里我便读到了这段简括的记载:
沙多涅夫的那位小姐是国王未去波兰以前的一个宠姬,后来和一个名叫安蒂诺蒂的佛罗伦萨人,在马赛管战船的军官,因一时冲动而结了婚,当她发现他放荡不羁时,便毫不迟疑地亲手杀了他。
利用这段故事和勃兰多姆的作品中充满着的那么多其他的故事,我在我的脑子里重新构思了一个性格,使亨利第三的宫廷中一位夫人复活起来。
假如把这样的习俗和我们目下的习俗做一个比较,并且看到在我们的习俗里强烈的热情已经衰退,因此得到了安宁,也许竟得到了幸福,这是很有趣的事。剩下的问题是要知道,我们是不是比我们的祖先更有价值,而这问题也不是容易解决的;因为,即使是对于同样的行为,人们的意见也依着时代的不同而有大大的改变。
因此,在1500年左右一桩暗杀案或毒害案所激起的愤恨就不会跟今天令人感到的相同。那时一位贵族暗杀了他的敌人,请求恩赦,并且得到了赦免之后,仍可以在社会上重新出现,并不会有什么人想对他摆出难看的脸孔。甚至有的时候,如果那暗杀是一种合理的复仇的结果,那么人们谈起凶手时,就像今天人们谈起一位受到一个下贱人严重侮辱,于是在决斗场中把他杀掉的翩翩公子一样。
所以,我认为十六世纪人的行为当然不该依我们十九世纪的意见来批判。在一个文化进步的国家里视为犯法的事,在一个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里看来,或者只是一种大胆的表现,甚至在一个野蛮的时代里,或者竟是一种值得称赞的行为。我觉得,要适当地对同样的行为下个判断,也应该随着国家的不同而分别对待,因为在一个民族和另一个民族之间存在着的差异,并不亚于一个世纪和另一个世纪之间存在的差异。
穆罕默德·阿里[11],因为土耳其埃及混合军的高级军官们跟他争夺在埃及的权力,一天邀请了这个军队的主要首领们到他的深宫里参加一场欢会。这些人一进去,所有的门户都重新关上了。一些阿尔巴尼亚(雇佣军)躲在土台上,向他们开了枪,从那时起,穆罕默德·阿里就在埃及实行独裁统治了。[12]
好吧!我们来谈论穆罕默德·阿里吧;他甚至受到欧洲人的尊敬,并且在所有的报纸上,他都被认为是个伟大的人物;人们说他是埃及的恩人。可是还有什么比唆使杀害一些猝不及防的人更堪痛恨的呢?事实上,这类的诱杀,由于一国的习惯以及除此之外更无别法可以采取的缘故,也就被许可了,所以费嘉罗的这句格言“Ma,per Dio,I'utilita!”[13]就被应用上了。
假如我们的一位大臣[14](故隐其名)也有一些愿听他的命令而开枪的阿尔巴尼亚人(雇佣军),并且在一场盛宴当中把左派的出色分子都杀害了,那么,他的行为事实上与埃及首长的行为是相同的,但在道德上来说,其罪行却大了百倍。因为按照我们的风俗习惯,这样的暗杀是不再允许的了。但是这个大臣却开除了许多自由党选举人——政府中不著名的职员;他以此威吓了其他的人,于是取得了如意的选举结果[15]。如果穆罕默德·阿里是法国的大臣,他也不会做得更毒辣;反之,法国大臣在埃及,毫无疑问,他也不得不借助于枪杀,因为对土耳其和埃及混合军的情绪来说,光靠这样开除,并不能产生足够的效果。
圣·巴托罗缪[16]大屠杀,就是在当时来说,也是一桩天大的罪恶;但是,我再说一遍,十六世纪的一场屠杀和十九世纪的一场屠杀比起来,绝对不是同样程度的罪恶。我们补充一句,参加这屠杀的是绝大多数的国民,有的是用实际行动,有的是用同情心来支持:他们武装起来,追击那些他们当作异族和敌人看待的胡格诺[17]。
圣·巴托罗缪就像是一场和1809年西班牙人的叛乱相类似的民族叛乱;巴黎的上流人暗杀异教徒时,坚决地相信那是顺着上天的意旨而行的。
本来不该由我这样一个编故事的人把1572年的历史性的事故,在这部书里做个概述;但是,我既然提起圣·巴托罗缪事件,我就按捺不住自己在这儿暴露出当我读到我们的历史里这血腥的一页时涌上心头的一些概念。
人们究竟有没有很好地理解哪些是导致这场大屠杀的原因呢?这屠杀事前是否经过了长期策划,或者只是一种突然决定的结果,甚至是偶然发生的事故呢?
对于这一切问题,没有一个历史学家给过我满意的答复。
他们把一些道听途说之词当作了证据,而不知道,要肯定这样重要的一个历史观点,那些街谈巷议是很不够分量的。
这些历史学家,有的把查理第九描写成一个作伪的行家;有的把他形容成一个粗暴、古怪和性急的人。如果远在八月十四日以前,他曾发脾气吓唬过新教徒……那就是他老早策划毁灭他们的明证;如果他对他们表示过亲热……那就是他作伪的明证。
我只想举出一桩故事,这桩故事是到处流传的,而且足以证明人们是何等轻率地容纳一切最不可靠的流言。
差不多在圣·巴托罗缪事件发生的前一年,据说,人们已经订好了一个屠杀计划。这计划是:必须在克列尔克草坪建筑一座木塔;要把古伊兹公爵跟若干贵族和天主教士兵安排在塔内,海军上将要指挥新教徒演习一场攻击战,好像要向国王炫示一场包围战的奇观。这种军事演习一旦开始,在一个约定的信号下,天主教徒就要拿起他们的武器来杀猝不及防的敌人。为了穿插这个故事,人们又说,查理第九有一个名叫理臬罗乐的宠臣可能不谨慎地揭穿了这一切阴谋,告诉这个对新教徒贵族们口出不逊的国王说:“呀!陛下,再等一等吧,我们当前有一座木塔,它将替我们对一切异教徒报仇的。”请你们注意,这座木塔,其实一块木板也没竖起来哩。国王于是就派人杀掉了这个多嘴的人。据说,那计划是侍从武官长比拉克想出来的,不过,有一句表达与此大不相同的意见的话:“为了使国王挣脱开他的敌人们,只要找几个厨子就行了。”这句话,人们也认为是他说的。这一个方法要比那一个方法实际得多,因为那个方法,由于过分出奇,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事实上,新教徒看到了这场小战事的种种准备后,怎么会不起狐疑呢?两个教派一向本是互相敌视的,现在竟这样面对面混在了一起,这能不怀疑吗?其次,为了要占胡格诺们的便宜,先让他们武装起来组成军队,也是一个很不好的方法。很显然的,如果那时要阴谋将他们一网打尽,倒不如干脆趁他们各个孤立而且还没有武装起来的时候就下手袭击,要好得多。
我呢,我坚决相信,屠杀并没有经过预先策划,并且我不能想象,会有某些作者既同意把凯瑟琳王后看作是一个十分恶毒的女人——那是真的——同时又说她是这世纪中一个最有政治头脑的女人,却会持有与我相反的意见。
我们暂把道德放在一边不谈,我们先就利害观点考查这个所谓的计划吧。啊,我肯定,它对朝廷是没有利益的,况且,这计划实施时笨拙非常,所以必须假定那些策划的人是男人当中最离奇古怪的人。
希望人们考查一下,究竟实践了这计划,国王的权力是有所得还是有所失,容忍这个计划的实践对国王是有利还是无利。
法兰西当时被分作三大党派:新教徒的党,从孔德亲王死了之后,海军上将[18]是党魁;国王的党,最弱的一个党;古伊兹派或那时急进保王党人的党。
显然地,国王由于同样害怕古伊兹派和新教徒,应该设法让这两个党派互相水火从而保全自己的权力。粉碎了其中的一派,便是把自己交给另一派任意宰割。
这种平衡两端的政策从那时起是颇为人所熟悉而通行的。路易十一说过“分化是为了统治”这句话。
现在考查考查,究竟查理第九是否是一个对宗教很虔诚的人;因为过分的虔诚,很可能引起他不惜采取一个违反自己利益的步骤。可是一切都相反地说明:他固然不是一个性情坚强的人,但也不是一个对宗教热心过度的人。况且,他的母亲在指挥着他呢,她如果有宗教顾虑的话,为了热爱权力叫她牺牲宗教顾虑,她也是不会迟疑不决的。
但是我们假定,查理或者他的母亲,或者他的政府曾经违反政治上的一切法则,决定要消灭法国国内的新教徒,那么,这个决定一旦被采取了,他们就很可能周密地策划足以保证成功的方法。啊,首先呈现在脑中的最可靠的主意是,屠杀要同时在王国的所有城市里发动起来,迫使宗教改革者们四面八方被优势的武力所袭击,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能够自卫。这样,只要仅仅一天工夫就足够消灭他们了。阿赛鲁斯就是这样做出屠杀犹太人的计划的。
不过我们谈过,国王发下屠杀新教徒的最先命令的日期是八月二十八日,就是在圣·巴托罗缪事件发动后的第四天,当这场大屠杀的消息已经在国王的诏文之前传开了,而且震惊了新教中一切的人的时候。
当时特别需要的是占领新教徒盘踞的地方。只要这些地方一天还留在他们的势力范围之内,国王的权力就一天得不到保证。所以,在天主教徒的一个假定的阴谋中,很明显地指出,最重要的步骤是要于八月二十四日占领罗舍尔,并且同时要有一支军队驻扎在法国南部,以便镇压改革者们的一切集会。
所有这一切一点也没有做到。
我很难接受,同是那一班人既然会想象出一个后果会那样重要的罪行,却又那样不善于实现它。结果,步骤进行得那样不好,弄到在圣·巴托罗缪事件之后几个月,战事就重新爆发,宗教改革者们一定因此感到十分光荣,甚至从中取得了新的利益。
柯里尼的暗杀案发生于圣·巴托罗缪事件前两天,这难道还不够驳倒那假定的阴谋吗?为什么要在整体屠杀之前杀害党魁呢?难道这绝对不是吓唬胡格诺们并且逼迫他们自我防范的方法吗?
我知道有几位作者要把侵犯海军上将人身的犯罪行为归罪于古伊兹公爵一个人;但是,除了舆论控告国王犯了这个罪行和凶手得到国王的奖赏之外,我还从这个事实里找出一点理由来反驳同谋的看法。事实上,假如同谋是确有其事的话,古伊兹公爵就必须参加这个同谋;那么,为什么不把替他家庭复仇的举动推迟两天,使它更可靠呢?为什么单单为了希望他的敌人提前两天送命而影响整个冒险企图的成功呢?
因此,在我看来,一切似乎都证实了这场大屠杀绝不是国王对付一部分人民的一种阴谋的后果,我觉得,圣·巴托罗缪事件是一种预料不到的而且是临时发作的人民叛乱的结果。
我将十分谦逊地写出我的晦涩难解的说明。
柯里尼曾经三次和他的至尊争强斗霸;这是被怀恨的一个原因。贞纳·德·亚尔培[19]去世之后,两个年轻的亲王——那瓦尔国王和德·孔德亲王过于年轻,不能行使权力,柯里尼才是宗教改革派的真正的唯一党魁。她死的时候,两个年轻的亲王,身陷敌人的阵营里,说来就是俘虏,只有听任国王摆布了。所以把柯里尼,只要把柯里尼一人置之死地,就是保证查理的权力的重要的一着,查理或者并没有忘记亚尔培公爵的一句话:“一只鲑鱼的脑袋比一万只青蛙好得多。”
但是,假如国王能够从同一事变中同时摆脱了海军上将和德·古伊兹公爵的话,那么,他当然会变成至高无上的主子。
这该是他所采取的主意:唆使暗杀海军上将,或者,必要时,把这桩暗杀案栽到古伊兹身上,然后把这个亲王作为杀人犯,命令追捕他,一面宣称将把他交付胡格诺们去报复。人们知道,古伊兹公爵,不管在摩尔维尔[20]的行为中是否犯罪,便急急忙忙地离开巴黎,并且那些表面上受到国王保护的改革派分子都纷纷出面,对罗林家里的亲王们示威。
巴黎的人民在这时期里,对宗教的狂热到了可怕的程度。上流人们武装组织起来,成立了一种国防军,一听见警钟的第一声,就会拿起武器。由于德·古伊兹公爵的父亲给人们留下的记忆和他自己的功绩,因此德·古伊兹公爵越是受巴黎人的爱戴,那些曾经两次围攻他们的胡格诺就越引起他们的憎恨。这些胡格诺当国王的一位姐妹和一位属于他们宗教的亲王联姻时,在宫廷中享到的一种恩惠加倍地引起了他们的气焰和他们的敌人对他们的仇恨。简单说一句,这时只要有一位党魁站在这帮对宗教狂热的人的前头,对他们喊一声“打”,他们就会马上奔去格杀他们的异教徒同胞。
公爵被朝廷放逐出来,受到国王和新教徒的威吓,只好从人民方面找寻支持。他集中了上流人警卫队的首长们,对他们说异教徒将有不轨行动,鼓动他们必须先发制人,在他们没行动之前杀掉他们,屠杀只是在那时候才策划下来的。因为从计划至执行之间只经过短短的几个小时,人们不难解释那伴随着这阴谋的神秘性和那么多人竟然会如此慎重地保守这阴谋的秘密;要不然,这就显得很奇怪了,因为在巴黎机密泄露得很快。
国王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参与屠杀,那是很难确定的;即使说他没有同意,他也一定听任那样做。在屠杀和暴行发生后两天,他否认了一切,并且要制止屠杀。可是人民的怒火已经燃起来了,只流这么一点点血,人民是安静不下来的。必须牺牲到六万人以上,逼得君主自己不得不卷入那条支配了他的洪流之中。他于是撤销了他的赦罪的命令,并且很快就发出其他的命令,使暗杀蔓延到整个法国。
以上就是我对圣·巴托罗缪事件的意见,在把这意见公之于世的同时,我要引用拜伦写的一句诗:
我只是说,姑且这样假定吧!
182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