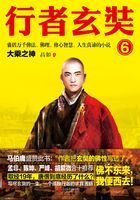
第5章 东印度论师
回到师尊面前,布隆陀耶忍不住对玄奘连连称赞:“东土法师的智慧真的很不一般,我从未听过如此逻辑严密又吸引人的讲座!听他讲经的人不只是那烂陀寺的,还有来自五印度各国的僧侣居士,人数之众真是难以言说!不仅大乘学僧听得如痴如醉,就连一些小乘论师和婆罗门也都欢喜称道。”
师子光长老被彻底激怒了:“你听着也很欢喜是吗?那你还回来做什么?干脆去听他的不是更好吗?”
布隆陀耶吓了一跳,这才意识到自己一时忘情了,忙垂手而立:“弟子失言,请师尊不要生气。”
师子光“哼”了一声,没有再说什么,他虽性子刚烈,却也知道这气不该朝徒弟发。
然而气在心里总是很不舒服的,师子光过后想想,觉得此事之过全在戒贤,若不是这个正法藏在同自己作对,自己又怎么可能丢这份面子?
转念再一想,玄奘以一个新任经师的身份,初次讲经就有如此威望,很难说不是戒贤在背后起作用。
一个人的心中一旦生疑,无论对方做什么,他都会朝着最接近他心中答案的那个地方去想。师子光长老原本就排斥瑜伽行派,对戒贤尊者也心怀不满,此时无明上来,真是越想越气,再次讲经时,语言中便开始夹枪带棒。
玄奘的讲座渐入佳境,听经的人数每天都在攀升,以室利般摩为首的一批大乘学僧,成为他在那烂陀寺的第一批弟子。
对于师子光的挑衅甚至损毁,玄奘心里是很清楚的,但他并不多加理会。在他看来,很多无谓的辩白都属于争论的范畴,是被胜负心所控制的,与真理相悖。更何况,他早已通解中观学派和瑜伽行派的义理,最近一段时间的讲经,他将自己从前所学贯穿起来,更看出马鸣、龙树之学和无著、世亲之说表面上立说各异,实则并无相违,都不离佛陀的真实言教。因而他还是抱着“会宗”的想法,最不济也求同存异了。
师子光在讲论时处处指称“中观”之旨能破“瑜伽”之义,对戒贤尊者和玄奘夹带攻击,玄奘却始终装聋作哑,只管讲自己的经,别的事情似乎都与他无关。师子光总觉得自己的拳头打在了棉花上,心中恼怒更甚,又联想到上次玄奘到他的讲坛前征诘之事,无明之火找不到消解之处,干脆直接去找戒贤。
“老僧年事已高,早已多年不参与辩论了。”面对气势汹汹的师子光,戒贤尊者只一句话就给他堵了回去。
然而师子光并不肯就此罢休,他冷冷地质问道:“正法藏自知年纪大了,我不能向你挑战。这样就可以无所顾忌地羞辱我吗?”
“长老此言差矣。”尊者微笑道,“老僧现在只是闭门修行,何时羞辱过长老?”
“正法藏当然用不着自己出面,因为你的东土弟子已经在替你做这一切了。”
“你是说玄奘吗?”尊者的神态越发平和,脸上泛着安详的光芒,“不错,是老僧让他担任讲经师的,并请他在雨安居期间设置讲筵。他已经完成了学业,寺中僧众都很喜欢他,目前我们那烂陀寺人才凋零,正需要像他这样辩才出众又有众生缘的讲经师。”
师子光轻哼一声:“正法藏只是想要光大那烂陀寺吗?为何要他羞辱于我?”
“老僧绝没有这个意思。”
“正法藏何必不承认呢?”师子光冷笑道,“那烂陀寺每天都有上百场经筵,都是本寺威望极高的长老所设。玄奘只是个新任经师,若无正法藏的暗中相助,他凭什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聚集起如此多的听众?”
“长老差矣。”尊者面含微笑,缓缓摇头道,“玄奘的威望早在来那烂陀寺之前就已经很高了,他在迦湿弥罗等国讲经时,下面的听众都是像潮水一般啊!长老这些年来潜心学问,想来还是不太了解外面的情况。”
师子光一时无语,其实这些事情他是了解一些的,他只是觉得北印度各国的佛学气氛和水平,如何能同中印度特别是摩揭陀国相比?
正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却听戒贤尊者接着说道:“如果玄奘真的羞辱了长老,长老只管去找他征诘,为何要来老僧这里聒噪?难道,这位新任经师的年纪也已经大到不能参加辩论了吗?”
师子光哼了一声道:“我找过他,可他并不应战。”
“这不可能吧?”尊者充满智慧的目光凝视着师子光,“作为论师是不能对挑战置之不理的,若说玄奘会做出这等无礼之事,老僧断然不信。”
师子光一时语塞,他虽与玄奘在同一地点各自讲经,但确实未曾向对方发出过正式辩论的邀请,玄奘的辩才和反应速度他是领教过的,热季中的那次短兵相接,使他对这位年轻的客僧多少有些发怵。
但是现在他知道,他已经不得不向玄奘发出挑战,而玄奘也不得不应战了。
那烂陀广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火爆场景,两位法师一边讲课,一边相互辩论,讲筵前的听众越聚越多,几乎挤不下了。
辩论很快呈现出一边倒的局面,玄奘显然比师子光更懂得说话和讲经的技巧。再加上他既通“瑜伽”理论,又通《中论》和《百论》,因而在阐述某一立论时,便能够纵横捭阖,互相印证,融会贯通;而师子光却只能从《中百论》一家之言论述,难免会有前后矛盾、互相脱节的情况出现,几个回合一过,已露捉襟见肘之弊。
几天下来,师子光始终无法自圆其说,被玄奘逼得节节败退,众多学僧都涌到玄奘的讲坛前听法,到后来,就连原本聚集在师子光讲坛前的学僧们也都纷纷移席,改投玄奘门下。
眼见自己法座下的听众越来越少,连门下弟子也渐渐离散而改宗玄奘,只剩下布隆陀耶等少数几个贴身弟子还在身边,师子光羞愤难当,未讲完就称病撤了讲筵。
雨季即将结束时,一位四十多岁、身材修长的中年僧侣来到那烂陀寺,径直来到玄奘的住处。
“真漂亮啊。”行走在铺满金链花的小径上,僧侣忍不住赞叹了一句,同时,他的嘴角却又露出一丝嘲讽,“这样的地方,是一个修行者应该住的吗?”
的确,眼前这个小小的院落,堪称那烂陀寺最漂亮最清净的一套院舍了。院内外盛开着各色鲜花,其中尤以郁金香和金链花树最多。眼下正是落花时节,金链花瓣从高大的树冠上掉落下来,或随风翻飞,或如细雨般飘落,因而又被称作黄金雨。
除金链花外,还有蒲桃和硕大的蔷薇树,将这座小小的院舍装扮得格外明媚耀目,空气中洋溢着醉人的花香……
这座院落就是当年护法菩萨的故居,自从玄奘做了讲经师,收了弟子,戒贤尊者便安排他搬离戒日王院,到这里居住。
玄奘不在,弟子室利般摩在一棵高大的金香木下接待了来访者。
“请问大师是从哪里来的,找我师尊何事?”室利般摩礼貌地问道。
“沙门乃是迦耶山大菩提寺比丘,法名旃陀罗僧诃,今日专程前来拜谒玄奘法师,烦请这位同修通报一下。”客僧的回答也十分客气。
旃陀罗僧诃?月亮狮子?这名字有些耳熟,莫不是个高僧?[1]
室利般摩好奇地打量着他,但见此人面貌清癯,肤色白皙,一袭深褐色僧伽胝长衣,潇潇洒洒,行止间果然有些不凡,却又实在想不起在哪里听说过这个人。
室利般摩毕竟不是见多识广之人,又想僧人的法名大同小异,自己又何必想太多?于是恭恭敬敬地回话道:“大师来得不巧,师尊现在不在寺中。”
“哦?”师子月有些意外,“尊师最近不是在设筵讲经吗,怎会不在寺中?”
“是这样的,这几日,每当经筵结束,师尊便离开了,回来时已经很晚,却并不耽误明日的讲筵。”
“原来如此……”
见客僧面露失望之色,室利般摩只当他也是慕名来听师父讲经的,心中顿生亲近之意,热情邀请道:“大师旅途劳顿,弟子先为您安排住处歇息一晚,待明日一早领您去听经,您就可以见到我师父了。”
“不必麻烦了,沙门有地方住。”师子月淡淡地说道,“不知尊师去了哪里?”
“这个,我们可不知道。”室利般摩笑道,“师尊的去向,做弟子的怎好随便打听呢?”
师子月还想再说什么,这时,玄奘的另一弟子,来自东印度的摩离多罗闻声走了出来:“大师找我们师父,有什么事吗?”
“哦,是关于大乘佛法的一些问题,沙门想找玄奘法师探讨一下。”
说到这里,师子月突然想起了什么:“法师既然不在,其新著《会宗论》,可否让沙门一观?”
“可以啊!”室利般摩一心只想替师父扬名,也不疑有他,转身便去将《会宗论》的抄本取了出来。
客僧接过《会宗论》,放在随身的搭包里,合掌道谢后扬长而去。
看着他的背影,摩离多罗皱了皱眉头:“这个人有点古怪,你没问问他是谁?”
“我问了,他说他是迦耶山大菩提寺的旃陀罗僧诃。”
摩离多罗的面容登时变得冷峻起来。
室利般摩见他这般,笑道:“师兄觉得这名字很耳熟,是不是?他是个高僧吧?”
“算是吧。”摩离多罗不冷不热地回答,“在摩揭陀国,知道他的人或许还不太多;但是在东印度,此人几乎家喻户晓,无人不知!”
“这么有名啊!”室利般摩兴奋起来,“我就说嘛,看他气度不凡,像个高僧的样子!想不到咱们师父的名气已经这么大了,连这样的高僧都来皈依!”
“他有说过他是来皈依的吗?”摩离多罗问。
“他说他是来请教的。”室利般摩对此倒是满不在乎,“高僧嘛,说话的语气总归要高傲一些,师兄不必在意啦。”
“师父也是高僧,你可曾见他使用过如此高傲的语气?”摩离多罗反问了一句,又说道,“我告诉你,这个旃陀罗僧诃是师子光长老的同门师弟,东印度中观学派最有名的论师,极善辩论。”
“啊?”室利般摩吓了一跳,“你怎么不早说?”
他连连顿足,懊恼不已:“我早该想到的!月亮狮子,当初听到这个名字就觉得不对,一定是师子光长老请他来的!说什么向师父请教探讨,说得可真好听,就是来找师父论战的!我刚才真是太大意了,真不该让他拿走《会宗论》。”
摩离多罗反倒冷静下来,安慰他道:“拿都拿了,还说什么?等晚上师父回来再禀报吧。”
室利般摩呆了一下,只得转身进屋,嘴里还在懊悔地自言自语:“怪不得他不肯住在这里,我早该看出他有些不对劲儿的!也不知师父什么时候回来,真急死人了……”
就在两个弟子为那个来自东印度的挑战者紧张不已时,玄奘却正悠闲地坐在那烂陀寺西边的一间茅舍内喝茶。他的面前是一位容颜枯瘦的老僧。
这是一间被丛林遮掩住的简陋的小屋,而进入到里面,则更像是一个石器作坊——地上遍布着碎石废料,以及石刻的盘子、盆等物件,上面雕刻着细细的纹饰。
沿墙还堆砌着一大片石板,有的雕绘着粗大的凸纹壁画,有的则刻着一些像扭曲的丝线一般的奇怪文字。这些石壁一直延伸到正屋的石案上,那儿供奉着一尊小小的石质佛像,其做工十分精巧细腻,形象逼真,别有一番情趣。
“这些都是我兄弟波罗耶舍刻的。”见玄奘关注这屋里的摆设,老僧便笑道,“他大概跟法师年纪相仿吧,父母去世后一直都是我在抚养他。他脾气有些古怪,不愿出家修行,也不肯娶妻成家,却偏偏喜欢做石匠。他什么都做,包括这房子上的梁托和墙边的浮雕石板,这些碗盘器具……对了,还有这尊佛像,法师你看,若不是这个,我这清净道场就要完全被他变成石器作坊了。”
玄奘看着那尊精致的佛像,不禁赞叹道:“这佛像如此庄严,能令人心生欢喜,可知制作者心怀善念,佛缘深厚。”
“法师过奖了。”老僧笑道,“如果我兄弟在这里,说不定会跟法师很投缘呢。”
“他去了哪里?”玄奘问道。
“去南印度找石头去了。”老僧回答道,“他说这里的石头材质太低了,即使是最普通的小蚂蚁也很容易把它变成无数粗糙的颗粒。他希望能找到一种坚硬光洁的石头,就像那些大食人带来的帕罗斯岛上的石头一样……他有些时候真的很固执。”
“我看这些石板都挺光洁的啊。”玄奘抚摸着一块石板,看着上面那弯弯曲曲的细线道,“这些文字真奇怪,不是梵文,也不是巴利文,倒像是一条条线虫一般。”
老僧忍不住笑了起来:“法师说得真是有趣。这些是婆罗米的线形文字,是一种消失了很久的文字。波罗耶舍在一些神庙里看到了它们,他并不知道什么意思,只是喜欢这文字的模样,于是就刻在了这里。”
“大师识得这些文字吗?”玄奘问道。
“年轻时有机缘学过一些。”老僧看着玄奘手中的那块写板,顺口翻译道,“优美的云啊!信度河缺水瘦成发辫,岸上树木枯叶飘零衬托出她苍白的形影;她那为相思所苦恼的情形指示了你的幸运,唯有你能够设法使她由消瘦转为丰盈……云啊!如果你到摩诃迦罗为时尚早,就一定要等候太阳从眼界消失,充当了祭湿婆的晚祷的尊贵乐鼓,你的低沉的雷声将获得完美的果实……”
“原来是婆罗门诗。”玄奘钦佩地说道,“大师真是才华横溢,无所不知。”
老僧呵呵笑了起来:“能博得玄奘法师一赞,当真是老僧之幸啊!其实老僧年少时是婆罗门教徒,一向非常敬重修行者的苦行与禁欲,但我更喜欢佛陀对人性的宽容。因此,长大后我皈依了佛陀,成为一个沙门。”
原来如此。玄奘想,佛陀对人性自然是宽容的,可是这娑婆世界是否能容纳得下这份宽容呢?
他又将目光投向另外几块石板,饶有兴致地看着上面那些线状的文字。
老僧坐在他的身边,解释道:“这些婆罗米文记载的也不全是婆罗门诗,其中还有很多有关《声明学》方面的东西呢。如果法师去到南印度的神庙,甚至还可以在石板上见到古代地方官员的记载,诸如谁从别人储水的井中偷打了一桶水,谁偷拿了人家一袋谷物这样的小事,都会被记录在石板上……”
玄奘不禁啧啧称叹。
老僧名叫般若跋陀罗,是一位精通萨婆多部三藏及《声明》《因明》的大德。难得的是,他对大乘唯识理论及各种外道学说也极为精熟。
玄奘也是最近才听说这么个人的,这段日子,他每天傍晚都抽空前来求学,并从这位语言幽默、学识渊博的长者这里,学到了很多东西。
“大师有如此学问,为何不去那烂陀寺任教呢?”玄奘抬起头,奇怪地问道。
般若跋陀罗笑道:“老僧还差得远呐!自犹未度,怎敢度人?再说那烂陀寺规矩太多,不是个修行的好地方,老僧可受不了那份管束。”
玄奘笑了笑,看来不管在什么地方,都有这样隐居的高士。
“说到你们那烂陀寺,最近很热闹是不是?”般若跋陀罗突然问道。
“是啊。”玄奘赧然道,“弟子已经焦头烂额,恨不能搬到这里来,同大师一起隐居。”
般若跋陀罗哈哈大笑:“玄奘法师都已经焦头烂额,那烂陀寺可以关门了。”
玄奘叹了口气,将自己与师子光长老的争论以及同戒贤尊者关于《会宗论》的对话简单地说了一遍。
般若跋陀罗津津有味地听着,突然说道:“老僧对法师的国家很好奇,在那里,不同观念的学派真的从来不发生争论吗?”
玄奘道:“偶尔也有,但同印度的学术辩论完全不同。至少,不是这种你死我活的形式。”
“听起来的确不可思议。”般若跋陀罗有些感慨,不紧不慢地说道,“老僧总觉得,所谓融通,并非共存于世,更有可能是共灭于世吧?又或者说,某种强势的观念,会通过另外一种方式而使其他观念屈服于自己……法师你觉得呢?”
玄奘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细细想来,汉地确实也曾有过学术辩论的历史,那是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时代,恰好与佛陀同一时期。中国的学术辩论虽不像印度这般残酷,却也异常激烈,各种观念相互碰撞,时有火花发迸出。其中有一家名辩之术,拥有一套完整的辩论体系,不比印度的因明差。那个著名的“白马非马”的典故,就出自这个学派。
可惜,在那样一个君权至上的年代,名辩术注定只能是昙花一现。一些优秀的名家走入宫廷,利用口才和辩术宣扬自己的主张,不承想却惹怒了君王,最终招致杀身之祸。
在这种情况下,名家很快就呈现出人才凋零的局面。特别是到了西汉时期,朝廷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诸子百家受到打击,几乎一蹶不振。擅长辩论的名家更是被一句“巧言令色者,鲜矣仁”给打压得抬不起头来,春秋时期的那种学术辩论风气自然也就越来越淡了……
如今的中土几乎没有辩论,因为没有哪一种思想可以同儒家相比,佛道两家加在一起也比不上儒家,这是君王倡导的结果,并非辩论所致。
也许这位长者说得对,没有辩论并不代表是一种融通,它更可能是某种强权对文化的一种干预。君王的力量使得一切学术变得像轻烟一样稀薄和微不足道,要不道安法师怎么会说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这样的话来呢?
佛门弟子要依靠君王来弘法,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无奈。
印度当然也有强权介入文化的现象,但君王的力量远没有那么强大。这使得各种哲学思维可以通过辩论的方式来为自己争取生存空间。这当然不是最好的方式,但就目前来看,却是最公平的……
“依长者所言,通过辩论的方式来明辨真理,虽然残酷,确实不失为一种较好的方式,至少比通过君王的提倡公平了许多。但是,任何学派都有不善言辞的人,这是学者各人的修为,甚至连修为都算不上,只是世智辩聪而已,完全无关法理。可是如今,这种残酷的辩论方式却可能对学者个人所持立论产生生死攸关的影响。”
“你说得没错。”般若跋陀罗道,“如今你们那烂陀寺就是这样,表面上众僧惜时如金,实际上要么是在鹦鹉学舌,要么就是坐枯禅,修为早已大不如前。不是老僧瞧不起他们,很多大乘行者不事修行,虽声称遍阅三藏,却从不敢参加论辩,有的则干脆不敢离开那烂陀寺一步!”
玄奘愕然道:“这是为何?”
“因为留在寺中,即使有人前来挑战,自有长老们应付。而一旦离开,别人知道你是那烂陀寺出来的,便会找你辩论,你能不应战吗?近些年来,一些外道论师越来越咄咄逼人,都想着一举战胜那烂陀寺,从而扬名立万。而寺中僧侣的胆子却越来越小,内忧外患啊……”
听到这里,玄奘不禁大为震惊,他的眼前出现了一个大大的白蚁巢穴,外形就像那烂陀寺一样,而寺中奔波于各个讲筵勤苦习经的僧侣们就像一只只快速移动的白蚁……
他的耳边又响起伐阇罗的话:“如果你知道自己在外面待得久了,脑浆子会开锅,你还会出门吗?”
见玄奘蹙眉沉思,般若跋陀罗不禁笑道:“相比较而言,你们的那位师子光长老倒是个真正的人才,至少他还有参加辩论的勇气。法师你想想看,如果有外道学者和部派论师前来挑战,你们那烂陀寺大乘学者中能够出迎的,除了你这个外国游僧,怕也就只有师子光长老还可抵挡一阵了吧?”
玄奘倒没有想到这一层,不由得一呆,心中暗叫“惭愧”。这段日子以来,他一直怜悯师子光眼光局狭,直到现在他才意识到,自己其实也很局狭。
他又想起《会宗论》,突然感觉有些可笑,他无意中使用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去套印度哲学,心中却不自知。
不错,的确有很多大德对《会宗论》感到新奇和赞赏,这其中就包括戒贤。然而对一个求法僧来说,这并不是正确的学习方式。
中观和瑜伽都是真正的佛法,这是毋庸置疑的。行者依此两者中的任何一个法门修行,皆可成就。若是有人两者皆修,依靠实证的方式,同样也可以成就。但这应该是修行者自身的选择和体验,而不应该由自己用语言和文字的方式将其一锅烩了。
我究竟是因为什么才到印度来的?他质问自己,我是来求法的,却偏偏要用我过去所知的一切自作聪明地指点当地的学者,真是可笑至极!如果这些就足够了,我又何必万里迢迢地跑到这里来?
我是一个修学者,本没有资格对佛陀的理论说三道四。我应该做的,是将佛陀及历代圣贤留下的话尽可能完整地带回我的祖国,让每一位修行者都能够毫无阻碍地站在佛陀面前,倾听佛陀的教诲,并自行选择修行的路径。这才是一个求法者的本分!如果我越俎代庖,自以为是地扬弃,说不定被我抛弃的,恰恰是我的国家的修行者们最需要的!
一念及此,玄奘起身合掌,向着长者深深一拜:“多谢大师开示,玄奘明白了。”
夜已经很深了,在那烂陀寺不远处的一间普通的房舍内,还亮着一盏灯树,来自东印度的师子月论师静静地坐在灯下,阅读玄奘的《会宗论》。
“这东土客僧倒真是才华惊人,名不虚传。”他轻轻翻阅着贝叶,喃喃自语,“单从这篇论著中便可知其佛学渊博,对大小乘法及佛学典故都极精通,信手拈来,毫无阻滞……”
转念间又想起师子光师兄的话,不禁喟然长叹道:“只可惜为人太过局狭傲慢,竟然仗着有几分辩才就污辱同修……修行人若是不肯修心,才华再高又有何用呢?”
想到这里,他放下手中的贝叶夹,闭目打坐,思索着明日见到玄奘时该说些什么。
玄奘还在那间简陋的茅舍内,全神贯注地阅读着龙树菩萨的《中论》之说。
早在国内修学之时他就接触过龙树的理论,读过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汉文《中论》;后来,又在磔迦国师从一位老婆罗门,学到了无著、世亲兄弟的理论,以及龙树的《经百论》和《广百论》。但是老婆罗门的佛学功底毕竟有限,所讲的龙树理论仅是皮毛,常令他深以为憾。今日在此读到原典,并得良师点拨,直入堂奥,顿时感觉如醍醐灌顶,佩服得五体投地。
“原来《中论》的一个支流便是法相。”玄奘手捧贝叶喃喃自语,“无著、世亲二菩萨的书,弟子自认也读了不少,却不曾细细揣摩思维,因而始终不得要领。”
“法师见地不凡,已登圣地了。”般若跋陀罗笑道,“老僧相信,在如今的那烂陀寺,怕是找不到几个比玄奘法师更加博学的。”
玄奘苦笑着道声“惭愧”,又说道:“法相认为,因果轮回的定律,只是若干虚幻的现象所显现的。轮回定律即是‘法’,虚幻之象即为‘相’,而唯识的知见可以解释‘法相’,这不正是瑜伽宗所说的‘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吗?”
“是啊。”般若跋陀罗笑道,“所以说,你融合中观与瑜伽二宗也没什么错,它们本来就是一棵大树上的两根枝杈。”
“如果玄奘不去会宗,会有别人去做这件事吗?”
“也许有吧。”般若跋陀罗道,“一切皆是因缘,佛法的未来走向谁又能看得清呢?老僧只知道,法师能够到这里来,一定是一个极大的因缘!”
听了这话,玄奘心有所感,又执经翻阅。
般若跋陀罗饶有兴致地看着他,突然问道:“听戒贤老和尚说,法师将三座宝阁内所有有关《唯识三十颂》的释论版本全都借了去?”
玄奘点头:“正是。”
“法师心中有所疑?”
玄奘放下经夹,轻轻叹了口气:“玄奘年少时在故土,曾在两所寺院的藏经阁中分别见过两个不同版本的《摄大乘论》,心中感到困惑难安,那时便起了西行求法之心。如今到了印度方知,这里的摄论版本还不止两个,而《唯识三十颂》的释论更是多达八个版本!”
“这令法师更加困惑不安了吗?”般若跋陀罗问。
玄奘没有答话。
般若跋陀罗淡然一笑:“法师想必知道,这《唯识三十颂》乃是当年世亲菩萨所造。世亲圆寂后,各大论师纷纷为此书做释论。据老僧所知,当时研究本论的共有二十八家,其中最著名的为护法、亲胜、难陀、安慧、火辨、德慧、净月、胜友、最胜子、智月这十大论师,他们相继为本论造释。另外,还有陈那、德光等论师,也对本论颇有研究,便是你师父戒贤老和尚,也写过一些释论。所以,仅就老僧所知,此论的版本至少有十几个,也许事实上还远不止这些,那烂陀寺收集了其中八个,也算难得了。”
“那么,另外几个版本在哪里呢?”玄奘忍不住问道。
“这老僧怎么知道呢?”般若跋陀罗道,“东印度?南印度?凡是有伽蓝和僧侣的地方,都有可能藏有经典。一部经书多个版本,这是极正常的事情。像一些冷门版本的下落,是很难打听清楚的。”
玄奘若有所思地沉默着,此时的他早已不是当年洛阳净土寺里的小沙弥,以为世间万物非此即彼,看到不同版本的经典就大惊小怪。多年的游学生涯和阅读经历告诉他,佛教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已经埋下了分裂的种子,佛陀在世时四处讲经说法并没有统一的教材,而是看到什么就讲什么。遇到不同根器的弟子,讲法的内容也不一样。弟子们记录佛陀的言行,观点体会很可能也会有增减和修正;佛陀入灭后,他的弟子们将他在各地的讲经说法整理结集,于是就有了《三藏》《五藏》之分,“上座部”和“大众部”之别。佛陀入灭一百年后,大众部首先分裂成九派,接着上座部也分成了新派和旧派……
有了这许多派别,佛典经论出现各种不同的版本确实没什么好奇怪的。况且,对佛教义理提供不同的解释,提倡较为宽大的学风,这本身就是大乘佛教的特色。
可是我需要知道什么才是真理!另一个声音在他心里喊道,佛陀的真义究竟是什么?我不相信辩论的胜利者就一定是真理的拥有者。虽然,通过聆听辩论,可以打开我的某一个心结,但我更相信自己的眼睛和心灵。即使由于业力的缘故,我不能与佛陀同时降世,不能亲耳聆听佛陀的教诲,但我至少可以尽可能多地收集各种不同版本的佛典,通过比较、研究,从字里行间找出佛陀的真义来!
这当然不是件容易的事,即使是号称娑婆世界佛教经典最集中的地方,也不是什么都有。我需要走出那烂陀寺,到更广大的地方去学习,去游历……
注释:
[1]“旃陀罗僧诃”是“月亮狮子”的意思,也可以意译成“师子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