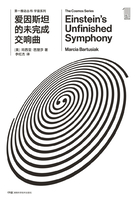
再版序 一个坠落苹果的两面:极端智慧与极致想象
连我们自己也很惊讶,《第一推动丛书》已经出了25年。
或许,因为全神贯注于每一本书的编辑和出版细节,反倒忽视了这套丛书的出版历程,忽视了自己头上的黑发渐染霜雪,忽视了团队编辑的老退新替,忽视好些早年的读者已经成长为多个领域的栋梁。
对于一套丛书的出版而言,25年的确是一段不短的历程;对于科学研究的进程而言,四分之一个世纪更是一部跨越式的历史。古人“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秋”的时间感,用来形容人类科学探求的速律,倒也恰当和准确。回头看看我们逐年出版的这些科普著作,许多当年的假设已经被证实,也有一些结论被证伪;许多当年的理论已经被孵化,也有一些发明被淘汰……
无论这些著作阐释的学科和学说属于以上所说的哪种状况,都本质地呈现了科学探索的旨趣与真相:科学永远是一个求真的过程,所谓的真理,都只是这一过程中的阶段性成果。论证被想象讪笑,结论被假设挑衅,人类以其最优越的物种秉赋——智慧,让锐利无比的理性之刃,和绚烂无比的想象之花相克相生,相否相成。在形形色色的生活中,似乎没有哪一个领域如同科学探索一样,既是一次次伟大的理性历险,又是一次次极致的感性审美。科学家们穷其毕生所奉献的,不仅仅是我们无法发现的科学结论,还是我们无法展开的绚丽想象。在我们难以感知的极小与极大世界中,没有他们记历这些伟大历险和极致审美的科普著作,我们不但永远无法洞悉我们赖以生存世界的各种奥秘,无法领略我们难以抵达世界的各种美丽,更无法认知人类在找到真理和遭遇美景时的心路历程。在这个意义上,科普是人类极端智慧和极致审美的结晶,是物种独有的精神文本,是人类任何其他创造——神学、哲学、文学和艺术无法替代的文明载体。
在神学家给出“我是谁”的结论后,整个人类,不仅仅是科学家,包括庸常生活中的我们,都企图突破宗教教义的铁窗,自由探求世界的本质。于是,时间、物质和本源,成为了人类共同的终极探寻之地,成为了人类突破慵懒、挣脱琐碎、拒绝因袭的历险之旅。这一旅程中,引领着我们艰难而快乐前行的,是那一代又一代最伟大的科学家。他们是极端的智者和极致的幻想家,是真理的先知和审美的天使。
我曾有幸采访《时间简史》的作者史蒂芬·霍金,他痛苦地斜躺在轮椅上,用特制的语音器和我交谈。聆听着由他按击出的极其单调的金属般的音符,我确信,那个只留下萎缩的躯干和游丝一般生命气息的智者就是先知,就是上帝遣派给人类的孤独使者。倘若不是亲眼所见,你根本无法相信,那些深奥到极致而又浅白到极致,简练到极致而又美丽到极致的天书,竟是他蜷缩在轮椅上,用唯一能够动弹的手指,一个语音一个语音按击出来的。如果不是为了引导人类,你想象不出他人生此行还能有其他的目的。
无怪《时间简史》如此畅销!自出版始,每年都在中文图书的畅销榜上。其实何止《时间简史》,霍金的其他著作,《第一推动丛书》所遴选的其他作者著作,25年来都在热销。据此我们相信,这些著作不仅属于某一代人,甚至不仅属于20世纪。只要人类仍在为时间、物质乃至本源的命题所困扰,只要人类仍在为求真与审美的本能所驱动,丛书中的著作,便是永不过时的启蒙读本,永不熄灭的引领之光。虽然著作中的某些假说会被否定,某些理论会被超越,但科学家们探求真理的精神,思考宇宙的智慧,感悟时空的审美,必将与日月同辉,成为人类进化中永不腐朽的历史界碑。
因而在25年这一时间节点上,我们合集再版这套丛书,便不只是为了纪念出版行为本身,更多的则是为了彰显这些著作的不朽,为了向新的时代和新的读者告白:21世纪不仅需要科学的功利,而且需要科学的审美。
当然,我们深知,并非所有的发现都为人类带来福祉,并非所有的创造都为世界带来安宁。在科学仍在为政治集团和经济集团所利用,甚至垄断的时代,初衷与结果悖反、无辜与有罪并存的科学公案屡见不鲜。对于科学可能带来的负能量,只能由了解科技的公民用群体的意愿抑制和抵消:选择推进人类进化的科学方向,选择造福人类生存的科学发现,是每个现代公民对自己,也是对物种应当肩负的一份责任、应该表达的一种诉求!在这一理解上,我们将科普阅读不仅视为一种个人爱好,而且视为一种公共使命!
牛顿站在苹果树下,在苹果坠落的那一刹那,他的顿悟一定不只包含了对于地心引力的推断,而且包含了对于苹果与地球、地球与行星、行星与未知宇宙奇妙关系的想象。我相信,那不仅仅是一次枯燥之极的理性推演,而且是一次瑰丽之极的感性审美……
如果说,求真与审美,是这套丛书难以评估的价值,那么,极端的智慧与极致的想象,则是这套丛书无法穷尽的魅力!

罗素·胡尔斯正在波多黎各的阿雷西博天文台操作计算机和电传打字机(1974年)。记录有PSR 1913+16“妙极了”的探测结果的表格上,还有胡尔斯在困惑中画掉的它变化着的周期。(版权归诺贝尔基金会所有)

约瑟夫·泰勒从PSR 1913+16这对中子双星的运动中找到了引力波的证据。(丽塔·娜尼尼)

40年前,约瑟夫·韦伯发明了共振棒探测器,从而创立了引力波天文学。然而,他报告的探测结果,至今仍备受争议。这是20世纪70年代他在马里兰大学一台共振棒探测器上工作时的照片。(由约瑟夫·韦伯免费提供)

约翰·阿齐博尔德·惠勒把广义相对论带进了天体物理学前沿,并给黑洞取了“黑洞”这个名字。(照片由罗伯特·A.马修拍摄,并由普林斯顿大学免费提供)

1887年艾尔伯特·迈克尔逊在地下实验室里建造了这台干涉仪,但并没有探测到以太;这个令人困惑的结果最终导致了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的提出。(卡内基天文台收藏,亨廷顿实验室,加利福尼亚圣马力诺市)

麻省理工学院(MIT)的20号楼就是著名的“胶合板皇宫”。20世纪70年代,瑞纳·怀斯在这里首次提出的激光干涉仪计划后来发展成了LIGO。(麻省理工学院博物馆)

加州理工学院的理论家基普·桑尼(拍摄于20世纪80年代)在被说服、从而相信了探测到引力波是有可能实现的之后,成了引力波天文学最坚定的支持者。他和自己的学生们精于预测可能的引力波辐射源。(由罗伯特·J.帕斯/加州理工学院免费提供)

罗纳德·德莱弗在苏格兰和加州理工学院都发展了工程上的革新措施,从而使激光干涉仪得以向前发展。(版权归詹姆斯·舒格所有)

来自锡拉丘兹大学的LIGO研究员彼得·索尔森:“我们正在努力争取的精确度水平是我们事业的标志;这样做的话,你就‘走上正道了’。”(彼得·芬格)

普林斯顿大学的罗伯特·迪克,摄于20世纪60年代。在20世纪后50年广义相对论实验复兴的过程中,他是一位关键人物。(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

詹姆斯·福乐、彼得·班德和R.塔克·斯特宾斯(从左至右)在科罗拉多大学的天文物理联合研究所发起了太空干涉仪研究。他们的工作最终发展成了拟议中的LISA工程。(由肯·阿伯特拍摄,版权归科罗拉多大学所有)

集中在阿贝尔2218星系团里的所有天体就像一面巨大的变焦透镜。正如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所预测的那样,这个距离我们一二十亿光年远的星系团把更为遥远的星系放大并弯曲成了一系列同心圆弧。(NASA:安德鲁·伏鲁西特和ERO小组)

左图为LIGO的主任巴里·巴里希(《费米新闻》)。右图为麻省理工学院的瑞纳·怀斯,激光干涉仪先驱,在很多人看来,他还是LIGO的建造之父。(加州理工学院)

VIRGO小组的成员,在他们的高级隔震塔——“超级衰减器”——前的合影。VIRGO的联合主管阿戴尔伯特·贾佐托位于后排,左起第三位。(由VIRGO免费提供)

身着无菌室工作服的LIGO研究员们正在巨大的干涉仪内建立起众多光学支持系统中的一套。(加州理工学院)

坐落在路易斯安那州利文斯顿松林里的激光干涉仪引力波天文台(LIGO)。它的一条4千米长的管道壁向上延伸开去,另一条向右延伸。另一同样的天文台建在华盛顿州的汉福德。(加州理工学院)

一位光学工程师正在捧起一块LIGO的纯硅镜片,它们是引力波探测器的核心部件。(加州理工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