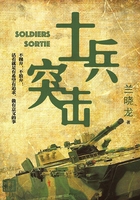
第9章
晚上熄灯后,上铺的史今,听到下铺许三多在不住地翻来覆去。
史今探头看了看,吩咐道:“早点休息。明儿早上五点半起床,连里得为春季演习做加强训练。”许三多呆在床上,不翻了,他借窗外的月光,怔怔看着史今。
“我今天表现不好,是不是,班长?”许三多突然轻声问道。
“现在不说这个,别打扰大家,别人还得睡。”
过了一会儿,许三多又说:“班长,我想家,还想五班,想我爸爸和大哥、二哥,还有老马。”
史今生气了:“许三多,我命令你,睡!这是你自己要来的,很多人想来这来不了,你在这折腾的时候最好想想,你对不对得住那些想来来不了的人。”
“班长我知道,这叫机会。”许三多慢慢地闭上了眼睛,没一会儿,他真的睡着了。
然而,史今却怎么也睡不着了,轮到他在床上不停地翻动了。
早上,天色微蒙,一阵哨声忽然炸响,黑暗中,兵们扑通扑通地跳落地上。等到灯被拉亮时,兵们已经在叠被子了,十几个人的被子,转眼成了一块块的豆腐块,实在壮观。
昏暗的走廊里,着装好的士兵,紧张而有条不紊地出去了。
大部分士兵已经在操场上列队,小声而清晰地报数。
铺了半个操场的士兵已经集结进几辆发动机早预热好的军用卡车,转眼拖起烟尘,往外开走了。这其实也只是三两分钟内发生的事情。七连这两个月都在练机械化人车协同,许三多算是赶上了。
拥挤的卡车里,士兵们都沉默着。风,在往疾驰的车厢里灌,刚从被子里爬出来的兵们,下意识地挤在一起取暖,有人利用这宝贵的时间抽上起床后的第一支烟。
透过车厢的缝隙,许三多看着外边的蒙蒙星光。
一支烟递了过来,是成才,许三多亲热地笑了笑:“你知道我不抽烟。”
“装甲兵不抽烟是不可能的。”成才凑了过来,“挤挤,想多穿件毛衣又怕妨碍冲锋。咱们训练烟尘大,叫作每天二两土,上午吃不够,下午还得补。你不抽根烟熏熏,肺里边见天一股土味。点上?”
许三多犹豫再三,还是不要。旁边的白铁军乘机把烟抢了过去。
车子去的是靶场。所谓靶场,就是一片宽阔的装甲车辆射击场,交错的车辙印,尽头是灰蒙蒙的山峦。一排三辆步战车正在空地上驰骋预热,射击场上早碾出了近尺深的浮土,顿时满天如起了茫然大雾。
对装甲兵来说,这早算正常了,但许三多却不停地打着喷嚏。
高城一步一个坑,从灰土里拔出脚来站到队伍跟前。
“立正稍息!今天的主要课目是步兵火力与战车火力的协同,你们一车连驾驶员十二个人,我眼里你们可是一杆枪一门炮,总之你们是一个而不是十二个单位,我希望你们能把协同观念给烙进脑子里……”
起了阵风,一阵子伸手不见五指后,满连的士兵顿时都落了层土。
灰雾蒙蒙中,现出几个人影,当头的是王庆瑞团长,他们比士兵也干净不到哪去。
高城一个敬礼,大声道:“报告团长,钢七连正进行人车协同训练,请团长指示!”
王庆瑞回了个礼:“继续训练。”
高城接着对部队喊话:“今天风沙大,显然会给咱们的射击增加难度。不过我希望大家伙儿知道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天气,战场上能见度多半要比这差得多,咱们又是刀尖子上的侦察连,必须学会不光靠肉眼也靠感觉射击!那个兵,你捂什么眼?我还开口说话呢!你以为我吃的土比你少吗?”
那个兵当然就是许三多了。他忙将灰迷了的眼睛睁开,使劲地眯着。
高城瞪了许三多一眼,继续下命令:“解散。上五号车领弹药,一排射击准备。”
士兵们散开后,高城转向王庆瑞:“报告团长,讲话完毕,请团长指示。”
团长拍拍高城的肩:“一嘴土吧?我的水你喝不喝?”
高城果然吐了一嘴的土,笑了笑:“这满地土让车碾多了,到嘴里都有股柴油味了。”
团长把茶缸子递过去,高城毫不客气地喝了口。
“您怎么还喝花茶?得换绿茶,在车里还不够上火的?”高城说。
“你小子什么都要挑三拣四,听说对我推荐过去的兵也不满意?”
“您也瞧见了,来把土他得捂眼睛,来颗子弹他不得尿裤子?”
团长乐了:“你父亲跟我说,你幼儿园那会儿就抱着漂亮女老师不撒手,他那会儿就怕你长成花心大萝卜。”
高城连忙往周围看看,确定没人,然后就有些赧然:“说那干吗?那事没意思。”
团长语重心长:“现在呢?就是说人都会变,而且这个变没有极限。”
一辆步战车突然驶过来停在许三多的面前,许三多看着宽阔的车体刚刚发愣。史今在忙碌,训练展开前班长是最忙碌的,百忙中跟许三多交代一句:“记住207!这咱们班的战车。”
许三多呆呆地看着:“这就是我的战车?”
史今不由得皱眉瞧他一眼,不过实在太忙,也没工夫去纠正单数式和复数式的区别。许三多就原地看着那车打心里叹出来,并且很想伸手去触摸一下。这时就听到了成才的声音,成才骄傲地让许三多去看他的枪!灰蒙蒙他举着一支纤长的狙击步枪。许三多正想过去。被伍六一叫住了,然后被伍六一带进了一辆步战车的后舱门。“你新来的,这段时间会对你从宽要求。可你也得注意学习,比如说车停在这,你就可以练练登车,你不练没人盯你,可最后做了后进的就是你。”
许三多连连点头。伍六一拉开舱门:“练吧。”说完让到了一旁。可许三多刚一上车,又被伍六一叫了下来说:“你这么上车就上你一个得了,全车都堵在外边。你以为战场上跟今天一样就刮个风?飞的可全是子弹弹片。下来,注意观察。”
伍六一把身体蜷成一团,嗖的一声跃进宽高不过一米二的舱门,顺手将舱门带上,这一切只是一秒内的时间。
许三多学着伍六一的样子,一收一跃,咚的一声,脑袋撞在了舱门上,虽是戴了钢盔,也有些晕晕的感觉。伍六一一看就生气了:“登车的要诀是,一个目标,三个注意。一个目标就是车里你的那个座位,三个注意是注意你的头注意你的脚还有注意你关门的手。几十公斤重的钢门一关是多大的力量?我亲眼见过一个兵,被关掉了俩手指头。”
许三多一听就有些害怕,但他还是蹿上了车,而后轻手轻脚将门关上。
伍六一还是说不行,他吼了一声:“重来!车里有人睡觉你怕吵了人是不是?这是打仗!”
指导员洪兴国这时跑过来,让伍六一在班里派两个报靶兵。伍六一没有多想:“白铁军,今儿轮到你了。”
白铁军有点不乐意:“干什么又是我的坑主?不都来新兵了吗?”
伍六一犹豫一下:“许三多,你也去。”
许三多:“去干啥?”
“跟我来就是啦。”白铁军抱怨着,“班副你知道坑主的苦,也不派个能聊天的。”
伍六一装没听见。许三多听话地跟着去。
甘小宁见许三多走远了,才说:“这么简单个动作都做不会,咱三班算是拖上个油瓶了。”
伍六一看他一眼,班副不便像士兵这样公开牢骚,他开始了射击准备活动。
这是埋在地底近十米深的一道钢筋水泥工事。
白铁军在地上找着一根粉笔头,在墙上乱写着。墙上早被人写了好些字了,其中有一行写着:“绝情坑主白铁军呜呼于此。”白铁军之下,又添了“又呜呼于此”几个字,然后在下面的几个“正”字上,又加了一杠。
“咱们来这干啥?”许三多有点茫然地问道。
白铁军在“绝情坑主”四个字的下边,加了一横,说:“做坑主呗。”
“坑主?什么叫绝情坑主?”许三多没明白。
“坑,就是这靶坑,它不能叫战壕,战壕是打仗的,这玩意它是躲自己家子弹猫在里边用的,它只能叫个坑;坑主,你蹲了这坑就是坑主了;绝情就是没了想头,你蹲了这坑,听着脑袋顶上单发、连射、三发点射、急速射打个稀里哗啦,车来车往轰轰隆隆,跟你啥关系没有。你只好数数枪声炮声,完事了上去报靶,你只好万念俱灰,这就叫个绝情。”
许三多说:“我还是不懂。”
“不懂没关系,你好好体会。坐坐,许三多,今儿就是我的坑主,你的副坑主啦。”
“那以后我就是副坑主啦?”许三多以为自己已经明白。
白铁军说:“不不,你很快就能转正。”白铁军心里在暗暗地算计着,“许三多,别人不喜欢你,我可喜欢你,因为咱们连一般是老末当坑主,你来了我就不是老末了,我这坑主很快就要撤了。”
“啥叫老末呀?”许三多不明白的太多了。
白铁军说:“老末就是……嘿嘿!你慢慢体会吧。”
靶场中的战车,轰鸣起来了。车后成班的步兵,在一个响亮的口令之后,如压进弹匣的成梭子弹,压了进去。眨眼间,战车的射击孔,冒出了一串串火舌,弹道将战车和它们的目标连成了一线。成才将一辆战车的瞄准镜套准了一个目标,周围震耳欲聋的枪声里响起狙击枪清脆而尖厉的一声,那个活动靶被洞穿。
成才很满意地退弹。周围的战友们凑在可四下俯仰的射击孔跟前打发掉一个一个冒出来的目标,两挺车载重机枪的急速射听得人透不过气来。
车体猛的震颤了一下,主炮射出的一发破甲弹飞了出去,一个车辆靶轰然爆开。
靶坑里的白铁军,盘腿坐着,如老僧入定,听着那些炮弹不停地飞来。
许三多则显得有些坐立不安,枪炮声和从工事口飘进来的火药烟雾,让他感到热血沸腾。他激动得不时地站起来,但一次次地被白铁军喊了下去。做坑主就得坐得住,因为子弹绝不会长了眼睛。
在战车们的轰击下,那些活动靶转眼就被完全地收拾掉了,剩下的只是一些半埋入式的地下掩体。
“下车冲击!下车冲击!”车上又传出了新的口令。
战车的舱门随声打开了,里面一身火药味的士兵被放了出来,匍匐着向那些目标接近,战车上的伪装烟幕发射了出去,烟幕中火焰喷射器的火光撩开了一个地堡,一发火箭弹飞出撩开了另一个地堡。
先锋车在山腰上把一个个简易工事,统统地碾为了平地。
突然,许三多从工事的缝隙里,看见成才匍匐着从工事前潜伏过去。
许三多激动得大声喊着成才。
前边的成才当然听不见,他跳起来跃入壕沟,又没影了。
“别喊了,听不见。”白铁军玩着手中的粉笔头,“现在知道啥叫绝情了吧?这就是个被人遗忘的角落。”
许三多茫然坐了下来,终算是体会到了。
两人就这么待着,直到偃旗息鼓,战车载着步兵轰轰地回驶。弹着点未尽的硝烟仍在冒着。
靶坑里的兵冒出来,查着靶用旗语报分,周围一片狼藉,挥着小旗的士兵看上去也像极了被打得丢盔弃甲的投降兵。
有人远远地朝这边喊着:“靶坑里的,出来吃饭啦!”
许三多茫然地从阵地上下来,在弹坑与车辙印中走着。
打饭的时候,史今问道:“许三多,有什么体会?”
许三多说:“我啥也没看见,就听见响了。我耳朵里现在还嗡嗡地响。”
史今苦笑:“明儿跟指导员说说,让你上车体会体会。可下午你还得去。”
正说着,忽然听到高城大声地吼着:
“起风啦!起风啦!赶紧隐蔽!找车后边蹲着去!把饭盒揣怀里!”
许三多一看,果然一阵风卷着烟尘,如同一座有形的山脉向他们压来。许三多端着刚刚打好的饭盒,在灰雾中一下傻了。
高城看见了,忙喊道:“你蹲着去!有心没肺啊?你这饭还能吃吗?”
大风过后,高城一看竟是许三多,顿时就来气了:“怎么又是你呢?”
看了看许三多的饭盒,却没有训他的心思,只说了句:“拨掉上面这层,赶紧吃了去!”然后走开了。
好在许三多能吃,他扒了扒,就大口大口地吃着那盒土黄色的米饭。
我入伍的第一个梦想是成才给我的,战车、硝烟、火炮、机枪、狙击步枪、大功率的发动机,在爸爸身边永远感受不到的一切。连长简而括之地把这些称之为战斗精神,他说我没那么些玄虚跟你们说,你们起床就进入了战斗,你们如果喜欢这种生活,就是战斗精神。我很想跟他说,我喜欢,可这种生活它不喜欢我。有个梦我做了很久,可它成了现实的时候,第一脚就把你踢得远远的。我知道我永远不敢跟他说,因为他说这种话的时候,目光就像跨越障碍一样直接从我身上跳过。
其实,这只是个开张,在后来的日子里,白铁军离开了那个绝情的靶坑,许三多成了唯一的坑主。他还经常在登车的时候把一个班的兵都堵在了身后;登了车,他又时常坐错了位置。轮到他在车内射击时,别人总是打在靶上,他却老是打在活动靶的周围,打得烟尘滚滚的,打得伍六一一脸的愠怒。许三多还晕车,晕得大口大口地吐,吐得旁边的兵不得不鄙视地看着他,没有人表示同情。
高城也已经熟视无睹,在对待许三多之事上,这位年轻的连长已经找出一个最简单的解决方法:不看,或者称之为漠视。这种态度会传染的,七连的其他士兵也很快学会了高城式的目光,他们心里下意识的自尊已经被损伤了,最悍勇的装甲侦察连居然存在着一个晕战车的士兵。
不到一星期,钢七连看我的眼神都像在跨越障碍,而且是那种毫无难度纯属多余的障碍。
钢七连的越障练习,障碍设得着实有些夸张,比旁边连队高出一米的垂直障碍就至少有四五道,而兄弟连队那个是标准高度。
这是七连尖子兵大显身手的时候,伍六一轻松得有些卖弄,并且看来他会远远抢在同僚之前到达终点。钢七连人的生存方式是给自己树一道不可企及的目标,然后“嗖”的一下把自己扔过去。能把自己扔过去的人就是连长眼里的红人。
在终点等待的高城显然很喜欢这种卖弄,在伍六一到达他身边时,他颇为得意地给自己嘴里塞上一根烟,给伍六一递过一根烟。伍六一很自然地接了,然后高城给他点火,小小地使了一个坏,从火机上一下喷出的火苗几乎烧掉伍六一的眉毛。高城大笑,并且伴之以逃跑和闪身,伍六一一脚飞起,不偏不倚,正中高城的屁股。这与军威军容无关,正好证明钢七连的一种独特:高城喜欢这样。
然后高城站定了看着障碍那边的人,这时他又是那个军仪十足的连长。然后他就会冰寒彻骨地问障碍那边的人——怎么还不过来?
许三多,他躲在一个角落,并且希望尽可能地不被人注意到。但史今一直注意到他,并且伸手拍了拍他,于是许三多鼓足勇气打算去再出一次洋相。
史今指了指旁边空荡如也的一些障碍——上那练。那是一片全团公有的障碍,就这个团的训练水平来说,是给全团人胜似闲庭信步解闷用的。于是许三多无比艰难战战兢兢去克服那片多少年前就被人征服的障碍。
七连的训练强度远高于兄弟连队,以致整个操场上只剩他这厉兵秣马的一小块。高城训话的声音显得很突出:“今天大部分人都征服了我以为不能征服的障碍。嗯哼,绝大部分人。”他有些促狭地笑了笑,目光从许三多身上不经意地扫过,绝大部分人绝对是不能包括他的。
“我这跟大家说句私话,先锋二连名不副实,哪战不是七连打的先锋?常胜四连是瞎吹,咱们可以跟老四比比谁打的胜仗多;大功六连那是寒碜自己,记了一次集体二等功就敢叫大功连。指导员,咱们七连记过几次集体一等功?三次!”
洪兴国有些难堪,他并不是太喜欢这么剑拔弩张地吹嘘,尽管高城所说的全是事实,尽管这是高城的风格,也可以说是钢七连的风格。
高城微笑着,让全连人在沉默中回味着那个惊人的数字。这个连队就是他的世界,所以他经常能对着一百多号人嚷嚷他的私话,说这种私话时他笑得又神秘又谦虚,让大家觉得,我们之所以没叫常胜、大功什么的,就为留着让兄弟连队寒碜自己。
高城的训话在继续:“三次集体一等功,表示在三次血战中阵亡超过三分之一,表示在三次血战中歼敌逾倍甚至二十倍,表示在三次血战中发挥了超越连建制的战役性作用。重要的,最重要的,我连到今天还没倒,还将永远这样继续下去,所以,我们叫钢——钢七连。”
他再次神秘而谦虚地微笑,再次扫视全场。看表情可以肯定,这个连绝大部分人有与他相同的骄傲,与他相同的自豪。
这就是钢七连,在人之后,你连呼吸都不顺畅,在人之前,你尽可以踢连长的屁股。
团中央的大操场边,成才正使劲翻着左眼的上下眼皮,以便许三多吹去他眼里落下的灰尘。他和许三多都是一身戎装,都是刚从靶场归来。成才像是灰堆里钻出来的,那是每次战车射击后的必然,许三多很干净,靶坑生活的唯一一个好处就是没靶场上那么多的烟尘。
成才狠狠地把他摔开:“出来了啦!你那么使劲干什么?对个狙击手来说最要紧的是什么?”
许三多仿佛知道自己又做错了,蔫蔫地站着。
“你正在损害我的视力。”成才眨着眼睛好让眼里的泪水流干净,然后拿出一瓶眼药水,让许三多帮他清洁自己的眼睛,成才确实很注意保护自己的这些资本:钢七连眼里揉不得沙子,许三多好像是他眼里的那颗沙子。
许三多感到莫名的沮丧:“我要是还在三连五班就好了,老马他们至少还把我当自己人。这儿……他们都不当我是自己人。”
“我最不爱听就是你说这种话,你得争取当骨干,做了骨干,像我吧,那就什么都好办了。”成才教育着许三多。
“我……我怎么可能是骨干?我上车都会吐,昨天给满车人吐了一身。我永远比不上你。”
成才挠了挠头,显然很愿意听到这话。“嗨,那也不能这么说,就算笨吧……你也不能由人叫你笨蛋,谁要这么叫我我就会打回去!”
许三多简直有点心灰意冷:“那怎么办?我除了内务还合格,啥都做不好。”
许三多的处境的确很不如意,班里的战友们都不愿意搭理他,当他涎着脸帮大家扫地、打水时换来的却是刺耳的话:“三班不需要扫地的兵。”
当成才正在准备继续做许三多的人生导师的时候,甘小宁从远处跑了过来让许三多马上回宿舍,班长找。
许三多没半个不字,跳起来便跑。
成才手插裤袋里,蹦了两下,开始倍轻松地在操场边活动。
许三多拿着忘还他的眼药水又跑了回来,他站住了——他的朋友绝没把他的烦恼放在眼里,他的朋友现在有一种终于摆脱他的快乐。
许三多看起来很孤独。
宿舍里许三多铺上的被子被翻开了,伍六一和史今正在屋里等着,许三多一溜跑进来。刚一进门,伍六一就拎起他的被子。
“你往被子上洒了多少水?我说你的内务怎么整得比老兵还平整,今儿一摸你被子,都湿的,背面都发霉了。你老实说,洒了多少?”
“一杯。”他吞吞吐吐地说,并指了指柜上的那一个大茶缸。
“那你每天晚上怎么睡的?”伍六一恨不得狠狠地给他一个巴掌。
“就……就这么睡了。”许三多好像没事一样。
一旁的史今终于说话了:“许三多,要求你搞好内务,并不是要你拿自己的身体扛,整齐划一是很重要,可你自己的身体重不重要?这笔账你算不算得过来?”
伍六一也在一旁嚷嚷:“你是钢七连的兵!为个优秀内务就啥也不顾了,钢七连需要的可不光是优秀内务!”说完,气得掉头就走。
许三多终于嗫嚅出那句话来:“我怕……我怕拖班里的后腿。”
史今为此有些感慨,目光都不由得温润了下来:“走吧,跟我去擦车。”
一桶水泼在那车体上顿时成了泥汤,哗哗地淌下来。许三多卖力地擦着。史今擦着车,扭头找许三多:“今晚上用我的被子。”
许三多摇头。
“别跟我犟。我知道你那心思,可很多事急不来。”
许三多使劲擦着车,一声不吭。
“也许起点低了点。可今天比昨天好,这就是有希望。”史今看起来也并不太信自己说的,尤其在对这事上,显得有些自我解嘲。
许三多使劲擦着车,终于开了口:“我知道就班长一个人对我好。”
史今只好苦笑:“许三多,这种话少说,你该跟全班每一个人搞好关系。”
许三多的眼圈有点发红:“七连眼里揉不得沙子,我就是七连眼里的一颗沙子。”
史今:“这话谁说的?不像你说的,谁跟你说的?”
许三多:“谁说的不要紧了。班长,你像我哥,我大哥陪我说话,我二哥帮我打架,你像我两个哥合在一块儿。”
史今气得挥了挥手:“我绝不会帮你打架,我陪你说话也不是我想陪你说话!我陪你说话,是想你明白得多一些……许三多,你是不是从小就这么过的?你大哥陪你说话,你二哥帮你打架,你自己什么事都不解决?”
许三多机械地擦着车:“我很努力了。”
史今苦笑着好像在自言自语:“后天就上演习场了,你这个样子怎么去啊?”
许三多毫无想法地瞧着他,一个人心事太重就没了想法。
演习终于开始了。
装甲部队,驶出了团部的大门,驶上公路旁的专用坦克车通道。小镇上车队驶过,两层楼的小酒馆竟与车顶上荷枪实弹的士兵齐平,酒馆二层的食客们与外面的钢铁巨物形成强烈的反差。
路边的一棵断树被火柴梗似的碾成两截,然后一辆辆车从上边碾过。这支不见首尾的装甲部队向草原挺进。
草原上却一如往昔,只是路边突然多了一处简易的小屋,屋边还扔了堆干了的羊粪,还有几头系在桩上的山羊。坐在里边的,却是团长和参谋长他们。一个牧民骑摩托车从路边经过,以为是新来的牧民,停下车,就推门进去。
嘴里还嘟哝着:“啥时候盖的?咋没人告诉我呢?”话刚说完,两名全副武装的士兵站在了他的面前。
“快走!”士兵轻声地吩咐道。
牧民不由得一愣,正要说什么,突然看见空屋中间掀起一块木板,王庆瑞等团部军官和几个参谋从下面的地洞里钻出来,木板下边是一个地洞。地洞下,全都是发报声、人声和发电机的声音,根本搞不清下边有多大的空间,藏了多少人。
王庆瑞笑着对那牧民说:“老乡,我们打扰几天,回头就走。”
牧民一时摸不着头脑,转身就踉踉跄跄地骑车走了。
他刚驶过的草皮被揭起一块,下边隐蔽的士兵监视着车后的烟尘远去。
王庆瑞得意地笑了:“成!能把本地人都瞒过了,我对这次伪装演习就有点信心了。”
参谋长在旁边警告他:“这不叫瞒过,该叫暴露。”
王庆瑞想了想:“对对对。这就是个破绽,咱这民房伪装外边没个活人也不合理!找两个会说本地话的兵,给我扒了迷彩放羊去!”
草地上有块与周围环境一体的山丘,贴近了看,草皮下居然有一个黑洞洞的炮口。这是钢七连的战车和人员掩体。史今带了几个人正在做最后加固。许三多一直凑在史今旁边,许三多喜欢跟史今待在一起。
伍六一却看不顺许三多呵斥道:“要真表现就别在这儿烦了!都进入倒计时了,知不知道?”
许三多噢了一声,低头走了。看着许三多的背影,伍六一觉得不可理解,问史今:“这小子怎么回事?现在就贴上你了?”
史今还没回答,前边的许三多又回头嚷嚷开了:“班长,早饭来了,快吃饭吧!”
果然是指导员洪兴国押着送早餐的炊事车来了。
伍六一几近恼火:“他嚷什么?不知道现在是伪装演习啊!”
史今苦笑:“如果你天天被全连当透明的,是不是也会出点动静让人注意到你?你们先去吃吧,我再垫巴垫巴这伪装坑。”
许三多这时又跑了回来:“班长,你先吃,吃完你再……”
伍六一终于听烦了,伸手捂了许三多的嘴往炊事车拖去。许三多那一套他听烦了,听出了仇恨来了。史今擦擦汗,又往伪装网上披着别处挖来的草皮。
士兵簇拥在炊事车边吃着今天的早饭,通信兵背着电台跑来和指导员洪兴国没说几句,洪兴国的脸色就变了。回头大声地命令:“立刻疏散。侦察直升机提前出来了,它是存心突袭。”
这块丘地上一个排正在吃饭的士兵,顿时炸了窝。
洪兴国有条不紊地发布着命令:“非武装车辆马上开出演习区域!特别是炊事车,它的热源太大。”
史今也跑了过来:“吃不完的东西都随车带走,别让假想敌看出痕迹。”
士兵从来都是无条件服从的,二话不说,手上啃了一半的馒头也放了回去。许三多也得意地笑着,跟着大家一起跑开。
炊事车驶下山坡,士兵们已经散入了半地下的伪装掩体,这山丘看上去顿时与周围的草原无异。
一架侦察直升机超低空掠过,它的任务是用机上五花八门的电子和红外仪器对方圆十几公里的伪装阵地进行扫描侦察,发现目标并对这次演习的成绩直接做出评估。
那俩士兵扮的牧民抽着烟,对着天上指点笑骂,一位脸皮厚的干脆旁若无人地解开裤子对草丛尿了一泡。直升机毫无觉察地飞过团部伪装所在地。
三班的士兵蛰伏在工事里看着那架直升机飞过,刚松口气,飞行员又很不死心地绕了回来,毕竟方圆几公里这唯一的小丘让人不得不注意。
直升机似乎发现了什么,从十五米降至十米,降至五米,几乎就悬停在三班的头顶上,史今、许三多和几个兵在一个伪装良好的工事里,咬牙死撑着。许三多一时有点慌了阵脚,但被一旁的史今给死死地盯住了,让他不要乱动。
直升机的机轮眼看就要触地的一瞬间,终于往上抬起了机头,毫不犹豫地飞过了山丘,飞到前边去了。史今几个终于睁开了眼。
他小声地传达着:“没吹哨就别动,兴许这小子能杀个回马枪。”
回马枪倒是没有,但一辆越野车轰鸣着突然停在了他们的身边。
连长高城的声音,在他们的头上横扫而过:“三班的,都给我出来!还藏什么?让人给发现啦!”
工事里的几个人一愣,呼地从高城的脚下钻了出来,吓得高城不由得退了一步。但他火气依旧:“忙了足足一个星期,你们怎么几分钟就让人抄出来了?”
“抄出来了?没有!”史今极力地争辩着。
“你以为人还下来逮你呢?他直接把可疑点标电子地图上,指挥部一看实时传输,经纬度都对,那就是咱们的事了!”
可伍六一向来自信:“别不是碰巧了吧?”
高城说:“碰什么巧?指挥部电话里说了,红外成像上明显的一个热源!你们的防红外作业怎么做的?什么叫热辐射知不知道?是不是哪位公子哥儿还揣了壶热水呢?很会保养啊?”
“三班没这号糊涂蛋。别不是师部的红外成像又换代了?”伍六一懊恼地问。
没换!高城也搞不懂原因,他看看周围的兵,有些沮丧:“大家坐下吧。”
三班早已一脸的屈辱,只有许三多,却显得宠辱不惊,他悄悄凑到史今身边说:“班长刚才没吃饭吧,我刚在炊事车上拿两个鸡蛋还烫手呢,快趁热吃了吧。”
许三多悄悄地给史今递了过去。史今伸手去接,鸡蛋真的很烫。
史今猛地站了起来,全班被他惊乍而起,史今对高城立正着,脸上表情又愤怒又沮丧,愤怒是对掩于他身后的许三多,沮丧是对自己。
“报告连长,热源找着了。”然后从怀里掏出许三多给的两个鸡蛋说,“早上没吃饭,我揣了两鸡蛋,回营我写检查。”
高城接过鸡蛋,眼睛狠狠地盯着史今。
“你把我当傻子呀?”高城咆哮道,“你当了五年兵,不踢正步快不会走路了,上回防红外作业你连热水都不敢喝!三班的,全体都有,真觉得你们班长对你好就别靠他挡事,谁干的?”
伍六一看了一眼史今,挺身而出:“报告连长,是……我。”
“鬼扯!行,行,我看你们协同观念挺强的,我再追究也没意思,你们全班检查吧。”高城嚷嚷完打算上车,许三多却拦住他,说:“连长,鸡蛋您别拿走了,我给我们班长带的,他没吃早饭呢。”
高城瞧他半天,终于明白这位仁兄并非在坦白认错,而是在惦记着他班长的早饭。他一步冲到许三多的面前,说:“我也没吃早饭。如果咱们这趟能不让人发现,我不吃明天的饭,不吃后天的饭,我三天不吃饭!”
许三多好像没有听懂,他说:“要不您吃一个,给班长留一个?”
“全连三个星期的作业全部泡汤,我吃不下,你说咋办?”高城的两只眼睛简直在燃烧。
许三多不管,他说:“那也得吃饭,那不行,那饭得吃……”
高城的怒火突然按捺不住了,他猛地吼道:“拖出去毙了!”
这当然只是一句气话,可所有的人都吓呆了。高城自己也愣了,他将鸡蛋突然往许三多的手上一拍,就掉头走了。大家看到,他的身子在气得微微地发颤。许三多捧着鸡蛋回头,愣住——连他都能感觉到来自全班的强烈敌意。
演习就这样结束了。
步战车在眼前轰鸣着,后舱门开着,士兵们上了车。几辆车上的士兵轻松地在说笑,701车前的三班没有这份心情,一个个沉默着尽早地钻进了车里。
准备回营的时候,成才悄悄地摸到三班,对甘小宁打听道:“听说你们班让人揪出来了?”甘小宁没有回答,只是两眼没好气地瞪着他。
成才只好转过话题,问:“许三多呢?”
“连长把他毙啦!”甘小宁说着钻进了车里。
成才一愣,但他随即笑了,他往车舱里瞧了瞧,看到一车都是苦大仇深的眼睛,成才知道是真的出事了,赶忙走开。
701车里那个空着的座位,是属于灾星许三多的。他现在正蹲在车边的地上,揪着草根,羞耻、沮丧,夹着轻微的恼火,那源于委屈,他真是只想史今吃上饭。
步战车驶动,从许三多身边驶过,后舱门从刚才就没关,史今探头,愠怒又有些怜悯地命令着:“上车。”
许三多顾头不顾腚地连忙上车,心不在焉,脑袋又在门檐上碰了个响,大家如没瞧见一样。
许三多想坐下,白铁军和另一位士兵不约而同往旁边挤了一挤,空出的地方顿时足够坐下两人。坐得宽敞,却绝不舒服,谁被躲瘟疫一样躲着都不会舒服。许三多回避着全班人的眼神,全班人也在回避着他,唯一一个与他直面的只有对面伍六一喷火的眼睛。
演习结束正是放松的时候,很多车上的士兵都打开舱盖,将大半个身子探在舱外吹风,有的车上传来整齐的拉歌声。701号车的舱盖紧紧合着,除了引擎声外没有人声。
一辆野战油泵车正停在输油管道边将燃油输给战车,老马和李梦几个如穿着军装的土包子一样在旁边张望问话:“是七连的吗?”被问到的兵都摇着头。
“认识许三多吗?上过团报的那个?”
回答还是不认识。最后,老魏干脆猛然一声大叫:“谁是七连的?!”
成才的车正好停在不远处,车上的士兵随即应道:“我们是钢七连的!”
听到这话儿,老马几个连忙兴高采烈地跑过去。
“认识许三多吗?”薛林问,“就是刚去你们连的那个许三多!”
一听到许三多的名字,那个士兵的神情,便古怪地笑了笑。
他转身看看成才说:“成才,许三多不是你老乡吗?”
成才显然是不太想搭茬:“也算是吧。”
老马顿时高兴起来,缠住成才不断地问:“许三多来了吗?他在哪辆车上?”
成才看了看身后的701号车,车如个缩了头的铁乌龟样毫无生气,车长的脸灰青,头蔫耷着。
“你找他有什么事?”成才决定不去惹那辆车。
老马说:“我们是一个班的,我是他班长,不,我是说,我是他原来的班长……”
701一车人都铁青着脸,从许三多这面的射击孔,可以看见和听到外边那几个人的谈话。五班的那四个人仍在那个需要费劲仰着头的位置说话。
看他们挺热情的样子,成才犹豫了:“他……留守,他没有来。”
老魏说:“我就说嘛,他刚来,这演习没准不带他,早听我的,去团里一趟好了。”老马却说:“这孩子有出息,我寻思他能进步挺快。大哥,你给我带个信好吗?”薛林说:“什么哥不哥的,他比你还小!”
老马说:“我都要走的人了,你们还跟我戗!兄弟,你给我带个信,我这就要退伍了,这一走,这辈子许就见不着了……”
成才的心有点软了:“你到底要说什么?”
“你让他得空回来看看,唉,战斗部队,也不能有空……”老马犹豫了。
薛林说:“没空也得有空!你告诉他要走的是谁!不是烂人李梦!不是鸟人薛林!是老马!大好人老马!”他几乎是愤怒,那种愤怒绝大部分源于分离在即,倒并非因为七连的兵对他们不大客气,“要走的是老马!他不能回来也得去送送!哪天走直接上红三连问指导员!”
成才的车,慢慢地往前开去了。
“你告诉他,千万得告诉他!最后瞧一眼!也许就是瞧这辈子最后一眼!”老马一边追着成才的车,一边喊道。
那几个孬兵终于被淹没在腾空而起的烟尘中。许三多早已经抱着头蜷成了一团,他抬头时已经泪眼婆娑。一车兵仍是那个样子,谁也不看谁。只有史今一直贴在射击孔里看那几个已经被灰尘淹没的身影,贴得那么近,让人觉得他简直可以从那个枪眼大的孔里探头出去。
然后他看看许三多,叹一口气,那口气的长度绝对长过叹气专家老马,长得让人觉着诧异。许三多有一种误会,他以为这口气是为他而发的,于是他被车从眼眶里摇晃出第一滴泪水,然后拄着枪不知羞耻地哭泣。
一车兵都绷紧了一言不发,他们的脸上写得明明白白——这里不同情这样的眼泪。
钢七连讨厌弱者!
车场寂静了。
车库的门一拉上,这一季度的训练,就暂时告一段落了。
伍六一打回宿舍之后,神色就一直不对,时不时地看着墙上那面“先进班集体”小旗发愣。他忽然听到有人进来,回头一看,是七班的成才,以为是找许三多的,开口就说:“许三多不在!”
成才却说:“我不找许三多。我们班长让我来的。”
“干什么?”伍六一看到成才的眼睛一进就盯住了墙上的那面小旗。他知道了。他说,“他火上梁似的干什么?待会儿我送过去!”
成才压着高兴说:“我们班长说,还是悄没声拿走就算了。”
“你这叫悄没声吗?……用得上悄没声吗?这玩意本来就是轮流挂的。”
成才摘了旗,看看伍六一,伍六一白了他一眼。成才有点尴尬了,只好掏出烟来递给伍六一。
伍六一没理这茬:“他没告你说吗?这旗不能单手拿,它大小是个荣誉。”
成才不敢再招惹他,笑笑就走了。伍六一在后边自己嘀咕着:“见这小子就有气,他心里幸灾乐祸着呢。”
被拿走的那旗,在三班实在是挂得太久了一些了,连墙上都有清晰的印痕。
“你们这帮懒家伙,还有军人的样子吗?把墙皮擦一擦,看着像什么样子!”伍六一朝着班里的战士们发着疯。
高城和指导员是全连唯一有权利住单间的人,十几平方米的一间房,因为连带家具都只放了简单的几件制式,反而显得空空荡荡。高城和史今如拔军姿,两个人私下时还站得如许挺拔,只能说一种自我惩罚。高城冷冷地看着,他也并不打算叫史今放松一点。
“我不会坚持要他走,他还是钢七连的人,但是炊事班……或者生产基地,基地一直要人,我说七连没人,但是……有时也该应付一下……”就这份吞吞吐吐来说,高城简直已经觉得自己有些委屈了。
史今:“不行,连长。”
高城他又要暴跳起来:“谁去都可以!他去就不行?”
史今:“谁去都可以。他去,尤其这个时候去,我们就是彻底否定他作为战斗人员的价值。”
高城在屋里足转了一圈,转回来时已经有些狐疑,史今是不是看到了什么他没看到的东西:“哈!战斗人员!他有你说的那个价值吗?我看兵的眼神不如你。说真的,他有你说的那个价值吗?”
高城的这份好奇实在比他的愤怒更让史今为难。
史今:“我……暂时还没有看出来。”
“我靠!”如此有失身份地大喊一句后,高城的恼怒也超过了临界点,“我已经让步了!我容许他在七连待着!只要他的成绩不记入本连——尤其是你们班的作训成绩!我不想被这么一个……这么一个心理上的侏儒废掉我最好的班长!”
史今吞吐到了结巴的程度,因为他维护的那个人实在没给他任何希望:“我……我想我们都是心理上的侏儒……我是说,曾经是。所以,所以应该给他个机会,让他能……至少能……长高一点。”
高城已经冷静下来,更确切地说,冷淡下来,没人愿意总重复一个话题:“你还要维护他吗?”
史今:“连长,就像您维护我们一样啊。”
高城不为所动,他对许三多实在已经深恶痛绝。
高城:“你坚持?”
“我……”史今长嘘了口气才把后两字说完,“坚持。”
高城:“那你走吧。”
史今犹豫了一下,规范地敬了一个礼后打算出去。高城不再看他,只是在史今将出门时嘘了口气:“以后我不会再跟你私下谈这件事情了。”
史今轻轻带上了门,看着营房外的空地发呆,在他的印象中,他的连长对他从来没有这样冷淡过。
成才在七班宿舍将那面先进红旗挂在墙上,刚看了看,发现许三多贴了墙根从外边过道经过。成才叫住了他。成才走出去,在他身边并没停顿,径直越过,那架势就像对墙上懒得掸去的灰尘。“你跟我来。”成才的声音很冷淡。许三多跟在他后边,只有三尺远,但像在两个世界。两人再没有原来的亲热。越好的部队里后进越没有容身之地,于是许三多对成才也只敢老实地跟在后边。
两人走到操场上,成才坐下拿出支烟点上,很有派地看看许三多,点点头。他像个领导,至少是带“长”的什么,尽管成才只在新兵连做过副班长。许三多于是坐下。
成才盯着许三多的眼睛:“我这两天一直在想你怎么办,我想出来了。”
许三多于是眼里放光,看着他,那几近感激,原来有人为他在想。
“你走。”成才很武断地说道。
许三多的脸色迅速黯淡下来:“我去哪?”
“你已经把印象搞成了这样了,那就很难再拧过来了。你在红三连不是干得挺像样吗?那块地盘是你的,你跟红三连领导说,你想回红三连,七连这边肯定放。听我的错不了,我是为你考虑的。”
“可我,我不想去。”
成才觉得奇怪了:“这是你想去不想去的问题吗?许三多,人这辈子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是不能勉强的,这叫定数。”
“你这是迷信。”许三多说,“我爸说的。”
“我当然知道这是什么!我是为你想的,你以为你在钢七连还能有什么出息吗?我也替钢七连说一句,你就根本不该在这个连队,连里天天在说的荣誉感你知道是什么吧?你能为它做什么吗?你……”
他恼火回头瞧一眼,其实不瞧也知道许三多在干什么,许三多在抹眼泪。
成才压了压自己的声音:“行了,这里烦这个。我也烦这个。”
冰寒彻骨,寒得许三多不再抹泪,只好任由眼泪往下淌,他现在甚至没有擦掉眼泪的权利。
“别流了。还流?你靠这个在七连混吗?……你知道什么叫荣誉吗?什么叫钢七连?叫什么不好干吗叫钢?……你浑身上下哪根毛当得起这个字?说这话是为你好,这哪是你来的地方?……哭什么?我真不想跟你说什么了……我跟你说,你现在就去找红三连的人说……你还哭?我不想跟你说了,跟你是老乡有什么好的?全连都笑话我!——我走了!”连那种居高临下的耐性也失去了,成才扔了烟头走开了。
许三多看着地上那个烟头发呆,远处的兵在打篮球,欢声喧哗,他很孤独。
许三多捡起烟头放进垃圾箱里。
许三多想想,觉得成才说得也对,于是红三连的指导员何红涛在前边走,许三多就在后边跟着,他不知道如何开口。
何红涛的心情很愉快,愉快到根本没有觉察后边的那位。许三多咽着唾沫,瞪着眼看着那个后脑勺,下着决心。转个弯何红涛倒不见了,许三多看着空空的路发呆。何红涛从他身后的小卖部里出来,手里拿着个奶瓶子。
何红涛看到许三多一愣,忙说:“可巧了,我正要去找你呢。我跟你说件大喜事啊,我他妈有儿子啦!不……”何红涛忽然发现自己说错了,忙改口说,“我要跟你说的不是这事,我是跟你说,你那老班长老马,就要走了,后天下午的火车,跟我说了好几次了,临走前得看见你,你得去送送人家。”
可许三多想对何红涛说自己的心事,连连说了几个我,就是怎么也说不出来。
“怕请不下来假是吧?知道你们七连忙,请不下假我去帮你请。”
许三多还是我我我的,怎么也说不出口。
何红涛:“我一直纳闷你干吗要去七连,现在我觉得你是挑对了。许三多,你是个会想事的人,当兵是得去七连这样的地方啊。你看你现在,结实啦我该说坚实啦,硝烟熏出来的坚实。你们连是耗弹大户嘛。什么事?”
许三多:“没……事。”
何红涛自顾自地说着,完全不顾及许三多的表情:“这话你可能不爱听吧,你刚来时那眼神吧,空空洞洞的,现在就有东西啦,在想事。有心事吧?是好事,你自个担当事了嘛。担当啥事?说我听听,不定还能帮你担当点。”
许三多:“我……没……指导员再见。”然后愣头青一般掉个方向就走了。
何红涛愣在那,过了会儿总算想起句话茬:“那你到底去不去送你班长哪?许三多,年年兵来兵往,人能惦记住人不容易!”
许三多茫然而愣冲冲地走,他在逃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