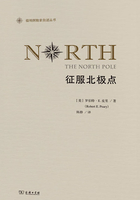
第1章 计划
把征服北极比作赢下一盘象棋似无不妥,在其中,所有通向有利结局的不同步骤远在游戏开始前都预先得到计划。这对我是一场熟悉的游戏——我已经玩了23年的游戏,只是境遇不尽相同。那是真的,我一直被击败,但是随着每次失败关于这场游戏的新鲜知识会到来,包括它的错综复杂、它的重重困难、它的难以捉摸,而且随着每次新鲜的尝试,成功一步一步靠近;以前显得不可能或者充其量是完全没把握的事情,开始呈现可能性的一面,并且最后甚至是很有可能。每次失败在它们的所有环节就其成因被分析,直到变得有可能确信那些成因可以在将来被防范,并且伴随着相当多的好运气,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败局可以转变成一次最终的全面胜利。
真实情况是,许多见多识广的聪明人对这个结论有不同的看法。不过其他许多人都分享我的观点,并且毫不吝惜地提供他们的同情和帮助,终于到现在,我最最纯粹的快乐是了解他们的信心没有被错置,正如过去很多次努力的境遇一样,他们对我的信赖和对我为之付出生命中最美年华的任务的信仰都被充分地验证。
不过虽然就计划和方法而言,北极点的发现确实几乎可以跟一盘棋局相比拟,当然,两者有着明显的区别:在象棋里,头脑在跟头脑竞赛。在北极的探索中,那是人类头脑和毅力跟原始物质环境难以捉摸的蛮荒之力搏斗,它常常在未知或者我们所知甚少的法则和推力下运转,因此很多时候看来任性、捉摸不定和不可预言,没有哪怕一丁点的确定性。因为这个原因,在驶离纽约的那一刻前,虽然有可能对进攻冰封北方的主要行动进行计划,却没有可能预料这个对手的所有行动。倘使这有可能,我1905—1906年创造当时最远北方的87°6′纪录的探险将会触及北极点。不过每个熟悉那次探险纪录的人都知道,它的全面胜利受挫于我们强大对手的那些无法预料的行动之一——在那次,持续一季的异常猛烈的大风破坏了极地包裹,使我与支持队伍离散,因为没有足够的补给,以至于当几乎在目标的攻击距离之内时,不得不因为饥饿危险的迫近而返回。当胜利最后看来几乎唾手可得时,我被一次绝不可能被预见的行动所阻挡,而且当我遇上它时,我只能无助地面对它。正如大家所知,我和那些跟着我的人不仅仅被挫败而且还几乎丧命。
不过所有这些现在只是当故事来讲讲。此刻,那是一个不同或者多一些启示的故事,尽管那些华丽失败的纪录都不是没有它们的启示。而这一点看来适合在开始时提出成功建立在多年努力之上,因为力量来自反复的失败,智慧来自早先的错误,经验来自没有经验,而决心来自上面每一点。
也许,考虑到最终事件以如此惊人的方式证明了我曾给出预言,将罗斯福号驶离纽约踏上前往北方的最后旅程两个多月之前发布的行动计划在某些细节上跟行动最终被执行的方式做比较也许会很有趣。
1908年5月初,在一份公开发表的声明中,我描绘了如下的计划:
“我将使用同一艘船,罗斯福号;将在7月初离开纽约;将沿着同一路径向北,途径布雷顿角的悉尼(Sydney)、贝尔岛海峡(Strait of Belle Isle)、戴维斯海峡、巴芬湾和史密斯海峡;将使用同样的方法、装备和补给;将组建最低限度的白人队伍,以爱斯基摩人做补充;将跟以前一样在鲸鱼海峡(Whale Sound)地区带上这些爱斯基摩人和狗,并且跟1905—1906年的冬季一样,将全力推进我的船到格兰特地(Grant Land)北岸相同或类似的冬季营地。
“雪橇行进将如往常一样在2月开始,不过我的路线将做如下变化:首先,我将沿格兰特地北岸向西远至哥伦比亚角(Cape Columbia),可能会更远,而不是跟我以前一样在摩斯岬(Point Moss)离开这片陆地。
“其次,离开陆地后,我的路线将比以前更偏西北,为的是避开我上次探险中发现的格兰特地北岸与北极点之间东移的浮冰,为它们留出空间。另一个必要的改变将是我的雪橇分队在途中将更加紧密地保持队形,为的是避免队伍的一部分由于浮冰移动而跟剩余的人分离的可能性,那会造成没有充足的补给提供给被拖长的行进队伍,正如前次探险中所发生的那样。
“在我脑海中,我上次探险中在向上游推进和返程时都遭遇到的这条‘大水道’(一道未结冰水面)本质上无疑是这部分北冰洋的一个持久特性。我将把这条‘水道’作为我带着满载雪橇的离岸点,而不是在格兰特地北岸,我有能力做到,对此我深信不疑。如果能够完成,它将缩短到北极点的路线接近100英里,并且明显地简化命题。
“在下次探险的回程行进中,我将可能有意做上次我无意中做的事情;那就是,撤退到格陵兰北岸(斜顺着浮冰流向的路线),而不是试图返回到格兰特地北岸(斜对着浮冰的流向)。这一计划的一个附属物可能会是格陵兰北岸上由最先回到船上的支持队伍建立的补给站。”
这项计划的主要特点概括如下:
“第一,史密斯海峡或者‘美洲’路线的利用。这在今天必须被接受为一次坚决的有进取心的上攻北极的所有可能路线中的最佳路线。它的优势是相对于在北冰洋整个外围任何其他已发现的地点离北极点近100英里的陆地基础,返回路上长距离的海岸线,以及在轮船遭遇任何灾祸事件时,安全和不依赖协助地(对我来说)已知撤退路线。
“第二,比北极地区任何其他可能基地控制更大中心极地海及其周围海岸范围的冬季基地的选择。谢里登角(Cape Sheridan)实际上离克罗克地(Crocker Land)、离格陵兰东北岸剩余的未知部分以及离我1906年的‘最接近北极’处是等距的。
“第三,雪橇和爱斯基摩犬的使用。人和爱斯基摩犬是仅有的具有如此调节能力来满足北极旅行广泛要求和偶然性的两种选择。飞艇、汽车、受过训练的北极熊等都是不成熟的,除非是作为一种吸引公众注意的方式。
“第四,极北地区原住民(鲸鱼海峡爱斯基摩人)作为雪橇队伍普通成员的使用。看上去没有必要来详述这一事实,传统上在那个特定地区生活和工作的人必定展现一支严肃的北极队伍人员所具备的最有可能用到的素质。这是我的计划。工作目标是美洲部分的北极地区剩余最大问题的澄清,或者至少按照他们通常的比例进行处理,还有就是为美国巩固事实上在过去三个世纪里曾是世界上所有文明国度努力和竞争目标的伟大的世界战利品。”
这项计划的细节在这里被如此明确地罗列,那是因为它们若被忠实地贯彻将构成北极探险编年史里或许是独一无二的篇章。如果你愿意,请将这项计划跟它被执行的方式相比较。确切地说,正如计划所安排的,探险于1908年7月6日在纽约起航。7月17日驶离悉尼,8月18日离开伊塔(Etah),9月5日抵达罗斯福号的冬季营地谢里登角,与三年前它抵达相同地点的时间不超过一刻钟。整个冬季都忙碌于狩猎、各种方面的旅行、制作我们的雪橇装备以及从罗斯福号沿格兰特地北岸运送补给品到哥伦比亚角,那里将是我们离开陆地向北极挺进的地点。
雪橇分队从1909年2月15日至22日离开罗斯福号,在哥伦比亚角集结,随后在3月1日探险队离开哥伦比亚角,穿越极地海洋向北极进发。84°纬线在3月18日被穿越,86°在3月23日,意大利人的纪录在下一天被超越,88°纬线在4月2日,89°在4月4日,而北极点在4月6日上午10点被触及。我花了30个小时留在北极点,随同的有马特·亨森(Matt Henson)、乌塔(Ootah),1906年曾跟着我到达当时的“最远北方”87°6′的忠实的爱斯基摩人以及其他三名在以前的历次探险中同样跟我在一起的爱斯基摩人。我们六人在4月7日离开众所期待的“北纬90°”踏上回程,于4月23日在哥伦比亚角重回陆地。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从哥伦比亚角到北极的旅程花费了37天,(尽管只有27次行进)我们从北极返回哥伦比亚角只用了16天。这次回程旅行的破例速度要归功于我们仅仅需要沿原路返回,而不是开辟新的路线,还因为我们幸运地没有遭遇任何延迟。良好的浮冰和气候环境同样有所贡献,更不必说成功的喜悦让我们疲惫不堪的双腿插上翅膀这一事实。不过爱斯基摩人乌塔有他自己的解释。他说:“魔鬼睡着了或者跟他的老婆闹矛盾,否则我们绝不可能这么顺利地回来。”
在这样的比较中需要被注意的是,事实上做出必要时偏离该计划的唯一特色在于返回格兰特地海岸的哥伦比亚角,而不是像我在1906年曾做的,在更向东的格陵兰北岸。做出这一改变有充足的理由,在它们适当的位置将得到解释。这项纪录上只有一个阴影——实际上是一次悲剧。当然我是指罗斯·G.马文(Ross G. Marvin)教授令人惋惜的死。他在4月10日溺亡,北极点被触及的四天之后,在哥伦比亚角以北45英里的地方,当时他正指挥着一支支持队伍从北纬86°38′折返。除了这次令人悲伤的意外,这次探险的经历是完美无瑕的。我们返回时跟离开时一样,在我们自己的船里,历经磨难却完好无损,处于良好的健康状态并且拥有全面胜利的纪录。
在所有这些幸事中也有一个教训——这个教训如此明显以至于指出来或许有些多余。这项计划,被如此仔细地设计并且被如此忠实于细节地贯彻,是由若干要素构成,缺少任何一个对胜利都可能是毁灭性的。没有我们忠诚的爱斯基摩人的帮助,我们几乎不可能成功;即便有了他们,倘使我们没有对他们工作和忍耐能力的了解以及多年的相识教会他们信任我的信心,都不能成功。没有为我们的雪橇提供牵引力的爱斯基摩犬,我们肯定也不可能成功,它们使我们能够在全然没有任何其他动力可以用所需速度和稳定性来移动我们的补给品的地方运送它们。没有雪橇形式的改善,使我有能力去建造它并且结合它的构造、力量、轻便及易于牵引使雪橇犬的沉重任务变得远比它本来可能的轻松,我们或许也不可能成功。假使没有我足够幸运地偶然发现的一种改进形式的热水器这样一件如此简单的事情,我们甚至都有可能会失败。在它的帮助下,我们能够在十分钟内融化冰块来泡茶。在我们前一次旅行中,这个过程曾花费一小时。茶在这样一次推进旅程中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必需品,而这个小发明每天可以节省一或一个半小时,当我们正在旅程中向北极奋进时,时间恰是成功的本质所在。
成功在于努力工作,这是真理。不过对于所有这一切,我要真正欣慰地表达的是,哪怕我们失败了,我应该不会因为疏忽了什么而对自己有所责备。多年的经验曾教会我对每一个可能预案都有所准备,每一个弱点都得到保护,每一个预防措施都被采纳。我曾花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参与北极的竞赛。我已经53岁,没有一个曾经尝试从事北极地区工作的人超越这个年龄,也许约翰·富兰克林爵士是唯一的例外。我有点过了我力量的巅峰期,也许稍稍缺乏更加年轻年岁里生机勃勃的灵动和锐气,刚刚过了大多数人把费力的事情留给年轻一代的时间;不过这些劣势或许完全被经受过磨练的坚定毅力、对自身以及对如何保存我的力量的完美了解所抵消。我知道这是我在伟大北极棋盘上的最后一局棋。要么这次赢,要么永远被击败。
北方的诱惑啊!那真是奇妙而有魅力的东西。不止一次我从伟大的冰冻天地回来,历经磨难、满身疲倦且困惑不已,有时候甚至伤筋动骨,告诉自己我已经完成了在那里的最后旅行,渴望属于我的类型的社会,文明所带来的舒适环境以及家所拥有的平和与宁静。但是莫名其妙地,不出几个月这种似曾相识的焦虑感就向我袭来。文明社会开始失去它对我的热情。我开始向往白色苍莽、跟浮冰和狂风的搏斗、长长的北极黑夜、长长的北极白昼、一小撮与我成为多年朋友的古怪而忠诚的爱斯基摩人以及白色偏远北方的沉寂和广漠。于是我回去了,一次又一次,直到最后,我多年的梦想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