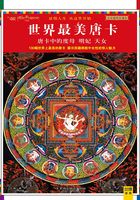
第十章 西藏神秘艺术的故事
远古时代的西藏传统应该属于一种泛亚萨满文化。这种传统为许多中亚文明所共有,其中也包括在15000年前至25000年前移民至北美洲的土著居民。他们正是从西藏-蒙古腹地将这一文化带到了大洋彼岸。两者在宗教符号上有很多的相似之处,譬如“万”字标记和沙画等。时至今日,在西藏的艺术和生活中,仍然可以见到这一史前文化的遗迹。
后来,藏族人又逐渐在他们的萨满传统基础上,吸收了强大民族的文化。西藏地处亚洲的中心,四周环绕着好几种发达的封建文明。西边是古波斯王国,早在公元前4000年,藏族人就已经开始受到波斯宗教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自己的“苯教”传统。到公元1世纪左右,苯教席卷了整个中亚高原地带,成为西藏大多数地区的主要宗教。
其次,东边为繁荣的唐朝。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藏族人就已经开始通过战争和和亲从内地吸收各种各样的传统文化。
第三,南边为印度。雅鲁王朝的第一任国王就极有可能是来自印度的流亡者。他的名字叫做聂赤赞普,生活在大约公元前4世纪。据说,将中亚部落联合在一起,并建立了吐蕃王国的藏王松赞干布正是他的第33代传人。
最后,丝绸之路环绕着西藏,一直向北延伸,穿过唐朝和波斯,并一路往西,直达埃及。在西藏的北部,沿着这条丝绸之路诞生了很多城邦,穿越东西方的沙漠商旅会在这里休憩、养息、补充粮草,然后再次踏上旅途。藏族人无疑也会经常与他们贸易,有时甚至还会占领一两座类似的城市。
早在佛教出现于印度之前,西藏就已经开始从这些文明中吸收养份。不过,自公元前3世纪开始,印度阿育王发起的文化交流,佛教开始沿着丝绸之路向外传播,并且进入了中亚地区。在公元7世纪中期,松赞干布统治时期,佛教正式成为了西藏的主要宗教。
正如之前所说,藏王松赞干布有两位杰出的妻子,一位来自尼泊尔,一位来自唐朝,她们鼓励他皈依佛教,并将佛教确立为吐蕃王国的主要宗教。他在拉萨为这两位妻子建造了两个宏大的寺院——大昭寺献给尼泊尔公主,叶莫切寺献给文成公主。除此之外,他还下令在王国内的108个主要圣地建造了寺院和纪念碑。

拉萨的一名藏族觉姆正在为我们讲解历史。
要开展这一系列建筑活动,自然少不了大量的画家、工匠和建筑工人。他们大都来自尼泊尔和唐朝,以及其他佛教国家和地区,如北部的和阗,西部的克什米尔等。藏族人与他们共同工作,并从他们那里接受知识和训练。
西藏今天的艺术传统在很大程度上都来自于松赞干布时代。他的两个后代—8世纪的藏王赤松德赞和后来的赤惹巴千——也同样为西藏的佛教文化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因此,在这一时期,西藏的佛教艺术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和传播。藏族人把这一时期称为“三法王黄金时代”。所有起源于这一时期的藏传佛教传承都被称为宁玛派,或“旧译派”。
西藏佛教艺术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出现在11世纪的宗教复兴时期,在这一时期,西藏开始出现风行全藏的寺院文化。尽管在这之前,西藏已经修筑了好几座寺院,但规模都相当有限,寺院中的僧侣也大都从贵族家庭选拔而来,他们更像是藏族的福神,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传法者。
在早期的藏传佛教中,传法的形式更多地类似于苯教,只在家族成员之间进行。佛法只传给家族内部成员,静修所也建筑在家族附近的山上,任何想要学习佛法的人都必须先拜见家族族长,恳请成为该家族的门徒。一旦获得接纳,就类似于被家族所收养,从此进入了该家族的族谱。
11世纪的宗教复兴给西藏的社会生活和艺术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浪潮首先开始于西部,由伟大的仁钦桑布译师发起,并发展到了整个藏地。继仁钦桑布之后,这一浪潮中的另一个最为重要的人物就是来自古印度萨诃罗国(今孟加拉达卡地区)的阿底峡大师,他在仁钦桑布的感召下来到了西藏。他就是拉萨附近那座著名的度母寺的建造者。阿底峡的大多数嫡传弟子都成为了僧侣或是觉姆,在西藏各地建立了各种寺庙和静修所。他的大弟子仲敦巴尽管并不是僧侣,但是却建造了拉腾寺作为阿底峡传承的法座所在。这一起源于阿底峡和仲敦巴的传承便是后来的噶当派,又称“口传派”。仲敦巴也成为了另一个被视作达赖喇嘛前世化身的历史人物。
与此同时,玛尔巴译师也在南部的洛达地区发起了自己的小型复兴运动。尽管他本人及其主要弟子都不是僧人,但是他的大弟子米勒日巴却决定让僧人冈波巴担任玛尔巴传承的继承人。冈波巴在达瓦波建造了一座寺院来延续这些传承,由此便诞生了噶举派,又称“耳语传承派”。冈波巴的四个主要弟子也全都是僧人,他们分别建造了自己的寺院。其中一位弟子帕嫫德鲁巴又有八位主要弟子,同样也是僧人,他们又分别建造了八座寺院来延续自己的传承,由此就诞生了四大老噶举派和八大新噶举派。
与此同时,藏西南卫藏地区的昆氏家族也决定从印度寻求新的密续。在这之前,昆氏家族一直信奉的都是宁玛传统。昆氏将贡觉杰布派往印度,师从卓弥译师。回藏以后,贡觉杰布在萨迦山建立了萨迦寺,并最终发展成为了萨迦派。萨迦派从这里开始发源,并逐渐壮大,成为西藏生活的主流力量之一。萨迦派之所以会如此成功,大概就在于它将家族传承的苯教和宁玛传统与这一时期兴起的寺院传统结合在了一起。萨迦派的领袖一般都并非僧人,法王权位也是通过世袭而不是依据个人成就推举出来的。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在中亚地区,萨迦寺庙比萨迦平民聚居地更加常见。

觉、仲师徒像局部
布画唐卡 17世纪 103厘米×68.5厘米
这幅唐卡绘有阿底峡和仲敦巴师徒二人,此图为局部,图中所示为此唐卡画面上的阿底峡像。觉即觉沃杰白登阿底峡,仲即仲敦巴。阿底峡在西藏进行传教活动的十多年中,跟随其学习佛法的弟子很多,其中以仲敦巴、雷必喜饶最为著名。仲敦巴于公元1057年修建了热振寺,雷必喜饶于公元1073年在拉萨河南岸修建桑浦寺。在藏区各寺院中,常能见到这师徒三人的塑像和画像。
这三大教派——噶当、噶举、萨迦——在11世纪的诞生以及他们所掀起的寺院文化热潮导致了这一时期建筑的蓬勃发展。各地纷纷建造起各种各样的僧院、寺庙和静修所。画家、工匠和建筑师再次成为藏地炙手可热的人才,西藏艺术得到了飞速地发展。与三法王黄金时期一样,这些人才大都是由印度、尼泊尔、克什米尔和中原地区输入,不过,在这时,西藏也已经培养了很多藏族自己的佛教艺术大师,并且在所有艺术领域都扮演起了日益重要的角色。
13世纪是西藏艺术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印度被来自阿富汗和波斯的穆斯林侵入,直接导致了佛教的衰落。另一件大事则发生在半个世纪以后的东亚,蒙古迅速崛起成为超级大国。蒙古人一直把藏族人看作是自己信仰上的兄弟,在建立元朝政权之后,他们开展了大规模引进藏传佛教的活动。马可·波罗也正是在这时来到了中国,他在这里遇见了萨迦派喇嘛秋吉八思巴,后者后来成为了忽必烈的上师。
在元朝,全国建起了成千上万座藏传佛教僧院和寺庙。蒙古统治者从西藏延请了艺匠和建筑师来监督工作,这无疑对中国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反过来,蒙古族、汉族的艺术传统也对西藏艺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建筑竣工之后,大多数藏族艺术家和建筑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但是,他们在中原所见所闻的丰富艺术形式,以及蒙古人从欧洲及朝鲜搜集来的很多艺术珍品,都毫无疑问对他们的作品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们不仅体验到了全新的灵感和材料,而且还学会了透视法。透视法曾经改变了文艺复兴早期的欧洲艺术,那时,它也同样改变了西藏艺术。
西藏艺术史学者有时也把这一时期称为萨迦时期,因为在这段时间,卫藏地区的萨迦喇嘛在西藏处于主导地位。这当然是因为忽必烈拜秋吉八思巴为师的缘故。然而,这一建筑运动中的艺术家却来自西藏各个地区和藏传佛教的所有派别。因此,他们的经验也对整个西藏地区产生了影响。透视画法现在几乎成为了所有西藏艺术家的必需技法。
当然,在这之后,西藏艺术还经历了很多个发展阶段。譬如,被罗伯特·瑟曼称为“兜率运动”的建筑风潮,这一风潮发生在14世纪—17世纪期间,宗喀巴和一世达赖喇嘛显世之后。曼娘派、曼萨尔派及噶热派等艺术流派都出现在这一时期。瑟曼将这些艺术上的发展看作是藏族人对于生命的观想,以及对兜率净土向往的延伸。当然,他的理论也不无道理,正如这些艺术派别也各有千秋一样。
还有清顺治九年(1652年),集西藏艺术大成的布达拉宫开始重建,这极大地推动了图库(转世活佛)传统及拉章的建设。这些拉章也就成了各地区艺术品的主要赞助人。今天,如果我们评价一件艺术作品为具有“拉章品质”,那就说明它是为过去某个时期的转世喇嘛的私人官邸所作。这也意味着这件作品是由当时最优秀的艺术家创作,所使用的也是最上等的材料。同时,艺术家自己也知道,他的作品将会获得艺术的永生。这件作品将会被供奉在活佛的拉章中,这位活佛的所有后世也都将继续珍视它,把它当作传统的一部分。艺术家本人的名字也将会进入拉章簿,也就是《拉章官方记录》,与他们的作品一起,持续利益后世众生。

拉萨的按尼桑库觉姆寺内,8位觉姆正在诵持经文。在15世纪初,宗喀巴的6位女弟子在这里的山洞内闭关禅修,获得证果,后来便在这了修建了这座女性禅修所。

在布达拉宫朝圣的三代女性。
转世活佛一直都为西藏艺术的最大支持者。很多活佛从孩提时代起就开始研究艺术,并且一生都将唐卡绘画作为自己的观想工具。当然,很少有活佛能够有时间或精力成为真正的艺术家——青年时代,他们把绝大多数时间都用在了宗教学习和了解各种各样的传承之上;成年时代,他们又把绝大多数时间用在了观想、讲法和传承佛法之上。尽管如此,几乎所有的活佛都仍然会对自己在艺术领域的知识和赞助成就感到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