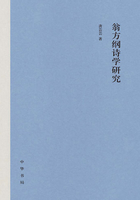
第二节 杜诗与“肌理”说
清代诗学中,杜甫的地位极高,乃与六经并立。这是清初在对文学史传统的梳理过程中达成的共识。但是,随着清人对诗学问题的深入讨论,围绕杜诗会产生很多理论桎梏,如辨体,如风与雅颂传统,如“温柔敦厚”,如正变,如“穷而后工”, ……若以这些传统的诗学范畴来论杜,则杜诗的价值根本无法达到与六经并立的独尊地位。很多诗学家的理论因此出现漏洞。坚守杜诗独尊地位的翁方纲,则是在辨析这些传统诗学范畴的基础上确立“一衷诸杜”的诗学观,然后以此为基础来建构“肌理”说。
一、“一衷诸杜”
在翁方纲的诗学中,杜甫一直是一个处在独尊地位的形象。“肌理”说的提出与完善,均与杜诗有关。
翁方纲十六岁始学诗,即从杜诗入手。他指导儿子也是如此:“从此不徒工试帖,杜陵诗法要研摩。”小字注云:“正谓研求忠孝,必自杜诗始耳。” 在他看来,将忠孝大义与诗法结合得恰到好处的,非杜甫莫属。其花半生精力为杜诗作《附记》,而且平日论诗,也处处以杜甫为宗。他在《石洲诗话》中便极力推崇杜甫:
在他看来,将忠孝大义与诗法结合得恰到好处的,非杜甫莫属。其花半生精力为杜诗作《附记》,而且平日论诗,也处处以杜甫为宗。他在《石洲诗话》中便极力推崇杜甫:
自初唐至开、宝诸公,非无古调。但诸家既自为体段,而绍古之作,遂特自成家,如射洪、曲江是也。独至杜公,乃以绍古之绪,杂入随常酧酢布置中,吞吐万古,沐浴百宝,竟莫测其端倪所在。
他曾不无遗憾地说:“杜公自言说诗能累夜,可惜当日无人从旁录其所说。” 为何他对杜甫有如此崇拜之情?首先与清代整个杜诗学的发展有关。清代杜诗学发展其中有一条线,就是秉承宋人观点
为何他对杜甫有如此崇拜之情?首先与清代整个杜诗学的发展有关。清代杜诗学发展其中有一条线,就是秉承宋人观点 ,将杜诗奉为诗中六经,如:
,将杜诗奉为诗中六经,如:
龚鼎孳《杜诗论文序》:诗之有少陵,犹文之有六经也。前乎此者,于此而指归,后乎此者,于此而阐发。文无奇正,必始乎经,诗无平险,必宗乎杜。此少陵之诗与六经之文,并不朽于天地间也。
吴兴祚《杜诗论文序》:然则杜诗非诗也,盖五经之遗文耳。 梁章钜《退庵随笔》卷二十一:犹忆少时闻先资政公言:读杜诗须当一部小经读之。此语似未经人道过。顾亭林亦谓经书有几部可以治天下,《前汉书》其一,杜诗其一也。
梁章钜《退庵随笔》卷二十一:犹忆少时闻先资政公言:读杜诗须当一部小经读之。此语似未经人道过。顾亭林亦谓经书有几部可以治天下,《前汉书》其一,杜诗其一也。
就官方而言,乾隆十五年(1750)编的《御选唐宋诗醇》,共选杜诗722首,占选诗总数的27.1%。学者指出,其中体现出较强的崇唐抑宋的观念,而在崇唐的前提下,更明显地体现出崇杜的倾向 。在这样的风气下,翁方纲直接将杜诗与六经联系起来,认为杜诗是继《三百篇》而兴。这个观念成为其诗学的主导,与他的官方学者和学政身份相契合。他又尝言“诗法上下千年必于杜是程”
。在这样的风气下,翁方纲直接将杜诗与六经联系起来,认为杜诗是继《三百篇》而兴。这个观念成为其诗学的主导,与他的官方学者和学政身份相契合。他又尝言“诗法上下千年必于杜是程” ,并欲“准杜法以程量古今作者”
,并欲“准杜法以程量古今作者” 。所有的诗学实践和理论都将“一衷诸杜”。
。所有的诗学实践和理论都将“一衷诸杜”。
杜诗中浓郁的忧国忧民情怀,引起了清初易代诗人的强烈共鸣,于是继宋代以后,在清代学术中又掀起了一股注杜高潮。清初人将明亡的原因归咎于学风的空疏,表现在杜诗学上,各种杜诗注本蔚为大观。现存清代的杜诗注本共有一百四十多种,而成于清初的就有四十多种,如钱谦益《钱注杜诗》、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仇兆鳌《杜诗详注》。杜诗研究的其他方面也很兴盛,囊括了宋以来形成的杜诗版本学、校勘学、阐释学等许多方面,还有各种专题专门研究,愈分愈细,愈来愈专。随着康乾盛世的到来,爱国忠君的道德典范早已成为杜诗学的应有之义。由于考据学风盛行,“证实”的思想又一次贯注在本已是颇重视典故考辨的杜诗学中,虽然其中不乏杨伦《杜诗镜铨》力求简明的努力,但典故、本事的探求,仍是最基本的注杜途径。
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杜甫的诗法,而胜过一味推崇杜诗的思想意义——当然这也是分析诗法的最终目的。翁方纲即做着这样的尝试。其《杜诗附记·自序》中记录了注杜经历:
予幼而从事焉,始则涉鲁訔、黄鹤以来诸家所谓注释者,味之无所得也。继而读所谓千家注、九家注,益不省其所以然。于是求近时诸前辈手评本,又自以小字钞入诸家注语,又自为诠释,盖三十余遍矣。乾隆丁丑、戊寅(1757—1758),馆于蠡县,搁笔不为诗者三年,始于诸家评语慎择之。惟新城王渔洋之语,最发深秘,乃遍摭其三十六种书,手抄一编,题曰《杜诗话》,自以为有得矣。然而渔洋之言诗,得诗味矣。深绎而熟思之,此特渔洋之诗耳,非尽可以概杜诗也。一日读山谷《大雅堂记》而有会焉。曰:诸先生之论说,皆剩语耳。于是手写杜诗全本而咀咏之,束诸家评注不观,乃渐有所得。如此又岁余,而后徐徐附以手记。此所手记者,又涂乙删改,由散碎纸条积渐写于一处。甲申、乙酉(1764—1765)以后,按试粤江,舟中稍暇,录成一帙。后乃见吴下有专刻杜诗全文无注释之本,便于携阅。庚戌(1790)以后,内阁厅事,每于待票签未下时,当午无事,则以此本覆核,如此者又十年。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一生对杜诗的尊崇不变,且对注杜事业精益求精,由读注而弃注,读别家注而自注,历半生而得《杜诗附记》二十卷。对于前人注杜的得失,他有着自己的看法:
从来说杜诗者多矣,约有二焉:一则举其诗中事实典故以注之,一则举其篇章段落分合意旨以说之,二者皆是也。然而注事实典故者,有与自注、唐注相比附者,则可也。其支蔓称引者,则不必袭之也。其注篇法、句法者,在宋元以前,或泥于句义,或拙于解诂,犹孟子云“以文害辞”者耳。在后则明朝以后,渐多以八比时文之用意例之,更非诗理矣。
他认为注典故事实,必须有根有据,而分析篇章意旨,宋元以前过于拘泥,明清时又有人以时文之法评说,均不得诗理。他极力反对为注杜而牵强附会。在翁方纲的时代,科举已经恢复试帖诗,且唐试帖抄本盛行。试帖诗是最讲究章法的,与时文大致相同。他历充各地学政,授人无数,并有《复初斋试诗》、《芸窗改笔》等批改试帖诗的本子存世 。但他反对以分析试帖诗的方法来对待一般的诗歌,特别是杜诗,“以八比时文之用意例之,更非诗理”。
。但他反对以分析试帖诗的方法来对待一般的诗歌,特别是杜诗,“以八比时文之用意例之,更非诗理”。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和把握杜诗?杜诗“沉郁顿挫”,多世态沿变感叹之音,已经是一个无可争辩的文学史事实。后人只能对这个事实进行价值判断。清代杜诗学的一个重要专题,就是对杜诗中书写患难流离的评价,因为这是判断杜诗是否符合传统诗学的核心“温柔敦厚”诗教的关键问题。
乾隆三十六年(1771),翁方纲视学广东,为与粤人言诗,校刊评点了程可则《海日堂诗集》,并为之作序。序言阐发的,却是对杜诗的看法 。他首先引入了汪琬的《海日堂诗集》原序:“今之学诗者每专主唐之杜氏,于是遂以激切为上,以拙直为壮,以指斥时事为爱君忧国,其原虽出于雅颂,而风人多设譬喻之意,亦以是而衰矣。”认为杜诗多雅颂而少“风”旨。其实汪琬承认《诗》中也有激切拙直之篇,但“古之圣贤未尝专以此立教。其所以教人者,必在性情之和平,与夫语言感叹之曲折,如孔子所云温柔敦厚是已”。认为杜诗的激切并不符合“温柔敦厚”的诗教。
。他首先引入了汪琬的《海日堂诗集》原序:“今之学诗者每专主唐之杜氏,于是遂以激切为上,以拙直为壮,以指斥时事为爱君忧国,其原虽出于雅颂,而风人多设譬喻之意,亦以是而衰矣。”认为杜诗多雅颂而少“风”旨。其实汪琬承认《诗》中也有激切拙直之篇,但“古之圣贤未尝专以此立教。其所以教人者,必在性情之和平,与夫语言感叹之曲折,如孔子所云温柔敦厚是已”。认为杜诗的激切并不符合“温柔敦厚”的诗教。
这在尊杜者翁方纲看来是一项莫大的罪名。他发现,汪琬与何景明《明月篇序》提出的杜诗雅多而风少的看法一致,是明七子的延续。所以要将杜甫与“温柔敦厚”联系起来,就必须打破将“风”与“雅颂”卓然分立的传统:
昔成周之世,周文公相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而天下大服,雅颂兴焉;而陈王业,被之管弦,写士女之伤悲,极町畽宵行之心曲,盖古圣贤人未有不通达家国天下之治理,而能婉喻一夫一妇之情者,谁谓风与雅颂可分哉!
他认为《诗》三百篇是一体的,“风”与“雅颂”不可分。《国风》中以夫妇之情所设之譬喻,不正是“雅颂”中直叙的家国天下之理么!所以“杜诗之教,即孔子之教也”,杜诗并合于风雅传统:
顾六经以外,韵语之不名一器,而足与圣人之旨相发者,其无过于杜矣。杜诗自有言情之什,深厚之至,切伦纪,关风化,与风人之旨合,然即以其朝庙边关,即境叙事诸作,亦足以见人心人理之大同,而得夫观感兴起之本。
明人学杜诗,以“激切拙直指斥时事为古,如汪先生之所言者,此乃正高谈貌古者之弊也,而可以为杜病乎?”他们并未懂得杜诗的好处,更不用说如何学习杜诗了。正因为杜诗如此博大,“与圣人之旨相发”,翁方纲极力反对视杜诗为“变风变雅”的说法:
其(按:指渔洋)论某体格当用某家也,曰:“乱离叙述,宜用老杜。”然则先生意中,岂不竟以变风变雅视杜矣?杜虽生于兵灾播迁之际,似竟一生言愁者,然此其面目耳,非其神髓也。设若杜公当周、召之遭逢,则《时迈》、《思文》之《颂》, 《皇矣》、《旱麓》之《雅》,舍此其谁也?
杜甫如若生于盛世,则如《皇矣》等被称为“正风”的篇章,正当出于他笔下。所以我们当看杜诗的神髓,而不是其呈现出的“乱离”、“愁”等面目。“愚尝谓周文公之雅颂非杜莫能为也,岂得因其在天宝至德之际,而目为乱离之作乎!” “神髓”就是,切风纪、关人伦,是为忠孝之作,这与诗歌面目为“叙述乱离”还是“盛世颂歌”无关,何可谓之离经训而为变者乎!所以,即使遭逢唐之乱世,杜甫也是继承了孔子“温柔敦厚”的诗教。
“神髓”就是,切风纪、关人伦,是为忠孝之作,这与诗歌面目为“叙述乱离”还是“盛世颂歌”无关,何可谓之离经训而为变者乎!所以,即使遭逢唐之乱世,杜甫也是继承了孔子“温柔敦厚”的诗教。
与此相关的,他最反感“穷而益工”之说:
欧阳子论诗,亦曰:“穷而益工。”吾最不许此言。若依渔洋之论杜,准以欧阳子语,则必评杜曰“变而不失其正”乎!夫见其时势之艰,则以为诗之穷;见其叙述之苦,则以为诗之变,此恶可与言诗也哉?
确实,我们声称能通过诗文,体会古人遭遇苦难的心理,甚至还在潜意识里期望这种苦难能更深刻地鞭笞古人的灵魂,以便产生更伟大的作品,当然同时我们会奉上无限的同情与感慨。可是不曾想,古人是否真的愿意以自身的苦难、心灵的摧残来换得真诗,留名后世呢?“穷而后工”,并不是主观意愿的追求,只是后人对既定事实的解释而已。提倡这种说法,过分夸大了时代环境对诗人的作用,而忽视诗人自身的才力:
诗人虽云“穷而益工”,然未有穷工而达转不工者。若青莲、浣花,使其立于庙朝,制为《雅》、《颂》,当复如何正大典雅,开辟万古!而使孟东野当之,其可以为训乎!
李、杜之地位,是因为他们才高所致,而与穷途无关。因为无论生活在盛世抑或乱世,他们都会有这样的成就,这不是孟郊之类的苦吟者可以比拟的。更可怕的是,提倡“穷而益工”会使人过分重视诗作中对际遇不满的描写,而导致怨尤之风气。所以,翁方纲整理黄仲则遗诗,只存五百首,并解释道:“予最不服欧阳子‘穷而益工’之语,若杜陵之写乱离,眉山之托仙佛,其偶然耳。使彼二子者生于周召之际,有不能为雅颂者哉!世徒见才士多困踬不遇,因益以其诗坚之,而彼才士之自坚也益甚,于是怨尤之习生,而荡僻之志作矣。” 他反对将杜诗之“工”与“穷”相联系,诗人不当以自身所处之穷境,作为诗歌事业成就的前提。
他反对将杜诗之“工”与“穷”相联系,诗人不当以自身所处之穷境,作为诗歌事业成就的前提。
翁方纲极其反对将杜甫称为诗之“变”,极其反对依欧阳修的思路评杜诗为“变而不失其正”者,因为“变风”的归属使得杜诗价值落入第二义,说明他虽然怀疑时运与诗运的关系,但仍未脱开“正”、“变”的价值判断体系,而这个“怀疑”,也仅限于杜甫。
古人对杜诗的价值评价,常依“辨体”观念,翁方纲则打破了这一点:
夫(渔洋)谓七律宜宗盛唐,则杜固居其正,无疑也。然又谓五古宜宗选体,选体之说,不能旁通也。故又变格调为神韵,而以王、孟、韦、柳当其正,则杜之五古,又居其变。同一杜诗,而七言居其正,五言居其变。然则仰窥弦歌韶武之音,其将必以《清庙》、《思文》之什为正,而《东山》、《鸱鸮》之音为变乎?其将何以为后学者之准式?吾故曰:作诗勿泥选体。
他认为,对于同一个诗人的评价必须一致。不能一体居于正,一体居于变,实则杜甫各体均可作为独尊的典范,如五律:
以唐贤五律言之,自当以右丞为主,知以右丞为主矣,然后知以少陵为主,此二语者,则已发其大凡矣。何为先右丞也?曰:右丞千古五律之正则也。然则少陵其稍变者乎?非也。右丞五律,玉色金声,千古无出其右者,然而天地之元气,至杜而其秘乃尽发耳。且如一题之作,拓为数篇,非杜不能也。开合起伏之章法,非杜莫备也。只此二家,而五律尽矣。
又如五古:
五言古诗亦以右丞开先,而少陵继之。
此正是与渔洋区别之处。渔洋《古诗钞》五言部分只选入陈子昂、张九龄、李白、韦应物、柳宗元五家,以证明关于“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的观点。翁方纲对这一个看法是完全否定的。在其为补渔洋《古诗钞》选五言古诗之失而编选的《小石帆亭五言诗续钞》中,增入杜甫诗二十六首,居唐人之冠 ,又增王维诗二十首。所谓五言古诗以王维、杜甫为正,其实王维的意义也与五律相同,作为杜甫之“开先”耳。而七律:
,又增王维诗二十首。所谓五言古诗以王维、杜甫为正,其实王维的意义也与五律相同,作为杜甫之“开先”耳。而七律:
七律至杜公千古一人。
又,杜甫七言的地位,是大家公认的。如渔洋《七言诗歌行钞·凡例》言:“杜七言于古标准,自钱、刘、元、白以来,无能步趋者。” 翁方纲在以渔洋此《钞》为底本而编的《七言诗三昧举隅》中,以杜甫《丹青引》一篇为三昧之正、万法归原处
翁方纲在以渔洋此《钞》为底本而编的《七言诗三昧举隅》中,以杜甫《丹青引》一篇为三昧之正、万法归原处 。
。
在古诗与律诗的成就上,翁方纲将杜甫置于高不可及的地位,却未谈到杜甫成就不大的绝句。我们注意到,打破辨体论诗,在翁方纲这儿也只适用于杜甫,如他认为李白的五古、七古“大而能化”,而“七律不工” 。他反对渔洋辨体论杜,其中包含了一个预设:杜甫是个集大成的全能诗人,即各体均可作为独尊的典范,均是对“风雅”的传承,这才是与并立于“六经”的地位相适应的表现。他不容后人对杜甫有半点质疑,显示了极力推崇杜甫、独尊杜甫的意愿,也是其诗学建构的坚实基础。
。他反对渔洋辨体论杜,其中包含了一个预设:杜甫是个集大成的全能诗人,即各体均可作为独尊的典范,均是对“风雅”的传承,这才是与并立于“六经”的地位相适应的表现。他不容后人对杜甫有半点质疑,显示了极力推崇杜甫、独尊杜甫的意愿,也是其诗学建构的坚实基础。
归而言之,“上自风骚汉魏旨格,下逮宋元以来流别,一举而衷诸杜法耳” 。翁方纲破除了明代何景明一派强调的分“风”与“雅颂”来轩轾杜诗,认为杜诗毫无疑问地体现了“温柔敦厚”的诗教。“若论杜诗,则自有诗教以来,温柔敦厚必归诸杜,兴观群怨必合诸杜,上下古今万法源委,必衷诸杜。”
。翁方纲破除了明代何景明一派强调的分“风”与“雅颂”来轩轾杜诗,认为杜诗毫无疑问地体现了“温柔敦厚”的诗教。“若论杜诗,则自有诗教以来,温柔敦厚必归诸杜,兴观群怨必合诸杜,上下古今万法源委,必衷诸杜。” 于是解决了杜甫可以作为唐代甚至历代诗人典范的学理基础。这是论者在唐宋诗之争中将唐诗的审美精神从盛唐诗移到中唐诗的最有力说明。
于是解决了杜甫可以作为唐代甚至历代诗人典范的学理基础。这是论者在唐宋诗之争中将唐诗的审美精神从盛唐诗移到中唐诗的最有力说明。
二、未刊稿《石洲诗话》卷十与翁方纲“肌理”说的完成
笔者于上海图书馆发现翁方纲《苏斋存稿》手稿本(索书号821732—39),其中收入《石洲诗话》卷十,封面题“大兴翁方纲”,并记“何端简公《然灯纪闻》一卷原本,翁方纲附记”, “此卷是端简公所撰,翁方纲全录于此,附以管见,非若前卷偶节录也”。即此卷是抄录王士禛口述、弟子何世璂所纂的《然灯纪闻》,并加诸按语 。其中关于学古人七律一条,集中展示了“肌理”说。原文录于下:
。其中关于学古人七律一条,集中展示了“肌理”说。原文录于下:
《然灯纪闻》:
七言律宜读王右丞、李东川,尤宜熟玩刘文房诸作。宋人则陆务观,若欧、苏、黄三大家,只当读其古诗、歌行、绝句,至于七律,必不可学。读前诸家七律,久而有得,然后取杜读之,譬如百川学海而至于海也。此是究竟归宿处,若骤学之,鲜不踬矣。
翁批:
窃按,此一条愚所未能惬服者。此一条盖有二失:一则谓苏、黄七律必不可学,此大误也。欧阳集中七律名篇尚不甚多,且不必说。若苏、黄二家七律,与其古体之沉顿雄恣,何所分别乎?不过不曾如明朝李、何辈貌为唐之格调耳。正当举此种七律如北宋自王半山(半山人无足论,其诗则工,其七律尤见真诣。)及苏、黄三家,实皆足以为明朝李、何、王、李辈貌袭唐调之千金良药,必知此是七律正宗,而后可以语唐七律也。陆放翁七律最圆足,足继前贤,亦正与苏黄七律克嗣也。唐七律以右丞、东川、少陵、义山为正宗,宋则半山、苏、黄、陆也,金则遗山,元则道园耳。且渔洋先生专取唐人七律之格调,而于其后之效唐音者,又尝推许李空同、李沧溟矣。然则此条内既综论古今七律,又何不并言学者当师法空同、沧溟耶?岂非先生亦自觉其非真耶?再则云“先读诸家,久而有得,然后读杜”,此又误也。杜少陵之诗,即儒者圣经也,若以为文例之,则在前马迁之史也,在后昌黎之文也;以艺事例之,即王右军之书也。今如读书者,且先诵法诸子史集,俟其有得,然后进而读六经,有是理乎?为文者且先学柳子厚、李习之、孙可之诸家,俟其有所得,然后再进而读韩文,有是理乎?学书者且先习学王献之、萧子云、羊欣,薄绍之,俟其有得,然后再进而学右军,有是理乎?正惟四书五经,布帛菽粟,人人日用饮食所亟需而不可须臾离者,未有以道高且美若登天然,而姑远之,姑俟之者也。且劝学者先从根柢下手。经史,根柢也,杜诗亦即根柢也,并非欲效其貌,效其浑古,效其沉雄徽壮也。学古人诗,断无效其貌者也。(所云“骤学之,鲜不踬”者,正谓学其貌耳。)正惟此中“细肌密理”,深研其虚实衔接、乘承伸缩之所以然。在诸家虽亦有之,而无若杜之正变开合、纵敛起伏,无处非规矩方圆之极则也。且如右丞七律,亦岂非“细肌密理”,可以见规矩方圆之则者乎?然而有说焉。右丞、东川七律,其肌理即在格韵之中,渊然不露,为难寻也。是以若刘文房七律即右丞、东川七律,所不及右丞、东川者,味稍薄耳。中唐十子七律,亦又何尝非此种七律?不过味又较更薄耳。其味渐薄矣,而其肌理格韵无以别于右丞、东川七律也。初无人敢以貌袭右丞、东川之伪体目之者,所以渔洋于右丞、东川七律外,必首举文房,其势然也。即使其学右丞七律,真到右丞分际者,亦只望之如是;即使其后中晚唐人学右丞,具体而非造真际者,亦复望如是,故曰,右丞七律,其肌理即在格韵中,渊然不露,为难寻也。杜则不然,杜之肌理于气骨筋节出之,于章法顿宕出之,学者诚能造其深微,得其肌理运转之所以然,则其外貌原不必斤斤杜诗之似也。既深得其肌理运转,则其外貌之浓淡傅色,且各有取材制胜处,岂必自名为学杜?此则义山、山谷、道园皆如是也。其不善学者,不知其内腠理密运之所以然,第以词色声音之末,步趋而橅仿之,则其嗜伪者艳以为近真也。其有识者则斥为伪体,若李空同、何大复、李沧溟是也。所以仿右丞,其真赝猝不及辨也,仿杜则真赝立辨。何者?于骨节辨之,不能欺人者也。由是言之,则右丞非不具肌理骨节,而仿之者,今人不觉孰真孰伪;杜则肌理骨节,箭在的中,能者从之,不能者无从着手,此所以渔洋教人尤在熟玩刘文房七律者,正是有唐一代学右丞者众手一同也。唐人七律,自李义山外无人知杜法者,非其不欲学也,为不能也。渔洋心眼超绝,固亦觑见义山、山谷之得杜意矣,然其意中究非能脱去空同、沧溟之格调,故于右丞、东川外必首举刘文房。文房岂后来李、何伪体可比?而渔洋之意,欲学者步趋向往之处则同也。推其如此,则诚似右丞、东川易效而杜难效也。学者居今日经籍昌明之会,皆知通经学古,非复渔洋所承从前格调模仿之派,愚则欲正告学者,既欲学诗,必先求其真际,必先讲其纵敛起伏之所以然,必宜先探杜之原,而又必合右丞、东川以植基地。至唐人七律若刘文房以下,即大历十子之伦,七律亦有佳篇,是宜随其质地所近,皆资取益。而学杜七律之正轨,则香山、义山、樊川以及东坡、山谷、放翁、遗山、道园,皆适道之圭臬耳。
唐人七律皆效右丞,即如刘文房是已。文房称“五言长城”,岂其七律非正矩乎?然只骨肉停匀,情景相称耳。杜七律则章法节奏,沉顿开宕,非仅一写景言情所能限矣。况七律唐始启之,至宋以后,事境渐增,人之所处与其讽谕赠处,又万有不同,又岂可概以一情一景尽之?所以东坡、山谷以后,乃无境不辟,其章法乘承接筍合缝,亦非唐人格律所能该悉也。而此条云“尤宜熟玩刘文房七律”,文房七律止一卷,才数十首,其中名作九首而已,右丞、东川七律虽亦篇什不多,而其深厚在文房上远矣。何以谓“尤宜熟玩文房”乎?此特偶对澹庵话及,此非通彻订定之语,学者或勿泥执焉可耳。
翁方纲著有《石洲诗话》八卷,据张维屏所作跋语,前五卷为其视学广东时所撰,草稿久佚,叶云素忽于都中书肆购得之,持归求翁方纲作跋。遂命人钞存,又增《评杜》一卷,及附说元好问、王士禛《论诗绝句》两卷,共成八卷 。依卷十前题识,应还作有卷九,是为“偶节录前人著述”加以附记,惜不存。八卷刊刻时间为嘉庆二十年(1815),故未及刊刻的手稿卷十,当作于嘉庆二十年之后。我们在先行的《石洲诗话》八卷本及其他文献中,都没有发现关于“肌理”说的成熟的论述,新见《石洲诗话》卷十当是考察翁方纲“肌理”说最终完成的重要资料。故而“肌理”说的最终成型时间(包括定名、理论完整建构及运用),当是在嘉庆二十年以后,是为翁方纲之晚年。
。依卷十前题识,应还作有卷九,是为“偶节录前人著述”加以附记,惜不存。八卷刊刻时间为嘉庆二十年(1815),故未及刊刻的手稿卷十,当作于嘉庆二十年之后。我们在先行的《石洲诗话》八卷本及其他文献中,都没有发现关于“肌理”说的成熟的论述,新见《石洲诗话》卷十当是考察翁方纲“肌理”说最终完成的重要资料。故而“肌理”说的最终成型时间(包括定名、理论完整建构及运用),当是在嘉庆二十年以后,是为翁方纲之晚年。
王渔洋教人学古人七律,提出先从易学的小家(刘长卿)入手,再学大家杜甫。杜甫七律第一,这是渔洋与翁方纲的共识。二人的分歧就在于,学习古人究竟应当是先河后海,还是直接从第一义入手。
研究翁方纲的学者,都注意到其诗学与杜诗的关系,但均语焉不详,并没有清楚地理出二者关系的细节。而更重要的是,多数研究者的论述,是建立在“肌理”为“义理”和“文理”这个定义的基础上,并将此套用于翁方纲注杜。如《清代杜诗学史》提到“借杜诗构建‘肌理’说的基本理论范畴”时,就是从“义理”与“文理”两方面考虑的 。前文已讨论过,这个解释是不正确的。那么,“肌理”究竟指什么呢?与杜诗的关系又是如何体现的?
。前文已讨论过,这个解释是不正确的。那么,“肌理”究竟指什么呢?与杜诗的关系又是如何体现的?
这段材料清楚地说明了“肌理”的内涵、特点及典范:“肌理”是指诗中“虚实衔接、乘承伸缩之所以然”。而“肌理”是诸家诗人皆有的,不过有显隐和粗细之别。杜诗的“肌理”达到极致。
诗歌的“肌理”细密与粗疏自是有价值之别。杜诗的“肌理”,清晰可循,是为学诗者之楷模。能学之人,必得之精髓;不能学之人,却露出马脚,只于词语声音等色相入手,落得貌袭的骂名,明七子便如是。而王维诗的“肌理”则藏于格韵间,难辨难寻,后学者同样于色相求之,却无法分辨究竟是缺失“肌理”,还是于格韵中蕴藏“肌理”。难以分辨真赝,也就难以分辨好坏。这样写出来的诗,或许能逃避“貌袭”之名,使得诗坛鱼龙混杂。作为诗学家的翁方纲,对这种情况很是担忧。所以强调学古人必须从“肌理”明显的杜诗入手。
那么,这个“虚实衔接、乘承伸缩之所以然”的“肌理”究竟如何呢?我们发现,“虚实衔接、乘承伸缩”,亦见于翁方纲《杜诗附记·自序》:
(杜甫)篇中情境虚实之乘承,筍缝上下之消纳,是乃杜公所以超出中晚宋后诸千百家独至之诣。
“情境虚实之乘承,筍缝上下之消纳”就是“虚实衔接、乘承伸缩”之意。翁方纲又指出,杜诗的“肌理”最精,这是杜甫超出中晚唐和宋以后各家的法宝。所谓“乘承”,即注重诗歌结构中上下单位之间的衔接,及其效用。“筍缝”即指结构单位之间交合连接的地方,“消纳”即自然开合,浑成一体。“虚实乘承,筍缝消纳”便是杜诗之精诣。弟子梁章钜也认为乃师的《杜诗附记》是“阐发肌理” 之大作。
之大作。
如《杜诗附记》卷三《行次昭陵》:
旧俗疲庸主,群雄问独夫。谶归龙凤质,威定虎狼都。天属尊尧典,神功协禹谟。风云随绝足,日月继高衢。文物多师古,朝廷半老儒。直词宁戮辱,贤路不崎岖。往者灾犹降,苍生喘未苏。指麾安率土,荡涤抚洪炉。壮士悲陵邑,幽人拜鼎湖。玉衣晨自举,铁马汗常趋。松柏瞻虚殿,尘沙立暝途。寂寥开国日,流恨满山隅。
(方纲附记)“寂寥”二字似与“开国日”三字不接者,此正以“寂寥”二字幽咽到极处,乃忽然“开国日”三字一声飞出,方是惊心动魄之笔也。上接“瞻”字、“立”字,下接“流恨”,则“恨”字即从“开国日”流出,正以无筍缝为筍缝耳。
前人评价此诗:“末乃行次昭陵而有感也……松柏尘沙,叹景色荒凉。伤今思昔,故对山隅而流恨耳。” 对章法的分析多是将全章分两层或三层,翁方纲却有独到的见解。他注意到了“寂寥开国日”的突兀,而立足于解释这种突兀。“‘寂寥’二字幽咽到极处”,正是承接上文,将读者的喉咙紧逼,突然冠以“开国日”三字,引来惊心动魄的效果。此处对“寂寥”与“开国日”连接的解释,正是词与词之间的“肌理”。他进而解释“松柏瞻虚殿,尘沙立暝途。寂寥开国日,流恨满山隅”这两联的“肌理”:前两句正是“寂寥”一语的来处,“寂寥”消纳了这两句的内容情感;“恨”字直接从“开国日”流出,很自然。“开国日”与“流恨”自然衔接,这两句间似无筍缝,其实筍缝已在“寂寥”与“开国日”之间,而这两个词所涵蕴情感的收束和突放,已经很好地解决了筍缝的消纳问题。而这两个词又分别消纳了前后句。
对章法的分析多是将全章分两层或三层,翁方纲却有独到的见解。他注意到了“寂寥开国日”的突兀,而立足于解释这种突兀。“‘寂寥’二字幽咽到极处”,正是承接上文,将读者的喉咙紧逼,突然冠以“开国日”三字,引来惊心动魄的效果。此处对“寂寥”与“开国日”连接的解释,正是词与词之间的“肌理”。他进而解释“松柏瞻虚殿,尘沙立暝途。寂寥开国日,流恨满山隅”这两联的“肌理”:前两句正是“寂寥”一语的来处,“寂寥”消纳了这两句的内容情感;“恨”字直接从“开国日”流出,很自然。“开国日”与“流恨”自然衔接,这两句间似无筍缝,其实筍缝已在“寂寥”与“开国日”之间,而这两个词所涵蕴情感的收束和突放,已经很好地解决了筍缝的消纳问题。而这两个词又分别消纳了前后句。
又如卷六《送远》:
带甲满天地,胡为君远行。亲朋尽一哭,鞍马去孤城。草木岁月晚,关河霜雪清。别离已昨日,因见古人情。
弟七句是筍节,是消纳。
前人均以四句为单位分此诗为两部分,并以“草木岁月晚,关河霜雪清”一联为诗人想象旅人途中之苦,或为代远行者答言 。翁方纲不以为然,他以第七句“别离已昨日”为筍节,而且指出此是“消纳”。此句将前六句之意都容纳消解了。《古别离》有“送君如昨日”之语,这就是后面说的“古人情”。而落实于此,就是“带甲满天地”的乱世景状,亲朋痛哭、鞍马独行的生离死别带给双方的孤独和伤悲,更是“草木岁月晚,关河霜雪清”的凄凉和憔悴之苦,尽在“别离已昨日”一语中消纳,再用一句“古人情”作结。前人分析的前四句与后四句的平行结构,在翁方纲这里变成了两层的包含关系,即“别离已昨日”包含了前六句之意,再与“因见古人情”平行。这就是立足于整首诗“肌理”结构间,深入探析其间张力所得出的结论。
。翁方纲不以为然,他以第七句“别离已昨日”为筍节,而且指出此是“消纳”。此句将前六句之意都容纳消解了。《古别离》有“送君如昨日”之语,这就是后面说的“古人情”。而落实于此,就是“带甲满天地”的乱世景状,亲朋痛哭、鞍马独行的生离死别带给双方的孤独和伤悲,更是“草木岁月晚,关河霜雪清”的凄凉和憔悴之苦,尽在“别离已昨日”一语中消纳,再用一句“古人情”作结。前人分析的前四句与后四句的平行结构,在翁方纲这里变成了两层的包含关系,即“别离已昨日”包含了前六句之意,再与“因见古人情”平行。这就是立足于整首诗“肌理”结构间,深入探析其间张力所得出的结论。
再如杜甫《秋兴八首》,翁方纲评曰:
论者但知“故国平居有所思”一句领起下四首,皆忆长安景事,此亦大概粗言之耳。其实“瞿塘峡口”一首,首尾以两地回环,其篇幅与“蓬莱”、“昆明”、“昆吾”三首皆不同,而转若与“闻道长安”一首之提振有相类者,盖弟四首以“长安”、“故国”特提,而“蓬莱”一首以实叙接起,弟六首以“曲江”、“秦中”特提,而“昆明”、“昆吾”二首以实叙接起,则中间若相间插入“瞿塘”一首,作沉顿回翔者,此大章法之节族也。若后四首皆首首从长安景事叙起,固伤板实,即不然,而一章特提,一章实叙,又成何片断耶?今弟五首实叙而弟七、八首又实叙,中一首与末二首层叠错落相间出之,乃愈觉“闻道长安”、“瞿塘峡口”二首之凌厉顿挫、大开大合,在杜公则随手之变,虚实错综,本无起伏收束之成见耳。
仇兆鳌《杜诗详注》曰:“‘故国有思’,又起下四章。” 论者多主此说。翁方纲不以为然,他认为第四首末联以“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提振,出句点“秋兴”之意,对句则特提“故国”,所以接下来的第五首便以实叙“故国”接起;而第七、八首却是直接因第六首“瞿塘峡口”提起“曲江”、“秦中”二词,分别以实叙接起。后四首并非均从“故国平居有所思”一句直接领起。“瞿塘峡口”一首的插入,使这一联章组诗产生了沉顿回翔的效果,“此大章法之节族也”。翁方纲对诗作内部结构、各诗之间关系的洞悉,对情境虚实、前后照应的阐释,都细致入微。诗法的奥秘,正在于此,而探究诗法的奥秘,其乐趣亦在于此罢!
论者多主此说。翁方纲不以为然,他认为第四首末联以“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提振,出句点“秋兴”之意,对句则特提“故国”,所以接下来的第五首便以实叙“故国”接起;而第七、八首却是直接因第六首“瞿塘峡口”提起“曲江”、“秦中”二词,分别以实叙接起。后四首并非均从“故国平居有所思”一句直接领起。“瞿塘峡口”一首的插入,使这一联章组诗产生了沉顿回翔的效果,“此大章法之节族也”。翁方纲对诗作内部结构、各诗之间关系的洞悉,对情境虚实、前后照应的阐释,都细致入微。诗法的奥秘,正在于此,而探究诗法的奥秘,其乐趣亦在于此罢!
这就是他在第八首的评注中说的,“言情之作与事物错综之理交合而出之”。于此,杜公已“极其至”。所谓“事物错综之理”,即“肌理”。《秋兴八首》是联章组诗,那么,每首诗之间的架构也必须符合“细肌密理”。而这八首诗又同是感秋遣怀,“一事叠为重章共述”,与《咏怀古迹》等组诗不同,更需要在各首诗的安排上费苦心。翁方纲还分析了八首诗中写秋景的虚实安排,认为杜甫的八首诗并不是全实写秋景,只有第一首“玉露凋伤”和第七首“昆明池水”中“波漂菰米沉云黑,露冷莲房坠粉红”为实写,其他则为虚写。而同为虚写,第二首“夔府孤城”虚含秋意,第三首“千家山郭”、第五首“蓬莱宫阙”都是“全不著秋”,各以一个词点出,让第七首的实写秋景给人亦实亦虚的感觉,如此则收束“秋兴”。第八首“昆吾御宿”已经“转于春字”,重与唱叹。八首诗皆与题旨有关,又不为之苑囿,这就是杜甫能够重章共述的原因。杜诗的开合离即,又尽在章法中。
《杜诗附记》集中体现了翁方纲对杜诗的解读态度和方法,其在自序中陈述的注杜经历,说明其倾注了半生精力,直至晚年才最后完成,吟哦不已。他对这部书的态度,正有其识语为证:“麻姑之爪可以搔痒,陈琳之檄可以愈风。” 虽然书中并未以“肌理”二字定义,但内涵与《石洲诗话》卷十所言一致。他在《杜诗附记》卷三《彭衙行》一诗后批注道:“近日名流或转高谈杜之神韵,而不肯向筍缝处用意,则又安得不剖析言之。”
虽然书中并未以“肌理”二字定义,但内涵与《石洲诗话》卷十所言一致。他在《杜诗附记》卷三《彭衙行》一诗后批注道:“近日名流或转高谈杜之神韵,而不肯向筍缝处用意,则又安得不剖析言之。” 可见他由“肌理筍缝”入手,也含有指摘“神韵”后学流弊的倾向。
可见他由“肌理筍缝”入手,也含有指摘“神韵”后学流弊的倾向。
如此,我们已经清楚所谓的“肌理运转之所以然”了。这与《诗法论》中“穷形尽变”之法正相合:
(杜)又曰“佳句法如何”,此法之尽变者也。……夫惟法之尽变者,大而始终条理,细而一字之虚实单双,一音之低昂尺黍,其前后接筍、乘承转换、开合正变,必求诸古人也。
与前人不同之处在于,翁方纲所论的章法,是立足于“肌理界缝”之间的“穷形尽变”诗法,强调两个平行单位之间的张力。他将“穷形尽变”的诗法追溯到杜诗“佳句法如何”,此句出于《寄高三十五书记》,该诗前两联为赞颂高适篇什之好:“叹惜高生老,新诗日又多。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杜诗详注》云:“各体中皆有法度,长篇则有段落匀称之法,连章则有次第分明之法,首尾有照应之法,全局有开阖之法,逐层有承顶之法。且章有章法,句有句法,字有字法。谨严于法,而又能神明变化于法,方称宗工巨匠。此云‘佳句法如何’,盖欲与之互证心得耳。” 即章有章法,句有句法,“大而始终条理,细而一字之虚实单双,一音之低昂尺黍”。注重字法、音节、句法、章法等,论者称之为“文本经营”
即章有章法,句有句法,“大而始终条理,细而一字之虚实单双,一音之低昂尺黍”。注重字法、音节、句法、章法等,论者称之为“文本经营” 。法之穷形尽变者,“立乎其节目,立乎其肌理界缝”也。“节目”,即指句子、章节等单位之间,“肌理”也就是“界缝”,还包括用字、用韵、平仄的变化所呈现的状态。每一法则又根据自身所处的位置——或为长篇,或为联章,或为首尾——而不尽一致,杜甫诗法不一,每随之变,此所谓“穷形尽变”者也,是为“活法”。但这里始终有一个原则,那就是“其前后接筍、乘承转换、开合正变”,即如何使诗的各个因素在即离间找到最佳的位置。无论是合辟,还是变化,都能使整体呈现出清晰细密的状态,最终达到“细肌密理”的效果。
。法之穷形尽变者,“立乎其节目,立乎其肌理界缝”也。“节目”,即指句子、章节等单位之间,“肌理”也就是“界缝”,还包括用字、用韵、平仄的变化所呈现的状态。每一法则又根据自身所处的位置——或为长篇,或为联章,或为首尾——而不尽一致,杜甫诗法不一,每随之变,此所谓“穷形尽变”者也,是为“活法”。但这里始终有一个原则,那就是“其前后接筍、乘承转换、开合正变”,即如何使诗的各个因素在即离间找到最佳的位置。无论是合辟,还是变化,都能使整体呈现出清晰细密的状态,最终达到“细肌密理”的效果。
在《石洲诗话》卷十中,翁方纲针对渔洋“古诗要辨音节,音节须响,万不可入律句,且不可说尽,像书札语”的言论,作出这样的评价:
谨按,古诗音节岂一端而已?姑勿论初唐四子体、张、王、元、白诸体不能,概以“不可用律句”绳之,即以杜、韩古体,其中险峻劲放之极,更必以谐和似律之句间插其间,所谓筋摇脉转处,正未可尽屏去以律之句也。此自在善于酌剂,岂得泥执曰“万不可入律句乎”?
此视其篇内上下音节相承,有必不可用谐句者,亦有其势不得不用谐句者,非可一概论也。尝见渔洋评杜诗《醉时引》末句云“生前相遇且衔杯”,批云“结似律,甚不健”。殊不知此篇末一段“先生早赋归去来”以下三平之调,叠唱作收场。若不束以相谐之句,则鼓声叠拍、马逸不能止之势,将何以结束乎?此则必有平仄相谐之一联拍节而住,方见收场之妙,必无此处复用三平之句者也。先生误执,谓古诗必不可用律句,其弊遂至于误评杜诗。……总视全局上下衔接应如何耳。至若杜诗“东西南北更谁论,白首扁舟病独存”,以下一连七八句皆相谐似律句,而其气纵横雄肆,较之末三字皆平者,更加古健。是又须按拍细论者矣。总之,五言则对句之三四五字,七言则对句之五六七字,自必以纯用三平为正调,而亦视其上第四字(五言视其上第二字)之平仄如何,抑又视其通篇乘承变转之势如何,岂得盖以“不可入律句”一语概之?
对古诗声调的研究是王渔洋的重要诗学成果之一 ,他认为古诗当有其特定的声调系统,却不能将律诗之句法间入其中,这是根本原则。对于这一点,对古诗的声调也颇为关注的翁方纲是极不赞同的。
,他认为古诗当有其特定的声调系统,却不能将律诗之句法间入其中,这是根本原则。对于这一点,对古诗的声调也颇为关注的翁方纲是极不赞同的。
这里具体分析了杜甫的《醉时引》(按,《全唐诗》作《醉时歌》),歌末云:
先生早赋归去来,石田茅屋荒苍苔。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不须闻此意惨怆,生前相遇且衔杯。
渔洋批点此诗末句“结似律,甚不健”。而翁方纲以为,杜诗结处用似律之句,是诗势使然:“荒苍苔”、“俱尘埃”皆为三平之调,叠鼓之节一直往前,需要一似律之句止之,方可显出乘承之妙。古诗中若恰当地加以似律之句,更会增加劲放的效果,所举杜诗《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亦如此。
声调的和谐,也在“肌理”范畴中。“五言则对句之三四五字,七言则对句之五六七字,自必以纯用三平为正调”,是渔洋古诗声调论总结的规则。但翁方纲认为,此不能一概而论,须视整篇之势,特别是上句第四字(五言为第二字)的乘承转换之理,即深求于“气骨筋节”之间的“肌理”。他特别注重整体的效果,“总视全局,上下衔接应如何耳”。所谓“上下衔接”,就是关注“其通篇乘承变转之势”。“所谓筋摇脉转处正未可尽屏去以律之句”,这些似律之句,若是诗歌的筋摇脉转处,则关乎全篇的乘承衔接。律句用与不用,本不当由“古诗不可入律句”的规则限制。正是着眼于气骨筋节间的和谐,入律句于古诗,也未尝不可,甚至会成为必需的手段,“其势不得不用”。
从分析可以看出,“细肌密理”所达到的最终目的,是诗歌整体的和谐。于是,我们可以这样总结:翁方纲的“肌理”说是以杜诗为典范,着眼于诗歌的“气骨筋节”的“乘承伸缩”的整体观。
而“肌理”二字,正是从杜诗中拈出:
少陵曰“肌理细腻骨肉匀”,此盖系于骨与肉之间,而审乎人与天之合,微乎艰哉!
所谓系乎骨与肉之间,就是说,“肌理”的细密状态,可以使骨与肉匀称。那么,在解释“肌理”时,自然要理会骨与肉的状态。但并不是说,“肌理”就是骨与肉。它存乎骨肉间,表现在诗中,便是“大而始终条理,细而一字之虚实单双,一音之低昂尺黍”,种种形式特征。在解释杜诗的过程中体现的“肌理”说,是关注整体的。而杜诗在被赋予的整体意义中,扮演的正是“温柔敦厚”诗教典范的角色,这个角色的定位,与整体观的效果不谋而合。
作为一种诗学概念,当然不能只对某个诗人生效,否则也会坠入“泥格调者”的深渊。翁方纲将从杜诗中抽绎出来的“肌理”学说,扩大运用于整个诗歌史,使得“肌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诗学范畴。“肌理”“在诸家虽亦有之”,如前面提过的“肌理”隐于诗中的王维,又如豪放飘逸的李白,其诗中也包含着“顺逆乘承之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