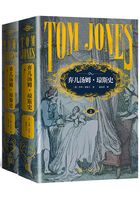
第四章
包括家庭历史中曾经记载的最大一场血战,或者毋宁说,最大一场交锋。
夫妇间有一种退让行动,为绝大多数做丈夫的所熟知;这种行动,像共济会 的暗号一样,对于任何人,凡是不属于那个深可敬重的社团的,都不能泄露;现在由于这种行动,再加上前一章所举出来的原因,派崔济太太深信不疑,她自己无缘无故就责怪了丈夫了,于是设法对丈夫施以恩爱,作为错怪丈夫的补偿。她的感情,不管向哪个方面发作,都一样地强烈;因为,她既然会不顾死活地盛怒,也同样会不顾死活地疼爱。
的暗号一样,对于任何人,凡是不属于那个深可敬重的社团的,都不能泄露;现在由于这种行动,再加上前一章所举出来的原因,派崔济太太深信不疑,她自己无缘无故就责怪了丈夫了,于是设法对丈夫施以恩爱,作为错怪丈夫的补偿。她的感情,不管向哪个方面发作,都一样地强烈;因为,她既然会不顾死活地盛怒,也同样会不顾死活地疼爱。
但是虽然这两种感情平常总是交替而发,而且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塾师很少不是在某种程度上作这两种感情同样发泄的对象;但是,在出乎寻常的场合,如果怒气发作得特别大,那平息的时间通常也比较长;现在这一次就是这样。因为,那一阵醋劲过去了以后,她那柔顺的态度保持得那样久,远过于她丈夫一向所经验的;并且,如果不是因为所有赞随批的信徒每天都必得作一些小小活动 ,那派崔济先生就可以有好几个月的工夫,都过一种绝对清静的日子了。
,那派崔济先生就可以有好几个月的工夫,都过一种绝对清静的日子了。
有经验的航海家永远担心,认为海上绝对风平浪静,就是暴风雨要来的先兆。我也认识一些人,他们平常都不笃诚迷信那一套,也往往担心,认为出乎常情的安宁或者平静,总要有相反的情况伴随而来。因为这种缘故,所以古代的人,遇到这种场合,都向奈米西斯女神 上供献祭;因为他们认为,这位女神,老带着忌恨的眼光看人类的幸福,特别高兴使幸福破灭。
上供献祭;因为他们认为,这位女神,老带着忌恨的眼光看人类的幸福,特别高兴使幸福破灭。
既然我们远远不信任何这类异教女神,更远远不鼓励任何迷信的想法儿,所以我们愿意约翰·夫——先生 或者其他像他那样的思想家能振奋兴起,把命运忽然由好变坏的真正原因考察出来;因为这种现象见得太多了,我们就要进而举出一件事例来;本来我们的职分就是叙述事实,我们要把叙述事实发生的原因,付之于更有才能的人。
或者其他像他那样的思想家能振奋兴起,把命运忽然由好变坏的真正原因考察出来;因为这种现象见得太多了,我们就要进而举出一件事例来;本来我们的职分就是叙述事实,我们要把叙述事实发生的原因,付之于更有才能的人。
人类永远对于知道别人的行为、畅谈别人的行为,感到极大的快乐。因此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国家,都曾有过某一些地方,专为公共聚会的场所,在这种场所,好奇的人,可以碰头,可以互相满足彼此的好奇心。在这种场所之中,剃须匠的铺子丝毫无愧,占有显著重要的地位。在希腊人中,剃须匠的新闻一语成为谚语,贺拉斯在他的《诗札》之一 里也用过同样的态度,盛夸罗马的剃须匠。
里也用过同样的态度,盛夸罗马的剃须匠。
英国的剃须匠 ,大家都知道,一点儿也不弱于他们的希腊和罗马前辈。你在剃须匠的铺子里,可以听到他们讨论外国事务,其盛况也不下于他们咖啡馆里
,大家都知道,一点儿也不弱于他们的希腊和罗马前辈。你在剃须匠的铺子里,可以听到他们讨论外国事务,其盛况也不下于他们咖啡馆里 的议论。至于谈论国内事务,则在剃须匠的铺子里,比在咖啡馆里,更是放言高论、海阔天空。不过这类地方,只有男性可以涉足。现在,这个国家的妇女,特别是下层阶级的妇女,既然比起其他国家的妇女来,更好群集、聚会,那么,如果她们没有一种地方,同样专为她们满足好奇之心而存在,那我们这个社会组织,就得说大有缺陷,因为她们的好奇心,绝不下于人类中的那一半。
的议论。至于谈论国内事务,则在剃须匠的铺子里,比在咖啡馆里,更是放言高论、海阔天空。不过这类地方,只有男性可以涉足。现在,这个国家的妇女,特别是下层阶级的妇女,既然比起其他国家的妇女来,更好群集、聚会,那么,如果她们没有一种地方,同样专为她们满足好奇之心而存在,那我们这个社会组织,就得说大有缺陷,因为她们的好奇心,绝不下于人类中的那一半。
因此,在享受这种聚会的地方这一方面,不列颠的女性,应该自庆,比起她们的外国姊妹来,更为幸福;因为我记不起来,在历史里读过,或者在旅行中看过,任何同样的情况。
这种地方,并非别的,就是日用杂货铺 。人人都知道这是英国每一个教区上一切新闻的中心点,或者,像鄙俗的说法儿,所有嚼舌的中心点。
。人人都知道这是英国每一个教区上一切新闻的中心点,或者,像鄙俗的说法儿,所有嚼舌的中心点。
派崔济太太有一天参加这种妇女聚会的时候,她的一个邻居问她,新近听到珍妮·琼斯什么消息没有?她说没有。于是她的邻居就微笑着说,区上真得好好感谢派崔济太太,因为她下了珍妮的工。
派崔济太太,像读者所熟知的那样,醋劲早已治好了,她又没有别的方面可以和她那个女仆发生冲突的地方,所以就昂然翘首地说,她不明白,区上怎么会因为那个,对她有任何应该感激的,因为她相信,珍妮走后,很难找到和她一样的女仆。
“不错,一点儿不错,找不出来,”那个好嚼舌的妇人说,“固然不错,我觉得区上不要脸的女人已经够多的了,但是我还是但愿别再找到她那样的。你刚才那么一说,那好像你没听说,她新近养活了一对小杂种儿了?不过,他们既然并不是在这儿生的,我丈夫跟另一个监视员 说,咱们没有养活他们的义务。”
说,咱们没有养活他们的义务。”
“一对小杂种儿!”派崔济太太连忙回答说,“这可真叫人想不到!我不知道咱们是不是该养活他们;但是我可管保,他们得算这儿的人,因为那丫头离开这儿还不到九个月。”
无论什么,都没有心理的活动那样迅速,那样突兀,特别是希望,或者恐惧,或者嫉妒(对于嫉妒,希望和恐惧只能算是打零工的),把它发动起来的时候。她马上就想起来,珍妮给她当女仆的时候,几乎从来都没离开过她那个家。于是她丈夫怎样斜靠在椅子上,珍妮怎样一惊而起,怎样说拉丁文,怎样微笑,还有许多别的情况,都一齐涌上了她的心头。她丈夫对珍妮离去表示高兴,现在看来,好像只是假模假式,但是同时,却又不错,千真万确高兴,那是由于饱餐大嚼,反胃酸心,还有一百样别的恶劣原因(都切实证明,她的醋劲,绝非事出无因)。总而言之,她对她丈夫的罪过深信不疑,马上慌乱骚动,沸腾汹涌,离开那一群人。
毛滑色润的家猫,虽然在它的族类中属于年纪最轻的一支,但是它的凶猛劲儿,比起它的族中各长支来,却一点儿也没退化,并且虽然不及兽王老虎躯伟力大,凶猛劲头却与之相等。它捉到一个小小的小耗子,逗着玩儿,把它折磨了一大阵之后,这个小耗子忽然一时逃出了它的爪子,它就又怒又恼,又急又躁,又吱吱地咒,又嘟嘟地骂。但是把小耗子在后面躲藏的小箱子或者大箱子一下挪开,它就像闪电一样,一下扑到小耗子身上,并且用最狠毒的怒气,又撕又咬,又抓又挠,又呜呜地叫,把那个小小的动物大卸八块。
现在派崔济太太就用同样的凶猛劲儿,一下朝着可怜的塾师扑去。她的舌头,她的牙齿,她的两手,往他身上一齐施展起来。他的假发 一下就从他头上揪了下来,他的衬衫一下就从他背上撕了下去,他脸上一下就五道血河直流;这只表示,天公不幸,把敌人武装起来的爪子是五个。
一下就从他头上揪了下来,他的衬衫一下就从他背上撕了下去,他脸上一下就五道血河直流;这只表示,天公不幸,把敌人武装起来的爪子是五个。
派崔济先生有一阵儿仅仅采取守势;说实在的,他只用手努力护着他的脸就完了;但是他看到他的敌人怒气仍旧没有稍有平息之意,他就想,他至少可以想法儿把她的武装解除,或者说,想法儿把她的胳膊抓住,叫她不得施展。这样一来,在争夺中,她的便帽从头上掉下来了,她的头发,因为太短了,垂不到肩上,就在头上直耸起来了;她的紧身衣,本来就凭穿过下部一个窟窿眼儿系在腰上,现在撑开了;她那两个奶头子,比头发可就多余得多,也耷拉到腰下了;她脸上溅上了她丈夫的血;她恨得把牙直咬;她的眼睛就冒火星儿,好像从铁匠炉里冒出来的一样。所以,总的看来,这位爱末怎 的女英雄,连比派崔济先生勇敢得多的人都要害怕。
的女英雄,连比派崔济先生勇敢得多的人都要害怕。
到后来,他很侥幸,到底抓住了她的胳膊了,因而她指头梢儿上装备的武器就失去效用了;她一见这样,她那种女性所有的柔弱之性,就立刻战怒气而胜之,她一下就哭得泪人一般,跟着又一下子就来了一阵晕厥。
在这一场暴怒中(到底为什么发作这场暴怒,派崔济先生直到这会儿,还完全蒙在鼓里),派崔济先生顶到现在,还一直保存了一点儿清醒的头脑;但是他一见太太晕过去了,那点儿清醒的头脑,完全离他而去。他马上跑到街上,大声吆喝着说,他太太和死挣命哪,他求告他的邻居得万分火急,快快来帮忙。有几位心眼儿好的女人,听他这一喊,都应声而至。她们来到他家,把治这种毛病的方法使用了,于是派崔济太太到底苏醒过来了,她丈夫一见,不觉大喜。
她的精神刚恢复了一点点儿,甜药酒 刚一使她的心情稳定下来,她就开始对那些人说起她在她丈夫手里都受到什么伤害;她说,他在枕席上使她受到伤害还不满意,还因为她对那个稍一抗议,就用人想得出来最残酷的方法虐待她,把她的帽子从头上抓掉了,把她的头发从头上拔掉了,把她的紧身衣从身上剥掉了,同时,还打了她好些下,打的伤痕,她得一直带到坟墓里去。
刚一使她的心情稳定下来,她就开始对那些人说起她在她丈夫手里都受到什么伤害;她说,他在枕席上使她受到伤害还不满意,还因为她对那个稍一抗议,就用人想得出来最残酷的方法虐待她,把她的帽子从头上抓掉了,把她的头发从头上拔掉了,把她的紧身衣从身上剥掉了,同时,还打了她好些下,打的伤痕,她得一直带到坟墓里去。
那位可怜的塾师,脸上带着他的太太愤怒之下给他的累累伤痕,都分明可见,听到这套控诉之词,只惊得口呆目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番控诉,我相信,读者都会作见证,远非事实;因为,他实在连一下都没打过她。但是他这样一言不发,却被“法院”全体解释为他对控诉承认,因此她们马上开始异口同声地训他、骂他,而且还常重念这句话,说除了床头上的汉子,别的人就没有打老婆的。
派崔济先生对于这一切,全都耐心忍受;但是他太太一指她脸上的血,作控诉他对她残暴的证据,他却忍不住了,不能不说那是他自己的血,因为一点儿不错,那是他自己的血嘛。本来,他自己的血会冒出而为自己复仇(像有人告诉我们,说被人谋害的人那样 ),他认为那太不合情理了。
),他认为那太不合情理了。
对于这一点,那些妇女没作别的回答,只说,可惜的是,那只是从他脸上流下来的,而不是从他心里流出来的;所有的妇人全都喊道,要是她们的丈夫敢动手碰她们一下,那她们非叫他们心里的血流得满身都是不可。
这一帮人对派崔济先生的以往,大大训诫了一番,对于他的将来,又好好地劝导了一回,然后到底都走了;只剩下夫妻二人单独交谈,在这番交谈中,派崔济先生才慢慢地明白了他这场大难的来龙去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