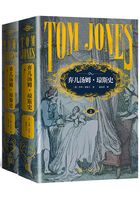
第九章
从寡妇的哭泣中,证明前章所说的方子万无一失;兼及随着死亡而来的附丽之物,如医生等等;还有一份不违通例的碑铭。
奥维资先生、他妹妹,还有另一位女士,都按照平常固定的时间,聚在晚餐餐厅里。他们在那儿等了比通常还久的时间以后,奥维资先生说,他对上尉迟迟不来,有点不放心起来(因为吃饭的时候,他永远是头一个按时而到)。他吩咐底下人,叫他们在屋子外面摇铃儿,特别朝着上尉常去散步那方面摇。
所有这种召唤他的办法都无济于事(因为上尉那天晚上,事出偶然,情离寻常,到一个新地方散步去了),于是卜利福太太说,她真提心吊胆地害起怕来。另外那位女士,本是她最亲密的好友之一,深知她对她丈夫的真正感情,就尽力安慰卜利福太太;她对卜利福太太说,说实在的,她也不能不担心,不过她还是得往最好的地方去想。她说,也许是今天晚上天气特别好,所以上尉才信步走去,比平常日子走得远了,再不,他也许到邻居家去,绊住了脚了。但是卜利福太太却说,不会是那样;她敢说,一定是出了岔儿了;本来他在外面待得稍微一久,从来就没有不往家里送个信儿回来的时候,因为他一定知道,她要怎么担心的。那另一位女士,没有别的话可说,就用通常遇到有这种情况的时候说的话求告她,叫她不要自己吓唬自己,因为那于她自己的健康,也许会有很不良的影响;同时,她倒出一大杯葡萄酒来,劝卜利福太太喝,卜利福太太起先不喝,后来到底给说服了,她才喝了。
奥维资先生现在回了小客厅了;因为他自己曾亲自去找上尉来着。他脸上的气色,足以把他担心的情况表现出来,说实在的,他都因为担心而不大能说出话来了;但是既然悲哀在不同的人身上有不同的表现,所以同样担心,使奥维资先生把声音压下,却使卜利福太太把声音提高。她现在大声哭着叙说起她的命好苦来,并且跟着悲痛而来的是如泉涌出的眼泪;那另一位女士,她的好友就说,她不能说卜利福太太不应该哭,但是却劝她不要由着性儿哭,说了一些富于哲理的话,把人类每天都得受的种种苦难列举出来,想以此减轻她朋友的悲哀。她说,这类苦难,让我们想起来,足以使我们能坚忍不拔地抵抗任何意外,不管这种意外来势有多凶猛,有多可怕。她说,卜利福太太的哥哥足以做她的榜样,教她学着忍耐;固然确实不能认为,他能像她那样关心,但是,却毫无疑问,他也很难过,不过他能老老实实委命于上帝的意志,所以能把悲痛限制在应有的范围内。
“你不要提我哥哥啦,”卜利福太太说,“只有我自己才是你怜悯的对象。在这种场合里,一个朋友的关心,怎么能和一个太太的悲痛相提并论哪?哦,他这个人是完了!一定有人把他谋害了——我是永远也看不见他了!”说到这儿,她泪如泉涌,大哭起来;一阵痛哭之后,随之而来的是默不出声,就和奥维资先生忍痛不发,默不出声一样。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仆人上气不接下气,跑着进了屋里,同时嘴里喊道,找到上尉了;跟着,还没等到他说别的话,另外两个仆人进来了,抬着上尉的尸体。
于是好奇的读者,可以看到,在另一种不同的情况下,悲哀发作了;因为,在这以前,奥维资先生默不作声,而他妹妹则由于同样的原因,放声大号;现在见了这种光景,则是奥维资先生潸然出涕,而他妹妹止住了哭声;因为她先猛然尖声一叫,跟着一下子晕过去了。
这时候屋子里都是仆人,其中有几个,和那位来客一块儿,赶紧照顾救护那位太太;别的仆人,就和奥维资先生一块儿,把上尉抬到一张暖和的床上,在那儿用一切办法,企图使上尉缓醒过来。
假使我们能告诉读者,说这两个失去知觉的人,都同样成功地掇弄过来了,那我们当然很高兴;但是事实却不然,因为虽然搭救太太那批人非常成功,由于她晕过去刚好不长不短的工夫,又缓醒过来了,大家没有不大大地高兴的;但是对那位上尉,却不论什么办法,像放血、搓身子、闻药等等,都毫无效验。死神,那位丝毫不讲情面的法官,已经对他宣布判决了,而且拒绝缓刑,虽然两位大夫,同时并到,并且马上就在同时同地收了酬金,做他的辩护士,也全无济于事。
至于这两位大夫,我们为了避免有人含沙射影,所以不提名道姓,只叫他们一个是甲大夫,一个是乙大夫,以示区别。他们二位,都试了上尉的脉搏,一位试左手,一位试右手,他们二位都一齐宣布他已经完全断了气儿了;但是得的是什么病死的,或者因为什么死的,他们却意见不同;甲大夫说是猝然中风,乙大夫就说是犯了癫痫。
因此这两位医道精湛的大夫,就争论起来。在争论中间,各人把自己所持那种意见的理由,大大发挥了一通。他们的理由,同样非常充分,足可肯定各自的思想感情而有余,但对于敌方却丝毫不发生影响。
实在说起来,每一位医生,对于疾病,都有专好,他把一切战人类天性而败之的胜利,都归之于他所专好的疾病。痛风、风湿、结石、尿砂、结核,在医学界中,都各有它们的赏识者;而神经炎,或者说精质炎 ,更有人赏识,没有别的可和它相比。医学学术界里最有学问的医生中间,有时对于病人致死的原因,会发生不同的意见,其所以那样,可以用这里所说的这种情况解释。这也是外界不明白我们刚才所说的那种情况,每每引为大可诧异的。
,更有人赏识,没有别的可和它相比。医学学术界里最有学问的医生中间,有时对于病人致死的原因,会发生不同的意见,其所以那样,可以用这里所说的这种情况解释。这也是外界不明白我们刚才所说的那种情况,每每引为大可诧异的。
读者诸公也许会觉得奇怪,那两位学识渊博的大夫,为什么不致力于病人的恢复,却马上辩论起死亡的原因来。这实在是因为,所有使病人复活的办法,在他们来之前,就早已都试过了。本来上尉已经放到暖和的床上了,他的静脉已经割开了,他的前额已经按摩过了,所有一切烈性闻药也都已经在他的嘴唇上或鼻孔上用过了。
大夫们一看,他们所要用的方法,已经先发制人,都用过了,可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才能待到通常应该待的时间,不失体面地拿人家的诊费,因此才不得不无话找话,以供谈资。那么除了谈致死的病因而外,还有其他更合适的话题吗?
我们这两位大夫刚要起驾离去,这时候,奥维资先生已经不指望上尉还能缓醒而把一切委之于天了,就问起他妹妹的情况来,同时希望他们离开以前,给她也瞧一瞧。
这位女士现在已经从晕厥中缓醒过来了,并且按照普通的说法,好到在她这种情况下也只能指望她能好到的程度了 。这两位大夫于是因为这是一个新病人,先尽到了一切初步的礼数,就按照主人之意,来到病榻之前,像刚才他们对那个死尸那样,每人抓过一只手来。
。这两位大夫于是因为这是一个新病人,先尽到了一切初步的礼数,就按照主人之意,来到病榻之前,像刚才他们对那个死尸那样,每人抓过一只手来。
这位女士的病情和她丈夫的正立于相对的极端:因为,他是任何医疗都帮不上忙的了,而她却实在不需要任何医疗帮忙。
世界上没有任何再不公平的事了,那就是,世俗之见,把医生糟蹋得不成样子,说医生都是死亡的朋友。 我是相信反面的意见的;因为,如果把经医疗而好起来了的人和因受医疗而作了牺牲的人比一下,那恐怕还是前者在人数上比后者多一点儿。不但这样,有的医生在这方面特别小心,他们为了避免可能害死病人,竟不使用任何医疗方法,并且除了叫病人服了也不会好也不会坏的药以外,决不开任何别的方子。我曾听到这样的医生,郑重其事地对我说过一句格言:须让自然得行其道,
我是相信反面的意见的;因为,如果把经医疗而好起来了的人和因受医疗而作了牺牲的人比一下,那恐怕还是前者在人数上比后者多一点儿。不但这样,有的医生在这方面特别小心,他们为了避免可能害死病人,竟不使用任何医疗方法,并且除了叫病人服了也不会好也不会坏的药以外,决不开任何别的方子。我曾听到这样的医生,郑重其事地对我说过一句格言:须让自然得行其道, 而医生只站在一旁,如果自然所行之道成功,拍她的后背,以示鼓励。
而医生只站在一旁,如果自然所行之道成功,拍她的后背,以示鼓励。
我们这两位大夫,对于死亡,并不怎么喜爱,所以他们要了一份诊费,就再不管那具尸体了;但是他们对于还活着的这个病人,却不那么厌恶;对于她的病情,他们马上就表示相同的意见,跟着忙忙碌碌地开起方子来。
既然这位女士开始的时候,说服了大夫,叫他们相信她有病,那么,是不是大夫随后依次而来,又说服了她,叫她自己相信她有病呢,我不想断言;但是她却有一整月的工夫,老不离病人应有的一切事物。在这个期间,她老有大夫诊视,老有护士看护,老有熟人传话,问候她的身体情况。
后来抱病应有和过分悲哀的适度时间,终于完结了,大夫都谢绝了,女士自己也开始接待亲友了。她跟从前的情况唯一的不同之处,只是她身上穿的衣服,是表示哀悼悲戚的颜色,脸上显出来的表情,是表示哀悼悲戚的神色。
上尉现在已经入土安葬了,并且也许往被人遗忘的路上走了老远了,幸而奥维资先生,不忘友情,给他刻了后面这个墓志铭,才保持了他身后的遗念。写这个墓志铭的人,不但才气横溢,还是正直不阿,而且完全深知上尉的为人,上面写道:
约翰·卜利福上尉
瘗骨于此,
静候欢乐复生之来临 。
。
伦敦
有荣为彼出生之地,
牛津
有幸为彼受教育之所。
其人之才能
为军旅之光,为国家之荣,
其人之平生
为宗教生辉,为人性增耀。
其为子则孝,
其为夫则爱,
其为父则慈,
其为弟则悌,
其为友则忠,
其为基督徒则诚,
其为人则贤。
其悲伤不已之遗孀
谨立此石,
以彰其人之懿德,
并志其未亡人之哀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