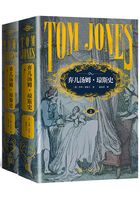
第十四章
医生之来,他动的手术,兼及苏菲娅和她的女仆之间的长篇大论。
他们来到威斯屯先生的厅堂上了,苏菲娅本来就很费力地身子摇晃、脚步不稳,现在一下瘫在椅子上;不过,借助于鹿角精和凉水 ,幸而免于晕去,而且精神相当恢复了;这时候,请来医治琼斯的医生到临。威斯屯先生认为他女儿这些征候,都是由于坠马而起,叫她马上放血,
,幸而免于晕去,而且精神相当恢复了;这时候,请来医治琼斯的医生到临。威斯屯先生认为他女儿这些征候,都是由于坠马而起,叫她马上放血, 以为预防。医生对他这种意见,立即附议,他还举出许多理由来,说怎样应该放血,并且援引了许多病例,说怎样因为病人没放血而出了事故,因此那位绅士更是坚决,实在是说一不二,非要他女儿放血不可。
以为预防。医生对他这种意见,立即附议,他还举出许多理由来,说怎样应该放血,并且援引了许多病例,说怎样因为病人没放血而出了事故,因此那位绅士更是坚决,实在是说一不二,非要他女儿放血不可。
苏菲娅一会儿就服从了她父亲的命令,虽然她出于本心,并不情愿;因为,我相信,她以为她吃那一惊,并不像她父亲和医生认为的有那样严重。她于是把她那圆润光滑的胳膊伸了出来,动手术的人就作动手术的准备。
仆人忙忙碌碌预备器物的时候,那位医生误认她趑趄不前,是由于害怕,就开始安慰她,对她担保,说一点儿危险也没有;因为,他说,放血本身,绝不会出错儿,除非那种卖假药的,完全愚昧无知,滥竽充数。他明显地示意,现在绝不用害怕有那种情况。苏菲娅说,她一点儿也不害怕,并且说:“即便你把我的动脉拉开了,我都答应你,也决不责备你。”“他妈的,真的吗!”威斯屯先生说,“我才不哪。他要是伤了你一丁点儿地方,那我不叫他心里的血往外淌,就不是人养的。”医生答应了就在这样的条件下,给她放血,跟着就动起手来。他像他答应的那样,做得灵敏轻巧,快当麻利,因为他只从她身上取出一丁点儿血来。他说,一会儿取一点,比一下取出好些,妥当得多。
苏菲娅把胳膊绑好了以后,回到自己的屋子去了,因为她不愿意(严格说起来,也不成体统)看着琼斯动手术。实际上,原先她所以反对放血(虽然她没明说出来),就是由于她怕耽误了琼斯接骨的医疗。本来,威斯屯先生只要一下子关心起苏菲娅来,那就除了她,别的事儿一概全顾不得理会;而琼斯自己呢,就坐在那儿,像“纪念碑上的忍耐之神,含笑看着悲伤” 。说实在的,他看到鲜血从可爱的苏菲娅那只白嫩柔润的胳膊上流出来的时候,几乎忘了他自己受伤的痛苦了。
。说实在的,他看到鲜血从可爱的苏菲娅那只白嫩柔润的胳膊上流出来的时候,几乎忘了他自己受伤的痛苦了。
医生于是叫受伤的人把上衣脱下来,只留下衬衫,跟着把胳膊完全露出来;他先把胳膊抻直了,检查起来,检查的时候,把琼斯疼得有几回直龇牙咧嘴。医生见他这样,觉得大为奇怪,问他,“怎么回事?我敢保,我不会弄得叫你疼的。”于是他把着那只折了的胳膊,引经据典,大讲特讲起解剖学来。在这番讲解中,他把单骨折和双骨折,顶精确地说明了一番;把琼斯的骨折可能有的几种情况,又研究了一气;又说,有多少情况,可以比现在这个骨折好,又有多少,可以比它坏。
后来他到底结束了他这番费时耗力的讲演。这番讲演,虽然使听者注意、羡慕,但是却并没得到多少益处,因为所有他说的,他们连半个字都没听懂。讲完了,于是他才认真动起手术来,这一动,却很快就完结了,比开始的时候快得多。
于是医生吩咐琼斯,叫他卧床静养;因为威斯屯先生死乞白赖,非要琼斯在他家里养病不可,于是琼斯就在他家里住下。跟着医生下了判决书,只许琼斯喝水冲麦片粥充饥。
在厅堂里,看着接骨的那一伙人里,就有昂纳阿姨。接骨的手术刚完,她小姐就把她叫到屋里,问她那个年轻绅士的经过怎样。于是她马上信口开河,夸起那个青年的行为怎么高尚风雅(不过在她嘴里说成烤烧风鸭了)。“那个样儿,在一个长得秀气的小伙儿身上,叫人看着,真叫迷人。”跟着她大大发了一通热烈的谄谀之词,夸他这个人生得多美;把好多的细处都数到了;最后说,他的肤色有多白皙。
这一番话大有影响,使苏菲娅的脸为之变色。这种情况,也许不会逃过那个老于世故的女侍的眼光,如果在她说话这整个时间里,她曾有过一次往她小姐脸上看的话;但是却有一面镜子,高低上下,恰好正对着她挂着;这面镜子给了她看那副面目的机会,而她也最喜欢看那副面目;所以在她说这番话的整个时间里,她的眼光,就一时一刻都没离开那副可爱的面目。
昂纳阿姨专心一意,舌弄笙簧,谈这个题目;目不转睛,眼神若定,看镜中倩影;把她所有的心思,都整个叫这种情况占去了而无暇他顾;所以给了她小姐时间,把缭乱的心曲,镇静平定下来。镇定下来以后,她朝着女仆微微笑着说:“一点儿不错,你是爱上了这个青年了。”“我爱上了他,小姐!哎哟哟,我的小姐,我敢说一定,小姐,我拿灵魂起誓,小姐,一点儿不错,小姐,这可是没影儿的事。”“哟,要是你真爱上了他,”她的小姐说,“我看不出来,那有什么可害臊的!因为他果真当然,是一个漂亮的青年嘛。”“不错,小姐,”那另一位答道,“他真是我这一辈子里看见过的一个顶呱呱、响当当、标标致致、漂漂亮亮的人儿。不错,一点儿也不错,他漂亮。再说,我不说瞎话,像小姐您说的那样,要是我爱上了他,我真不知道我有什么可害臊的,虽然他比我身份高。我不说瞎话,绅士和我们当下人的,还不是一样,都是爹生娘养的。再说,琼斯先生,斯(虽)然因为有乡绅奥维资先生,把他架弄得成了个绅士,可是要说起出身来,他还没有我高哪。因为我穷归穷,可是一个好人家的女儿,我爸爸和我妈妈,都一点儿也不含糊,是像模像样地结了婚的 。有的人尽管把头高抬着,可不敢说这种话。伊啊咳!呀呼咳!咳!咳!伊呼呀呼咳!
。有的人尽管把头高抬着,可不敢说这种话。伊啊咳!呀呼咳!咳!咳!伊呼呀呼咳! 我敢说一定,我的傻乖乖,他的肉皮儿斯(虽)然那么又细又白,我不说瞎话,他是所有的人里面肉皮儿顶细顶白的;可我也和他一样地是正经八百的,没人能说我出身下作。我爷爷是当牧师的
我敢说一定,我的傻乖乖,他的肉皮儿斯(虽)然那么又细又白,我不说瞎话,他是所有的人里面肉皮儿顶细顶白的;可我也和他一样地是正经八百的,没人能说我出身下作。我爷爷是当牧师的 ;我确实知道,他要是想到他家里的人,有捡媢丽·西格锐姆吃剩下的残羹剩饭、馊了臭了的东西,他不火冒三丈才怪哪。”
;我确实知道,他要是想到他家里的人,有捡媢丽·西格锐姆吃剩下的残羹剩饭、馊了臭了的东西,他不火冒三丈才怪哪。”
也许苏菲娅因为缺乏足够的精神,所以才让她的侍女滔滔不绝地这样说个没完没了(读者可以猜想出来,叫她闭口,并不是件容易事);因为她说的话里,有好些地方,她的小姐听起来,不见得很受用。但是,原先好像是没有完的泉水,汩汩不绝,现在受到她小姐的阻拦,却遇到了壅塞。“我不懂得,你怎么能这样不知轻重地谈论我爸爸的朋友。说到那个丫头,我吩咐你,永远也不许在我面前提名道姓地说她。至于那位年轻绅士的出身,那般对他没有别的坏话可说的人,顶好不要在那上面做文章。这是我希望你以后也要照办的。”
“真对不起,招您生气,”昂纳阿姨说,“我一点儿也不撒谎,我也跟小姐您一样,就是讨厌媢丽·西格锐姆那个丫头。至于说寒碜琼斯少爷,那我敢教咱们宅里所有的用人都给我当见证人,每次遇到有谈起私生子的话来,我就没有不向着琼斯少爷的。我对那些家人说过,要是你们是私生子,可能有人教你们变成了绅士,那你们有谁不愿意当私生子?再说,我也说过,我敢保,他是一个很神气的绅士,全世界的人,都没有他那么白的手;因为我一点儿也不撒谎,是那样。我还说过,他是全世界上脾气顶和气、顶和气、顶和气,性格顶温柔、顶温柔、顶温柔的人。我还说过,所有的底下人和所有这一带的街坊,没有不喜欢他的。再说,我一点儿也不撒谎,我还能告诉小姐您一档子新鲜事儿哪;不过我恐怕,您听了要嗔着我多嘴的。”“你能有什么事儿告诉我,昂纳?”苏菲娅说。“那也没有什么,小姐,我一点儿也不撒谎,他那也并没有什么用意,因此我也就不必白白惹小姐你嗔着我多嘴多舌的啦。”“你告诉告诉我好啦,”苏菲娅说。“我马上就想知道知道。”“就是这么回事,小姐,”昂纳阿姨说,“上星期有一天,我正在屋里干活儿,小姐您的手笼就放在一把椅子上;我一点儿也不撒谎,他把手伸到那副手笼里,就是小姐您昨儿刚刚给我的那副手笼。‘哎呀!’我说,‘琼斯少爷,你这样一来,可就要把手笼撑大了,那可就用不得了。’可他仍旧把手伸在手笼里面,还亲了它一下——我一点儿也不撒谎,我这一辈子简直从来也没见他亲那副手笼那个样儿。”“我想他不知道那是我的手笼吧?”苏菲娅说。“小姐您先别忙,一会儿就知道啦。他把那副手笼亲了又亲,亲了又亲,嘴里还说,那是世界上再也没有那么漂亮的手笼了。我就说啦,‘哟,我的少爷,这副手笼您见过不止一百回了。’‘不错,昂纳阿姨,’他喊着说,‘不过,有你家小姐在跟前,那除了她,就不管有别的什么,谁还能说那个美哪?’还有哪,我的话还差得远,还没完哪。不过我只指望,小姐您可别嗔着我多嘴多舌才好,因为我一点儿不撒谎,他并没有什么用意。有一天,小姐您正对着老爷弹拨弦钢琴,琼斯少爷刚好在隔壁屋里,我觉得,他当时好像愁眉苦脸的样子。‘哟,’我说,‘琼斯少爷,怎么回事啊?想什么哪?您告诉告诉我,我就给个钢镚儿。’‘啊,你这个丫头!’他说,好像一惊,刚从梦里醒过来一样。‘你那位天使小姐弹琴的时候,我还能想别的什么?’跟着他把我的手使劲一捏,说,‘唉,昂纳阿姨啊,’他说,‘那个人有多幸福啊!’——跟着他叹了一口气。我说实话,他喘的气就跟花球一样地香——不过,话又说回来啦,他一点儿用意都没有。我只指望小姐您对这话,一个字也别露才好;因为他给了我一个克朗,叫我对着一本书起誓,永远不要说出去。不过我相信,一点儿也不错,那本书并不是《圣经》。”
苏菲娅听了这番话以后,她脸上的颜色是什么,不等到我找到比朱砂更美的颜色,我是说不出来的。
“昂——纳,”她说,“我——如果你不再对我说这番话——也不对任何别人说,那我就不会出卖你——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见你的怪;不过,我恐怕你那个嘴老闭不严。我说,你这个丫头,你怎么就是管不住你那张嘴,老这么信口开河哪?”“并不是这样,小姐,”她回答说,“我一点儿也不撒谎,我豁着把舌头拉掉了,也不敢惹小姐您生气呀。我一点儿也不撒谎,只要小姐您不教我说,那我就半个字都不说——”“那样的话,我不要你再提刚才这番话啦,”苏菲娅说,“因为这个话也许会传到我爸爸的耳朵里,他知道了,要生琼斯先生的气的。尽管我相信,他,像你说的那样,并没有什么用意。我自己也要生气的,如果我认为——”“哟,小姐哟,”昂纳阿姨说,“我一点儿也不含糊地说,我相信,他并没有什么用意。我觉得,他说这番话的时候,好像把魂儿丢了似的。不错,他说,他相信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好像一颗心都没有着落似的。我说,‘唉,少爷,不错,我也觉得你好像一颗心没有着落似的’。‘不错,昂纳,’他说,‘不过我得请小姐您原谅我;我这个舌头要是惹您生气,那我把它拉掉了好啦。’”“说吧,不要紧,”苏菲娅说,“你以前对我没说过的话,还可以说。”“‘不错,昂纳,’他说(这是以后过了一些时候,他给我克朗那一次),‘我也不是那种花花公子,也不是那种浑头浑脑的浑蛋,所以我只有拿她当我的天神对待,才能感到快乐。我只要会喘气儿的时候,我就要永远当天神崇拜她,当天神供奉她。’我敢起咒赌誓地说,小姐,我记得的一点儿也不差,他对我说的就是这么些。我听了他那番话,本来要发作的,可后来一看,他并没有什么用意,我才忍住了那口气。”“一点儿也不错,”苏菲娅说,“我相信,你对我真有感情。前几天,我说要下你的工,那时候,那是真把我惹急了。不过你要是不愿意走,仍旧愿意待在这儿,那你就不要走了。”“我不说瞎话,小姐,”昂纳阿姨说,“我从来就没有想要离开小姐您的时候。我不说瞎话,您告诉我,说要下我的工那时候,我差一点儿没把眼都哭瞎了。我要是起意要离开小姐您,那就是我太忘恩负义了;因为,我说实话,我离了这儿,就永远也找不出和这儿一样的好地方来。我一点儿也不撒谎,我要和小姐您活也在一块儿,死也在一块儿。因为,像可怜的琼斯少爷说的那样,那个人是幸福的——”
说到这儿,吃正餐的铃声响了,把她的话头打断。这番话,对苏菲娅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因而使她现在越发感激她那天早晨的放血,这是原先放血的时候所没感觉到的。至于她现在是什么样的心情,那我要紧紧遵守贺拉斯的法规,不作描写,怕的是成功无望。 我这些读者中的绝大多数,都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出这种情况来。至于少数的几位猜不出来的,那这番描写,即便描写得很好,他们也不能懂得这幅图画,或者至少要认为我这幅图画并不自然。
我这些读者中的绝大多数,都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出这种情况来。至于少数的几位猜不出来的,那这番描写,即便描写得很好,他们也不能懂得这幅图画,或者至少要认为我这幅图画并不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