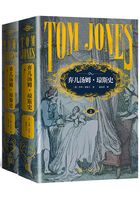
第一章
论文学中之庄与谐及论此点之目的。
在这部庞然巨制里,读者读起来较感索然无味的部分,也许莫过于作者写起来最费惨淡经营的章回。而我们置于本书叙事各卷之前的引言,大概都得算在这种章回之中。这种引言,我们坚决认为,是我们这种著作里必不可少的东西,我们所以在这方面自居首位,唯此而已。
至于为什么我们坚决认为必不可少,我们觉得,我们并没有绝对的责任,非得举出理由来不可;反正我们订了这样一条规则,让一切庄谐兼备的散文史诗,都严紧遵守,只此一说,也就算很可以的了,不必再多费唇舌。时间的一致性和地域的一致性,现在已经约定俗成,为韵文戏剧里必不可少的东西了 。但是谁曾问过,这种细致的规定,理由安在?一个剧本里,可以包括一天的时间,而不许包括两天
。但是谁曾问过,这种细致的规定,理由安在?一个剧本里,可以包括一天的时间,而不许包括两天 。但是为什么,也从来没有人向批评家问过。也没人问过,观众(比方他们能像选民一样,可以免费旅行)既能瞬息达到五里之处,为什么就不可以瞬息达到五十里之处?古代一位批评家,曾给戏剧限定一种范围,即每个剧本,不得多于五幕,也不得少于五幕
。但是为什么,也从来没有人向批评家问过。也没人问过,观众(比方他们能像选民一样,可以免费旅行)既能瞬息达到五里之处,为什么就不可以瞬息达到五十里之处?古代一位批评家,曾给戏剧限定一种范围,即每个剧本,不得多于五幕,也不得少于五幕 。从来是否有过注释家,把这种限制,透彻地解说明白?我们近代的戏剧批评家,一来就说戏剧下流
。从来是否有过注释家,把这种限制,透彻地解说明白?我们近代的戏剧批评家,一来就说戏剧下流 ,这两个字到底什么意思,是否有活人曾经试作解释?(就是用这两个字眼,他们才幸而把所有的幽默,一齐赶下了舞台,使舞台变得和客厅一样地死气沉沉
,这两个字到底什么意思,是否有活人曾经试作解释?(就是用这两个字眼,他们才幸而把所有的幽默,一齐赶下了舞台,使舞台变得和客厅一样地死气沉沉 !)在所有这种场合里,世上之人,好像把我们的法律里一句格言,即Cuicunque in Arte sua perito credendum est
!)在所有这种场合里,世上之人,好像把我们的法律里一句格言,即Cuicunque in Arte sua perito credendum est 这句话,紧抱死守;因为,丝毫没有根据,而就以权威自居,为文理各科学术订立法律,这样大胆狂妄的人,似乎难以令人想象。因此,我们才动辄认为,在这种场合里,如果深入下去,总要有其充足、正当的理由,只是不幸,我们见识浅薄,看不到其中的底蕴而已。
这句话,紧抱死守;因为,丝毫没有根据,而就以权威自居,为文理各科学术订立法律,这样大胆狂妄的人,似乎难以令人想象。因此,我们才动辄认为,在这种场合里,如果深入下去,总要有其充足、正当的理由,只是不幸,我们见识浅薄,看不到其中的底蕴而已。
但是,实在的情况是:世人对批评家奉承太过,认为他们有多渊博,把他们推崇得远过其实。批评家让这般顺情说好话的人一恭维,就放开胆量,独断独行,通行无阻。因而大权在握,怡然自信,给作家订起法则来,其实这些法则,本来都是由前人继承而来的。
如果以正确的眼光看待,批评家只不过是一些录事,他们的职责,只不过是把别人订的规章法则,传抄下来;订这些规章法则的,都是一些伟大的法官,由于才气卓越,才在各自统辖的学术领域内,取得了立法者的煊赫身份。古代的批评家,志在传抄这般法官所订的规章法则,如果没有法官的裁可判断,以为凭借,他们从来不敢自作主张,妄赞一词。
但是,既经时光流转,又历愚昧时期 ,于是录事乃渐渐篡其主人之权力,窃其主人之威仪。写作之法则,乃不以作家之实践为据,而变为以批评家之诰谕为准,抄录员变而为立法家;起初仅以传抄法令为事的胥吏,一变而为说一不二、发号施令的巨公。
,于是录事乃渐渐篡其主人之权力,窃其主人之威仪。写作之法则,乃不以作家之实践为据,而变为以批评家之诰谕为准,抄录员变而为立法家;起初仅以传抄法令为事的胥吏,一变而为说一不二、发号施令的巨公。
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种明显易见、并且也许得说不可避免的错误;因为这班批评家,既都才疏学浅,所以非常容易把仅为形式的外表,看作构成实质的内容。他们的作风,也和法官一样,一味死抠法典中毫无生气的成文,完全不顾法律里生动灵活的精神。一些琐碎情节,本来也许只是一个大作家毫未经意、而在作品里信手拈来的东西,却让这班批评家抓住了,看作是作家主要的优点,当作写作中必不可少的东西,传给后来的作家,叫他们奉为圭臬。时光和愚昧,本是欺骗蒙蔽的两大支柱,它们对攘窃篡夺,授予了权势威力;因而许多得怎样写才算妙文佳作的规章法则,就成了约定俗成的东西;其实这些规章法则,不论在事实上,也不论在自然中,都丝毫没有根据。它们一般也无其他作用,而只是用来束缚天才,限制天才。如果论舞蹈的鸿文名著,都订下一条必不可违的规则,说舞蹈的时候,脚上一定得戴着脚镣,那舞蹈师当然无从施展其技巧了。上述的规章法则,何以至此?
道理既是这样,那么,为了免得别人归咎于我们,说我们只依据“言必称夫子”那类的话注7(说实在的,我们对这种话,并不十二分尊重),就给后代订立法则,所以我们就不必再斤斤计较,前面所说的立法之权,究应属谁,而一直对读者说明,我们为什么在书里穿插了那些斜枝旁杈的短议简论。
注7言必称“夫子”那类的话:原文为拉丁文ipse dixit,拉丁文又出于希腊文 ,意为“他(大师或夫子)自己说的”。据说,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的门徒们,称某句话为其师所说时,就用这两个字表示。
,意为“他(大师或夫子)自己说的”。据说,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的门徒们,称某句话为其师所说时,就用这两个字表示。
我们在这方面,势有必至,得在知识领域之内,找到一种新的矿苗,这种矿苗,即便前此有人发现过,但据我们所记得的而论,却也从来未经任何古人或今人钻采开发过。这种矿苗,并非别的,乃是对比手法。这种手法,贯串于宇宙间一切事物之中,并且大概在形成我们对于美的概念方面(不论是自然之美,还是人为之美),还起过很大的作用。因为,一切事物之美与善,除了与之正相反的丑与恶,还有什么别的东西,能把他们衬托得更加明显?白昼与夏日之可爱,因为有黑夜与冬季之可憎,才能彰明而突出。 而且如果有可能,一个人只能看到白昼与夏日,那我相信,他对于它们的美,只能有一个非常不完整的概念。
而且如果有可能,一个人只能看到白昼与夏日,那我相信,他对于它们的美,只能有一个非常不完整的概念。
不过我们不要永远这样一本正经,而换一种说法儿说说。假设有一个最美的女人,只经一个从未见过其他类型女人的男子看见过,那这个女人,会在这个男子眼里,失去她一切使他倾倒的力量,这还能有人怀疑吗?名媛闺秀自己,对于这一点,好像非常了解,所以她们才煞费苦心,以取得与美相反的衬托之物 ;不但取得衬托之物,她们甚至于以自身衬托自身;因为我曾看见过,特别在巴斯
;不但取得衬托之物,她们甚至于以自身衬托自身;因为我曾看见过,特别在巴斯 ,她们在午前尽量使自己显得丑,为的是在晚间,好把她们要在男人眼里现出来的美,显得更美。
,她们在午前尽量使自己显得丑,为的是在晚间,好把她们要在男人眼里现出来的美,显得更美。
大多数的艺术家,都懂得这种秘诀,而付之实行,尽管他们也许很少有人研究过它的理论。珠宝商人也都晓得,最精良的钻石,也需要用银箔垫起,以作衬托;画家们也用人物对比的办法,博得极大的称赞。
我们中间出了一位伟大的天才,就可以作一个范例,来把这件事充分说明。说实在的,我们不能只把他列入任何一般艺术家的行列就完了,因为应该和他并驾齐驱的,是那般
Inventas qui vitam excoluere par artes.
以艺术之发现与创获,增人生之兴趣与娱乐
的人们。我这儿说的是发明英式哑剧——一种顶精妙优美怡情悦性之游艺——的人物。
这种怡情悦性的玩意儿,由两个部分组织而成,发明人分别名之为“庄”部与“谐”部。在庄部里出场的,是一些异教的天神和英雄,从来出现于观众面前的角色,没有比他们再蹩脚、再呆笨的了。但是这种蹩脚呆笨,都是成心故意做出来的(这是很少有人懂得的诀窍),为的是叫它们把这种玩意儿里叫作“谐”的那一部分,衬托得更明显,教哈里昆 玩起他那套把戏来,能加倍地引人入胜。
玩起他那套把戏来,能加倍地引人入胜。
这样玩弄天神和英雄,也许未免有失尊敬;但是说实在的,这种巧妙手法,却得说是独具匠心,而且还真有其作用。如果我们不用“庄”“谐”这两个字眼儿,而换用“顶温”和“较温” 来代替,那这种巧妙手法的作用,就更清楚明白地可以看得出来。因为这种玩意儿里,即便所谓谐的部分,毫无疑问,也比向来舞台上所出现的光景都更“温”,只有组成“庄”的部分那样“顶温”的东西,把它衬托一下,才能使它显得还有“谐”的味道。实在说起来,那些天神和英雄,都“庄”到令人不能忍受的地步,所以哈里昆(虽然英国叫这个名字的绅士和法国叫这个名字的,并非一家眷属,无甚瓜葛可言,因为这位英国绅士,比起那位法国绅士来,要“庄”得多多)一出台,永远是受人欢迎的,因为他可以使观众免于非看“温戏”不可之苦。
来代替,那这种巧妙手法的作用,就更清楚明白地可以看得出来。因为这种玩意儿里,即便所谓谐的部分,毫无疑问,也比向来舞台上所出现的光景都更“温”,只有组成“庄”的部分那样“顶温”的东西,把它衬托一下,才能使它显得还有“谐”的味道。实在说起来,那些天神和英雄,都“庄”到令人不能忍受的地步,所以哈里昆(虽然英国叫这个名字的绅士和法国叫这个名字的,并非一家眷属,无甚瓜葛可言,因为这位英国绅士,比起那位法国绅士来,要“庄”得多多)一出台,永远是受人欢迎的,因为他可以使观众免于非看“温戏”不可之苦。
聪慧精干的作家,一向就实行这种对比手法而功成名就。荷马采用这种手法的时候,曾受到贺拉斯的挑剔,这是起初我觉得诧异的;不过在紧跟着而来的那一行诗里,贺拉斯马上就把自己的话驳斥了;因为他说:
Indignor quandoque bonus dormitat Homerus,
Verùm opere in longo fas ef obrepere somnum.
如果伟大的荷马,会身入梦乡,我亦为之惆怅;
但是文富篇长,睡魔偷入暗袭,本属事理之常。
有的人也许会认为,一个作家,正在写作当中,会当真身入梦乡,我们在这儿却不那么想;因为,固然不错,有的读者,非常容易不胜睡魔的侵袭;但是,如果一个作家,写起文章来,像欧勒得米克孙那样洋洋洒洒,那他欣赏自己,还应接不暇,哪里还有工夫打盹瞌睡?他那时就要像蒲伯先生说的那样:
他自己得双目炯炯,才能使读者倦眼蒙蒙。
说实在的,这种引人入睡的部分,正是我说的那种“庄”的部分,本是成心故意,以巧妙的手段组织起来,以便把其余非“庄”的部分衬托而出。不久以前故去的一位好开玩笑的作家 ,常对读者说:不论多会儿,只要他们发现他“温”起来,那他们准可确信不疑,他是在那儿故弄玄虚:我前面那句话,正是他的真意。
,常对读者说:不论多会儿,只要他们发现他“温”起来,那他们准可确信不疑,他是在那儿故弄玄虚:我前面那句话,正是他的真意。
我希望读者,就按照我这番越说越明白的话,也可以说越说越糊涂的话,来看待我这部书里的引言绪论。并且,他听完了这番交代以后,如果认为,他在这部书里别的地方,看到的所谓“庄”的部分,也就很够瞧的了,那他尽可以把这些打鼓开张的引言,一概略过(因为这些引言都是我们惨淡经营、成心故意,使它们“温”的),而从以下各卷的第二章读起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