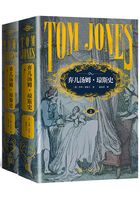
第八章
所叙之事,虽属自然应有,而却令人不欢。
在那个女管家高山一般的颧骨上,盐水所以那样汩汩成河,除了为她主人悲伤以外,还有别的来源。她刚一退出病房,马上就用下面这种令人称快的风格,对自己嘟囔起来:“我本来想,一点儿不错,主人有八成儿要把我从别的底下人里单独挑出来,另眼看待。我想他一定给我留下了丧服。不过,说真个的,要是那就是他留我的全份儿礼物,鬼才会给他穿孝哪,反正我可不。我得叫他老人家知道知道,我并不是叫花子。我伺候他,给他省了有五百镑,但是闹到末了儿,可落到这样一个下场——这倒可以好好地教唆教唆那些底下人,叫他们别捣鬼赚钱。再说,倒是不错,我斩头去尾,有的时候,也赚了他一星半点儿的,可别的人赚的比我十份还多啊。这阵儿可好,一根绳儿拴蚂蚱,把我们大伙儿都混到一块儿啦。要是事情都是这样,那这些留下的遗产跟着留遗产的人见鬼去吧。不过话又说回来啦,我还是不能不要这个钱,因为要是不要,那有的人就该高兴啦。不错,我还是得要这个钱,我要用它买一件顶鲜亮花哨的衣裳,穿起来,在这个老悖晦了的财迷疙瘩坟上跳舞玩儿哪。 这一块儿所有的人,都因为他那样抱养了那个小杂种儿,没有不骂他老不要脸的,我可老站在他那一面,这就是他对我这份忠心的报答。可这阵儿,他就要到他得把所有的债都还清了的地方去了。他这阵儿躺在他要死的床上,顶好忏悔所有的罪过吧,那比自己仍然觉得还挺不错的,把他老家留下来的产业,分给一个小杂种儿好多了。在他床上找到了的!还怪不错的哪!多么好听啊!一点儿不错,一点儿不错,只有隐藏的,才知道在哪儿寻找得着。
这一块儿所有的人,都因为他那样抱养了那个小杂种儿,没有不骂他老不要脸的,我可老站在他那一面,这就是他对我这份忠心的报答。可这阵儿,他就要到他得把所有的债都还清了的地方去了。他这阵儿躺在他要死的床上,顶好忏悔所有的罪过吧,那比自己仍然觉得还挺不错的,把他老家留下来的产业,分给一个小杂种儿好多了。在他床上找到了的!还怪不错的哪!多么好听啊!一点儿不错,一点儿不错,只有隐藏的,才知道在哪儿寻找得着。 我只求上帝宽恕他。要是把事情抖搂出来,那我敢保,不定有多少小杂种儿都得归到他名下哪。有一样事,倒叫人觉得舒服。他到了他这阵儿要去的地方,什么都会露馅儿的。‘我的底下人,都可以在那里面找到作为纪念的一些表示’,这就是一字不差他说的话。我就是能活到一千年,我也决忘不了他这些话。不错,不错,我决忘不了他都怎么把我和别的底下人,葫芦搅茄子,都乱掺和到一块儿。我本来还只当他也要像对斯侩厄那样,把我的名儿单提出来哪。不过,斯侩厄可确实不错,真够个绅士的格儿啦。他刚一来到这儿的时候,连块遮身蔽体的破铺衬都没有。这样的绅士,狗屁!他在这儿待了这么些年,我不知道这宅里有哪一个底下人见过他的钱是什么色儿
我只求上帝宽恕他。要是把事情抖搂出来,那我敢保,不定有多少小杂种儿都得归到他名下哪。有一样事,倒叫人觉得舒服。他到了他这阵儿要去的地方,什么都会露馅儿的。‘我的底下人,都可以在那里面找到作为纪念的一些表示’,这就是一字不差他说的话。我就是能活到一千年,我也决忘不了他这些话。不错,不错,我决忘不了他都怎么把我和别的底下人,葫芦搅茄子,都乱掺和到一块儿。我本来还只当他也要像对斯侩厄那样,把我的名儿单提出来哪。不过,斯侩厄可确实不错,真够个绅士的格儿啦。他刚一来到这儿的时候,连块遮身蔽体的破铺衬都没有。这样的绅士,狗屁!他在这儿待了这么些年,我不知道这宅里有哪一个底下人见过他的钱是什么色儿 。这样的绅士,依我说,只有鬼才伺候他哪!”她还嘟囔了好些同样的话,不过只尝尝这一脔,也足够叫读者尽知其味的了。
。这样的绅士,依我说,只有鬼才伺候他哪!”她还嘟囔了好些同样的话,不过只尝尝这一脔,也足够叫读者尽知其味的了。
斯威克姆和斯侩厄,也同样对他们分到手的财产大不满意。他们虽然并没把他们的愤怒之情,表示得那样高声大嗓,但是从他们脸上表现的不快之色和下面他们的谈话中表现的不快之感,就可以推而知之,占据他们心头的,并非狂欢大喜。
他们离开病榻大约有一个钟头的工夫,斯侩厄在厅堂里碰见了斯威克姆,对他开口说:“我说,老兄,咱们离开了你那位朋友以后,你又听到什么消息没有?”“要是你的意思说的是奥维资先生,”斯威克姆回答说,“我认为,你倒是应该称呼他是你的朋友才对;因为据我看来,他应该受到那个尊敬的称呼。”“在你那一方面,这个尊称,我觉得,好像也同样适用,”斯侩厄回答说,“因为他给咱们两个的恩赐,且别管是多是少,反正都完全一样。”“我本来不想头一个提起这番恩赐来,”斯威克姆喊着说,“不过你已经先开了头,那我就得让你知道一下,我是有另一种看法的。自动的惠赠和应得的报酬,有很大的区别。我在他府上所尽的职分,我教育他那两个孩子所费的精神,都有极大的功劳,有的人也许会指望他能因为这种功劳,得到更大的报酬。你可不要认为,我的意思是要叫你觉得,我因此就感到不满意;因为圣保罗曾教导我,叫我对于我的所有,虽然为数很少,也要知足。 即便他给的这个区区之数更少一些,我也应该明白我的职分所在。但是,虽然《圣经》劝我不得不以知足为上,它可没逼我,说叫我对我的功劳闭目不问;也没逼我,叫我把我受到和别人一律对待这种不公平的损害,装着看不见。”“你既然这样招我惹我,”斯侩厄回答说,“那我就得说,受损害的是我自己。我从来也没想到,奥维资先生竟会把我的友谊看得那样轻如鸿毛,竟把我和一个吃工资的人,放在一对天平秤儿上,等量齐观。我晓得,他所以这样做,根源是从哪儿来的。这都是从你长久以来,一直不断灌输给他的那种狭隘原则而来;那种原则,教导人们对一切伟大、高尚的事物,全都不看在眼里。友谊之为物,太美丽、太可爱了,视力茫茫的人,竟让它把眼睛晃得视而不见。除了用那种决无误解的物之准则,不可能用任何别的媒介,把它辨认出来。但是你对这种决无可误解的物之准则,老嘲笑辱骂,所以才把你那位朋友,在理解方面,引入歧途。”“我一心只愿,”斯威克姆怒不可遏地喊道,“我一心只愿,为他的灵魂起见,你那种该死的主义,没让他的信仰把他引入歧途才好。我认为,他现在这番举动,这样不配做一个基督徒的举动,都是因此而起。除了一个无神论者,还有什么别的人,能不把一生的功过,算一笔总账?能不把一生的罪过,都坦白出来,同时接受罪恶的赦免,就离开这个世界?
即便他给的这个区区之数更少一些,我也应该明白我的职分所在。但是,虽然《圣经》劝我不得不以知足为上,它可没逼我,说叫我对我的功劳闭目不问;也没逼我,叫我把我受到和别人一律对待这种不公平的损害,装着看不见。”“你既然这样招我惹我,”斯侩厄回答说,“那我就得说,受损害的是我自己。我从来也没想到,奥维资先生竟会把我的友谊看得那样轻如鸿毛,竟把我和一个吃工资的人,放在一对天平秤儿上,等量齐观。我晓得,他所以这样做,根源是从哪儿来的。这都是从你长久以来,一直不断灌输给他的那种狭隘原则而来;那种原则,教导人们对一切伟大、高尚的事物,全都不看在眼里。友谊之为物,太美丽、太可爱了,视力茫茫的人,竟让它把眼睛晃得视而不见。除了用那种决无误解的物之准则,不可能用任何别的媒介,把它辨认出来。但是你对这种决无可误解的物之准则,老嘲笑辱骂,所以才把你那位朋友,在理解方面,引入歧途。”“我一心只愿,”斯威克姆怒不可遏地喊道,“我一心只愿,为他的灵魂起见,你那种该死的主义,没让他的信仰把他引入歧途才好。我认为,他现在这番举动,这样不配做一个基督徒的举动,都是因此而起。除了一个无神论者,还有什么别的人,能不把一生的功过,算一笔总账?能不把一生的罪过,都坦白出来,同时接受罪恶的赦免,就离开这个世界? 他分明知道,他宅里就有一个人,是按适当的本分,能做这种事的。他一旦到了那种只有号啕大哭和咬牙切齿的地方
他分明知道,他宅里就有一个人,是按适当的本分,能做这种事的。他一旦到了那种只有号啕大哭和咬牙切齿的地方 ,就该后悔原来没做这些一定得做的事了,但是已经太晚了。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他才能看出来,那个伟大的异教女神——你和各时代一切自然神论者所崇拜的那种道德,要把他放在多么了不起的地位上了。那个时候,他就要想到该请牧师了,但没有牧师可请了;那个时候,他就该后悔,他没举行赦免罪恶的仪式了,而没有这种仪式,任何罪人,都不能免于下地狱之苦。”“如果这件事这样重要,”斯侩厄说,“那你为什么不自动地为他举行这件事?”“除了有足够的天恩那种人需要这个以外,对于任何别的人,一概没有灵验。不过我何必对一个异教徒和反宗教的人说这类话哪?他所以这样,都是因为受了你的教导。这种教导,在这个世界上,你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报酬了,我也毫不怀疑,你的门徒,不久就要在另一世界上,得到很大的报酬。”“我不明白你说的报酬是什么意思,”斯侩厄说,“不过如果你是指着他认为应该留给我的那一点点儿友谊纪念品,那是我看不起的;只是我的境遇里那种不幸的情况,才使我不得不勉强接受。”
,就该后悔原来没做这些一定得做的事了,但是已经太晚了。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他才能看出来,那个伟大的异教女神——你和各时代一切自然神论者所崇拜的那种道德,要把他放在多么了不起的地位上了。那个时候,他就要想到该请牧师了,但没有牧师可请了;那个时候,他就该后悔,他没举行赦免罪恶的仪式了,而没有这种仪式,任何罪人,都不能免于下地狱之苦。”“如果这件事这样重要,”斯侩厄说,“那你为什么不自动地为他举行这件事?”“除了有足够的天恩那种人需要这个以外,对于任何别的人,一概没有灵验。不过我何必对一个异教徒和反宗教的人说这类话哪?他所以这样,都是因为受了你的教导。这种教导,在这个世界上,你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报酬了,我也毫不怀疑,你的门徒,不久就要在另一世界上,得到很大的报酬。”“我不明白你说的报酬是什么意思,”斯侩厄说,“不过如果你是指着他认为应该留给我的那一点点儿友谊纪念品,那是我看不起的;只是我的境遇里那种不幸的情况,才使我不得不勉强接受。”
现在医生来到,开口问那两位争论不休的人,楼上情况怎样?“一片糟烂。”斯威克姆答道。“这正不出我所料,”医生喊道,“不过,我离开这儿以后,又出现了什么症状?”“我恐怕,没有什么好转的症状,”斯威克姆答道,“照我们离开那儿的时候出现的情况看,我认为,没有什么希望。”这位医治身体疾病的大夫,也许误会了那位医治灵魂疾病的牧师;但是还没来得及等到他们进行解释,卜利福先生就面带顶忧伤的愁容,来到他们跟前,对他们说,他带来一个噩耗,他母亲在索尔兹伯里寿终。他说,他母亲在回家的路上,痛风病发,串经入络,攻到心脏和胃脏,不到几个钟头,就与世长辞了。“哎呀,哎呀!”大夫说,“真是人有旦夕祸福;不过我可恨不得当时就在跟前,能受邀效劳才好。痛风这种病是很难治疗的;不过,我对这个病,非常地拿手,能妙手回春。”斯威克姆和斯侩厄两个人,都对卜利福先生的丧亲之痛,致慰唁之意,一个就劝他做一个男子汉,咬牙忍受,另一个就劝他做一个基督徒,咬牙忍受。那位年轻的绅士就说,他深深知道,人都不免一死,所以他要尽力而为,忍痛节哀。但是,他说,他对命运这样特别严重地打击他,不能不加以抱怨;它这样出其不意地给他带来这种巨灾大难的噩耗!而且还在这样一个时候!他每时每刻,都可以看到他可能受到噩运最严重的打击。他说,这一回正是他从斯威克姆先生和斯侩厄先生两个人那里所受的基本教训遇到考验的时候。如果他能在这番不幸中活得过来,那都完全是他们两个人的教育所赐。
现在他们辩论起来,应不应该把奥维资先生的妹妹死亡的消息告诉他。医生坚决反对告诉;我也相信,所有医界中人,都要和他同样反对。但是卜利福先生却说,他从他舅舅那儿听到无数次绝对不可违背的命令,说永远也不要害怕引起他不安,而对他保守任何秘密;因此卜利福说,违背他舅舅那番话,他是不敢设想的,不管告诉了以后,会有什么后果。他说,据他看,如果把他舅舅那样的宗教和哲学思想都考虑一下,他就不能像医生那样,有所疑惧。因此他决定把这个消息告诉他舅舅:因为,如果他舅舅恢复了健康(这是他衷心祈祷的),那他知道,他舅舅对于他尽力想把这个消息对他保守秘密,他舅舅绝不会宽恕他的。
医生对他这种决心没有办法,只好屈从,而那两位学识渊博的绅士,就对这种决心,大加赞扬。因此卜利福先生和医生就一块儿往病室走去。医生先进了屋里,走近床前,为的好给病人诊脉;他刚一诊完,就宣称病人已大见好;他说,他最后这次采用的办法,奏效如神,使高烧暂退。因此他说,他刚才害怕希望太小,现在他又认为危险已过。
说实在的,奥维资先生的病情,从来就没像医生说的那样严重,都是医生出于小心谨慎,才大大言过其实。这也很像善于用兵的大将,不管敌人的力量有多弱小,从来绝不轻视敌情。因此,一个善于医道的医生,虽然病情并不严重,却也从来不轻视病情。这很像一员大将,尽管对手并非强敌,但是却也照常严维军纪,照常谨布守卫,照常精设岗哨;所以一个医生,虽然遇到的只是微恙小病,却也照样保持满脸的郑重之色,用煞有介事的神气摇头晃脑。他们所以采取这种办法,除了其他的原因而外,还有坚强充足的理由;因为,这样一来,如果他们得到胜利,就可以享到更大的荣誉,如果有任何不幸的意外,使他们遭到失败,他们也可以因之而少受耻辱。
奥维资先生刚把双眼抬起,向天感谢他痊愈有望,跟着卜利福先生就走上前来,哭丧着脸,把手绢捂在眼睛上,或者是擦眼泪,也或者是做奥维得在别的场合下所说的那种动作,
Si nullus erit, tamen excute nullum.
如果什么也没有,就把那个没有掸掉。
他把读者刚刚知道了的消息,报告了他舅舅。
奥维资先生听到这个消息,又关心难过,又咬牙忍受,又听天由命。他掉了几点友爱的眼泪,跟着使脸上的表情平稳安静。后来到底喊道:“一切一切,都要依着上帝的旨意而行。 ”
”
他现在问送信的人在哪儿;但是卜利福对他说,连叫送信的人待一分一秒都不成,因为看他那个忙碌劲儿,他手头上一定有要紧的事非办不可;他抱怨说,他忙得、累得、急得简直都不要命了;他老在嘴上重复说,他要是能分成八瓣儿,也有地方安插每一瓣儿。
奥维资先生于是吩咐卜利福,叫他妥善办理丧事。他说,他要把他妹妹埋在他自己的圣堂里 ;至于丧事的细节,他一概都让他外甥自己斟酌处理,只把他要用哪个人来承办这次的丧事,说了一下。
;至于丧事的细节,他一概都让他外甥自己斟酌处理,只把他要用哪个人来承办这次的丧事,说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