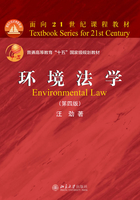
第一节 预防原则
一、预防原则的概念
环境法上的预防原则,是指对开发和利用环境行为所产生的环境质量下降或者环境破坏等应当事前采取预测、分析和防范措施,以避免、消除由此可能带来的环境损害。预防原则要求在环境利用行为实施前,采取政治、法律、经济和行政等各种手段,防止环境利用行为导致环境污染或者破坏现象的发生,即所谓“防患于未然”。
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开展环境保护工作时便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原则作为防治工业污染的方针政策。它要求将保护的重点放在事前防止环境污染和自然破坏之上,同时也要求积极治理和恢复现有的环境污染和自然破坏,以保护生态系统的安全和人类的健康及其财产安全。
为强调环境保护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强化人们对事前防范环境危害的重视程度,2014年《环境保护法》第5条规定了环境保护坚持“保护优先”“预防为主”和“综合治理”的原则,其总体思路还是源于“预防”的基本理念。其中,“保护优先”是指从源头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合理利用资源,避免生态破坏;“预防为主”是指要事前预防与事中、事后治理相结合,并优先采用防患于未然的措施;“综合治理”是指对各项环境要素的污染防治思路、目标与方法等应当统筹考虑、综合运用、协调一致和联防联治。[54]
从国内外环境立法实践分析,预防原则应当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运用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对开发和利用环境行为带来的可能的环境危害事前采取措施以避免危害的产生;二是在科学不确定的条件下,基于现有的科学知识去评价环境风险,即对开发和利用环境行为可能带来的尚未明确或者无法具体确定的环境危害进行事前预测、分析和评价,促使开发决策避免这种可能造成的环境危害及其风险的出现。[55]
在对上述含义的理解中,“可能的环境危害”与传统行政法有关警察法或秩序法所谓“危险”的概念相似,一般指运用通常的知识或者经验,就足以判断决策对象具有较高的造成公众环境权益等具体危害可能性的状态。而“风险”则是指运用现有的科学知识可以得知决策的对象存在着某些具体危险,但又无法肯定针对该危险所采取的对策措施能够避免该危险及其可能造成危害的状态。
实际上,对已知的开发和利用环境行为所要造成的具体环境危害采取措施本身已超越了预防的范畴,而具有对策的性质。因此,预防原则的关键应当放在防范可能的和抽象的环境危害及其风险之上。否则决策的结果便会造成违法或者降低法益的保护。
在国际社会,1980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IUCN)制定的《世界自然保护大纲》曾就“预期的环境政策”作出规定,“试图预测重要的经济、社会及生态事件,比试图只对这些事件作出反应的政策,越来越重要”。“这种预期的环境政策包括所有行动以确保任何可能影响环境的重大决定,均在其最早阶段,充分地考虑到资源保护及其他的环境要求。这些政策并非企图代替反应性或治理性的政策,而是纯粹起加强作用而已。”[56]1985年,联合国在《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中明确提出了预防原则。
针对不确定性对环境决策的困扰,1987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提出了一个更为严格的环境政策和法的原则——谨慎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谨慎原则是指当某些开发行为的未来影响具有科学不确定性的情形下,只要存在发生危害的风险,决策者就应当本着谨慎行事的态度采取措施。
目前谨慎原则已被许多国家的环境立法和国际组织的活动采纳。与预防原则相比,谨慎原则要求在科学的不确定条件下,认真对待可能的环境损害和风险,即使在科学不确定的条件下也必须达成一定的措施,尤其是不作为的措施。而预防原则则是适用于所有环境利用活动的普遍性原则。
另外,预防原则与后述的协调发展原则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因为预防环境损害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必然而适宜的途径。
二、预防原则的适用
由于预防原则需要由具体的环境政策和法律制度予以确定才能有效地贯彻执行,因此该原则在中国没有直接的法的拘束力。预防原则的适用表现在与开发决策相关联的若干方面,具有多功能性。
为执行预防原则,就必须有计划地开发利用环境和资源,为此各国在环境立法上专门确立了环境保护规划和环境规划制度,要求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和相关企事业单位对工业发展与环境保护事前作出合理的计划和安排,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应当与生态保护相结合并有计划地实施。
另外,我国的环境政策与法律还确立了“全面规划与合理布局”的环境保护措施。其中,全面规划就是对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生产和生活、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各方面的关系作统筹考虑,进而制定国土空间主体功能区规划以及国土利用规划、区域规划、城市规划和环境规划,使各项事业得以协调发展;合理布局主要是指在工业及其发展过程中,要对工业布局的合理性作出专门论证,并且对老工业不合理的布局予以改变,使得工作布局不会对周围环境和人民生活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的不良影响(参见第五章第三节)。
由于环境污染危害起因于污染物向环境的排放,因此,控制和减少向环境排放污染物就成为减轻和消除环境危害的最根本的环节。
控制和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在环境法律制度的实施方面就是执行环境标准制度。即以环境质量标准为依据确定某地域(水域)保持良好环境质量的基础数值,在此基础上以该地域(水域)的环境容量或者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最大限度为限,将排放进入环境的污染物的种类、数量和浓度控制在一定的水平之内(参见第五章第二节)。
为了防止因新建、改建、扩建生产工艺和设备造成新的污染,各国环境立法也对企业的生产设施和设备提出了不同的要求。例如,在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环境法律要求在原有生产规模基础上对设施进行改造或者新增的,应当采用现实可得的最佳实用技术(best available technology, BAT),否则不予许可和批准。我国目前也制定有《清洁生产促进法》(全国人大常委会,2002年制定;2012年修正),意在通过实行清洁生产措施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和避免污染物的产生。
另外,民法有关预防性民事责任措施(如消除危险、排除妨害等)在诸如噪声妨害、光照妨害等领域的运用,也是私法上的一种消除和减轻环境损害的保障措施(参见第十三章第三节)。
从预防原则的内容言之,避免环境污染发生比减轻环境污染显得更为重要。作为环境法上的一项基本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是各国适用预防原则最直接的体现。
该制度要求,一切可能造成环境影响的决策、规划和建设项目等,均应当在公众的参与下对其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然后才能由政府行政主管部门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
为了保障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实施的有效性,我国还确立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三同时”制度(参见第五章第四节)。
科学的不确定性常常是决策者忽视环境风险的最大理由。但是,限于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决策者们应当时刻想到“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现在国际社会联合在臭氧层耗竭、气候变化问题上采取行动的做法就是一个例证。
对危险性的预防比对危险的预防更为重要,因为危险性比具体的危险出现在时间和空间上更有距离,即危险性属于德国学者所谓的“危险尚未逼近”的状态。[57]为此,谨慎对待具有危险性的开发利用活动应当着重从如下几方面采取对策:第一,将有关在时间和空间上视为较为遥远的危险(包括对未来世代可能产生的危险)的决策作为国家的责任,予以事前的规划和预防;第二,对于危险出现的可能性较低或者只有危险嫌疑的决策,只需损害的出现具有可能性、可预见性或者可想象性即可认定危险存在,而无需明确的证据证实该危险。
世界银行的专家认为,对于决策者来说,当一种活动造成危害人类健康或环境的威胁时,应该采取预防措施,即使有些因果关系在科学上还不能完全确定。这时,证明的负担应该由活动的支持者而不是公众来承担。此外,应用预防原则的过程必须是公开的、知情的、民主的,包容可能受影响的各方。同时,还必须审查所有的备选方案,包括不采取行动。[58]
由于预防的本意在于防患于未然,因此增强决策者和管理者的风险防范意识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对于大型建设项目、改造自然项目(如在河川筑坝、发展核电、兴建大型工业、农业、水利、交通等项目)以及对外来物种的有意引进等行为,更应将可能造成的长久不良环境影响放在首位考虑。本书认为,在对具有环境影响的重大开发决策过程中,开发政策和政治利益应当让位于公众利益,此方面的决策更应当体现民主化、科学化和规范化(参见第四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