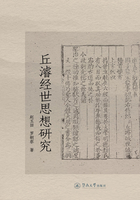
第二节 早期商业化与“人心”迷失
与农民及农村贫困化形势不同,至成化时期,明朝经过百余年发展,社会财富增多了,城镇积累了大量物质财富,而财富也越来越多集中于少部分人手中,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及时享乐与奢侈之风已逐渐形成。是时,从宴饮到服饰,从服饰到民歌时调,从上层社会到下层社会,从市井到乡里,竞奢风气成为当时城乡社会的普遍现象,社会等级制度及规范受到冲击。较早关注晚明竞奢之风的学者是台湾的徐弘教授与林丽月教授。他们首先提出:“嘉靖以后,社会风气侈靡,日甚一日。侈靡之风盛行,消费增加,提供人民更多就业机会,尤其是商品贸迁质与量的增加,更促进商品经济的发达。侈靡之风盛行,又影响明末社会秩序的安定,僭礼犯分之风流行,对‘贵贱、长幼、尊卑’均有差等的传统社会制度,冲击甚大。尤其侈靡之风,刺激人们欲望,为求满足私欲,乃以贪污纳贿为手段,破坏嘉靖以前淳厚的政治风气,使贪贿成风,恬不以为怪。而贪黩之风,又倒过来刺激社会风气,使其更趋奢靡。”
一、成化时期的奢靡之风
成化以后,嘉靖以前,重商观念与拜金主义思潮在社会上颇为盛行,世风由俭入奢。早在天顺元年(1457),社会上已出现奢靡现象。是年,刑科都给事中乔毅等疏请“禁奢侈以节财用。谓财有限而用无穷。进来豪富竞趋浮靡,盛筵宴,崇佛事,婚丧利文僭拟王公,甚至伶人贱工俱越礼犯分,宜令巡街御史督五城兵马严禁之”。 成化以来,拜金主义与奢靡之风日炙。丘濬痛感:“今夫天下之人,不为商者寡矣。士之读书,将以商禄;农之力作,将以商食;而工、而隶、而释氏、而老子之徒,孰非商乎?吾见天下之人,不商其身而商其志者,比比而然。”
成化以来,拜金主义与奢靡之风日炙。丘濬痛感:“今夫天下之人,不为商者寡矣。士之读书,将以商禄;农之力作,将以商食;而工、而隶、而释氏、而老子之徒,孰非商乎?吾见天下之人,不商其身而商其志者,比比而然。” 且“凡百居处食用之物,公私营为之事,苟有钱皆可以致也。惟无钱焉,则一事不可成,一物不可用”。
且“凡百居处食用之物,公私营为之事,苟有钱皆可以致也。惟无钱焉,则一事不可成,一物不可用”。 又如时人何瑭(1474—1543)称:“自国初至今百六十年来,承平既久,风俗日侈,起自贵近之臣,验及富豪之民。一切皆以奢侈相尚,一宫室台榭之费,至用银数百辆,一衣服燕享之费,至用银数十两,车马器用务极华靡。财有余者,以此相夸,财不足者,亦相仿效。上下之分荡然不知,风俗既成,民心迷惑。至使闾巷贫民,习见奢僭,婚姻丧葬之仪,燕会赙赠之礼,畏惧亲友讥笑,亦竭力营办,甚至称贷为之。官府习于见闻,通无禁约。间有一二贤明之官,欲行禁约,议者多谓奢僭之人,自费其财,无害于治。反议禁者不达人情。一齐众楚,法岂能行。殊不知风俗奢僭,不止耗民之财,且可乱民之志。盖风俗既以奢僭相夸,则官吏俸禄之所入,小民农商之所获,各亦不多,岂能足用?故官吏则务为贪饕,小民则务为欺夺。由是推之,则奢僭一事,实生众弊,盖耗民财之根本也。”
又如时人何瑭(1474—1543)称:“自国初至今百六十年来,承平既久,风俗日侈,起自贵近之臣,验及富豪之民。一切皆以奢侈相尚,一宫室台榭之费,至用银数百辆,一衣服燕享之费,至用银数十两,车马器用务极华靡。财有余者,以此相夸,财不足者,亦相仿效。上下之分荡然不知,风俗既成,民心迷惑。至使闾巷贫民,习见奢僭,婚姻丧葬之仪,燕会赙赠之礼,畏惧亲友讥笑,亦竭力营办,甚至称贷为之。官府习于见闻,通无禁约。间有一二贤明之官,欲行禁约,议者多谓奢僭之人,自费其财,无害于治。反议禁者不达人情。一齐众楚,法岂能行。殊不知风俗奢僭,不止耗民之财,且可乱民之志。盖风俗既以奢僭相夸,则官吏俸禄之所入,小民农商之所获,各亦不多,岂能足用?故官吏则务为贪饕,小民则务为欺夺。由是推之,则奢僭一事,实生众弊,盖耗民财之根本也。”
嘉靖以来,以两京、各省都会及江南、华南、大运河沿岸等地为核心区域的城镇繁兴,城镇社会商业化趋势尤为强劲,奢靡之风愈演愈烈,奢侈成为一种生活“习惯”与身份地位象征。如万历年间,时人称:“中州之俗,率多侈靡,迎神赛会,揭债不辞,设席筵宾,倒囊奚恤?高堂广厦,罔思身后之图;美食鲜衣,唯顾目前之计。酒馆多于商肆,赌博胜于农工。乃遭灾厄,糟糠不厌。此惟奢而犯礼故也。” 万历二十一年,礼科都给事中张贞观疏请禁奢:“今天下水旱饥馑之灾,连州亘县。公私之藏,甚见溃绌,而闾巷竞奢,市肆斗巧,切云之冠,曳地之衣,雕鞍绣毂,纵横衢路。游手子弟,偶占一役,动致千金。婚嫁拟于公孙,宅舍埒乎卿士。懒游之民,转相仿效。北里之弦益繁,南亩之耒耜渐稀。淫渎无界,莫此为甚。”
万历二十一年,礼科都给事中张贞观疏请禁奢:“今天下水旱饥馑之灾,连州亘县。公私之藏,甚见溃绌,而闾巷竞奢,市肆斗巧,切云之冠,曳地之衣,雕鞍绣毂,纵横衢路。游手子弟,偶占一役,动致千金。婚嫁拟于公孙,宅舍埒乎卿士。懒游之民,转相仿效。北里之弦益繁,南亩之耒耜渐稀。淫渎无界,莫此为甚。” 是年八月,明神宗亦称:“近来士庶奢靡成风,僭分违制,依拟严行内外衙门访拿究治,法之不行,自上犯之。近闻在京庶官概住大房,肩舆出入,昼夜会饮,辇穀之下,奢纵无忌如此。”
是年八月,明神宗亦称:“近来士庶奢靡成风,僭分违制,依拟严行内外衙门访拿究治,法之不行,自上犯之。近闻在京庶官概住大房,肩舆出入,昼夜会饮,辇穀之下,奢纵无忌如此。” “竞奢”也促进了奢侈品加工业的发展。如万历年间,时人称:“今也,散敦朴之风,成奢靡之俗,是以百姓就本寡而趋末众,皆百工之为也。”
“竞奢”也促进了奢侈品加工业的发展。如万历年间,时人称:“今也,散敦朴之风,成奢靡之俗,是以百姓就本寡而趋末众,皆百工之为也。” 与奢侈之风的弥漫相伴的,是以“阳明学”为导引,以“百姓日用是道”说为抽绎,宣扬个性解放、反传统及“工商皆本”
与奢侈之风的弥漫相伴的,是以“阳明学”为导引,以“百姓日用是道”说为抽绎,宣扬个性解放、反传统及“工商皆本” 等思想为潮流的早期启蒙思潮的兴起。其中,抒发个性、追求自我、享乐自适,寻新求变之商业文化精神萌生而流行。如自称“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
等思想为潮流的早期启蒙思潮的兴起。其中,抒发个性、追求自我、享乐自适,寻新求变之商业文化精神萌生而流行。如自称“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 之“异端”人物李贽(1527—1602)则积极宣扬:“士贵为己,务自适。如不自适而适人之适,虽伯夷、叔齐同为淫僻;不知为己,惟务为人,虽尧、舜同为尘垢秕糠。”
之“异端”人物李贽(1527—1602)则积极宣扬:“士贵为己,务自适。如不自适而适人之适,虽伯夷、叔齐同为淫僻;不知为己,惟务为人,虽尧、舜同为尘垢秕糠。” 事实上,竞奢风气和社会生活中的僭越行为结合起来,形成一股横扫社会传统价值观的变异力量,加剧社会失范。民众热衷于奢靡,却不肯、不愿承担国家赋役。奢靡风背后,并未形成商品生产条件下对于旧有观念的真正冲击,而只是更突出地表现了对于享乐的追求。因此,成化以来明代竞奢之风也就很难显现出对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
事实上,竞奢风气和社会生活中的僭越行为结合起来,形成一股横扫社会传统价值观的变异力量,加剧社会失范。民众热衷于奢靡,却不肯、不愿承担国家赋役。奢靡风背后,并未形成商品生产条件下对于旧有观念的真正冲击,而只是更突出地表现了对于享乐的追求。因此,成化以来明代竞奢之风也就很难显现出对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
另一方面,成化时期,在饥荒折磨下的农民时时面临着死亡威胁或亡命他乡的未卜命途。生亦悲,死亦悲,此等遭遇加剧了农民的躁动心理;城镇奢靡之风加速普通市民贫困的同时,也催生了市民的浮躁情绪。凡此,整个社会都处在躁动与彷徨之中,文风、学风及民风等随之骤变。如成化九年,翰林院编修谢铎疏称:“臣窃惟今日治道之本,莫先于讲学。学之道无他,孔子曰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臣窃观今日之天下,有太平之形无太平之实,盖因仍积习之久,未免有循名废实之弊。天下之事,恒所令非其所好;天下之人,皆奉意而不奉法。如曰振纲纪,而小人无畏忌;如曰厉风俗,而士大夫无廉耻。” 如丘濬所言:“曩时文章之士固多浑厚和平之作,近(按:指成化时期,下同)或厌其浅易而肆为艰深奇怪之辞”;先前“议政之臣固多救时济世之策,近或厌其寻常而过为闳阔矫激之论”。又称:“至若讲学明道,学者分内事也,近或大言阔视,以求独异于一世之人。”
如丘濬所言:“曩时文章之士固多浑厚和平之作,近(按:指成化时期,下同)或厌其浅易而肆为艰深奇怪之辞”;先前“议政之臣固多救时济世之策,近或厌其寻常而过为闳阔矫激之论”。又称:“至若讲学明道,学者分内事也,近或大言阔视,以求独异于一世之人。” 成化十一年,国子监祭酒周洪谟亦指出:“洪武间学规整严,士风忠厚。顷来浇浮竞躁,大不如昔。奏牍纷纷,欲坏累朝循次拨历之规,以遂速达之计。且群造谤言,肆无忌惮。”
成化十一年,国子监祭酒周洪谟亦指出:“洪武间学规整严,士风忠厚。顷来浇浮竞躁,大不如昔。奏牍纷纷,欲坏累朝循次拨历之规,以遂速达之计。且群造谤言,肆无忌惮。” 可以说,社会陷入了道德与方向迷失的状态。
可以说,社会陷入了道德与方向迷失的状态。
二、“成化症候”的社会危害
成化时期的频繁灾荒加剧了原本生活贫困而备感迷茫的农民的惶恐不安及悲戚心理;城镇生活日渐奢靡与及时享乐风气亦催生市民的浮躁情绪;拜物教在整个社会中弥漫扩张。社会风气为之一变:节俭不再是为人所看重的美德,贫穷反倒成为令人嘲笑的事情;世人以追逐奢靡生活为时尚,金钱至上,享受第一。至此,明初以来的传统价值观念和道德伦理规范渐已模糊、走样。无论贫苦还是奢靡,失去“规则”与“常态”的现实生活充满迷茫和变数,民众自觉或不自觉地游离于原有“规矩”和“框框”边缘,实则在否定传统、否定社会及否定自我中寻找着传统、寻找着社会、寻找着自我,最终受制于“早期商业化”社会不成熟的事实而陷于思想混乱、无所适从,茫然自失的状态。凡此种种,预示着成化以来的明代社会进入了一个人心迷失的畸形商业化特殊阶段。进而言之,成化以来,随着明代社会沦为“灾害型社会”,整个明代社会处于急剧变化、躁动不安之中。换言之,嗷嗷待哺之灾民与渐次萧索之乡村,商业风气浓郁的城镇及文化自觉中的市民,连同日趋奢靡与浮躁的民众心理等同体异质诸元素耦合变异,一并把明王朝拖进一个波谲云诡、人心彷徨、危机与生机并存的特殊时代——一个充满变数的“灾害型社会”早期商业化时代。
明中叶以来,“成化症候”不断加重。灾荒频发,瘟疫屡作,农业生态环境持续恶化,无地少地的广大农民处于破产与死亡“威胁”之中,朝不保夕,心理普遍趋于脆弱与焦虑;城镇商品经济畸形发展,社会转型造成的失范现象增多,奢靡与“僭越”成风。明初以来原本强势的传统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规范渐已失去控制人心的功效,社会充满不确定性,危机重重。至此,明代可谓“祸”不单行,天灾与“人祸”密集袭来,天灾不断加重人们焦虑恐惧的心理,社会失范问题又持续加重人们的不安全感,二者恶性互动,“焦虑恐惧心理”与“不安全感”叠加,社会心理表现出普遍性脆弱与紊乱,社会趋于无序。换言之,“成化症候”已经严重威胁明朝统治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