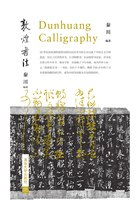
中国书法界的核爆
时光回转到一百年前的敦煌。
1907年3月27日,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在玉门关附近考察汉代长城线,发现了一座削去顶尖的烽燧。在这座被他命名为T.XXVI的烽燧周围,斯坦因进行了地毯式搜索,发现细沙砾中有一些细碎的废料。老到的斯坦因即刻意识到这里极有可能存有古代文物,他们用铲子在地面上刮了又刮,竟刮出一间堆满各种垃圾的小屋废墟。最先翻出来的是一块长10英寸、宽1英寸的木牍,上面整齐地书写着5栏汉字,随行的蒋师爷很快认出这是九九算术表的一部分。接着还有3枚木简也重见天日。这让斯坦因大喜过望。在随后的发掘中,他们又获得了大批简牍,其中一枚写有“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的纪年简,证明这是汉光武帝时期的木简。

斯坦因的考察队在敦煌玉门关一带的汉代长城线上进行考古挖掘(斯坦因摄)

↑著名学者罗振玉
斯坦因兴奋地写道:“毫无疑问,这是我考察过的遗址中最早的一处古边墙,它至少可以早到公元1世纪。因此,我手上的木简文书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汉文文书。这是一个令人高兴、使人激动的发现。这个考古发现让我信心百倍地考察长城古迹,而且现在对考察的成功又增添了新的信心。”
斯坦因没想到的是,他的这一举动在中国文化界会产生如此强烈而又持久的反应。他无意中打开的是一座罕见的汉代书法宝库,那里面珍藏着中华先民最早的书法真迹。

←王国维(左)和罗振玉合撰出版日本京教版《流沙坠简》↓
在流沙中掩埋了一两千年的敦煌汉简重见天日,震惊了国际汉学界。
首批约3100枚敦煌汉简被斯坦因运回英国,法国汉学家沙畹博士近水楼台先得月,他很快对其中的700多枚汉简进行拍照,并影印出版。但他毕竟不是中国人,他对这批资料的研究存在很多误读,包括一些西北地名、历史上的一些官职名,他都不太清楚。国学大师罗振玉看到如此珍贵的出土资料被老外草草出版,心里很是着急,便给沙畹写信,希望博士把敦煌汉简资料提供给他做更深入的研究。沙畹倒也痛快,很快把书稿的图版寄给了罗振玉。罗振玉如获至宝,立刻与亲家王国维分头整理考释。
罗振玉和王国维自1898年结识订交,相伴相偕了30年之久。两人同属中国近代承前启后的国学大师,他们共同创立了20世纪新史学,就是利用地下出土的资料,跟文献记载的资料结合起来研究历史问题,史称“两重证据法”。他们以安阳出土的甲骨、敦煌出土的汉魏简牍、莫高窟出土的唐宋典籍文书等新资料为研究对象,不仅把中国文明史向上推进了一千余年,而且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学术成果。

敦煌马圈湾王莽新简

《流沙坠简》收录的敦煌汉简


刘正成
国际书法家协会主席、《中国书法全集》主编
陈寅恪先生在为陈垣著《敦煌劫余录》写的前言里也说,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碰到的问题,但是每一个时代都有新发现的文献资料,利用这些新的文献资料来解决碰到的问题,这就是时代学术的潮流。
罗振玉和王国维很快把敦煌汉简资料整理成一部国学专著《流沙坠简》,对所收录的敦煌汉简和残纸、帛书都作了精确的分类和详尽的考释。全书按简牍的内容之不同,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是小学、术数、方技书。第二大类为屯戌丛残,为主要部分,下分簿书、烽燧、戍役、廪给、器物、杂事等项。第三大类是出土简牍中文字不清、残折厉害的简牍,进行考释。书稿完成后,原打算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定金都预付了,却因筹不齐印书款最终没有付梓。但罗振玉、王国维对这本书的学术价值非常自信,他们自比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钱大昕,认为即使钱大昕在世也只能做到这份儿上了,出版只是迟早的事。
几经辗转,罗振玉、王国维合撰的《流沙坠简》终于在1914年出版,只不过出版方变成了日本京都出版社。无论如何,这都是一部划时代的国学巨著,首次全面解读汉简的开山之作。一贯声称反对“整理国故”的鲁迅先生,在看了王国维《流沙坠简》序言后都不禁赞叹:“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热风·不懂的音译》)
《流沙坠简》的出版在中国书法界引发的震动更为强烈,国际书法家协会主席、《中国书法全集》主编刘正成先生甚至用“原子弹爆炸”来形容这种震动。他说:“汉代简牍就像原子弹爆炸一样,灵光一闪,在几十年之间影响了书法艺术,一下子打开了书法家们创作的新天地。”
在汉字的正体字中,篆书成熟于秦,衰亡于汉;隶书成熟于汉,衰亡于晋;楷书成熟于唐,衰亡于宋。篆书、隶书和楷书成熟之后,作为“万世法程而不可易者”,它们的形式开始凝固僵化,成为教条法式,限制和束缚着人们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迫使他们亦步亦趋,走向拘谨呆板。从宋代一直到清代,正体字的创作都徘徊于低谷,后继无人。陈寿卿言:“有李斯而古籀亡,有中郎而古隶亡,有右军而书法亡。”(沈曾植《菌阁琐谈》)

康有为书法
清代中期金石考据的兴起,三朝鼎器、两汉六朝碑版的大量出土,给书法改革带来重大转机。人们看到了与前人截然不同的另一个方向——体现平民精神的六朝碑版和造像墓志。邓石如、包世臣等书法大家认为,要想复兴书法,就要打破“二王”桎梏,取法北碑,以北碑之厚重古朴,纠正南帖之妍美漂浮。把长期不为人看重的北碑书法提到与“二王”比肩的高度,于是掀起了碑学运动。康有为概括了碑版书法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跃;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远;九曰结构豪放;十曰血肉丰美”,并奇怪前人对这部分传统怎么会视而不见,无动于衷,“而诸家书品,一无见传,窦《述书赋》,乃采万一,如斯论古,岂为公欤”!(《广艺舟双楫》)通过邓石如、包世臣、何绍基、赵之谦、康有为、沈曾植、吴昌硕、李瑞清等书家的大胆实践,清朝中后期书法形成了堪与唐代楷书、宋代行书相媲美的雄强书风,有力地冲击了宋代以来的帖学传统和江河日下的颓靡书风,推动中国书法迈入了第三个高峰期。
由于当时人们只看到汉魏六朝碑刻,没有手写的真迹,因此,声势浩大的碑学运动只在篆书、隶书和北魏碑体等正书的创作上取得了重大突破,而在行、草书的创新上却因缺乏可资借鉴的新材料而难有更大作为。
20世纪初叶,正当书法家们为碑学的行、草书寻求突破的时候,原汁原味的汉唐书家笔墨真迹——敦煌汉简和写经残纸横空出世,与中国书法的变革需求一拍即合。

肖文飞
中国书法院理论部主任、博士

敦煌马圈湾西汉简
中国书法院理论部主任肖文飞在研究相关资料时注意到,当时众多书法大家看到敦煌汉简和写本时都兴奋莫名。沈曾植说,看到这些汉代墨迹简直是幻若神明,好像突然开窍了,以前猜想的一些东西,终于找到了实证。又比如梁启超,他一直很怀疑王羲之《兰亭序》的真伪,因为汉魏六朝的碑刻书法与王羲之的书风差距太大。而在敦煌汉简墨迹中,王羲之书风已初现端倪。在亲眼目睹了敦煌汉简书法后,梁启超才觉得《兰亭序》没有问题了,觉得那个时代出现这样的作品是必然的。
大书法家李瑞清、郑孝胥则认为汉简出现后,“书法之密尽泄”“书法复古指日可待”,振兴书法大有希望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肖文飞解释道,碑版毕竟是刀刻的产物,跟毛笔写的还是有差距的。千百年来人们都是通过这些刀痕推测汉代的笔法,包括隶书到章草的过渡,一直到楷书的过渡,所谓“透过刀锋看笔锋”。但这只能是一种猜测,始终与真实的墨迹隔着一层。流沙坠简一出土,这些猜测就豁然开朗了。书法家们终于能够挣脱碑、帖的窠臼,冲破魏晋唐人的蕃篱,从而开拓出新的艺术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