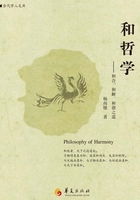
二、和合效应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古典表达
人类与环境交往互动之所以可能,首先是因为事物的意义理性是可以感知的,是人类德性与环境之间达成和合效应的重要表现,进而表现为人类与万物、与环境的精神和解,有着丰富的内蕴与维度。其具体表现为,无论是远古还是现代,无论是社会人文学科还是自然科学学科,无论是感性还是理性,或多或少都含有精神和解的内在价值诉求。其基本机制可以概括为:和合、和解、和谐,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德性自觉,一种人类共有的同质性与内在的同一性,一种非此难以实现更好的自我存在和发展的基本范式与路径,一种人类在价值自我实现上的统一理论。同理,在人与人交往互动过程中,人们不难得出这样的意义理性和理智判断:从差异性的角度来考察人类,人人各有其异;从同一性的角度来考察人类,没有谁不是人。换言之,差异性和同一性只不过是人类的一体两赋而已。这说明,人类历史虽然纷繁复杂,但通过人类自身的德性及其对事物意义理性的理解和表达来认识,是一个简明扼要的方法。
从这一角度来看,科学并不排斥常识和常理。科学与其说是现代人的一种神器,毋宁说是人类精神和解的一种内在价值诉求,一种方式方法。例如,“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种源于人们的感知和经验的常识和常理,与我们常说的科学并不冲突。而两千多年前,老子就有这样的言论:“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41]这里的基本义理就是“天无私覆,地无私载”[42]是“公”最自然的形象和形态,“公”(公平公正)与“道”则具有高度的重叠,所谓“公道”,常理而已。在社会人文环境中,“和以公为基,公则生和,和以生物,物生其利,利以守和”,亦可谓“和”或“和合效应”的应有之义。但是,受高度专业化的现代知识环境的裹挟,以及某些现代观念和文本教育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干扰,人们对工具理性高度重视,但对常识和常理的重要性的重视却显得不足,常识和常理被边缘化和素地化。
《道德经》中有这样一句名言:“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基于这样的理念,“孤阴不生,独阳不长”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常识。也就是说,不仅“和”含有复数的意义,事物的生成也含有复数的意义。由此观之,所谓“和”可谓事物生成性及其与环境之间的哲学抽象。还需要注意的是,个体与环境之间含有整体性和系统性的关系,在生成上又具有一定的连绵效应。通俗地说,万物的生成是源于宇宙背景下展开的无穷无尽的婚姻嫁娶活动。正因如此,在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理念中,“和”含有和谐、和睦、和平、友善、平衡、中庸、公道、恰如其分、公共最适度、获得感等意涵,是人的德性自身以及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环境以至物与物之间处于良好状态的反映。从这一角度看来,所谓“和”就是在一定条件下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环境以至物与物之间的“和合效应”,同时还可以视为事物处于良好状态或处于较优和合环境中的自然法则和公共标准,实可谓“万物得其善而和,因其和而生,失其和则弊”。
其中的道理不难理解。历史上,人类文明首先产生于某些特定的区域,根本就在于这些区域含有更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和合因素;同理,社会的公平性或者说社会的和合性与和合度是否处于较优状态,同样会潜在地影响族群的生存和发展。从较大的时间尺度来看,人类历史是发展的,这中间既有环境的因素,又有人的和合能力与环境相适应的因素,从而成为人类历史发展性的重要内涵,概而言之,不外乎人类与环境的和合性与和合度所产生的和合效应而已。

汉字是一种象形文字,对事物的意义理性有其独特的表达能力,并且含有中华先民对事物的意义理性的丰富感悟。从字源学的角度来看,“和”为禾旁,禾声,本于禾,含有庄稼收获之后,人们载歌载舞、其乐融融,以示感恩和庆祝的意蕴。所以,“和”或“和合效应”虽然比较抽象,而且不好把握,但在现实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却是可以感知和测度的。正如《周易·中孚》所言:“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亦可谓人与人、物与物在天地之间相互唱和的和合效应。
又如:“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相彼鸟矣,犹求友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作为人类的我们啊,怎么可以不相友而生呢)?神之听之,终和且平(让我们静心聆听宇宙之神的天籁之声吧,从中不难感受那份极致的和谐、吉祥与静穆的安宁)。”[43]从中我们不难领会与体悟到天地之间、环境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友善与和乐之美,以及由此而来的身心快乐与身心喜悦。此亦可谓古人对德性需求的推崇及其典范表达,读之难免受其感染,心中得到共鸣、解悟和愉悦。其中的原因和道理其实就是人皆有之的德性需求,是以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和合效应。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借助各种发明创造,人类对环境的适应性虽然在不断地提高,但由于环境的非均质性,人类对较低和合度的环境的适应性是有限的,而不是无限的。换言之,人类对环境的适应性必须在适当的和合度范围内才有效、才有意义,超出必要的和合度范围,适应性就会失去其有效性和意义。
由于适度性的失落常常有一定的过程,在现实生活中,必要的适度性一旦失去,不仅会灾害频发,而且要修复和恢复过来也不是容易的事。因此,在日常生活中,随着适度性的失落,“和合效应”与“和”的尺度意义也会随之失落,以至于在人们觉醒时,适合人类生存发展的必要和合度已经渐行渐远。进一步说,无论是“和”还是“和合效应”都是具有规律性和内在规定性的客观存在,但并非总处于适合人类生存发展的良好状态。如果将最低限度设定为0,在此之上的和合度产生的和合效应为正效应,在此之下的和合效应为负效应,那么我们不难意识到,虽然人类对资源和环境的利用能力在不断提升,却是有限的,客观上必然限定在和合度之内。在正的和合度之内,和合效应会相应地增加;在负和合度之内,就会产生排斥性和合效应,使环境的适度性发生逆转,人类就会陷入得不偿失的负效应状态。相应地,在日常生活和实践中,需要注意或者采取相应的措施和制度安排,对适度性的“度”进行把握。它既是一门无处不在的生活艺术,又是一门无处不在的哲学,并且常常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有一定的交叉和重叠。
历史上,孔子的弟子有子曰:“礼之用(作用或效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44]本书所言的“知其性、识其情、和其意、合其度、悦其美、尚其德”,虽然含有不少影响“和”的变量,但总的来看,亦可谓“六位一体”的“和为贵”,一种拥有内在多元结构并且以“度”来总括其情态与样态的和合之道。换言之,人类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对规律的认知,对事物之间最佳和合度的把握和遵循。
“和”与“道”有密切的关联,甚至可以说,“和”就是“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表现。两千多年前,老子有这样的论述:“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45]“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46]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常常不知足、不知止,有时为了一己之私或短期、局部的利益,失于度的约束与规制,因而老子还说:“物壮则老,谓之不道。”[47]“反者道之动。”[48]孔子则说:“过犹不及。”[49]其中的思想义理无疑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并且含有事物之间具有和合效用递减律与和合周期律的内在规定性的意涵,而事物拥有自身的周期律则是事物拥有持久性或无限性的必要动因和内涵,自然界的昼夜、寒暑、春夏秋冬等莫不如此。人类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基于对其中规律性、内在规定性的认知、遵循和利用,在现实生活中合其和、用其和、共其和,使人的德性与天地的德性和合如一,逐渐形成主动应对因而富有自身预见性和主体性意义的生存与发展之道,具体表现为思想理念、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各种制度安排等。
所以,如果问何谓中华文明,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中华文明一个极为重要的特征就是对人的过度物欲化和动物化蜕变的永不止息的抗争,有如长江、黄河,冲破万般艰难险阻,演绎出一路恢宏壮阔的独特神采。例如,孔子就有这样的言论。学生子游请教何谓孝道时,他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50]孟子则基于“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稀)”[51],进一步阐述人之为人的意义理性,也就是著名的“四端”说: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燃),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52]
正因如此,以人的姿态来处理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环境的关系,实现人的意义理性与精神和解的最大化,亦可谓中华文明的精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