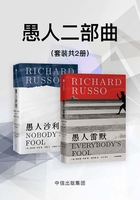
离世策略
门上的小铃铛终于停止了叮啷响,当沙利看到露丝瞪着他的眼神时,他几乎希望罗伊·帕迪能转过身来。当年他和露丝还不是普通朋友时,那眼神意味着他有一阵子忘了做爱了。而最近,那眼神没那么恶狠狠了,但更加不祥。“好吧,”她最后说,“有件事你是对的。”
“真的?没想到我还有做对的时候。”
“通常人们会越变越糟糕,”很明显,她指的不是罗伊,“你最近是怎么了?”
他还没来得及回答,男洗手间的门开了,卡尔走了出来,一条裤腿的内缝上渗出一块尿渍。他刚做完手术的几个星期里,穿了医生推荐的成人尿布,但他对沙利说穿那个东西太令人感到羞辱了,所以一旦重拾了他的撒尿功能,他就不穿了。问题在于,偶尔的失禁还在持续着,多半在晚上或一大早。在提起裤子离开马桶时,他会耐心地站在马桶前等小便解干净,但往往他提上裤子以后尿液才会流出来,这似乎是那尿道口现在变得更不受控的表现。显然,刚刚就发生过这事儿。
“你什么时候能碰到罗布?”他说,还没觉察到不对劲,“跟他说我需要他和他的挖土机。”
“那挖土机可不是他的,”沙利提醒道,“那是镇里的。”
“我们可以借来用用,”卡尔边说边滑上了他的椅子,沙利立马闻到一股新鲜的尿骚味。
“你自己的挖土机呢?”他问。
“在院子里呢,”卡尔说,“暂时瘫痪了。”
有块毛巾搭在烤箱门上。沙利起身,绕过了吧台,露丝正怒视着他,这可是个冒险的举动。当他有正经事要做,而她的心情恰巧不错时,他会勉强被允许在这附近出现,反之则不然。“我肯定你那个市长好朋友会愿意把它租给你的。”
“是的,可能吧,但我可不想花钱。”
“我为你干过活,很清楚你这点。”
“所以,”他说,这时沙利正擦拭他俩中间的柜台上并不存在的污点,“你真的没再想过性吗?”
“不太经常。”
“好吧,”卡尔说,明显松了一大口气,“希望我到你这年龄时,这一切也能结束。”
“你以为你能活到我这年龄?”接着,他压低声音说,“看,你可能会用到这个。”他把毛巾颇有深意地推到卡尔面前。
卡尔回他一个“这是什么鬼”的眼神,紧接着明白了。“老天,”他从凳子上跳起来,就好像尿湿是那一刻发生的,而不是两分钟前发生在厕所里。沙利捕捉到露丝的反应要比卡尔快得多,她正生气地盯着他,好像怀疑是沙利尿了裤子一样。而沙利不知咋的,竟然也觉得是这样。
“一条毛巾根本没用,”露丝对着正在拼命用力擦那斜条纹裤的卡尔说,“跟我来。”她说,示意他跟着她,他很不情愿地跟了上去,脸红到了耳根。
当通向卧室的门在他身后关上时,沙利被单独留在了这世界上他最喜欢的地方。在深沉的寂静里,他可以听到柜台那端咖啡壶传来的滴答声,带着金属的质感,像是闹钟在走动。外面的热浪仿佛让窗户起了涟漪。他看着车经过,有人从五金店里走出来,一条狗快步跑过街道……他突然有一种深深的混乱感,好像他所知道的真实世界只是电影的场景,电影中,他是唯一的演员,其他的演员甚至剧组人员都回家了。是今天休息?还是到了周末?还是电影已杀青,而人们却懒得告诉他?最终连咖啡壶都没有滴答声时,沙利感到整个胸口充满了恐慌。难道他刚刚经历了医生给他的警告——心脏病会随时突袭他吗?这就是生命中止的感觉吗?一切都停止了,除了意识仍恍恍惚惚地存在,忠诚地履行见证的职责?
“嗨。”一个声音响起来,他一开始觉得是露丝,后来他眨眨眼,看清了是杰妮——露丝的女儿。这几年,她们的嗓音变得越来越相似,以至于他总是难以区分。她的卧室门现在半开着,从里面传来一个小设备刺耳的呜咽声。“回回神吧,沙利。”
“嗨。”他回应,有些尴尬,但也很是感激,因为她的声音让一切又动了起来。一个男人正要跨出五金商店,街上传来汽车的喇叭声。心脏科医生曾警告,他有可能会经历短暂的“叙事紊乱”,甚至幻觉。因为心律失常会使大脑供血过多,或者供血太少。
“知道不,你一天比一天奇怪了。”杰妮说,给自己倒了些咖啡。她睡意惺忪的眼睛下有黑眼圈,她打量着沙利,眼神中的漫不经心丝毫不加以掩饰。“说到奇怪,卡尔·罗巴克怎么会在我的浴室里用我的吹风机吹他的裆部?”
“哦……”沙利拖着尾音,因为杰妮可能是整个巴斯唯一不知道卡尔窘况的女人。
“男人啊,”杰妮叹道,这让沙利也成了一丘之貉,不管行为有多愚蠢。
“嗨,”露丝回来了,盯着女儿说道,“我希望你不要像现在这样,穿着睡袍进餐厅。”
毫无意外,杰妮并不在乎她妈妈的想法。“好啊,那我希望你没带男人在我还没醒时走进我的浴室,不经我的容许就把我的吹风机借给他们。”
“那就请你在中午前起床。”露丝建议道。
杰妮指着闹钟,上面写着11∶29。“还没到中午呢。昨晚是我关的苹果蜂的店门,就不允许我稍微喘口气吗?”
她俩大眼瞪小眼,瞪了好一会儿,直到母亲软了下来。“好吧,洗手间的事我道歉,”她说,“但卡尔刚刚遇到了意外。”说到他的名字,她稍微加重了语气。记得吗?她好像在说,我是怎么跟你说过卡尔的?
“噢,好吧,”杰妮耸耸肩,“我猜已经弄好了吧。”
“是我的主意,”露丝说,“很高兴你也赞同。”
杰妮转了转眼珠,表示她可不赞同,但她不想追究了。“我之前听到的是我那白痴前夫的声音吗?”露丝显然把这当成个反问句了,因为她没有回答。“他把那禁令看得太严重了,”她转向沙利,“这次她给他吃了啥?”
“啥也没有,”露丝说,但马上就看起来心虚了,“一杯咖啡,还有一块放了一天的馅饼。”
“妈,你得把他想成是条狗。如果你喂他,他就会不停地回来。”
“目前他还没有惹麻烦,也还没这迹象,”露丝扫了沙利一眼,“不像有些人。”
“这就是罗伊,”杰妮边说边把她喝空了的马克杯放在了塑料洗水槽里。“他平时不响,但一闹惊人,到时候我的下巴会被他打烂的,像以前一样。”
“他打你下巴是因为你经常顶嘴。”
“不是,他那么做是因为他喜欢打人。”
“就像你喜欢顶嘴一样。”露丝在杰妮路过她时说。
“噢,是吧,”杰妮沉思着,在她卧室的门口停下来说,“让我想一想,这毛病他妈到底是从谁那里遗传来的?”
杰妮一离开,露丝就转向沙利。“我不想听了。”她说。
果然如他所担心的那样,她不愿意再就他们之前争论的话题继续下去。“你不愿意听啥?”
“就是你想讲的那些。”
实际上,沙利非常乐意缄口不谈。因为这些小插曲,他很确定现在的风向对他有利。没有什么比她和自己顽固的女儿产生点小摩擦,更能帮助沙利重获露丝的青睐了。他严重怀疑露丝会在两个不同的战线同时作战,这又不是什么你死我活的死战。很明显,他是对的,自从他让她在瞪眼中占了上风,她的姿态就软了。“谢谢。”她真心实意地说。
“不客气,”他回道,“说不定我要说的是些好话呢。可惜你永远听不到了。”
她向他抛了一个眼神,表示自己乐意冒听不到的险,之后又给自己倒了些咖啡,接着绕过他拉了个凳子过来。她用手指背触摸着他的脸颊。这是几个月以来他俩最亲密的接触,这个姿势足以驱散他残存的迷茫。这才对,这才是他的生活,不是电影。
“你生什么病了?”露丝问。她之前问过同样的问题,但当时她很生气,现在她的语调完全不同了。当时,她这么问是怪他为什么去刺激罗伊·帕迪,至于现在她为什么这么问,他就不能确定了。
“他很危险,露丝。”
“你以为我不知道?”
他并不肯定这点,她真的知道罗伊很危险吗?
“我知道,你觉得自己是在帮忙,但你帮不了的。如果他爆发了,会让你住进医院,或者直接进山谷区墓地。”
“我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他说,借用了罗伊的话,尽管这话出自他口有点软弱无力。
“他比你有四十岁的年龄优势,沙利。而且他打架从来不光明磊落。”
“我明白。”沙利说,他想象中的要除掉罗伊·帕迪的手段同样也不是公平打斗。“如果他惹了我,他就得回到监狱,那样你们就能摆脱他了。”
“是的,可是如果他杀了你,到时候我摆脱的可就是你了。”
只有两年。或许不到一年。难道这才是他为什么去挑衅罗伊的原因?是一种潜意识的离世策略,用自己的方式结束生命,而不是坐等那颗变糟了的心脏停止跳动?你听说过有人在一条黑暗的路上加速,然后挑一棵方便些的树撞上去,或者突然撞向对面的车而自杀吧。如果把罗伊·帕迪放到那个场景如何?一个蠢蛋自杀了?
这个设想有问题,因为它的前提是沙利想死,而他很确信自己不想死。之前,当卡尔解释他为什么要给罗布那份工作时——那份工作可是任何头脑正常的人都不愿意去做的——沙利实实在在地感到了一股刺痛的妒忌,这感觉他很难解释。如果从工厂的地板上咕咕冒出来的肮脏黏液是来自炼油厂的话,要把它清理干净将会是令人恶心得不能再恶心的活。没有人会享受这苦活,包括沙利。他还不至于自我厌弃到去相信,自己应该去做这么可怕的一份工作。他的解释是,吸引他的是那种被需要感。那是他和罗布过去常干的活儿:肮脏但必须有人干的活儿。一旦做完,与之而来的是和所受的苦难完全相反的满足感甚至愉悦感。在冷得要命的天气里砌石膏,感觉不到被冻僵的手指,直到不小心用锤子打中它们,这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事儿,但当你最终冒着严寒回到家,那感觉却很好。之后洗个长长的热水澡,虽烫但能忍受的热水也让人感觉很好,一个小时后就能坐到白马酒吧的吧凳上了吧?完美。一天的劳作后,回到舒适地带,会感到啤酒分外凉爽。只要啤酒足够凉就很好,你不会在乎它是否廉价,不会在意是不是只能与便宜的酒相伴。接着到了周五,他们会追着卡尔·罗巴克到处跑,逼着他把手伸进裤兜里拿出那厚厚的一卷二十或五十美元面值的纸币,看着这狗娘养的很不情愿地一张张抽出来,直到他付清你辛辛苦苦应得的酬劳,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满足的?直到最近,沙利的生活都是如此。不,他并没有厌倦这种生活,只是因为年龄和虚弱的身体让他靠边站了,说实话,这会发生在每个人身上。只不过,这一次轮到他了。
他又看了看他的女房东,她也在看他。不要自欺欺人了,她好像在说。沙利觉得她指的是之前那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有关上帝赐予了他生命而他是否后悔没有善加利用。这是换了种法子问他,他是不是想要改变生活:在刺骨的寒冷中砌墙,在炙热的阳光下挖沟,或者是坐在吧凳上,一场接一场地喝,没有止境,越来越激烈地争论是否真有性上瘾这事。是因为怀疑自我存在的价值,才使他之前短暂地怀疑现实吗?杀了罗伊·帕迪,或诱使罗伊杀了他,能让他的存在更有意义些吗?
“听着,”他对露丝说,“我会解决掉他,如果这是你想要的。”
“想要?我想天上掉下来个重家伙砸中他的尖脑壳。为什么上帝从来不严惩像罗伊·帕迪这样的人?”
看露丝只是抱怨下,他对这个问题也就没有提供意见。“不管怎样,”他说,“不用担心我。我只是有点不安。”
“不安也是有原因的,”她说,“彼得啥时候回来?”
哈,这才是她想知道的。好吧。这意味着她更不可能知道真相了。“周二吧。怎么了?”
“也许他会改变主意。”
“不,他已经准备动身了,”他瞥了她一眼。“怎么了?”
“如果我说我从来都对他没什么好感,你会难过吗?”
“露丝,他是我儿子。”
“也许我只是希望他能有儿子的样子。”
“他也许还希望在他小的时候,我能有父亲的样子吧。”
“为什么这些让人头痛的事就这么没完没了呢?”
“我不知道。应该有吗?”
“我也不知道,”她坦言,“我们的生活都一团糟。”说到这儿,她朝女儿房间的方向瞅了瞅。
“我们的确是一团糟,”他赞同,“实际上,我觉得彼得基本上是原谅我了。绝大多数时间我们都相处得很不错。”
确实如此。尽管彼得看上去仍然很困惑——为什么两个这么不同的人却被血脉连在了一起。但过去几年里,他们的关系融洽了很多。沙利退休前那十八天他们一起工作的日子起了作用。也许彼得仍然不理解,为什么他父亲是这个样子,但至少,他知道了沙利白天的生活节奏,更别提晚上了。至于彼得,尽管他俩的关系还没那么尽如人意,也还不能深入交流,但沙利还是很高兴且惊讶地发现,彼得并不像看起来这么柔弱了,他对做艰辛的苦力活也没太大抵触。
当然,当彼得又回去教书时,他一点也不惊讶,他和斯凯勒的学术朋友们一起度过大多数空闲时间也无可厚非。但彼得还是会时不时地逛进白马酒吧,对博蒂狡黠地眨眨眼,然后坐到沙利旁的吧凳上。他会一直在那儿待到关门,看上去还挺惬意的,这让沙利很开心。彼得和他自己正处在青春期的儿子的关系,也时不时令人担心。有关该怎么跟孩子相处,他从来不问沙利的意见——沙利也还没笨到要主动指点——他似乎挺感激父亲愿意倾听并给予他同情的。有时候,沙利甚至觉得自己越来越喜欢彼得了。而彼得要的不是原谅而是遗忘——他似乎也越来越喜欢他父亲了,但每次快要喜欢上他的时候,他就退缩了,就像坐在火炉边要碰到了火那样。反过来,沙利担心,在某些方面,儿子还跟以前一样是个深深的谜团,这种神秘感就像他对自己的父亲,也像威尔时不时显露出来对彼得的一样,令人困惑。是因为父子关系本就这样的吗?父子关系应该是怎样的呢?
沙利逐渐感到儿子过得不快乐,这种不快乐扎根在他的挫败中。沙利不理解儿子的处境,他觉得彼得没有做错什么。彼得在斯凯勒最负盛名的文理学院任教。三年前,当校友杂志那个浮华的衰人编辑退休时,彼得接任了他,给这杂志带来了新的生命力。同时,他在电影、书、音乐方面的评论,也时常见诸奥尔巴尼免费报纸的报端。而且,尽管已经步入了中年,他仍然很好看,他轻松悠闲的迷人气质一直都如磁石般吸引着年轻一些的女人们。他抚养长大的儿子,一月就要毕业了,比他高中同学都早半年,春季学期他就要在斯凯勒上大学课程了。到了秋天,他会以全额奖学金在宾尼法尼亚大学注册,成为第二学期的新生。这实在值得骄傲,沙利认为。
而彼得则是从不同的视角看待这一切的。自从被最初雇用他的州立大学拒聘后,他一度欣欣向荣的事业就再也没能恢复元气。现在,作为兼任讲师,他无疑是个二等学者,世界就是如此无情,他可能就只有一直这样下去了。他的工资只有那些全职的、有终身教席的同事的一小部分,也没有就业保险。是的,他是在写评论,可那不是书或剧本。他的婚姻也失败了,拜他那特有报复心的前妻夏洛特所赐,他很少能见到他问题多多的二儿子。那些他生命中出现的女人们不久就会发现,在他轻松悠闲的迷人外表之下,他的内心是何等的苦涩和不堪。
沙利最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彼得一心想离开巴斯,这又能改善什么。他猜是因为威尔要上大学了,事情在变化,如果他想离儿子近一些也情有可原。当然,在大都市里会有更多的教学机会,但如果他搬到纽约市,这似乎是他的计划,那儿也会有更多的竞争,不是吗?他的生活成本会一下子翻上三番,甚至更糟。但当沙利提出这些问题时,彼得——毫无意外——不予理睬。“爸爸,”他说,“威尔走了,我为什么还要待在这儿?为了给你养老吗?”这根本就不是沙利的意思。他其实是想让彼得知道,如果他不是特别想,就没有必要这么匆忙地离开,如果彼得想继续住贝丽尔小姐楼下的大房间,沙利会很乐意住在房车里。那样的话,威尔到了假期就可以回来住。事实上,他很愿意当场签合同把房子转给彼得。毕竟,他总有一天要走的,这可能比他想象中的还快。“我要这房子干吗,爸爸?”时机对时,可以卖了它啊,沙利建议说,但彼得却露出他那种会意的微笑,这往往让沙利非常恼火,因为这笑意味着彼得觉得沙利在骗他。
但另一方面,他真的能责备彼得怀疑他的动机吗?如果哪天卡尔·罗巴克搬出了楼上的房间——那间房是沙利的女房东活着时沙利住的——到时沙利再搬进去也合情合理,他能想象到时彼得会有多么紧张吗。也许他是没有想过让彼得或其他什么人来照顾他,可他儿子不知道这一点。儿子可能想的是,保不齐哪天他摔倒了,摔了屁股,或者中了风得坐轮椅。如果有任何类似的破事发生,他不会责备彼得想要搬得远远的。
而且,如果彼得搬到纽约,沙利会想念他在走廊走路的脚步声,会想念他车的引擎在车道冷却时的滴答声,会想念他突然出现在白马酒吧,坐到那个吧凳上。当然,他也会想孙子。其实,他和威尔倒是有更多共同之处,当然威尔的父亲毫无疑问也感觉到了这一点。这男孩可能继承了彼得的智慧、好相貌和迷人的特质,但他更强壮,他是个很有天赋的三项全能运动员。在他三年级时,他是橄榄球队的开球中后卫。当看到威尔和他一样把对手打得屁滚尿流时,沙利偷偷笑了。这孩子抢球干净利落,他从不伤人,但能让对手牙齿打战。最令他欣慰的是,十年前,威尔刚到巴斯的时候,他还是个胆小到甚至害怕自己影子的孩子。
彼得似乎对儿子的强健也很自豪,尽管他并没有坦率地承认这点。他很高兴看到威尔爱沙利,但他似乎也不急着让儿子去崇拜或者效仿他。彼得甚至认为,威尔有必要冷却下他对祖父如何掌控世界的狂热兴趣,唯恐工具袋、吧凳这些东西扎根进儿子心里。实际上,让威尔在达到合法饮酒年龄之前离开巴斯,是彼得的用意之一,可能也是想要保证,他在白马沙利旁边的吧凳不会被威尔继承吧。
沙利认为,彼得所做的这一切都是露丝所反对的,用她自己的话说,这就是无法对他产生好感的原因。
“如果你心神不定的话,为啥不出去一阵子,休个假?”她建议,“换换环境可能才是你需要的。”
“休假?我本来就退休了。”
她耸耸肩。“我不知道。离开巴斯。离开白马。离开这个地方。”说到这儿,她做了个横扫一切的手势。“可能也需要离开我。离开彼得。你不离开他,他怎么会想你?”
她似乎想说的还有,他不离开她,她怎么会想念他。“那我去哪儿呢?”他说,想知道她脑子里在想什么。
“挑个地方呗,”她说,“阿鲁巴岛。”
他哼了一声。“我跑到阿鲁巴岛干吗?”
“你在这儿干吗?”
“你是说在巴斯?”
“不,我是说这儿。比如说现在,在这个餐馆。”
沙利涌上一股替自己辩白的冲动,这让他自己也很惊讶。“我以为我在帮你。”绝大多数早上都是他在帮她开门,需要的时候,帮忙添添烧烤盘或烤瓷盘。“但如果我碍了你的事的话……”
“你是碍了自己的事,沙利,”她说,“一直如此。你知道我很感激你的帮助,但……”这一次,当她摸着他的脸颊时,这感觉就不那么愉悦了,也许是因为他很确定这姿态是源于怜悯。
“好吧,就阿鲁巴岛吧,”他说,“你可以一块来,既然你觉得那是个好主意。让杰妮管一两周店好了。”杰妮也能胜任。她可能确实是根令人生厌的刺,但她有她妈妈的职业道德。一周要在海蒂之家值三到四次白班,还要在苹果蜂上四到五次夜班,偶尔博蒂在当班时生病,她也会在白马应急。
露丝朝他咧嘴笑。“难道还要邀请上我丈夫?”
“我个人是不想的,但如果这对你很重要的话……”
她揉着太阳穴,好像得了偏头疼。“他最近的行为很怪异。”
“怎么了?什么情况?”
“他变得很体贴。几乎是……处事周到了,”她解释说,“这搅乱了我的心。我一抬头,就能看到他盯着我看,好像他才注意到我在那儿一样。”她耸耸肩,脸上的表情看上去像是羞愧。但并不是,应该是吗?他们曾经这么多年的情人关系,露丝也从来没有流露过丝毫羞耻。她也不恨她丈夫,即使是早期她和沙利的感情如火如荼时,她也没提过要离开他。但同样,就沙利所知,她也没觉得自己背叛了那个男人。沙利自己反而有时会有罪恶感,因为扎克虽然是个彻头彻尾的笨蛋,但他人并不坏。“我想尽量对他好些,”她承认,“三十年前我曾经这么尝试过,不奏效,现在可能有用了。”
“那么,”沙利拖着长音,好道出她语焉不详之处,“是因为罗伊·帕迪我才不能再到这儿来,还是因为扎克?”
“我并没有说你不能再到这儿来。”
“你是没有。但你说的是我应该去阿鲁巴岛。”
她没马上回答。“你知道上周杰妮跟我说什么吗?”
沙利把食指放在太阳穴上,闭着眼睛,假装在全神贯注地思考。“等等。别跟我说,是让我去阿鲁巴岛?”
“她说,‘你俩都不发生关系了,他干吗还一天到晚待在这儿?’”
“你怎么回答的?”
“她还说,‘你知道每天早上我听到卧室墙外传来的第一个声音是我母亲前男友的声音,那是什么见鬼的感觉?’”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我说跟她没半毛钱关系,”但她眼睛没看他,“我能多少明白她的意思。”
“我也能。”沙利坦言。
“还有蒂娜。”她的外孙女。“我知道她看起来反应慢,但她并不蠢。她在看。她明白所有的事。”
“是的。”
她将报纸掉了个面。现在贝丽尔小姐正看着她,而不是看沙利了。“你怎么想?”她问,“她那废物儿子会出现吗?”
她指的是小克莱福。他是“终极逃亡”乐园项目的推动者。他用他的积蓄投了资并贷了款,还鼓动其他人做了一样的事儿。结果在最后一秒,当州外的投资者突然撤资,扔下当地的投资人,项目陷入困境时,他跑路了。
“不会了,”沙利说,“恐怕我们见他的那是最后一面了。”
“什么?”她说,很明显被他的语调弄糊涂了,“你在替他难过?你忘了他试过多少次让他母亲把你赶走?”
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因为沙利抽烟。小克莱福一直担心沙利离开时,会留下一个没熄灭的烟头,把房子和里面的贝丽尔小姐烧了。但是,他们持久的冲突之所以加深并非只因为沙利的粗枝大叶,虽然那是事实。贝丽尔小姐和她的丈夫老克莱福看到沙利家里的生活那么悲惨,就欢迎他住到他们家来,像对儿子一样对待他。小克莱福,他们自己的儿子,把那看成是一种侵犯,他甚至觉得,他们可能更喜欢沙利而不是他。成年了以后,他们也互相看不顺眼。沙利经常把小克莱福叫做“银行”,以让他在像海蒂之家这样的地方当众出丑为乐。他知道沙利继承了自己母亲的房子吗?那样就更证实了他当初觉得母亲喜欢沙利胜过亲生骨肉的担忧吧?
“也许是年纪大了,我也变得心软了。”他承认道,从凳子上滑下来,把钥匙放到了兜里。
“看,”她说,“不要弄错了。我之前说的根本不是有关扎克、杰妮、蒂娜,而是……你到这里来根本就不再是为了我。”他正要开口反对,她摆摆手。“我并不是说你不在乎我了。我知道你在乎。但你到这儿来是因为你不知道有什么其他地方可去。最近你只是坐在那儿盯着你的咖啡出神,这样太让我心碎了。还有……”
还没等她说完,从沿街的某个地方传来一声轰隆巨响!这冲击如此之大,以至于饭店的窗户也在咯吱作响。两只水杯从架子上倒了下来,摔得粉碎。一会儿后,地面也在震动,像被挤压了一般,盐罐胡椒瓶沿着柜台又蹦又跳。
“什么鬼——”露丝说。她一边抓住柜台保持平衡,一边看向沙利,期待着他的解释,但他也一片迷茫。两人都呆立了一会儿,直到露丝笔直冲向前门。沙利的反应略慢,但也上气不接下气地跟着,到了门口,他感到心脏怦怦作响。外面,人们从各个商店拥上街道。一辆警车呼啸而过,警笛高鸣。隔壁那家经营不善的瑞克苏尔药店的老板乔可也来到了他和露丝这儿,沙利把手放在膝盖上弯下了腰。
“天呐,”乔克说,“该不会是日本鬼子 又来了吧?”
又来了吧?”
大约半英里外的街道的那一头升起了一团黄褐色的灰尘,直冲屋顶。好多天以来,一直祸害巴斯的那可怕的恶臭突然变得更浓烈了,这让沙利的咖啡差点呛到了嗓子口。
露丝一只手放在他的手肘上。“你还好吗?”
“嗯,没事。”他站了起来,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像个会去——该死的叫什么来着——阿鲁巴岛的人,而不是一个只有着两年甚至一年寿命的人。“我有些头晕。可能是突然从空调间跑到热浪里引起的吧。”也许真的是这样,因为他说完就感觉好多了。
这时卡尔·罗巴克出现在了人行道上。斜纹裤干了,他活跃的本性又重燃了。很明显,吹着吹风机,关着浴室的门,他并没感觉到引发全镇人关注的震动。他推推沙利,压低声音秘密地说:“猜猜我在那儿吹我的老二时在想什么,”这时,他才注意到街上的骚动。“天呐,发生了什么?”
沙利惊讶地发现,他想到了一种可能性。他指着那团黄褐色的云,它正开始膨胀,并慢慢地像以前西部的沙尘暴一样向他们的方向飘来。“问你个问题,傻瓜,”他说,“那边是什么?”
血色从卡尔的脸上褪去。沙利现在可以很肯定他不会再想到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