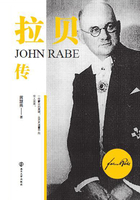
二 北京剪影
拉贝是那么满足地在古老的石头庭院过着宁静而富足的生活。生意之余,领略中国文化的精髓,是他的一大爱好。逛逛博物馆、庙宇、宫殿、市场,他常常会在这里把印象之河中形成的“精美”“高雅”与实物划上等号:青铜器、玉雕、象牙、瓷器、漆器、绘画、书法卷轴、丝绸、挂毯,所有极其古老的一切,让人惊叹,让人赞不绝口。
他带着妻子,去周围的田野和乡村,爬附近葱绿的山坡,享受着北京生活中所有的幽趣和美丽。每年一部分时间,大风把来自戈壁滩的沙尘暴吹在他们身上,但是在其余的时间内,北京以其宽广而清澈的天空、绚丽的色彩,展示出无法形容的永恒和诱人之处。
拉贝最感兴趣的事情,是到古玩市场去。有着辉煌遗迹的古城,虽经历了漫长的岁月,现代商业的畸形丑陋还未触及它,工厂还未损毁其外貌,它是工匠和手艺人的乐园。古董和手工制品充满了市场,拉贝在那里收集了许多铜铸的佛像、瓷器和手工艺品。
这些有着鲜明中国特色的艺术品一直跟随着他,从北京到天津,又从天津到南京,1937年又装运回德国。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它们给了他无限的安慰和美好的回忆。他把它们作为精神象征留给了子孙。1997年,他的外孙女莱茵哈特夫人来南京,向我们展示了这些工艺品的照片,其中不乏有着淡雅花纹的瓷质大花瓶和瓷盘;一个红木的首饰箱,是他自己设计、请人制做的,上面雕刻了拉贝的名字,这是他献给妻子道拉的礼物。莱茵哈特夫人还向笔者展示了挂在她脖子上的一个铜铸小佛像,那是半个多世纪前外公的深情祝福。
拉贝对中国的古建筑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早在18世纪初,德国华肯巴特河上,就有一座比尔尼茨宫,那是德国模仿中国大屋顶元素的第一座建筑。到1773年,德国学者温赤(Lud wig A.Unger)出版了一本书,竭力推崇中国的园林建筑,那小桥流水、曲径斜坡,无一不呈曲线,组成生动多姿而又异常和谐的美。在德国乡村,拉贝曾见到过一些贵族建造的中国乡村别墅。现在,拉贝常常漫步中国古典园林之中,身临其境地细细品味欣赏这种幽凄曲折的建筑之美,心境一如德国文学家歌德那浪漫美丽的诗句:
我想说的就是赏心悦目的游苑,
依依不舍,无法离开。
那里有深谷和高丘……
宝塔、岩洞、草坪、山石和一线天……
处处皆芳草,地地有木樨……
搭起的渔舍和凉亭,
中国——哥特式的洞府、水榭和庭院。
每当有德国客人来,拉贝总要尽地主之谊,竭力推荐他们去参观北京的古典园林和古建筑,领略中国古老文化的精髓。有一次,德国西门子总部派来一位商业审计员胡戈·迪约尼斯先生,这是一位幽默的老先生。拉贝鼓励他去参观一下紫禁城。他们很幸运,一直进入到极少向游客开放的内层宫殿。整个宫殿里,只有他们两名游客,他们静静感受着建筑师想要唤起的印象:当人们穿过这些大厅,靠近皇帝的宝座,会感到自己是那么的渺小。他们登上宽阔的阶梯,到了位于中心的建筑——金銮殿。站在金銮殿前的平台上,视野开阔,可以看到紫禁城里最后一个祥和、孤寂的宫殿全貌。
他们俩都默默无语,向四周眺望,各人都在想着自己的心事。拉贝并非第一次来,可是每次他都会被深深地震撼。突然,迪约尼斯先生从头上拿下他的黑色硬质皮帽,打破了沉默,他说:“拉贝先生,您知道最打动我的是什么吗?”
“是什么?”
“这一切都如此完美地对称,不像纽伦堡,这儿是高高的尖顶,那儿又是低低的尖顶。这一切是如此地匀称!”
拉贝微笑着回答:“您说出了一句经典之言。”他认为这位年老可爱的会计说得很有道理,说出了中国建筑的精妙所在。
拉贝喜爱中国,喜爱这种幽雅的生活。但是美丽的北京也有着太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豪华的宫殿、精美的艺术品之外,更多的是贫穷和落后,以及简易的生活环境。但这并不影响拉贝对这座城市的钟爱。
拉贝碰到过许多近乎荒诞的传奇故事。有一次,在他公司所在的胡同里,竟溺死了一头驴。而看似荒诞的故事背后,其实是有其历史根源的。当时北京的道路基本上是土路。“无风三尺土,微雨满街泥。”北京排水系统百年淤塞,至清末已陷于瘫痪状态。清政府终于认识到北京年久失修,低洼不平的道路不能适应发展需要。他们提出“内政始于道路”,先后拨巨款,派亲信重臣肃亲王善耆督修街道。
拉贝记下了城市街道建设工程中一段稀奇的见闻:西门子北京办事处当时设在苏州胡同内,下雨天路很不好走,市政府为解决下雨天胡同里淤泥堆积问题,清洁道路,想出了一个主意,在胡同的一边挖了一条长长的深约一米的沟。挖出的硬土放在路的另一边,把淤泥填到沟里,那头可怜的驴就溺死在这条沟里。有人对此表示怀疑,拉贝信誓旦旦地说:“我可是亲眼看着驴活活溺死的。谁不相信,谁就要付出代价,夜晚没有灯光的胡同里,这样的事同样可能发生在路人身上!”(2)
他在北京还经历了一场令人谈“鼠”色变的鼠疫。那时,所有听说过鼠疫的人都相信,在一定距离内,病人的气息也可传播疾病,即使注射了疫苗,这样的病在4小时之后就可使人丧命。鼠疫是从哈尔滨传来的,渐渐在北京蔓延开来。在市区地图上,西门子所在的胡同被作为瘟疫嫌疑区用红笔标了出来,他们平静的工作和生活一下被打断了。普弗策和他的家人搬到了德国公使馆居住。拉贝的家也转移到了公使馆,拉贝和另两名职员留守在办公大楼里。每人都注射了疫苗,发烧到摄氏40度,难受得要命。他们准备好了充足的食品,呆在办公室里,严格禁止中国人进入西门子办公大楼。一天,办公大楼前突然人声嘈杂,一个警察请求进来打个电话。在拉贝他们看来,警察是不好拒绝的;他进来后立即给警察总局打电话:“我是警察某某某,我在西门子办公大楼,请求立即派一辆救护车来,毗邻的房子里发现了一名瘟疫病人。”拉贝和其余人,包括警察,都戴上了口罩和鼻罩,如临大敌,站在大门口等着。几分钟后,一辆救护车呼啸而来,车上下来几名全副武装、只露出两只眼睛的救护人员。警察带着他们冲进隔壁房子。一会儿,病人被架着塞进了救护车,如同一只令人厌恶的动物,等待他的命运就是送进隔离房间等死。
拉贝作为旁观者,注视着这一幕,不由摇头叹息说:“这做得太过分了!”病人是一名忠于职守的警察,曾为无数市民提供了帮助,可是在他最需要安慰和帮助的时候,却没有人对他温情地伸出双手,哪怕是给他一些不起作用的安慰。
在与中国人的交往上,拉贝和妻子道拉对此也比较满意。他们并不费力就融入了中国社会,当然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融入,中国淳朴的民风,使他们与中国人相处得十分友好。这期间,他们的一双儿女先后出生。中国成了他们的第二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