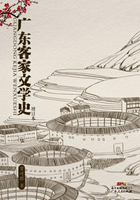
第一节 根在中原
追根溯源,是客家民系的优良传统。客家人的根在中原,客家文学的根也在中原。中原的汉文化是客家文学的源头。
位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以及长江中下游的楚吴地区,对岭南来说都是北方。南迁的汉人由中原而来,带着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在迁徙的过程中,又不断吸收迁徙经过的吴楚地区的丰富营养,从而形成自己的特色文化。文学的表现最为明显,以客家山歌为例,“它随客家先民由中州一带迁来,上承《诗经》遗风,常用重章叠句,尤以双关见长”。 一路风尘一路歌,南迁汉人的歌声保持了中原文化的本质,也不断吸取沿途地域文化的气息,定居岭南山区又有了地方风味,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诗经》中十五《国风》的民歌,运用赋、比、兴的表现手法,一唱三叹,反复歌咏,表现了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它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很广阔,生活气息十分浓厚;它是中原汉文化的结晶。其文化基因在客家山歌中表现得颇为充分。几乎到处都可见《国风》的影子。
一路风尘一路歌,南迁汉人的歌声保持了中原文化的本质,也不断吸取沿途地域文化的气息,定居岭南山区又有了地方风味,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诗经》中十五《国风》的民歌,运用赋、比、兴的表现手法,一唱三叹,反复歌咏,表现了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它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很广阔,生活气息十分浓厚;它是中原汉文化的结晶。其文化基因在客家山歌中表现得颇为充分。几乎到处都可见《国风》的影子。
催人出门鸡乱啼,送人离别水东西。
挽水西流叹无法,从今不养五更鸡。
这是梅县地区家喻户晓的山歌,其意境,其表现手法,其文化氛围,我们都可在《国风》中找到痕迹:
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匪鸡则鸣,苍蝇之声。
东方明矣,朝既昌矣,匪东方则明,月出之光。
虫飞薨薨,甘与子同梦。会且归矣,无庶予子憎。
《齐风·鸡鸣》
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既见君子,云胡不夷!
风雨潇潇,鸡鸣胶胶。既见君子,云胡不瘳!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郑风·风雨》
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
将翱将翔,弋凫与雁。
弋言加之,与子宜之。宜言饮酒,与子偕老。
琴瑟在御,莫不静好。
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
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
《郑风·女曰鸡鸣》
借“鸡鸣”把男女爱情中恋恋不舍的真情生动地表现出来,客家情歌与《国风》真可谓是一脉相承。当然,这相承不是照搬照抄,而是其合理内核的留存,是文化基因的传承。对于客家山歌和十五《国风》的关系,清末著名的大诗人黄遵宪早就有所觉察,他在辑录客家山歌后的《题记》中说:“十五国风妙绝古今,正以妇人女子矢口而成,使学士大夫操笔为之,反不能尔。以人籁易为,天籁难学也。余离家日久,乡音渐忘,辑录此歌谣,往往搜索枯肠,半日不成一字,因念彼冈头溪尾,肩挑一担,竟日往复,歌声不歇者,何其才之大也!”
黄遵宪在这里强调客家山歌和十五《国风》一样,都是真情的流露,是人民的杰作。他并不是专门论述其传承关系,但是,这段话已明确告诉人们:客家山歌继承了《国风》“矢口而成”以表现真情实感的可贵传统。
“诗言志”是《诗大序》中提出的创作原则,它是前人经验的总结,又成为后代文学创作的指针,客家文学的创作实践说明,这一原则使其成为表现客家人思想感情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就拿客家情歌来说吧,就有“引歌”“对歌”“唱和”“发问”“道身世”“讲年龄”“表心思”“提条件”“拒绝”“安慰”“嘱咐”“离别”“相思”“感叹”“谴责”“自慰”等等十分丰富的内容;从过程来说,又有“初恋”“失恋”“热恋”“结合”等不同阶段、不同情态的区别。如果我们把客家山歌予以精选排列,像《邶风·静女》《陈风·月出》《秦风·晨风》《卫风·氓》那种情思、那种意境都可大体表现出来。
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形成的楚文化和吴文化对客家文学也有一定的影响。南迁的中原汉人的迁徙路线已经证明,他们在楚吴地区跋涉过,居住过,他们的语言吸收了许多新的词汇,语音、语调也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变化。从文学的角度来说,以“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为特点的楚辞,则直接启迪了客家山歌。作为与中原歌谣不同的新诗体,楚辞不是整齐的四言体,而是以七言居多,可长可短,灵活多变。在句尾和句中常用“兮”这一语气词。客家山歌中的句式灵活,特别是“哩”“呀哩”“来”的功能,就与“兮”十分相似,只是起停顿或连接的作用。例如:“你系唔肯也好哩,伥也唔敢苦甘你,苦甘人情会得失,检兜好人做呀哩”“颠也狂来狂也颠,牙牙邪邪鬼呀般”,都是在句中或句尾作语助词,本身无义。至于客家文学与吴文化的关系,已有不少有识之士发表了深刻的见解。黄遵宪认为,客家山歌“颇有子夜读曲遗意”; 朱自清在《粤东之风》的序文中也明确指出:客家山歌“一是比体极多,二是谐音双关极多,这两种都是六朝时吴声歌曲的风格”;
朱自清在《粤东之风》的序文中也明确指出:客家山歌“一是比体极多,二是谐音双关极多,这两种都是六朝时吴声歌曲的风格”; 张雪伦的《客家山歌探源》和陈摩人、颜新腾的《客家歌谣溯源,兼论吴歌谣》对吴歌与客家山歌进行对比研究后,得出结论:客家山歌和南朝的《子夜歌》,“两者艺术构思和表现手法可说是一脉相承的”“客家山歌确确实实继承和发展了吴声歌曲”。
张雪伦的《客家山歌探源》和陈摩人、颜新腾的《客家歌谣溯源,兼论吴歌谣》对吴歌与客家山歌进行对比研究后,得出结论:客家山歌和南朝的《子夜歌》,“两者艺术构思和表现手法可说是一脉相承的”“客家山歌确确实实继承和发展了吴声歌曲”。
至于客家文学中的文人创作,其思想内容及其表现手法,更是中原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儒家思想是客家士子的主导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他们的人生理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文以载道”的创作理论,被他们奉为圭臬。他们的诗文作品,或有感而发,抒情言志,或阐明事理,状物探源,思想以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为主,志在有补于世。“学韩学杜学髯苏”(宋湘《说诗八首》)说明杜甫、韩愈、苏轼是客家文人心目中的泰山北斗。然而由于地处岭南,远离中央政权,他们自感地偏人轻,即使如前贤张九龄那样,位居辅宰,仍难免有“孤鸿”“海燕”之感(这种心态,直到洪秀全、孙中山起,才有所改变)。但是,总的来说,就文学家而言,从他们的思想及创作的实践来看,无论是盛唐的张九龄,还是清末的黄遵宪,都不因地处岭南而存在“远儒性”。恰恰相反,中原儒家文化的传统,始终是他们作品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