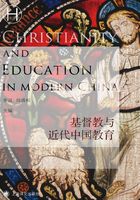
使者的足迹、文明的桥梁: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教育
(前言)
李灵
2016年的金秋十月,上海大学一年一度的菊花展正以婀娜的娇姿、绚丽的色彩绽放出“我花开后百花杀”的傲人气势。一场别开生面的学术会议——“基督教与中国近代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也在校园内的“乐乎楼”隆重地拉开了帷幕。来自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20余所院校,以及英国、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国的共40多位专家学者递交论文参会。除此以外,近40位来自上海大学和当地其他院校的教师及研究生也参加了会议。可以说这是一场学术盛会。
其实,这不是国内第一次以“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教育”为题举办学术会议。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学术界就已经开始关注近代西方宣教士在中国办学的话题。30多年来,包括港台地区学术机构在内举办的以此为话题的会议大大小小有40余次。发表与此话题相关的文章百余篇,出版论文集及专著不下数十本。如果将史学、文学、哲学、语言、政治、社会、科学等学科涉及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教育的文章、著作也算上的话,那就真的不计其数了。
此次举办这样的研讨会依然能够引起学术界重视的原因,诚如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博士生导师马敏教授在大会主题发言中所说:此方面议题的最新研究趋势,强调要打破现代史和当代史的界限,从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内在规律的高度重新审视教会大学的历史对当今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启示,客观全面地看待教会大学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汲取教会大学的办学经验,切实推进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进程。一言以蔽之:百年虽逝,但教会大学对中国社会现代化依然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
从此次会议所收到的40余篇论文来看,主要围绕以下几个主题:一、教会学校与相关的非教会学校的比较研究;二、教会大学是如何融入中国主流社会、开始“中国化”历程的;三、关于教会女子大学的研究;四、从教会学校看基督教对中国教育以及中国社会的影响等。尽管文章的切入点不同,但是都涉及基督教对中国教育的影响以及对近代中国现代化的作用。虽然谈得比较多的是历史话题,实际上却在表露对当代中国教育现状的关怀。
一、使者的双重使命
宣教士们为什么会竭力兴办学校,改善、普及中国近代教育?
19世纪宣教士来华之初,并未有办学兴教的打算,只是由于语言的障碍使得宣教士们实在难以与华人交流沟通,再加上文化的隔阂,华人不论男女老幼对这些宣教士们无不表现出异常冷漠的态度,以至于半个世纪过去了,他们的宣教成效依然甚微。正是迫于这样的窘境,一些宣教士才开始想到是否可以通过提供免费教育的办法首先吸引孩童作为听众。所以,为了能够比较畅通地向中国民众传教,宣教士开始办教会学校。因此,早期教会学校的教育从形式到内容基本上都是以宗教为核心,围绕着圣经和教义而展开。
1877年,西方宣教士在上海举办入华以来的第一次宣教大会,应该被视为西方宣教士改变对华宣教策略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大会总结了西教士们在华70年的宣教经验,不仅对办学兴教有了基本共识,而且还进一步将兴办教育作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举措,因此对当时的教会学校过分强调宗教内容提出了批评。诚如当时美国宣教士狄考文(1)所指出的:这种付印花办学模式无法真正推进传教事业,教会学校的目标应是培养既受基督教影响又能在中国社会发挥重要作用的人才和领袖。(2)狄考文对教会办学的思考之所以能够越出教会的藩篱,看到对中国社会的作用,是因为他意识到“西方文明与进步的潮流正向中国涌来,这股不可抗拒的潮流将遍及全国,许多中国人都在探索,渴望学习使西方如此强大的科学”(3)。这是世界现代化的历史潮流,而狄考文清楚地看到了中国正在努力融入这股潮流,看到了当时正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的新的“形势”,因此才提出“传教士要努力培养在中国这场注定要出现的变革中起带头作用的人才”。狄考文还提出了三个非常重要的洞见:
1.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精通地理学、物理学、化学和天文学知识的中国牧师将取得其他途径无法取得的声誉和影响”,而且“传教士由于掌握了傲慢的中国士大夫无法否认又难以抵御的科学知识,也会取得士大夫的尊敬和信任”;
2.“中国五花八门的迷信邪说很不容易死亡……他们会与基督教相混淆,并玷污基督教”,而教会学校传播“科学和艺术将有效地根除迷信……为基督教的全面胜利开辟一条大道”。
3.“如果虔诚的基督教徒不准备控制和指导这场变革的话,他就会被异教徒所控制。科学和艺术的提高就将落入非基督徒手中,被他们用来作为阻碍真理和正义发展的强大武器。”因此“基督教会的良机,就在于培养能够以基督教真理来领导这场伟大的精神和物质变革的人才”(4)。
狄考文毕竟是个宣教士,言谈之中始终不忘他的宣教使命并不令人意外。但是,令人诧异的是:他深刻认识到中国文化中还存在大量的“迷信”(巫术)成分;认识到中国的士大夫虽然抵抗基督教,但又完全接受以科学知识为核心的西方文明。由此,狄考文断定中国的精英阶层学习西方文明、努力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转型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这也是狄考文在宣教士中推动在中国大力兴办教育的认知基础。
狄考文的见解得到宣教士们的广泛响应,特别是“自由派”传教士。他们认为,教育和宣教的目标是一致的,传教运动“最主要目标是推广基督教文明”(5)。有的甚至认为“教育不仅仅是实现目标之手段,其实本身就是目标”(6)。这样的说法确实有些“极端”,让一些坚守传统宣教路线的保守派难以接受,认为这完全违背了教会办学的初衷,甚至是本末倒置。但是,“教育的主要目标是推广基督教文明”的观点被广泛接受,“宣教”和“教育”本是教会办学体现出的两大功能,自那时起便出现了“此消彼长”的趋势,宣教士们也基本上肯定了自己身负“宣教和教育的双重使命”。再加上西学和西式教育很快为中国的士大夫们所认可,教会学校大步走向社会。1868年,《蒲安臣条约》规定美国人可以在华开办学校。1900年,清政府又宣布“嗣有外人呈请在内地开设学堂,亦无庸立案”(7)。20世纪初,教会办学进入迅速发展的新阶段。尤其在“戊戌变法”前后,“新学”和“西式教育”也确实顺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潮流。
二、教育成为文明的桥梁
1877年,上海举办的宣教大会将对华宣教的指导思想改变为“宣教与教育”并重,宣教士承担的是“宣教与教育”的双重使命,为教会办学就是要“传播基督教文明”成为共识。在一点上狄考文应该是主要推手、功不可没。英国长老会的传教士麦肯齐说:“我非常钦佩狄考文的远见卓识,……让我们尽一切办法给在教会中成长的孩子们提供一个自由的基督教教育,我们的教育办得越来越好,我们教会就会更英明,就会有更大的力量来影响整个中国。”(8)该宣教大会在韦廉臣(9)和丁韪良(10)的建议下成立了“学校教科书委员会”(也称“益智书会”),专门负责策划出版教科书。这样也就尽可能地保证了各校教育质量相对统一。应该说,1877年5月在上海举办的这次宣教大会对于基督教教育在中国的发展起到了里程碑式的作用。从那以后,宣教士在中国近代史上更多地起到了传播西方文明的“桥梁”作用。
如上所述,进入20世纪后中国社会也普遍认同、接受了教会“办学堂、传西学”的举措。同时,教会学校也相应做了一些大的调整,以进一步使这些学校的教育步入正规。譬如,确立了完整的学制;教学内容上增加“中学”的分量,体现“中西并重”;以前教师绝大多数都是牧师和宣教士兼任,1890年后,教师基本上实现了专职专任,相当多的宣教士也因此改行成为非常优秀的教育家;以前生源大多数是社会底层人士,随着以上几个重要变化的出现,社会上层开始关注并将子弟送往教会学校。20世纪初,清廷废除了科举制度后,也有意无意地将西式教育进一步推向高潮。这一切又都反过来刺激学校的办学方针进一步向高精尖方向发展。
1900年至1925年是教会学校发展最快的一段时期。在校学生从1890年不到200人发展到1925年的3500人,到1936年又翻了一倍,达到7000人之多。这一大批由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精英,在当时社会各个领域中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容闳就是其中之一。他不仅自身因为受西学影响而开阔了视野,能够在中西文明之间有了比较和鉴别的能力,因而对自己身处的社会环境和国家的未来有了更加沉重的负担,而且他一生都在致力于帮助中国人留学海外的工作,因为他深信:让更多的中国学生接受西方文明教育是“中国复兴的希望所系”(11)。
提到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我们很长时间以来都对他们接受基督教信仰颇有微词,甚至认为他们接受的是殖民教育,更有甚者在他们头上扣上“洋奴”的帽子。因此,相关文献出现两种情况:一是基本上不提近代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二是如果某人的确在近代对社会或国家做出非常重大的贡献,就绝不提他曾经在教会学校受教育的经历。当然,更不会提起他们基督徒的身份。这种狭隘的民族意识(恕我直言,其实是更加狭隘的夷夏之辨心态下的“种族”意识)一旦和极端的意识形态(极“左”思想)结合起来,就会以极其简单粗暴的方式将宣教士来华、教会办学校等一系列有利于推动近代中国社会进步的举措与近代帝国主义列强侵华的行径划上等号,放在一个锅子里煮。
这种情况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有所改变,学术界开始公开谈论近代教会办学或“基督教教育”这样的话题,去挖掘近代史上具有开创性的办学人物或所办学校的史料,这样的研究在学术界至今兴趣不减。原因就在于,近代西方宣教士在华办学这百年,不仅为当时培养了许许多多活跃在社会各个领域内的精英人才,他们以各自专长和志向为推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发挥了巨大甚至是关键性的作用;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洋务运动”中像唐廷枢等众多翻译皆出自教会学校,推动“戊戌变法”的维新党人的思想观念主要就是受到宣教士传播的西学的影响,康有为之所以倡导维新,主要就是得力于广学会的书籍。梁启超在《康有为传》说:“既出西樵,乃游京师,其时西学初输入中国,举国学者,莫或过问。先生僻处乡邑,亦未获从事也。及道经香港,见西人殖民政治之完整,属地如此,本国之更进可知。因思之所以至此者,必有道德学问以为之本原,乃悉购江南制造局及西教会所译出各书尽读之。彼时所译者,皆初级普通学,及工艺兵法医学之书,否则耶稣经典论疏耳。于政治学,毫无所及。而先生以其天秉学识,别有所悟,能举一以及三,因小而知大。自是于其学力中,别开一个境界。”(12)同样,辛亥革命中的孙中山、陈少白、陆晤东等都是基督徒,陶行知等人也是从教会学校出来的。
“五四运动”期间,教会学校的学生也是这场反帝爱国运动中不可忽视、不容否认的力量。1919年,由于北洋军阀政府的妥协退让,导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努力惨遭失败的消息令举国震惊。5月4日,北京的协和女子大学、协和女医学校、协和看护学校、贝满女中、慕贞中学、培德女校、笃志女校等教会学校的学生冲破层层阻力,高举反帝爱国的大旗义无反顾地加入运动之中。5月7日,这些学校的学生会同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女师附中、中央女校的40余位代表举行集会,表示坚决声援北京大学学生的爱国行为,通电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要求他们拒绝在丧权辱国的条约上签字,以“申公道、抑强权”。(13)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不准该校学生参加“五四运动”,把学生代表江一平、章益等开除。(14)天主教的教会学校学生也义无反顾参加了这场反帝爱国运动,震旦大学、中法学堂、徐汇公学的学生一起参加了上海的“三罢”(罢工、罢课、罢市)斗争。(15)教会学校出来的学生还有相当一部分参加了共产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为什么基督教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仅与普通的中国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具有同样的反帝爱国的情感和立场,有的甚至还放弃了自己的信仰投身共产主义的革命洪流当中?教会大学把西方现代教育模式直接移植到了中国,这是教会大学对近代中国教育做出的最大贡献。现代教育不只要把现代的科学技术传授给了学生,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自由、理性、独立思考的能力。这些学校中的教授基本上都是基督徒,有些曾经还是专职的宣教士。可是,他们并没有只向学生们灌输基督教信仰,而是教会学生如何在信仰、政治、社会等观念中学会做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这就是“现代教育”。只有这样的“教育”才能培养出具有“现代”意识的学生,也只有这样的学生才能在走出校门后参与到推动中国社会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
教会学校在中国近代确实起到了传播现代西方文明的桥梁作用。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是近代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群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三、人散曲未尽
从20世纪初国民政府收回教育主权开始,教会学校就已经走进了历史。可是,教会学校所传播的现代文明却并没有走进历史。整整一百年过去了,学术界还在津津乐道这段历史、回顾这段历史,说明教会大学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所起的重要示范与导向作用还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教育。人类历史延续至今,不同的族群在不同社会环境、不同历史阶段创造出了不同的文明形态。但是,任何文明形态一旦进入人类历史就属于全人类,可以为不同族群所借鉴、学习甚至仿效。发展至今的人类历史就是一部不同文明形态之间的交流史。诚如马敏教授的文章题目点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由于当年教会学校(特别是教会大学)把西方近代教育模式直接引入在华办学的过程,所以教会学校在办学体制、教育机构的设置、教学计划的安排乃至课程设计、教学方法及规章制度等诸多方面都着眼于适应、有利于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这就与中国传统的教育完全不同。近代中国受到西方文明的影响,先贤们逐渐形成了一个至今不变的共识,就是努力使中国从传统社会转型。对于这个转型的认识也有一个从技术层面(洋务运动)逐渐向政治体制层面(戊戌变法、宪政改良、辛亥革命、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革命)深入的过程。现在,我们也逐渐意识到政治制度(政治体制)背后的文化心理和宗教信仰的影响、作用。通过对教会学校不断深入的研究,我们也许还可以发掘得更深,找到更多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从而使我们的大学教育更具有现代性、前瞻性、全球性。
李灵
2017年8月
(1) 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 1836—1908),美国长老会来华传教士。1864年到山东登州(今蓬莱),传教40多年。又创办中国境内第一所现代高等教育机构文会馆,传播西方的科学和文化,以后规模不断扩大,为今日著名的齐鲁大学的前身。
(2) Calivin W. Mateer, “The relation of Protestant Missions to Education” in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10-24, 1877, pp. 171-180. 转引自史静寰、王立新:《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知识分子》,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3页。
(3) 同上,第43页。
(4) Calivin W. Mateer, “The relation of Protestant Missions to Education” in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10-24, 1877, pp. 171-180. 转引自史静寰、王立新:《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知识分子》,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4页。
(5)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63页。
(6) 转引自史静寰、王立新:《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知识分子》,第45页。
(7) 学部:《咨各省督抚为外人设学无庸立案文》,《学务杂志》第6期。转引自史静寰、王立新:《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知识分子》,第47页。
(8)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10—24, 1877, p. 203.
(9) 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 1829年12月5日—1890年8月28日),苏格兰来华传教士,最初由伦敦会派遣来华,以学术研究、翻译工作和创建同文书会著称。他是李提摩太的前任。
(10) 威廉·亚历山大·巴尔森·马丁(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1827年4月10日—1916年12月17日),汉名丁韪良,字冠西,美国长老会派至中国的传教士。在中国生活了62年(1850—1916,其间有4年不在中国),曾长期担任中国著名教育机构北京同文馆的负责人,是当时的“中国通”。1898年起被清朝皇帝任命为京师大学堂首任总教习,也就是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
(11)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22—23页,转引自史静寰、王立新:《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知识分子》,第4页。
(12) 梁启超:《康有为传》,第9页。转引自史静寰、王立新:《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知识分子》,第175页。
(13) 黄新宪:《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变迁》,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44页。
(14) 李子迟主编《学府往事》第一卷。
(15) 宴可佳:《中国天主教》,五洲传媒出版社2004年版,第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