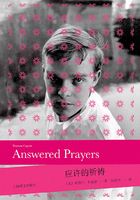
第2章 编者手记
1966年1月5日,杜鲁门·卡波蒂与兰登书屋签署一部新书合约,拟名《应许的祈祷》,预付版税25000美元,交稿日期:1968年1月1日。杜鲁门声言,该小说将是普鲁斯特的杰作《追忆逝水年华》之今日再现,并将一览欧洲及美国东海岸豪富——部分是贵族,部分是咖啡馆社交界名流——的小世界。
1966年的杜鲁门可谓是志得意满。在他签约《应许的祈祷》两个星期后,《冷血》即以书籍形式出版,并为他赢得巨大的声誉和普遍的赞许。随后一周里,作者照片登上几家国家级杂志封面,且在每期的周日书评栏目中,他的新作都风骚独领。那一年时间里,《冷血》销量超过300000册,三十七个星期位列《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单。(最终,除两部自助类书籍外,该书1966年销售量超过了所有其他非虚构类书籍;时至目前,该作已有外语版本二十多个,并且单在美国,销量就已达约5000000册。)
这一年里,杜鲁门骤然之间变得无处不在——大量的访谈,无数次现身电视脱口秀节目,在游艇上与豪华乡间别墅中度假——尽享名望与财富之乐。这段令人陶醉的好时光的巅峰是1966年11月末,他在纽约广场酒店为《华盛顿邮报》出版人凯瑟琳·葛兰姆举办的那场至今仍记忆犹新的“假面舞会”。这家全国性大报对于该舞会报道的篇幅,不亚于报道一次东西方首脑峰会。
杜鲁门觉得自己有理由享受一下这样的放松,他大多数朋友也这样认为;为了创作《冷血》,他花了几近六年时间用于调研与写作,这也成了一段在他心中留下创伤的记忆。不过,尽管心猿意马,他仍时不时在此期间谈起《应许的祈祷》。然而,在随后几年时间里,除了一些短篇和杂志文章,他并未着手这部小说的写作;结果,1969年5月,最初的合同为另一份三本书的协议取代,交稿日期也延至1973年1月,预付版税也大幅度提高。1973年年中,交稿期限延至1974年1月;六个月之后,再次延至1977年9月。(后来,1980年春,稿约最后一次修订,明定1981年3月1日交稿,并进一步追加预付版税至1000000美元——交稿后即刻付酬。)
这几年里,杜鲁门仍出版了几部作品,尽管其大多数内容都写作于1940和1950年代。1966年,兰登书屋出版了《圣诞回忆》——最初写于1958年;1968年,《感恩节来客》——1967年发表于某杂志的一个短篇小说;1969年,《别的声音,别的房间》二十周年纪念版,新写言辞优美的前言一篇——此为他的第一部小说,1948年的成名之作;1973年,一个集子:《犬吠》——一共就三篇文章,且是多年前旧作。唯独《致变色龙的音乐》里面有新的内容,包括小说和非虚构作品。该书定于1980年出版,一些人——包括他的朋友和评论家——觉得赶不上他前期的作品。
且听听杜鲁门自己谈一谈他这一时期的情况吧。在《致变色龙的音乐》前言里,他写道:
四年中,大致从1968年到1972年,我大部分时间都在阅读、挑选、改写和编目1943年至1965年期间我自己的书信、日记和日志,以及他人的书信(其中有数以百计的有关场景与谈话的详细记述)。我原有意将其中相当部分的材料用在一部计划已久的书中:一种非虚构小说的变体。我将这部书命名为《应许的祈祷》——书名来自圣特雷莎[1]的一句话:“让人流泪更多的是得到应许的祈祷,而非未应许的祈祷。”1972年,我开始该书的写作,首先从最末一章着手(知晓故事的走向往往让人心里踏实)。然后,我写了第一章“原姿原态的怪物”。然后第五章“严重有辱智商”。然后第七章“巴斯克海岸餐厅”。我继续以这样的方式随机写作不同的章节。之所以我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整个故事情节——或者更准确地说,这一段段的情节——都是真实的,所有的人物也都属实:记住所有这一切并不难,因为我不曾有任何的编造。
最后,1974年末和1975年初的几个月里,杜鲁门给我看了《应许的祈祷》的四章——“莫哈韦沙漠”[2]、“巴斯克海岸餐厅”、“原姿原态的怪物”和“凯特·麦克劳德”——并宣布打算将它们发表在《时尚先生》上。我对这计划表示反对,因为我担心他会过早透露这部作品太多的内容。但自以为是宣传专家的杜鲁门却不予理会。(要是同为作者的朋友和知己的本内特·瑟夫还在世——他已于1971年去世——或许我们合力表示反对还能劝说住杜鲁门,虽然我仍对此表示怀疑;他觉得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结果证明,他并不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莫哈韦沙漠”一章首先面世,并引来了一些议论;然后第二篇,《巴斯克海岸餐厅》却引爆了一颗炸弹,在杜鲁门打算刻画的那个小圈子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几乎他在这世界上所有的朋友都因为他几乎毫无掩饰的披露隐私而与之绝交,其中很多人再没跟他说过一句话。
杜鲁门公开声称,自己不会为这样的愤怒吓倒(“他们指望如何?”有人曾听他说,“我是一名作家,什么我都拿来作为素材。难道所有那帮人都以为,我与他们为伍仅仅就是为了取悦他们?”),不过显然,他被这样的反应给镇住了。我确信,1976年在《时尚先生》发表“原姿原态的怪物”和“凯特·麦克劳德”之后,显然他至少是暂时停止了《应许的祈祷》的写作,这即是其中原因之一。
自1960年我们初次晤面到1977年,杜鲁门和我经常见面,无论是在办公室还是工作之余。他写作《冷血》的时候,我们一同两度去堪萨斯州旅行,并曾去新墨西哥州首府圣达菲待过一个星期。冬天的时候,我还去加州棕榈泉拜访过他三四次——有几年时间,他在那地方拥有一套别墅;此外,他在长岛东岸近海一个叫萨加波纳克的小型农业区拥有一套别墅,我碰巧也在那里租过一套房。
从专业的角度讲,这期间我为杜鲁门做的工作并不算难。(比如,《冷血》的编辑工作基本上全由肖恩先生和《纽约客》其他同仁经手——《冷血》最初分四期于1965年10月至11月刊载于该杂志。)不过,我们的合作仍大有裨益。回想起1975年的一个下午,杜鲁门给我读“原姿原态的怪物”一章的情形时,我仍是由衷的高兴。我用一个晚上看完了该章,发现除一处小注释有误外,它几乎是完美无瑕。第二天早上他打电话来问我的意见,我振奋无比,不过同时也提出了自己吹毛求疵的一点意见——读者初见维多利亚·塞尔夫小姐仅半页之处,她在对话中使用的一个词。“她不可能用那个词,”我告诉杜鲁门说;“她可能说的是……”(我忘了自己建议的替代词语)杜鲁门开心地大笑。“我昨晚重读了一遍这章,”他说,“唯有一处我想改一改。我这会儿给你电话,正是要告诉你把那地方改为你刚才建议的那个词。”鉴于作者与编辑这一特殊关系,如此的互相赞许实属罕见。这并非自我陶醉;而是我们为彼此所取悦。
我在这里再次引用杜鲁门《致变色龙的音乐》前言里的接后几行文字吧:
……1977年9月,我的确停止了《应许的祈祷》的写作。不过,这与该作已发表选篇所引发的公众反应并无关系。我中止写作,是因为自己陷入了一大堆的麻烦之中:同一时间里遭遇到创作危机和个人危机。鉴于后者跟前者并无关系,或关系甚微,所以在此仅需谈谈创作方面的紊乱。
此时此刻,虽然这是场折磨,我却很高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毕竟,这件事彻底改变了我对于写作的领悟,我对于生活与艺术及其二者平衡关系的态度,以及我对于何为真实与何为真正的真实之间异同的理解。
首先,我觉得大多数的作家,甚至是最优秀的作家,都存在写得太多的问题。我倾向于少写。简明,清澈,如一条乡间小溪。但我感觉自己过去的写作越来越过于厚重,我常常花三页纸的篇幅才取得仅需一段文字就能达到的效果。我一次又一次地阅读已写就的《应许的祈祷》的所有篇章,我开始疑惑丛生——并非是怀疑写作的材料或我的写作方法,而是文字本身的质感。我重读《冷血》,也是这同样的反应:其中太多的地方,我都未尽自己所能,没能将其潜势完全传递出来。慢慢地,但带着越来越急迫的警觉,我读完了自己曾发表过的每一个文字,这时我确定,在我写作生涯中,我从不曾——一次也没有过——将材料所蕴含的能量及其令人震颤的美淋漓尽致地释放出来。甚至就算是不错的文章,我发现自己写作才能的发挥也从不曾超过一半,有时仅只三分之一。为什么呢?
数个月的冥思所得出的答案简单却并不十分令人满意。无疑,这并不能让我的沮丧减轻一分;相反,却是加重了这种沮丧。因为,这答案引出来了一个显然无法解决的问题。如果我不能解决此问题,我也就可以放弃写作了。这个问题便是:一个作家,如何才能成功地在某个单一形式中——譬如短篇小说——融汇他所掌握的所有其他写作形式?因为,这就是为什么我的作品常常亮度不足的原因;电压在那里,我却将自己囿于当下我正运用的那一种文体形式的相应技巧,而非充分运用自己所掌握的各式写作技巧——所有那些我从电影脚本、戏剧、报告文学、诗歌、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中学来的技巧。一个作家理应在同一块调色板上,综合调制他力之能及的所有色彩、所有才华(而且,在合适的情况下,对它们同时加以运用)。但何以做到这一点呢?
我又回到《应许的祈祷》的创作中。我去除一章[3],改写另外两章。[4]我取得了改善,确确实实的改善。然而事实却是,我不得不回到幼儿园去。于此,我再次押下一个令人憎恶的赌注!不过我却非常兴奋;我感觉有一个看不见的太阳在我头顶照耀。只是,我初始的这些实验还显得笨拙。我真切地感觉自己就像一个手里拿着一盒彩色蜡笔的小孩。
遗憾的是,上面两个摘录片段中,杜鲁门所说的一些东西却不能照单全收。例如,在作者死后,尽管他的律师与文学遗嘱执行人艾伦·施瓦茨、他的传记作者杰拉尔德·克拉克以及我本人彻底清理过他所有的财物,但他所提及的信件、日记或是日志,几乎一件也不曾见着。[5](这尤其能证明他撒谎,因为杜鲁门是个敛物狂;他几乎什么东西都会保存下来,也没缘由会毁掉这些文件资料。)此外,关于《严重有辱智商》,或者他在前言中宣称首先写就的该书最后一章,也没见任何证据。(最后一章题名“神父弗拉纳根之通宵黑鬼娘娘洁食咖啡馆”;另外的篇章,他在跟我和别的人交谈中时不时提及的其他章节还有“游艇及其他”和关于好莱坞的一章“奥德丽·怀尔德唱歌了”。)
1976年之后,杜鲁门与我的关系逐渐恶化。我隐约感觉,这始于他意识到我不赞成他在《时尚先生》上分次发表那些文章是对的,尽管我自然是从不曾指责过他。他也可能是意识到自己写作才能的衰竭,又害怕我的评判会太过严厉。此外,他肯定也为《应许的祈祷》进展缓慢而感到内疚和紧张不安。最后的几年里,在关于这部小说进展的问题上,他似乎着意在糊弄我和其他好友,而且甚至包括一般公众;至少有两次他对访谈者宣称刚刚完成书稿,并已交由兰登书屋,六个月内便将出版。之后,我们的公关部和我就会接到铺天盖地的电话。对于这些电话,我们只能回答说还没见着书稿。很显然,杜鲁门肯定是焦灼万分了。
侵蚀我们关系的最后一个因素是1977年以来,杜鲁门越来越依赖于酒精和毒品。如今,我终于意识到,那时我本应对他所处的困境给予更多的同情;可是,我却只看到才华如何被浪费,看到他自欺欺人的行为,看到无尽的散漫与混乱,看到他常常凌晨一点打电话来是如何的不可理喻——最根本的是,我自私地为自己失去了这位诙谐、喜欢恶作剧、十六年来一直相处愉快的同伴而深感懊丧,却对于他日益加重的痛苦少有关切。
关于《应许的祈祷》丢失的三章有三种推测。第一种推测是,手稿已经完成,要么是藏于某处的保险箱里,要么是被某位前任恋人出于恶意或为求谋利而握在手中,或者甚至是——最近有传言——杜鲁门将手稿放在了洛杉矶灰狗公共汽车站的一个储物柜里。但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这些脚本也益愈显得不足为信。
第二种推测是,1979年《凯特·麦克劳德》发表后,这本书杜鲁门压根儿没再写一行字,部分也许是因为他被公众——以及私人朋友——对于那些章节的反应所击垮,部分也许是因为他逐渐意识到自己永远不可能企及当初为自己设定的普鲁斯特水准。这一说法最具说服力,其理由至少有一点:杰克·邓菲——杜鲁门最好的朋友、三十多年的伙伴——也这么认为。不过,杜鲁门极少跟杰克讨论他的作品。而且最后一些年里,他们更多时间是各行其是,很少在一起。
第三种推测——对此,我有保留地持赞同意见——杜鲁门实际上的确写了至少上面所提及篇章的部分内容(很可能是“严重有辱智商”和“神父弗拉纳根之通宵黑鬼娘娘洁食咖啡馆”),但在1980年代初期的某个时刻,故意又把它们毁了。对这一说法有利的是,至少有四位杜鲁门的朋友声称读过(或听作者向他们朗读过)本书中三章之外的一章或两章。当然,他也曾让我确信还有更多的手稿存在;在他生命的最后六年里——当时他因为毒品或酒精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常常几近于思维混乱,语无伦次——他在午餐时无数次和我极其详细地谈起四个丢失章目里的内容。讨论之细致,甚至于他每每引用的同一人物对白总是一字不差,尽管我们的讨论会相隔数月甚至数年之久。事情通常都是这样一个套路:当我问他讨要我们所讨论的篇章时,他会答应说隔天就寄来。到这天天黑,我给他打电话,杜鲁门又总说正重新打印,周一就寄过来;到周一下午,他的电话再无人接听,而且他也会消失一个星期或是更长时间。
我赞同这第三种推测,并非是因为我不愿意承认自己轻信受骗,而更是因为杜鲁门对那些篇章的描述太具说服力。当然,有可能那些文句不过是存在于他大脑中,但我们很难相信,在某个时节,他不曾在纸上将这些文字写下来。他对于自己的作品相当自得,但同时也超乎常人地客观。因此,我怀疑在某个时候,他将本书三章之外的所有文字内容彻底毁尸灭迹了。
唯一知道事情真相的,只有一个人,而他已经死了。愿上帝保佑他。
——约瑟夫·M·福克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