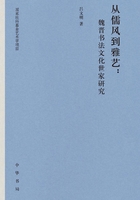
第二节 儒学嬗变与魏晋文艺精神的崛起
自汉末以来,随着儒家思想的式微和道家、法家等思想的崛起,儒学失去了原来那种源自政治权力的强制推行力,士人对儒学的态度发生明显变化。此时,儒家思想内部也开始发生裂变,旧思想逐渐被扬弃和改造,而新思想从旧思想中生发出来,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曹魏正始年间出现了玄学。玄学的兴起使士人的思想高度解放,这种解放引发的自由精神是整个魏晋时期文艺精神崛起的关键。
一、玄学兴起与文艺精神的涌动
汉末儒学分化与裂变带来的直接结果是思想的多元发展,儒学不再是一枝独秀,道家、法家等思想纷至沓来,形成思想文化领域的新格局。然而,儒学本身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因为它的根系实在太发达,还没有到了要完全烂掉的地步。但是,儒学此时必须进行改良,否则它将失去蓬勃发展的生机与活力,因此,借助其他学说和思想对儒学进行改造的活动自汉末至魏晋从来都没有停止过,直至最后援道入儒,推动了玄学的产生。
东汉末年,朝廷暗弱,四方诸侯并起,群雄割据的局面逐渐形成,汉家政权名存实亡,再加上党锢之祸的影响,士大夫在朝廷里逐渐失去了政治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原来致力于维护皇权的士人开始改变态度,他们不再纠缠于朝廷政治的是是非非,转而开始讨论形而上的哲学问题。陈寅恪言:“大抵清谈之兴起由于东汉末世党锢诸名士遭政治暴力之摧压,一变其指实之人物品题,而为抽象玄理之讨论,启自郭林宗,而成于阮嗣宗,皆避祸远嫌,消极不与其时政治当局合作者也。”(45)这样的转变既是时代使然,同时也是清议自身发展逐渐趋向高深和抽象的结果,从某种程度来说,这是哲学思辨发展至成熟的表现。曹魏中期以后,随着国家政权的暂时稳定,士人开始对天地万物的有无问题进行探讨和辩论。他们的讨论实际是以老庄融会儒家思想,援道入儒,充满了哲理和玄机,因此被称为玄学清谈。汤一介言:
魏晋玄学是指魏晋时期以老庄思想为骨架企图调和儒道,会通“自然”与“名教”的一种特定的哲学思潮,它所讨论的中心为“本末有无”问题,即用思辨的方法来讨论有关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的问题,也就是说表现为远离“世务”和“事物”形而上学本体论的问题。(46)
这种清谈追根溯源可与汉末清议相联系,但却一反清议品鉴人物和抨击朝政的现实性,转而论说宇宙自然和天地万物。当然,清谈还只是这一时期玄学发展的初级表现,王弼、何晏等人对《老子》《庄子》《周易》等经典进行的新注解和阐发,才是玄学中最重要的内容,并逐渐形成一种学术风气,开新学问之先河。
王弼首先进行了关于有无问题的思考。他将《老子》中具有物质性的“道”转化为非物质性、具有逻辑意义的“无”,认为天下万物都是“有”,皆本于“无”。这里的“无”是一种抽象概念,没有确切的指向和表征。《三国志·魏书·钟会传》注引何劭《王弼传》云:
时裴徽为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见而异之,问弼曰:“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也,然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者何?”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无所不足。”(47)
王弼的理论虽然还仅限于思辨层面,但已经使人们思考和想象的空间无限拓展,思维开始具有一定的发散性。他接下来进行的关于名教与自然关系的论述则使哲学思辨开始贴近现实生活。孔子与老子被认为是最早的名教与自然的代表,孔子强调礼治,而老子主张无为。西汉董仲舒建立的儒家思想体系,在孔子礼治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等级和名分,使名教思想达到极致。但是,这样的思想体系随着汉末儒家思想的分化与裂变而逐渐濒临崩溃的边缘。于是,王弼从“以无为本”的哲学体系进一步延伸,认为自然是本、是体,名教是末、是用,自然与名教是本末体用的关系,二者在逻辑上是统一的。王弼主张“举本统末”,用自然统御名教,只有如此,已经分崩离析的名教才能逐渐归于平静。王弼的思想对于当时的政治统治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乱世之后的国家重新走向稳定和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何晏与王弼的思想非常接近,也是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但何晏更加直接地挖掘道家思想。他主张以老庄思想为体,以儒家名教为用,认为老子也是圣人,主张从崇敬自然中建立一种和谐自在的社会秩序。《世说新语·文学》“何晏注《老子》未毕”条注引《文章叙录》云:“自儒者论以老子非圣人,绝礼弃学。晏说与圣人同,著论行于世也。”(48)何晏将老子与孔子放到等同的地位,这实际是对儒、道两家思想的打通,援道入儒在何晏这里得到实际性开拓,儒、道融合有了突破性进展。陈明说:“作为玄学最高范畴,‘无’这个否定性概念,消解的是经学中的道德之天。”(49)何晏实际是在用道家思想消解儒家思想,以使儒家思想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时代形势,这其实就是对儒家思想的改良。这样的改良指向的是人的精神自由,对士人自由思想的出现具有重要的启蒙作用。
王弼与何晏的学说首先稳定了人心,使士人的思想逐渐归于平静,继续围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而奋斗。但是好景不长,正始十年(249年),一向标榜名教至上的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掌握魏国政权。对于司马氏表面尊奉名教实际却要篡权的险恶用心,许多士人都表现出鄙视和不满。于是,阮籍、嵇康等开始强调名教与自然的对立,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这一思想既是对王弼、何晏思想的进一步发挥,同时也是他们与山水亲近后情感开始爆发的表现。汉魏时期的高门大族大多拥有山林庄园,《后汉书》中仲长统自论其志云:“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匝,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50)与政治绝缘而亲近山水,使士人的思想进一步解放,他们的内心不再被俗事和烦恼羁绊,而是沉浸在晤对山水的哲学玄思中,或静处以默,或高谈阔论,这种状态对于文艺精神的振奋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郑振铎评价这一时期的文学说:“玄谈的风气也扭转了汉人的酸腐的作风,而回复到恣笔自放,不受羁勒的自由境地上去。”(51)儒学精神影响下的文人士大夫,思维偏重于理性,而文学却是感性的,所以,两汉时期政治上非常有作为的士人大多无文学名作传世,即或有之,也多是带有一定文学色彩的政论文章,纯文学作品还比较少。当然,这一时期的文学与哲学还未完全分开,当时的政论文即是文学,但这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因为作品中还缺少浪漫的一环。从汉末开始,文章的风气为之一变,文学与哲学开始分离,真正的文学开始出现,“建安七子”这一具有独立品格和自由精神的文学群体横空出世。到了竹林时代,不仅仅是文学,整个文艺世界都开始高度自由和解放,“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对于整个士族阶层来说都是一种新风尚,回归自然成为一种风气,名教被彻底抛诸脑后。
从这个意义上说,玄学对于文艺精神的催发和振兴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章太炎说:“玄学者,固不与艺术文行牾,且翼扶之。”(52)阮籍和嵇康既是音乐家又是诗人,他们在王弼和何晏之后对玄学思想进行了文艺创作的实践检验,玄学与文艺开始发生联系。如阮籍的《首阳山赋》,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而不食周粟,本来是作为维护旧纲常道德的典型,但在阮籍笔下却遭到强烈批判。可以看出,玄学思想的影响使阮籍对于个体生命和精神自由都极为看重,他以此赋来表达对司马氏的不满。陈去病言:“独阮步兵忧时悯乱,凄怆不平,作《首阳山赋》以自标亮节。足为当途后劲,固不仅咏怀诸什,横厉无前已也。”(53)这样情感丰富的诗文此前是极少见的,阮籍虽处于压抑和忧闷中,但其内心的情感是那样充沛,可以想见,如果任由他随意抒发,其诗文将出现怎样的境界!阮籍还创作了《咏怀》诗八十二首,以表达内心的不满与彷徨。在诗文中寄托情感是这一时期文人诗歌的主要特点,章太炎对此有深刻的认识:“本情性限辞语,则诗盛;远情性喜杂书,则诗衰。”(54)
嵇康的《述志诗》则主要描写自己身为曹魏宗亲而不容于司马氏,他表面上忍气吞声,而内心却向往逃遁和隐逸。当写到“慷慨思古人,梦想见容辉,愿与知己遇,舒愤启其微”(55)时,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达到顶峰。当他最后赴死时,在断头台前的从容和坦然将其思想中的自由精神诠释得淋漓尽致。他不再有任何牵挂,也不再因为害怕司马氏的迫害而小心翼翼,而是从容地弹奏《广陵散》,艺术情感的表现达到极致。明代王世贞有感于斯:“每叹嵇生琴夏侯色,令千古他人览之,犹为不堪,况其身乎!”(56)而这些情感就是从玄学影响下的思想解放中涌来,最终成为文艺精神的灵动。
不仅是文学,这一时期的文艺发展在深层次上都与玄学密不可分。比如书法,曹魏时期的洛阳已经开始出现新书风,卫恒《四体书势》云:“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57)邯郸淳是汉末最著名的篆书家,《三国志·王粲列传》注引《魏略》曰:“淳一名竺,字子叔。博学有才章,又善《苍》《雅》、虫、篆、许氏字指。”(58)陈思《书小史》亦云:“(淳)志行清洁,才学通敏。书则八体悉工,师于曹喜,尤精古文、大篆、八分、隶书。自杜林、卫宏以来,古文泯绝,由淳复著。”(59)正始年间的《三体石经》(图1-1)为曹魏官方所立,却已抛却邯郸淳古法,可见这一时期的篆书已经在推陈出新。此时,楷书和行书等新字体更在钟繇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且这两种新字体已经得到官方认可并广泛使用。而草书则出现了卫瓘的“草藁书”,卫瓘继承张芝草法,同时参以其父卫觊之法,使草书出现了迥异于前人的风格。以上所述各种变化都是曹魏时期书法变古为新的动作,这些变化出现的背景就是儒家思想的裂变和玄学思想的产生。可以想见,当时文艺的各个领域都在酝酿着这样的新变,正像喷薄而出的思想潮流一样。

图1-1 三国魏《三体石经》(局部)
引自孙伯翔主编《中国书法全集·三国两晋南北朝碑刻摩崖一》,荣宝斋出版社,2007年。
这种文艺革新的思想缘起就是“以无御有”和“越名教而任自然”,即思想上的超越有限而追求无限。嵇康云:“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60)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人文精神,士人的思想不再为外物所累,而是任由情感宣泄和表达,“各任其性,苟当其分,逍遥一也”(61)。这样的思想意识与文艺发展联系在一起,思想的倾泻便在文艺作品中全然表现和流露,所以,这一时期的文学艺术几乎都是赤裸裸的情感宣泄。艺术家们在这种表达中无拘无束、自在潇洒,正如他们自由的思想世界,笔触的指向是浩瀚的宇宙和自然。李泽厚说:“由于超越有限而达到无限是玄学的根本,同时对无限的达到又是诉之于人生的体验的,这就使玄学与美学内在地联系在一起了。”(62)士人的思想追求在本质上是无法实现的,所以只能诉诸情感和想象,“要求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以成其迈远之狂狷的情操”(63)。因此,在思想的纵横驰骋中发现自然的美,这是魏晋士人的思想指向,而这种指向与文艺精神的无限追求是殊途同归的。
二、名士的境界与文艺精神的升华
汉末以来,社会动乱,思想解放,有思想有才学而又言行不俗的名士比比皆是,这成为当时社会的奇观。《世说新语·文学第四》“袁彦伯作《名士传》成”条刘孝标注曰:
宏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辅嗣为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刘伯伦、阮仲容、王濬仲为竹林名士,裴叔则、乐彦辅、王夷甫、庾子嵩、王安期、阮千里、卫叔宝、谢幼舆为中朝名士。(64)
魏晋时期名士很多,但境界却各有差别,缪钺言:“正始名士只言玄理,而竹林名士于谈玄之外,兼崇山林隐逸之趣,故正始名士多居庙堂,而竹林名士则喜亲山水。”(65)如果单纯从精神旨趣来看,竹林名士比正始名士境界更高,其思想更容易与文艺发生联系。因为与谈玄相比,亲近山水和崇尚隐逸能使人放松下来,进入自由自在的思想境界。魏晋士人在高度的思想解放之后,在谈玄几至癫狂的精神状态中,开始了他们对于文艺精神的探索和追求。
首先进入魏晋名士视野的是因为思考宇宙和人生而出现的起兴,这是文艺精神升华的重要方式。《说文解字》云:“兴,起也。”(66)兴是《诗经》的一种表现手法,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从而激发读者联想,增强感情意蕴,产生形象鲜明、诗意盎然的艺术效果。魏晋名士在打破儒家思想的束缚之后,终于把灵魂解放,将情感表现出来,这种表现就不可避免地与起兴联系起来。但是,这时候的起兴已与先秦时代大不相同,先秦起兴多借助于景物和生活,而此时的名士因为要彻底冲破思想的牢笼,思考的问题早已远离生活而进入到宇宙和自然中,所以,他们的起兴也往往站在这样的高度。这也是后人常言魏晋多玄言诗的主要原因。但是,魏晋士人又绝不是在虚无缥缈的世界里自我陶醉和妄自尊大,他们往往是带着情感思考问题,而且是王弼所说的“有情而无累”。《三国志·钟会传》注引何劭《王弼传》云:
何晏以为圣人无喜怒哀乐,其论甚精,钟会等述之。弼与不同,以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今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失之多矣。(67)
圣人的境界是魏晋士人追崇的精神目标,圣人有情感但不为情感所累,这是圣人高明的地方。从这个角度理解魏晋名士的文艺精神,既能关照到其思想高度,同时又能审视到其中的情感元素,思想与情感的高度融合是我们定位魏晋文艺精神的重要准则。
而思想和情感的融合还只是升华文艺精神的内因,外部环境和创作者的人格也在对文艺精神的酝酿和生发起作用。阮籍是正始文学最杰出的代表,八十二首《咏怀》是他的经典之作。《文选》卷第二十三李善注曰:“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故粗明大意,略其幽旨也。”(68)因身处险恶的政治环境而有感而发,这样的文艺表现隐含着对于人生和国家的忧虑,这是阮籍文艺精神的真实写照。而这种外部环境的压迫实际是在刺激创作者的内心情感,因为与人伦道德相联系,所以表现为创作者的人格。牟宗三先生言:“魏晋名士人格,外在地说,当然是由时代而逼出;内在地说,亦是生命之独特,人之内在生命之独特的机栝在某一时代之特殊情境中迸发出此一特殊之姿态。”(69)人格与人的生命情感联系在一起,当作用于文艺创作的时候,其产生的巨大影响力正可对文艺精神的升华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其次是对唯美的追求和感悟,这是文艺精神进一步升华的核心因素。宗白华说:“这截然地寄兴趣于生活过程的本身价值而不拘泥于目的,显示了晋人唯美生活的典型。”(70)对唯美的追求是魏晋士人最突出的人格特质,这种追求表现在各个方面。首先是外貌之美,魏晋士人多喜欢装饰和打扮,面如冠玉、仪表堂堂是对那个时代美男子的典型描述。《世说新语·容止》载:“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憘(饼)。既噉,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71)像何晏这样肤色美白的男子在魏晋时期非常普遍,甚至有男子人为的美髯和敷粉。但这还只是唯美的表层含义,更深层次的则是精神层面的表现。魏晋时期战乱不断,士人的生活环境非常险恶,再加上政治压迫,他们纷纷躲避和逃亡,远离政治漩涡,逍遥一身,无拘无束,只有如此,他们才能充分地寄托自由精神。他们首先把这种唯美的精神追求表现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阮籍葬母还是刘伶裸形,他们不受约束的异常行为在我们今天看来或许是另类、神经质,但在他们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却是最大的美感,因为他们的身心获得了极大的自由。所以,这里的唯美便不仅仅是外貌、形体的表现,而是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思想满足和精神享受。《世说新语》对嵇康的风姿赞美有加: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72)
《晋书》本传亦云:
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73)
这样的风度实际已不只是外表和形貌的表现,而是上升到气质和精神的层面。在这样非凡的气度中,嵇康的文艺创作才能脱于尘俗,《三国志·王粲传》注引《嵇康传》云:“善属文论,弹琴咏诗,自足于怀抱之中。”(74)嵇康是“竹林七贤”中最有才华之人,其四言诗取法《诗经》,清新脱俗,极具浪漫色彩,是魏晋玄言诗和游仙诗的开创者之一。除了作品本身的高妙境界,魏晋士人的文艺精神还表现在创作过程中,比如嵇康临刑前从容弹奏《广陵散》、张翰鼓琴凭吊顾荣、左思十年作《三都赋》等,都是文艺创作走向极致的表现。这样的过程在今天看来似有神经质的嫌疑,但这恰恰是魏晋名士精神世界的真实表露,这样的表露往往是因为受到玄学思想的影响。可以说,魏晋士人思想的解放程度决定了其文艺创作的深入程度,而创作的深入程度又是衡量文艺作品影响力最重要的标准。《世说新语·雅量》载:“夏侯太初尝倚柱作书。时大雨,霹雳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神色无变,书亦如故。宾客左右,皆跌荡不得住。”(75)夏侯玄书写中的忘我和从容正可作为那个时代名士文艺精神的真实写照。正是有了这样的神态和风范,我们才把那个时代名士的言行举止称为魏晋风度,魏晋风度很重要的一个体现就是文艺精神的穿透力和表现力。
文艺最高层次的境界是对于道的追寻,到了这种境界,文艺精神已经升华到极致。对于文艺境界的探索是魏晋士人思想高度解放和审美范畴不断扩大后出现的必然结果,这样的探索到了一定程度就是对人生、宇宙和自然的反思与追问。文艺创作的情感来源于主体的思想,当这种情感受到思想意识的全力影响和控制时,便会表现为一种抽象的审美范畴,如气、韵、象、意等。而这些范畴最容易与道联系在一起,因为它们的场域恰恰与道的境界吻合,所以,魏晋士人的文艺创作往往通过这些范畴与道发生关系。王羲之《晋天台紫真笔法》云:“若书之器,必达乎道,同混元之理。”(76)宗炳云:“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77)刘昼亦云:“歌之舞之,乐发于音声,形于动静,而入于至道,音声动静,性术之变,尽于此矣。”(78)魏晋时期,几乎所有的文艺形式都与道相联系,就是因为当时名士的思想空间正在无限扩大。这在以往是从未有过的,尤其是在文学和艺术领域,这样的境界被第一次发现和达到。
在这一过程中,《庄子》对文艺产生的影响最大。《庄子》受到《老子》思想的影响,但比《老子》更加形象生动,思想境界也更加逍遥自在和无拘无束,与魏晋时期刚刚解放的士人的内心世界非常契合。当时的士人正在儒学精神解体的纷乱中徘徊和惆怅,急需寻找到可以让心灵栖息的新土壤,《庄子》恰好符合这样的要求。所以,当时的名士大多受到《庄子》影响,整个社会的文艺空气也为之一振。比如《庄子》中提到的“虚静”,与文艺精神的凝聚和表现便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创作者只有在虚静中才能排除一切外在干扰,全力以赴进行文艺创作。嵇康就看到了“虚静”之心在音乐鉴赏中的重要作用,其《声无哀乐论》云:“琴瑟之体,闻辽而音埤,变希而声清,以埤音御希变,不虚心静听,则不尽清和之极。是以听静而心闲也。”(79)“虚静”在整个魏晋时期一直都是文艺创作的主流思想,并有进一步发展,晋宋间出现了宗炳的“澄怀味象”,南朝时更出现了刘勰“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的审美观照理论。但是,《庄子》思想对魏晋文艺影响最大的还是“神思”。庄子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神思”二字,但其作品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如《逍遥游》中的“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达生》中的“游乎万物之所始终”,《齐物论》中的“游乎四海之外”等,对人的思维都有重要的启发作用。庄子的思想最终指向了道,这对魏晋士人的文艺精神是一种巨大的提升,他们丰富多彩的文艺创作都达到极高的境界,此时,文艺与思想实现了绝对契合与完美统一。
三、家族文化转型与文艺精神的群体自信
玄学思想影响下的名士是魏晋社会最重要的人文标志,而这些名士并不是孤立的存在,他们往往是在高门大族中以群体的形式出现。这些大族之前都是以经学传家的儒学家族,而此时,因为儒学嬗变而导致的思想解放和文化多元,旧的经学世家正在向文化世家转变,这是当时非常重要的社会现象。
在汉代,当研习经学成为士子进入官场的重要途径之后,经学在士人群体中的地位就异常重要起来。西汉武帝时,朝廷罢黜百家而独尊儒术,确立官方意识形态,并立五经博士,传授儒家经典。经过秦朝焚书坑儒,儒家经典劫后余生,传播混乱,朝廷只能选择在社会上有重要影响且师法传承脉络清晰的学派和经师,立于学官,这是汉代经学重师法的主要原因。皮锡瑞云:“汉人最重师法。师之所传,弟之所受,一字毋敢出入;背师说即不用。师法之严如此。”(80)史书所载西汉士子研习经学多谓其“有师道”“有师法”,如《汉书·张禹传》云:“望之善焉,奏禹经学精习,有师法,可试事。”(81)《汉书·匡衡传》亦载:“望之奏衡经学精习,说有师道,可观览。”(82)随着经学的发展,一些经学大师逐渐创立自己的一家之说,并得到官方或社会认可,于是,从经学的师法中开始衍生出家法。皮锡瑞这样评价经学从“师法”到“家法”的转变:“前汉重师法,后汉重家法。先有师法,而后能成一家之言。师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也。”(83)“家法”于此时受重视主要是基于两个原因:一是家族学术传承的私密性要求;二是当时学术研究的人数增多、深度强化,导致学术开枝散叶,流派增多。东汉时期共立十四家博士学,正是受“家法”学术风气的影响。《后汉书》所载名臣列传中频频出现“传父业”“传家学”的字眼,如杨秉“少传父业,兼明《京氏易》,博通书传,常隐居教授”(84),琅琊伏湛“性孝友,少传父业,教授数百人”(85),孔昱“少习家学”(86)。从“师法”到“家法”的转变正是汉代经学进一步发展的表现。但是,东汉重“家法”不代表就不要“师法”,“家法”中实际也包含了“师法”的含义,“家法”与“师法”在东汉的经学研习中是合而为一的。这样的局面实际是在进一步增强家法的分量,为汉代经学世家的形成奠定坚实的基础。陈乔枞《齐诗遗说考自叙》云:
汉儒治经,最重家法,学官所立,经生递传,专门命氏,咸自名家。三百余年,显于儒林,虽《诗》分为四,《春秋》分为五,文字或异,训义固殊,要皆各守师法,持之弗失,宁固而不肯少变。(87)
这种学术坚守对于家族文化品格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即经学的“家法”中已经在酝酿着家族文化的传承法则,所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世家大族多有家风家训,这应该是东汉经学“家法”的进一步拓展和延伸。
汉末以来,军阀割据,战乱不断,朝廷失去了原有的号召力和权威性。当此之时,京都洛阳的高官和士大夫纷纷辞官离职,潜回原籍,归隐山林,教授子孙,逐渐形成士大夫之“家学”。陈寅恪言:“故东汉以后学术文化,其重心不在政治中心之首都,而分散于各地之名都大邑。是以地方之大族盛门乃为学术文化之所寄托。”(88)因为经学取士的逐渐衰落,高门大族对子孙的文化教育也开始突破经学的范畴,而进入到对子孙道德理想和文艺才能的培养上,家族教育模式和内容的变化使当时的学术氛围为之一变。齐鲁之地因距京都洛阳较近,且汉代经学大师多出自齐鲁,所以,上述回籍的高官中有许多齐鲁士人。他们在传经过程中已经形成经学世家,此时回归乡里实质是在进行从经学世家到文化世家的转变。自此以后,经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汉末魏晋盛行以文化和道德立家的风尚,这些家族的家学便开始向着这样的方向发展。
世家大族在从都城大邑向地方乡里转移的时候,玄学开始风靡全国。在遭受了参政议政的失败与打击之后,士大夫阶层的精神状态出现衰退和分化,正如余英时所言:
盖自东汉中叶以来,士大夫之群体自觉与个体自觉日臻成熟,党锢狱后,士大夫与阉宦阶级相对抗之精神既渐趋消失,其内在团结之意态亦随之松弛,而转图所以保家全身之计,朱子所谓“刚大方直之气,折于凶虐之余,而渐图所以全身就事之计”者,诚是也。自此以往,道术既为天下裂,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之精神逐渐为家族与个人之意识所掩没。(89)
士大夫放弃了对于国家的责任,转而重视家族和个人的发展,这是汉末出现的一种风气。在受到玄学清谈思潮的影响后,士人原有的儒家精神开始低落,这时候士人更关心的是生命和个人的生活,自由精神开始崛起,与自由精神紧密相连的文艺便随之而来。许多士人通过文艺创作来表现情感,这种表现具有相当大的冲击力,能使艺术感受自由驰骋,而且,这种表现往往带有深刻的思想文化内涵,因此境界颇高,开始形成文艺精神。
汉末的世家子弟不再对明经取士抱有怀想,转而开始重视个人修养和家族的内涵式发展,诗歌、书法、绘画等文艺形式便成为能让家族焕发光彩的重要内容。首先出现在世家大族中的文艺形式是诗歌,文人诗自汉末以来已经有了长足发展,当时的世族出现了许多父子诗人、兄弟诗人,如三曹父子,萧涤非说:
曹氏父子之产生,实为吾国文学史上一大伟迹,曹操四言之独超众类,曹丕七言之创为新体,既各擅场千古,而五言之集大成,子建尤为百世大宗。以父子三人,而擅诗坛之三绝,宁非异事?(90)
曹氏家族的文学创作自曹操开始,一直延续到高贵乡公曹髦,文学成为曹氏的四世家学。其他如山阳王氏、荥阳潘氏、陈留蔡氏、汝南应氏、谯郡嵇氏等家族,也都以文学传家,并有著名文学家出现,如山阳王粲、荥阳潘岳、陈留蔡邕、汝南应玚、谯郡嵇康等。各家族在文学上的传承与发展往往成为后世子弟炫耀的资本,如应亨就曾非常自豪地夸耀自己的家族:“自司隶校尉奉至臣父,五世著作不绝,邦族以为美谈。”(91)书法因为在日常生活中的广泛使用,也引起了各家族的重视,汉末曹魏时期比较著名的书法文化家族有敦煌张氏、博陵崔氏、陈留蔡氏、颍川钟氏、河东卫氏等。这些家族原本都以儒学传家,但是在汉末儒学嬗变自由精神崛起之时,纷纷转向对于书法的研习,并逐渐形成家族的独特书风,如敦煌张氏擅长草书(图1-2),陈留蔡氏善写篆隶,颍川钟氏以行、楷书名世,河东卫氏善草书,他们标立的家族书风成为后世学者认识和解剖其家族文化精神的重要内容。经过这一转变,经学在各家族中的地位已不十分重要,而文化艺术的繁荣成为家族声望提高的显著标志,这时候的世家大族已经从原来的经学世家转变成文化世家。

图1-2 东汉张芝《冠军帖》(局部)
引自尹一梅主编《懋勤殿本淳化阁帖》,商务印书馆,2013年。
但是,这并不是说当时的士人已经完全背离了儒家道德,他们只是不再纠缠于经学章句的繁琐,对于儒家思想,他们一直不肯也不敢完全抛却。钱穆先生说:“门第即来自士族,血缘本于儒家,苟儒家精神一旦消失,则门第亦将不复存在。”(92)余英时也认为:“唯独齐家之儒学,自两汉下迄近世,纲维吾国社会者越二千年,固未尝中断也。而魏晋南北朝则尤为以家族为本位之儒学之光大时代,盖应门第社会之实际需要而然耳!”(93)凝聚门第理想的核心就是挺立儒家道德精神,自有门第以来就是如此,即使到了汉末魏晋,儒家思想开始分化裂变,谈玄成为一种风潮,早已深深浸渍到士人思想中的儒家精神也不可能被完全涤除,因为社会的道统还没有被彻底打烂,支撑国家和社会运转的根本仍是儒家思想。所以,魏晋士人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对于儒学精神的追求和坚守,也正是因为这种坚守,当时的世家大族才不至于在失去朝廷信任和高官厚禄之后而一下子萎靡不振,儒学精神使世家大族无论何时何地都始终保持高贵的姿态。只有在这样的坚守中,刚刚发展起来的文艺才能表现出持续不断的冲击力和感染力,在世家大族中长期受到重视并有所发展,使文化世家整体表现出不俗的气象和面目。
从经学世家到文化世家转变的关键是经学取士的式微,出现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儒学自身的衰落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内外两个原因导致了经学世家的退化,代之而起的文化世家正是在思想大解放的氛围中充分展开。世家大族的思想状态决定了其家族文化的存在形式,家族文化的发展催生了家族文艺的繁荣。正是在汉末魏晋思想大解放的链条上,文艺快速生长和发展起来。世家大族失去了原来经学传家的文化自信,文艺开始充当家族繁荣的资本,有了优美的文艺精神,家族门第便具有了另外一种文化自信。当时的多数文化世家都表现出这样的特征,即使在玄学风气非常浓厚的家族,玄学的招摇和恣肆也没有影响到家族的文艺精神,这实在是与当时高门大族对儒家精神的坚守有关。中国文艺的发展一直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从最早的《诗经》到汉代《古诗十九首》,这种影响完全内化在作品的精神实质中。所以,在汉末魏晋世家大族的文化转型中,文艺精神的儒学表现仍然十分深刻,这既保证了文艺发展的方向,同时也使文艺能够真正替代经学而成为世家大族的身份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