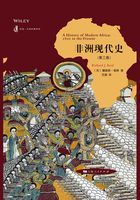
商业视野:奴隶与象牙
东非的奴隶贸易持续了几个世纪,但它的大幅度扩展是18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情,这有好几个原因:俄罗斯帝国的扩张开始切断那些地区对伊斯兰世界的奴隶供应,伊斯兰世界就把东非视为一个潜力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来源。印度洋上法属岛屿的蔗糖和咖啡种植园,对奴隶劳动力的需求也在增长,这些种植园从18世纪70年代开始扩张;19世纪早期,巴西因种植园的扩展对奴隶劳动力的需求也扩大了,而大西洋海岸一带的老来源已经衰败,所以巴西的奴隶贩子就开始作更长途的买卖,由南大西洋深入到印度洋,从莫桑比克地区和赞比西河流域购买奴隶。更为重要的是,桑给巴尔自身开始种植新的作物,包括北边的奔巴(Pembar)岛。特别是丁香种植园,它们为岛上的阿拉伯统治者所有,并且通常有印度资本来支持,从非洲内陆吸纳奴隶。基于这些原因,东非的奴隶贸易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强化阶段,从18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80年代,持续了近一个世纪。东非的奴隶人数由于大量没有记录,以及这种贸易的“非法”性质,比起大西洋非洲更难以统计。1800年时,奴隶出口可能已达到每年6000人,而到了19世纪20年代,人数则达到每年两万到三万人。在60年代奴隶贸易的顶峰时期,大约每年有七万奴隶输出。这些奴隶均来自内陆,这是由于交易兼抢掠的前锋继续深入,延伸至大湖地区和东刚果一带。同样,值得记住的是,当大西洋非洲的奴隶贸易慢慢衰退时,东非的奴隶贸易却在持续增长。[7]
英文版原书页码:49-50

19世纪的东部和南部非洲。
在东非,桑给巴尔苏丹国成为反奴隶贸易压力关注的焦点,这尤其来自英国。1822年,莫尔兹比港条约签订,因此阿曼停止从东非获得奴隶,英国则行使权力,如同在大西洋所做的那样,开始派遣反奴隶贸易巡查舰队到印度洋巡逻。但在桑给巴尔和奔巴,奴隶出口仍是可以合法操作的,直到1873年,桑给巴尔当局才终于同意终止它。[8]奴隶贸易在其他地方仍然暗中进行直至20世纪初,但还是随着这一地区进入欧洲人的控制而最终地、明确地寿终正寝了。在19世纪80年代的布干达,穆特萨说的话与三十多年前达荷美国王盖佐所言惊人相似。大约1881年,据说他对一些传教士讲:“如果英国女王能像当年帮助桑给巴尔的赛义德·巴加什那样帮助我,我当然会废除奴隶制。但我的首领和我的民族的力量都依靠这种贸易,我没有权力来阻碍它。”1883年,他再次重申了这个观点:“我能做什么呢?……那些可恨的奴隶贩子事实上统治着我的民族,对此我以前是鼓励的。它现在已经到了如此规模,我担心已经停不下来了。”[9]
奴隶贸易的快速增长对19世纪的整个东非有很深影响。总体来说,它意味着内部战争不断升级,并且奴隶暴力瓦解着众多社会。这种暴力由于武器的引入而继续恶化,海岸一带的商人通常用武器来购买奴隶,尽管也未必是百分之百如此。在白热化的战斗中,武器的使用常常既是为了伤害身体,也是为了造成心理震慑。[10]然而,广泛而言,武器的获取与使用加速了“传统”权威的崩塌,促进了新形式的军事领袖和政治统治的建立。而且,如同在大西洋一带,将潜在的劳动力输出,这对社会和经济都是严重损害。人们认为,非洲贸易者通过参与贩卖奴隶有明显的发财机会,无论是大规模的——例如尼亚姆韦齐首领米拉姆伯这类人,对此我们下文会加以考查,或者是小得多的规模——如通过绑架的方式。尼亚姆韦齐人、尧人和卡姆巴人热切地抓住了发财的机会,充当了奴隶贸易的贸易者、中间商或运输者。一些最具戏剧性的社会政治变化在尼亚姆韦齐人中发生,他们经历了贫富差异的快速拉大,以及旧有政治结构的坍塌。原有生存系统的瓦解在许多地方也都发生了,野心勃勃的年轻男子忽略农耕,到生意或战争中讨生活,或者是两者兼做。[11]这是一个社会变迁的年代,向上和向下的社会流动性都大大增强,新的社会体系和新的政体在代际冲突中建立起来。
英文版原书页码:51
象牙的需求从18世纪后期也开始增长,印度仍是一个重要市场,但东非的象牙在欧洲和北非也受追捧,并且欧洲贸易在19世纪里变得越发重要,尤其是1869年苏伊士运河建成之后。不过,如同一位学者所言,这是一个“消耗过程”。由于随着19世纪的推移,象牙供应在萎缩,一年又一年,成千上万的大象被杀以满足需求,对象牙的搜寻越来越被推向中非内陆。[12]
尽管运进非洲各地的货物种类基本相同,但大西洋非洲与东非之间在经济发展上却颇为不同。在东非疆域,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言,奴隶和象牙出口代表的是“通向不可避免的死亡终点的过程”。[13]这些活动对这一区域的长期经济发展有害:象牙越来越稀缺,“大象边疆”越来越被推向内陆深处;奴隶作为出口商品也没有前途,因为这一区域越来越受欧洲影响。这就意味着随着19世纪的结束,中东部非洲与过去的经济大部分决裂了,奴隶和象牙被放弃,出口农业——代表着“合法”的贸易,它在非洲大陆的另一端早已实行——在新建立的殖民政体的支持下被陡然引入。尽管象牙仍可通过组织大型车队而相对容易地运出去,但只有修建铁路,东非内陆才能与全球经济相连——这种连接在海岸一带已经实施几个世纪了。
尽管17世纪和18世纪时,埃塞俄比亚地区的政权重心向北移动,但这一区域的奴隶贸易无疑没有那么广泛,没有那么具有毁灭性。阿姆哈拉人和提格雷人每年通过海岸边的马萨瓦出口高达一万的奴隶。高原人有时也把这种商品装进自己的车队里,但他们经常不愿意在炎热的海岸低地旅行,于是这项贸易越来越被纯粹的商人阶层掌握——通常是穆斯林。19世纪时,一些奴隶本身就来自高原,在阿拉伯半岛卖到了好价钱;但被俘获者却越来越多地来自埃塞俄比亚西部低地和苏丹东部,他们被蔑称为“山卡拉”(shankalla)。奴隶被出口到阿拉伯半岛和波斯湾地区,少数被运到广阔的中东。除了奴隶,黄金、象牙、毛皮和香料也从埃塞俄比亚地区出口,尤其是用来换取武器。不过,不同于中东非,武器通常使得原有的阿姆哈拉和提格雷政治上层增加力量,使得他们更有能力去维持贸易垄断,控制海岸和高原之间的商道。尽管如此,随着19世纪的推进,贸易规模扩展到一定程度,一些群体也比从前更有能力来挑战国家了。即使是特沃德罗斯以及后来的约翰尼斯统一了埃塞俄比亚国家,犯罪和反叛也依然猖獗。[14]
英文版原书页码:52-53
东非湖泊地区和埃塞俄比亚高原的那些国家和社会,都面对一个问题:为了能够加入全球贸易,他们不得不与沿海族群进行贸易往来,而这些人常常是他们的敌人。19世纪的埃塞俄比亚国王们,依据对过去的一些想象,或许还可以宣称对红海海岸拥有权利,但实际上马萨瓦是由奥斯曼人通过埃及人来掌管。奥斯曼人拥有终止贸易的力量,或者是控制它的力量。19世纪后期,那些越来越感觉到自己被隔绝的非洲统治阶层,要寻找其他途径来获取武器。例如绍阿国国王迈拿里克,他通过吉布提与欧洲人贸易。[15]身为埃塞俄比亚皇帝的约翰尼斯,被迫向那些在马萨瓦偶尔出现的宗教挑衅者妥协,正统基督教的供应商要与穆斯林买主打交道了。同样,穆特萨以及更为戏剧化的米拉姆伯都越来越认识到一个事实:他们已经成为桑给巴尔倾向态度的人质,因为他们依靠它来提供枪炮、弹药和布匹。米拉姆伯意识到参与全球贸易需要妥协和外交,正如需要武力和恐吓一样。比起他们的尼亚姆韦齐供应商来,桑给巴尔的商人在对峙中有着更多的选择。

约1870年的东非。引自E.弗林特所编《剑桥非洲史》第5卷《约1790—约1870年》(剑桥,1976),第281页,地图10,1976年版权属剑桥大学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许可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