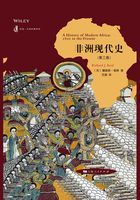
第二部分
非洲与伊斯兰教:19世纪的复兴与变革
英文版原书页码:85
在非洲历史中,伊斯兰教极为重要,就塑造这个大陆历史的外部影响而言,伊斯兰教到目前为止是最主要的,至少在19世纪欧洲介入日益增加之前是如此。尽管非洲历史上一些最剧烈的变化发生在晚近时期,是因与基督教欧洲的交互作用而产生,并在殖民占领时期达到顶点,但伊斯兰教已经改变了非洲大片地区好几个世纪。的确,伊斯兰教适时地构成了非洲人抵抗欧洲扩张的一大部分基础。这里的关键点就是在北部非洲,在撒哈拉,在红海地区等大片地区,伊斯兰教长期以来提供着巨大社会政治变化和统一行动的一种框架。从18世纪后期以来看,这一点尤其清楚,这个时期目睹了伊斯兰教非洲大部地区改良传统的重新出现。
非洲的大片地区已经是穆斯林超过了基督徒。北非加入伊斯兰世界显然已有千年之久,这个渐进过程开始于7世纪和8世纪的阿拉伯占领,接着是一些关键群体皈依伊斯兰教,以及阿拉伯部族向马格里布地区的迁移。西非是穆斯林居支配地位,这个局面主要是穿越撒哈拉沙漠的兴旺的贸易网络将大沙漠南北联系起来的结果。这个网络在8世纪和9世纪之后急剧扩展,推动了伊斯兰教的逐渐渗透,它越过撒哈拉,进入草原地带,在这里主要被城镇上层所吸纳,至少开始时是这样。另一方面,东非和南非在今天是基督教占支配地位,尽管伊斯兰教对于东非一种独特的海岸文明的创建也起到了基础作用。这就是斯瓦希里,它将非洲、伊斯兰教和阿拉伯影响融合在一起。伊斯兰教在东北非也有巨大影响,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的穆斯林与北非和阿拉伯半岛都有紧密联系。所以,就塑造现代非洲自身文明的力量而言,伊斯兰文明如同基督教一样重要,有时甚至更重要。很重要的一点是,非洲穆斯林属于一种全球文明,它超越了非洲自身,把奥斯曼帝国、波斯和印度都包括进来,这各个部分都与非洲有着贸易和文化联系。非洲穆斯林是一个全球族群的一部分,这个族群中的信息交换——比如在麦加朝圣时,激发着政治意识。对于这个世界其他地方的发展,穆斯林常常信息灵通,19世纪后期对欧洲帝国主义的反应,其基础常常就是对欧洲人在其他地方行为的知晓,比如对印度穆斯林力量的征服。
概括而言,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生长有一种历史平行,但各自的初期阶段有着重要的不同,随着时间推移这种不同变得极为重要。在欧洲,从中世纪以后,基督教的政治重要性逐渐下降,世俗统治与宗教领导之间出现了鲜明的区分;然而,在伊斯兰教世界,信仰与国家是合而为一的,宗教事务与政治事务之间没有区分。而且,基督教是以“失败”而开始的,罗马对基督徒的系统迫害,意味着早期基督教会是一种地下的、被剥夺力量的运动,对政治和政府都不关心。但伊斯兰教从一开始就很成功,它夺取了政治力量,在数十年的时间里通过征服就铸就了一个帝国,穆斯林领袖们关注的核心就是政治权威怎样实施。于是,伊斯兰教的法律、政府和税收制度及财产制度都被视为与精神方面不可分割。在基督教中,这些事务绝大部分都是世俗性的。还要注意很重要的一点:伊斯兰教没有基督教那么强的宗教层级,政治领袖担当着基督教神职人员的角色。不过,伊斯兰教中也有一些群体具有特殊地位,比如“乌拉玛”(ulama)——解说和应用伊斯兰教法律的专家,“苏菲”(sufi)——从事冥想和身体操练的神秘家和苦行者,由此可达到与神的紧密联系。在非洲,苏菲兄弟会对伊斯兰教的传播和融入当地环境起到了关键作用。
英文版原书页码:86
西方学者常说,伊斯兰世界从17世纪以后就进入一个停滞和衰退时期。根据这种观点,伊斯兰教法律已经变得保守,在它的裁决中,先例替代了独立判断。15世纪至17世纪这段时间内,出现了现代早期三种伟大的伊斯兰文明:奥斯曼帝国、萨法维(Safavid)帝国和莫卧尔(Mughal)帝国。它们的鼎盛期不亚于、有时还超过了西欧所能提供的东西。然而,从17世纪以后,人们认为它在政治上、社会上或经济上都没有取得什么“进步”。不过,不应夸大这种衰退的观点,也的确有一些学者反对这种伊斯兰体系内在停滞的说法,认为这是欧洲中心论的产物,是基于文化傲慢的历史扭曲。
有一点很清楚,18和19世纪的伊斯兰教历史体现为紧密交织的三个宽广主题。首先,工业化中的基督教欧洲就其增长的科技和军事力量而言,形成了一个严峻的挑战,最终是一个以工业化为力量的帝国主义时代,在欧洲殖民国家对伊斯兰世界大片地区的征服中达到了顶峰,这个历史过程直到今天仍在持续带来影响。到20世纪开始时,欧洲与俄国的控制和/或影响已延伸至中亚、印度、中东和北非,在相连的两个世纪里,欧洲人的扩张逐渐威胁到穆斯林核心地带。拿破仑对埃及的征服是一个深远的打击,克里米亚战争之后俄国的影响又扩张至黑海地区。接下来的两个主题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着穆斯林对欧洲扩张的回应。18和19世纪出现了伊斯兰教复兴运动席卷穆斯林世界的现象,寻求“纯洁”和“本性”的伊斯兰教的恢复,伊斯兰教法规(“沙里亚”,shari'a)的严格执行。在这种背景下,值得关注的就是早期伊斯兰教历史,尤其是穆罕默德本人的历史,为历代穆斯林提供了一种抗议、抵抗和变革性改变的模式与意识形态。复兴运动常常也是救世主性质的,断言“马赫迪”(Mahdi,救世主)或救星的即将降临,他将在世上恢复纯洁的伊斯兰教。这种救世主降临说与伊斯兰教什叶派联系最紧密,什叶派在历史上对早期哈里发起到了关键作用,因为阿里(什叶派的名称就因他而来)是穆罕默德最后的直系后裔,而他于661年被倭马亚(Umayyads)篡位了,并且被暗杀。这些说法和其他的复兴运动宣称改革是在内部,背离纯洁的伊斯兰教法律在根本上就错了。他们常常是暴力的,使用武装造反,即所谓的“圣战”。许多时候,他们的敌人并不仅仅是基督徒或其他“异教徒”,也包括被他们谴责为无信仰者的穆斯林。与此同时,一些穆斯林社会也试图现代化和世俗化,这通常就意味着要仿效欧洲模式,以回应西欧带来的挑战。这往往就涉及在公共生活中减少伊斯兰教,引进西方风格的宪法、立法、教育和税收制度。非洲伊斯兰教必须放在这样一些背景中来理解。
英文版原书页码:87
19世纪伊斯兰教复兴运动的来源,有许多可以在18世纪找到,而且并不令人吃惊的是在非洲大陆之外。比如,在阿拉伯半岛,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勒·瓦哈比(1703—1792)就是严格执行伊斯兰教法律的一个极端信奉者,他与一个当地首领穆罕默德·伊本·沙乌德结盟。瓦哈比教派倡导纯洁伊斯兰教的恢复。在印度,随着18世纪开始后莫卧尔帝国的衰落,出现了瓦利·阿拉(1703—1762)这样的人物,他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复兴主义学派,强调伊斯兰教的纯洁性、《古兰经》的中心性和伊斯兰教传统的研习。在西非草原,富拉尼人作为一系列伊斯兰教改革运动背后的激励者而行动,通过“圣战”来夺取权力。这方面最鲜明的例子或许就是现在尼日利亚北部一带的乌斯曼·丹·弗迪奥,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会详细谈到他。不过,重要的是要注意,这种种运动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只是对欧洲力量的反应,在出现欧洲帝国主义的挑战之前,在伊斯兰教内部就存在着持续改革的传统,阿拉伯半岛和西非的情况无疑就代表着这样的传统。伊斯兰教复兴运动旨在国家和社会的道德回归,这个运动如同伊斯兰教本身一样古老。不过,穆斯林社会在防止欧洲侵蚀上的失败,的确是以复兴和世俗现代化的两种形式来要求改变的一个强力因素,这种要求从18世纪中期就开始了。西方帝国主义和一些本地政权的现代化政策,为受欢迎的复兴运动领袖们提供了新的焦点。一些领袖利用已有的兄弟会,另一些人则靠纯粹的个人魅力创建了新的组织。然而,他们全都注重将反外国或反政府的抵抗力量团结起来,使用的就是拯救即将降临,神圣法律要纯化、恢复,或者救世主解救的信息。
英文版原书页码: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