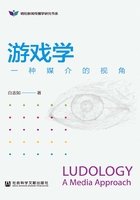
第一节 中国传统游戏观念与思想
关于中国游戏的观念与理论,往往分散在其他领域的著作中,并没有完整、集中、系统的游戏层面的研究。不过,这些相关著作,也正是游戏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笔者通过对这些涉及游戏观念的材料进行整理和分析,来探讨中国传统游戏思想。
这里的传统主要是与当代对立,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思想、著作、政策、法令等资料中体现出的游戏观念。“观念”一词源自希腊文,原意是“看得见的”形象。这里笔者取“立场”“态度”“看法”的含义。接下来的章节分别从中国传统思想认识、国家的政策法令、游戏组织的发展以及游戏在人际和社会方面扮演的角色等方面来分析中国对待游戏的观念。
一 中国传统游戏的观念
中国传统社会对游戏的态度不一。从个体的角度来看,游戏可以陶冶性情、教化、强身健体、消遣、慰疗伤痛等。首先,强身健体是游戏的基本功用。例如战国末年《吕氏春秋》所谓“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暗示了一种朴素的运动哲学。唐代孙思邈《千金要方》:“养性之道,常欲小劳,但莫大疲及强所不能堪耳。”所谓“小劳”,就是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地进行日常运动。其次,陶冶性情是社会持有的普遍态度。例如,南朝梁武帝在《围棋赋》中充分肯定围棋的“游神”“安思”作用。唐代体育运动风靡全国,因为“当时,几乎一切体育运动,均被人们视为游戏逸乐,故而有‘象戏’‘武戏’‘水嬉’‘蹴鞠之戏’‘击鞠、角抵之戏’‘拔河、翘木、扛铁之戏’等种种称呼。这并非偶然的现象,充分体现出唐代社会关于体育的嬉戏观,反映了唐人对体育的娱乐功能的认识和肯定”[1]。其实,并非唐人对体育的娱乐功能具有深刻的认识,而是游戏和体育本来就同源而出,只不过在不同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赛场上你争我夺的赛事,在赛场下就变成了娱乐的游戏。游戏具有运动的天然属性,是人们锻炼身心的良好途径。游戏观念伴随着社会发展和变迁,也呈现新的价值取向。例如与《晋书》认为“相扑下技”及唐代对相扑“且多猥俗”的看法不同,宋代调露子的《角力记》对于相扑的观点,代表了宋代对于摔跤游戏的积极看法,而且市民们已经将相扑当成不只强身健体,而且颇具特色的社会风俗性运动。再次,游戏还具有促进个体精神发展的功能,包括慰疗伤痛、解除苦闷等,这在中国传统文人骚客的作品里尤为常见。例如,东晋北伐名将祖狄认为,围棋能使人“忘忧”;白居易有诗:“兴发饮数杯,闷来棋一局。”进而,游戏也被视为寄予壮志和情思的有效路径,是情怀的出口,因此成为一种隐喻和象征,是情绪的寄托。这是将游戏视为一种生活态度和存在方式。如卓文君给司马相如的《怨郎诗》:“七弦琴无心弹,八行书无可传,九连环从中折断,十里长亭望眼欲穿”;李清照早年的代表作《点绛唇·蹴罢秋千》:“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等等。游戏在个人化成长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它在链接个体与社会情感方面所扮演的中介作用,使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意象,因此其功能从工具属性过渡到了社会属性。
从社会的角度而言,游戏被视为一种教化的路径,具有链接作用,发挥着符号和象征的价值。首先,游戏对社会而言是社会教育的手段,也是个人发展和成长的途径。游戏的教化功能始于游戏诞生之初,并且一直是游戏的一个重要功能。南朝梁元帝《金楼子》记载:“尧教丹朱棋,以文桑为局,犀象为子”[2];宋代罗泌《路史·跋》记载:“帝尧陶唐氏初娶富宜氏,曰女皇,生朱。兄弟为阋,嚣讼女曼游而朋淫。帝悲之,为制弈棋以闲其情。”而宋代司马光在《投壶新格》[3]中认为:“夫投壶闹事,游戏之类,而圣人取之以为礼……投壶可以治心,可以修身,可以为国,可以观人。何以言之?夫投壶者不使之过,亦不使之不及,所以为中也。不使之偏波流散,所以为正也。中正,道之根底也。” 可见,围棋、投壶等游戏是社会教化和个体成长的重要路径。
其次,游戏被视为人们消遣、社会娱乐以及人际交往的纽带。荀子也在《乐论》中认为,“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以不能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则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4],这是指音乐的教化游戏娱乐功能。而《论语·阳货》中也写道:“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5]这些记载表明社会普遍追求游戏娱乐,而更大规模的社会交往方面,游戏也成为必要方式。例如,宋王谠《唐语林》卷七中记载:“旧制,三二岁,必于春时,内殿赐宴宰辅及百官,备太常诸乐,设鱼龙曼衍之戏,连三日,抵暮方罢。”[6]更为人们所熟知的《醉翁亭记》中记载:“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奕者胜,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其中“射”,一般指投壶游戏。最后,在更为抽象的层次上,游戏是一个社会的符号和象征系统。在清代小说家李汝珍的《镜花缘》后50回中,武则天开科考试,录取 100名才女。她们多次举行庆贺宴会,并表演了书、画、琴、棋,赋诗、音韵、医卜、算法、灯谜、酒令以及双陆、马吊、射鹄、蹴球、斗草、提壶等,尽欢而散。可见,游戏不仅具有具体的功能,而且成为提高身份和地位的路径,这就意味着游戏被社会所认可。游戏不仅是技艺的体现,而且具有符号和象征价值。
但是游戏也被认为具有负面效果,主要包括游戏的低俗化、浪费时间和颓废精神以及可能影响社会正常发展。例如上文提到《晋书》认为“相扑下技”,而唐代认为此游戏“且多狠俗”。更为甚者,有人认为游戏浪费时间、颓废精神,并且影响社会的健康发展。例如,赵抟的《废长行(辨其惑于无益之戏而不务恤民也)》写道:“紫牙镂合方如斗,二十四星衔月口。贵人迷此华筵中,运木手交如阵斗……莫令终日迷如此,不治生民负天子。”[7]这里斥责了游戏所带来的负面作用,意在关心民生疾苦。而且某些特殊的游戏形态更有可能被认为负面作用胜于积极作用,例如,博戏是非常容易引起争议的一种游戏。关于麻将,在徐珂《清稗类钞·叉麻雀》中记载:“光、宣间,麻雀盛行,达乎诸侯大夫及士庶人,名之曰看竹,其意若曰何可一日无此君也。其穷泰极侈者,有五万金一底者矣。”这种“一局五万金”的博戏,真可谓“穷泰极侈”;而其结局“四圈输八吊,一客累三家。包子连连吃,头儿屡屡拿。不愁输得苦,明日早来些”[8]。其实,麻将之类的博戏,因为它与钱财和功利紧密相连,有人质疑其是否为游戏。从本质来看,博戏是游戏,不过视其赌博性质和运作方式而有别。如果以钱财为终极目的,无快乐可言,其结果不具备游戏追求的自由、自足,而是被自我的功利欲望所牵引,就是应该禁止的赌博行为。如果只是作为消遣和娱乐的牌戏,回归游戏的精神,就是有益于人类的游戏。因此,游戏和应该禁止的赌博有性质和目的不同,而在特定的条件下,两者有不同的价值取向。
二 社会游戏政策与法令的立场
从更为宏观的角度来看,国家政策与法令的颁布表明整个社会或者权利集团对于游戏的基本观念和态度。这又较为集中地表现在节假日中游戏的繁荣程度上,同时和每个朝代的经济发展、统治者的意志、文化繁荣程度等都密切相关。
游戏是节假日的重要构成元素,也是国家游戏政令的反映。例如,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由于为母服丧,住在永乐(今陕西芮城县),听说长安正月十五花灯,自己无法看到,十分想念,因而写下了如下七绝《正月十五闻京有灯恨不得观》:“月色灯光满帝都,香车宝辇隘通衢。身闲不睹中兴盛,羞逐乡人赛紫姑。”[9]唐代城市管理严格,一年通常只有正月十四、十五、十六三天的晚上准许百姓通宵上街游玩,观赏灯火。所谓元宵夜看花灯,在不少诗词中亦有反映,例如唐朝崔液《上元夜》:“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10]或者张祜的《正月十五夜灯》:“千门开锁万灯明,正月中旬动帝京。三百内人连袖舞,一时天上著词声。”[11]
国家或者官方对游戏的态度既有提倡,也有约束和禁止。从社会结构的层面来看,游戏可以成为国家的专门组织。例如,唐代官方设立的棋待诏等职位,表明当权者对于游戏的肯定和认可,从而在组织和机构上保证了游戏的传承和流行。甚至,游戏成为统治阶级选拔人才的参考因素。例如,“唐代大力推行科举制度,朝廷‘取人,令投牒自举’,文人学子‘趋仕,靡然成风’”。[12]从参与主体的构成来看,游戏成为统治阶级亲自参与的活动。例如,“孔桂性便辟……晓博弈,故太祖(曹操)爱之,每在左右,出入随从”。[13]因此,游戏实际上是统治阶级维护利益关系的重要途径。根据《旧唐书·东夷传》记载:景龙三年(709年),唐中宗亲自主持了一场隆重热烈的击球赛,这场球赛显然给和亲活动增添了轻松和融洽气氛,成为和亲双方交流的桥梁,进一步拉近了汉蕃之间的友好关系。开元二十五年(737年),新罗国王去世时,唐玄宗皇帝也特意在唐朝吊唁使团中增加了围棋高手,以备棋艺交流,实则投新罗所好,促进了新罗王朝和唐朝的友好情谊。
但是游戏和娱乐的双面作用成为国家和官方颁布政令进行规制的重要原因。《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四十一记载:“上尝谓给事中丁公著曰:‘闻外间人多宴乐,此乃时和人安,足用为慰。’公著对曰:‘此非佳事,恐渐劳圣虑。’上曰:‘何故?’对曰:‘自天宝以来,公卿大夫竞为游宴,沈酣昼夜,优杂子女,不愧左右。如此不已,则百职皆废,陛下能无独忧劳乎!愿少加禁止,乃天下之福也。’”[14]可见国家态度影响到游戏的发展,因为游戏是把双刃剑。例如,唐初太宗皇帝在诏令里不无担忧地指出:“比年丰稔,闾里无事,乃有堕业之人,不雇家产,朋游无度,酣宴是耽。”[15]因此国家提倡饮酒礼,是通过对游艺和娱乐的规范以保障价值导向和巩固礼制。生活于初唐和盛唐年间的萧昕在《乡饮赋》中描述道:“今国家徵孝秀,辟贤良;则必设乡饮之礼,歌《鹿鸣》之章,故其事可得而详,立宾立主,或陛或堂;列豆举爵,鼓瑟吹簧。”[16]实际上,游戏本身更多的是渠道和中介作用,而其效果的正负是由多方面因素综合的结果。
三 游戏作为一种社会仪式
从更为抽象的层次来看,无论是游戏的起源、形式,还是游戏的功能、作用,都具有仪式作用。一方面,游戏被统治阶级当作一种统治的手段,因此其仪式和符号的功能被统治阶级放大。例如,“体育的庆贺功能还启发了统治者,可以寓伦理道德的教化于体育活动之中,让人们在愉悦融洽的氛围和心理共鸣的状态中,几乎不知不觉地接受了官方道德观念的潜移默化。是故,自西周以来的‘明君臣之礼’及‘明长幼之序’的礼射,‘习兵之礼’的田猎,‘乐宾习容讲艺’的投壶,直到唐代御前击球的尊君‘头筹’,宣扬‘仁义’道德的木射,乃至于围棋同封建道德修养的微妙关系等,莫不清清楚楚地反映出体育对于伦理道德的灌输传播,对于君臣关系以及其他人际关系的调适,所能产生的特殊作用。”[17]
另一方面,在特定的时间和场合,游戏的出现意味着意义的到来。比如,婚庆的特定时空里,适当的游戏成为烘托气氛、享受快乐的途径。这个时候,婚庆的意义大于游戏本身的意义。因此,游戏越来越成为一种仪式状态的存在,在社会关系方面扮演着多重角色。在唐代,“进士发榜后,照例还要举行一系列的社交礼节仪式,如拜谢座主,参谒宰相,加上名目繁多的游赏宴集活动”[18]。而与此相对,游戏作为一种社会仪式,也会成为各种力量交织的焦点,进而成为引发矛盾,甚或导致历史悲剧的中介因素之一。其中,广为人知的例子包括唐代薛胜的《拔河赋》以及《聊斋志异》中《促织》一文所带来的隐喻。实际上,这也意味着中国传统社会对游戏的观念和态度也是多重的。
总的来说,中国传统社会中游戏观念呈现以下几个基本的特征:一是带有强烈的阶级性,尤其是官方和民间、贵族和平民、正统和非正统等这些对立面的冲突,在游戏观念方面得以充分体现;二是游戏观念和游戏本身的属性有着密切关联,不同的游戏,民间或官方或者文人学士对待它们的态度不同,例如棋戏多为人们所倡导,博戏多为人们所诟病;三是游戏既是个体发展的路径,也是社会交往的纽带,还是社会文化的集中反映,可见游戏可以被视为整个社会的象征和符号系统,这暗示了它的媒介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