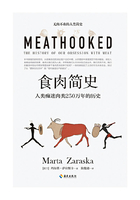
推荐序
大口吃肉
《食肉简史》不是一本肉香四溢,让人口舌生津,想要大块朵颐的文人式的美食书。而是与吃肉相关的社会文化史,其中有生物学、历史、化学、社会学,也有经济学,洋洋洒洒,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盘中之肉,仅仅是一个媒介,可以借以揭开肉背后的人类行为的历史。一块肉的历史里,暗藏着进化、政治、性、冲突、人口爆炸、代际关系、法律……一块肉串联起了上古时代与未来社会。
我日常的酒肉生活中,有许多酒肉朋友。年纪渐长,愈发觉得“酒肉朋友”并非贬义,“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因酒肉而纯粹,而长情。吃肉,似乎是我们日复一日的生活,事实不是这样。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7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9.3%,比1978年的63.9%下降了34.6个百分点。2018年,中国人几乎吃掉了超过世界肉制品总量的1/3的肉,人均达到68公斤。而30年前,中国人年均消耗的肉制品仅有13公斤。
至少在几十年前的中国,吃肉,还代表着一种奢侈与奖励。饥饿成为基因,写在我们的命运深处。在漫长的农业文明时代,人多地少,人们需要活着,需要摄取蛋白质,这就需要缘木求鱼、涸泽而渔,无所不尽其能。我经常听一些比我年纪大的人讲述自己童年时期的苦厄,对油脂的深切缅怀,对猪油渣的热情回顾——因为贫瘠,不轻易得到,故而印象深刻。
食物的获取来源与方式,变革着我们的餐桌文化,同时也隐约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态度。
如果把时间回溯2000年,那时候的中国人是如何吃肉的?这种有趣的联想,似乎可以和《食肉简史》做出一种有趣的交叉印证。
那时候,关于吃肉留下来的一个最著名的文字记载是《鸿门宴》:“……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哙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项王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张良曰: ‘沛公之参乘樊哙者也。’项王曰:‘壮士!——赐之卮酒。’则与斗卮酒。哙拜谢,起,立而饮之。项王曰:‘赐之彘肩。’则与一生彘肩。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啖之。”(《史记·项羽本纪》)
“拔剑切而啖之”,六个字,至今读来仍觉有冲冠霸气。
在更古老的年代,关于吃肉,有非常多细致的讲究,如今都消散在历史的尘埃中。还好有一本书,记录了一些痕迹。这本书是汉朝许慎编著的《说文解字》。
《说文解字》之中,也有不少纰漏,原因是许慎并没有见过甲骨文,甲骨文的现世,一直要等到1899年,王懿荣的出现。瑕不掩瑜,《说文解字》依然是了解古代生活细节的一个线索。
在先秦岁月,猪被称为豕。豕是普通家庭的财富,“陈豕于室,合家而祀”,这便是“家”的本意。在西周的时候,猪对于普通人家是珍贵的财富,不是天天能吃的。然而相对于牛和羊而言,猪肉则更为日常,即便是庶民也能吃得上,牛肉和羊肉则都是有等级规格的食物,并非寻常百姓能吃到的。
在我们这个时代,对猪的称谓往往是词,诸如公猪、母猪、猪心、猪肺、猪头、猪骨……而在先秦时代,猪的不同形态与不同部位则有着固定的字,其种类繁多,严格有序,比现在的称呼复杂许多。由此可见,先秦时代并非粗鄙,在饮食上,细致讲究,花样繁多。在我看来,其中包含着先民对食物的敬重与珍惜。
“豚”指的是小猪,这是用来祭祀的。古人当然知道乳猪的妙处——越小越嫩。在《论语》中,阳货想要拜会孔子,就为他准备了一只蒸熟的小猪,“归孔子豚”。豚字还有另外一种含义,是指被阉割的猪,能长得很肥硕,这个词在日文中被传承了下来,许多日本餐厅里都必有的是“豚骨拉面”。“豨”特指的是三个月大的小猪;“豵”指的则是六个月大的小猪;长到一岁的猪则称为“豝”;而到了三岁,猪被叫做“豣”。
与此相类似的叫法还有牛。初生的小牛称之为“犊”(这个叫法沿袭至今),公牛称为“牡”,母牛叫作“牝”,没有阉割去势的牛称为“特”(后来这个词被引申为超乎一般的,特别的),四岁的牛称为“牭”,八岁的牛称为“犕”。
这仅仅是一小部分的专属名词,翻阅《说文解字》,能见到更多的字,它们被古人用来形容细碎的事情。
养好的猪,需要被宰割。在古代的文字中,有一篇著名的《庖丁解牛》,出自《庄子》,宰割技术之高妙,可以达到艺术的层面。宰割牲畜,也有诸多讲究,一口猪先是被一分为二,左边一半叫“左胖”,右边一半叫“右胖”。
孔子说“割不正,不食”,在先民时代,切割是大义,一块没有切割好的肉,如同一棵长歪的树,无法成材。关于割肉的方法与形状,古文中也有许多专用名词,这些词大多也消失不见了。“膞”是指切成块的肉;“胾”是大块的肉;“䐑”指的是切得很薄的肉片;而“脍”指的是切得很细的肉,著名的一句话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散”是杂碎的肉……
干肉,也就是腊脯,这是一种储存肉的方法——把肉做成各种干肉。在周朝的时候,有一个职业叫“腊人”,专门负责制作各种腊肉。腊肉也用于祭祀。关于祭祀的腊肉,又有颇多讲究,比如长度需要是一尺二寸。
不同风味的腊肉有不同的叫法,其中有“脩”,这是姜桂等香料腌渍过再风干的肉,味道似乎更有风味。“脯”则是肉片;“腊”是整个的风干。
楚辞《招魂》中有段落描述楚地美食:“室家遂宗,食多方些。稻粢穱麦,挐黄梁些。大苦醎酸,辛甘行些。肥牛之腱,臑若芳些。和酸若苦,陈吴羹些。胹鳖炮羔,有柘浆些。鹄酸臇凫,煎鸿鸧些。露鸡臛蠵,厉而不爽些。粔籹蜜饵,有餦餭些。瑶浆蜜勺,实羽觞些。挫糟冻饮,酎清凉些。华酌既陈,有琼浆些。”以现在的眼光即便读着有点拗口,也能在字里行间闻到油脂芬芳。
在更早的时候,人们已经发明了煮羹的器具“鬲”。最早的羹不加调料,讲究“大羹不和”,就是纯肉汁,再搭配上种种的酱料。那时的酱料文化也极为发达,不同的菜搭配不同的酱,讲究极其严格。到了后来,羹的种类越来越多,也越来越讲究调和之味。古时有五味,常规的说法是“酸、苦、辛、咸、甘”。孔子还有一句话“不得其酱,不食”。古人做酱醯也有固定程序:先把肉切薄片晒干,再把肉干切碎成肉末,用粱曲和盐搅拌,然后加入美酒,放在坛子里,封好口,一百日即成。不同口味的酱用来搭配不同的食物,搭配错了,是叫人笑话的。
许多食物都掩映在文字的缝隙中,那些食材与讲究,那些稻谷与果蔬,还有那一夜的鸿门宴,人们在宴席上喝酒吃肉,钩心斗角,一个瞬间的犹豫,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许多都无从谈起,与那场宴席距离最近的一本书是《吕氏春秋》,为秦朝吕不韦所编。翻遍《吕氏春秋》,写美食的有一段:“肉之美者:猩猩之唇,獾獾之炙,隽燕之翠,述荡之挈,旄象之约。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凤之丸,沃民所食。鱼之美者:洞庭之鳙,东海之鲕,醴水之鱼,名曰朱鳖,六足,有珠百碧。藿水之鱼,名曰鳐,其状若鲤而有翼,常从西海夜飞,游于东海。”
这本书的成书时间与鸿门宴相隔30年。我并没有在其中见到一些具体的食物,这更像是用想象中的食物写的一首诗。我与鸿门宴相隔2 200多年,我也想着用那些美味的食材写另外一首诗。尽管我没有找到一条能飞的鱼,可以“从西海夜飞,游于东海。”
几千年之后,我们掉书袋似的追忆从前的吃肉岁月,在漫长的人类生存的历史上,“大口吃肉”不仅仅是一个动作,也是一种善良的祝福。
小宽 诗人美食家
2020年5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