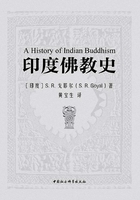
二 吠陀宗教传统
吠陀文献编年
在印度河流域文明衰亡后,主导印度舞台的吠陀雅利安人的宗教可以从他们的文献中获知。一般说来,梵语文献可以分为两大类:吠陀的和非吠陀的(或吠陀之后的)。本集  、梵书
、梵书 、森林书
、森林书  和奥义书
和奥义书  被包括在吠陀文献中[29],而经书
被包括在吠陀文献中[29],而经书  、律书
、律书  、史诗、古典文学、哲学著作、注疏和手册,这些属于吠陀之后的文献。现在无人怀疑《梨俱吠陀》是最古老的雅利安人文献。尽管普遍认同这种观点,而对于其可能的年代则观点不一。马克斯·缪勒(Max Müller)确定为约公元前1200年。他的观点十分流行,尤其是在西方印度学家中间,虽然惠特尼(Whitney)提出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为最古老的颂诗时期[30]。应该记住的是,在古代世界,从印度到欧洲,没有见到哪里的印欧人(吠陀雅利安人是它的一个分支)早于公元前2000年。例如,巴比伦的卡西特人,安纳托利亚的赫梯人,希腊的迈锡尼人,都出现在公元前两千纪初。因此,印度雅利安人的出现和《梨俱吠陀》的起始不可能早于公元前2000年。另一方面,它不可能晚于这个年代很多,否则,在公元前1400年的波卡兹科易文献中出现的吠陀神名就变得不可理解。这样,印度雅利安人的出现和《梨俱吠陀》的起始在公元前2000年,与考古学、吠陀语文学、古代印度史和西亚史的证据达成一致[31]。关于吠陀文献的上限,一般能正确地相信完成于公元前六世纪。然而,可以再次强调指出,吠陀文本互相重叠,以致《阿达婆吠陀》的起始被认为几乎与《梨俱吠陀》同样早(虽然其中大部分晚于《梨俱吠陀》的大部分),而《梨俱吠陀》的目前形式也被认为包含最晚期的吠陀文献材料[32]。
、史诗、古典文学、哲学著作、注疏和手册,这些属于吠陀之后的文献。现在无人怀疑《梨俱吠陀》是最古老的雅利安人文献。尽管普遍认同这种观点,而对于其可能的年代则观点不一。马克斯·缪勒(Max Müller)确定为约公元前1200年。他的观点十分流行,尤其是在西方印度学家中间,虽然惠特尼(Whitney)提出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为最古老的颂诗时期[30]。应该记住的是,在古代世界,从印度到欧洲,没有见到哪里的印欧人(吠陀雅利安人是它的一个分支)早于公元前2000年。例如,巴比伦的卡西特人,安纳托利亚的赫梯人,希腊的迈锡尼人,都出现在公元前两千纪初。因此,印度雅利安人的出现和《梨俱吠陀》的起始不可能早于公元前2000年。另一方面,它不可能晚于这个年代很多,否则,在公元前1400年的波卡兹科易文献中出现的吠陀神名就变得不可理解。这样,印度雅利安人的出现和《梨俱吠陀》的起始在公元前2000年,与考古学、吠陀语文学、古代印度史和西亚史的证据达成一致[31]。关于吠陀文献的上限,一般能正确地相信完成于公元前六世纪。然而,可以再次强调指出,吠陀文本互相重叠,以致《阿达婆吠陀》的起始被认为几乎与《梨俱吠陀》同样早(虽然其中大部分晚于《梨俱吠陀》的大部分),而《梨俱吠陀》的目前形式也被认为包含最晚期的吠陀文献材料[32]。
在近些年,乔希(L.M.Joshi)[33]试图证明吠陀文本出现于很晚的年代。他的观点需要略加讨论,因为它们与佛教观念的起源和古老性有直接关联。乔希猜测公元前1400年著名的波卡兹科易铭文中提到的米坦尔人的神祇代表伊朗人和印度雅利安人“尚未分离的”雅利安人的历史阶段。这些神祇后来(即公元前1400年之后)出现在吠陀雅利安人的万神殿中。他认为“吠陀文献传统的起始可以安排在约公元前两千纪中叶哈拉巴文化衰亡之后的一些世纪”。《夜柔吠陀》的《泰帝利耶本集》不晚于公元前600年。梵书可能编撰于公元前八世纪和公元前五世纪之间,虽然好几种梵书的晚出部分可能增添于佛陀之后的一世纪。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将甚至最古老的奥义书定在佛陀之前的年代。《大森林奥义书》、《歌者奥义书》的出现或许能安排在公元前五世纪,但其他的奥义书,即《泰帝利耶奥义书》、《伽陀奥义书》、《由谁奥义书》、《爱多雷耶奥义书》、《憍尸多基奥义书》、《剃发奥义书》、《疑问奥义书》和《白骡奥义书》或许“属于公元前三、四世纪”。《摩诃那罗延奥义书》、《弥勒奥义书》和《蛙氏奥义书》“属于公元一世纪”,即到达贵霜王朝时代[34]。这位佛教学者渴望确定吠陀文献可能的最晚年代,与他一心想要证明与佛教相联系的观念和体制的古老和深远影响相匹配。他奇怪地猜测[35]遮那迦牟尼佛和他的后继者迦叶佛(非常晚出的过去佛构想)完全可能是真实人物,出现在公元前900年和公元前800年。他处处提出奇怪的设想:与佛教观念或体制哪怕只有模糊相似的每种观念或体制都必定是这种宗教影响的结果,因此都晚于佛陀的年代。他似乎认为雅利安人除了祭祀崇拜外,没有任何实质贡献。他甚至试图推定后来怛特罗佛教成就师依随的密教实践极其古老,以致他认为莫亨焦达罗出土的著名兽主印章上刻画的男性神是“密教成就师的原型”,以及在同一遗址出土的著名青铜“舞女”塑像是“怛特罗瑜伽女的原型”[36]。我们认为如果有人将沙门观念追溯到吠陀和印度河流域文明,这十分合理。然而,如果有人试图证明印度河流域文明中存在怛特罗成就师传统,实在是太过分。这只能说明这是处心积虑想要证明印度宗教传统中的一种特殊派别的古老性。认为《梨俱吠陀》起始于公元前两千纪中期之后若干世纪以及所有吠陀奥义书构成于公元前五世纪之后,某些在贵霜王朝,这种理论也代表同样的心理状态。众所周知,约公元前400年,随着摩诃钵德摩难陀终结吠陀刹帝利王朝,吠陀时代终止。现在,整个北印度由首陀罗  和弗拉底耶(
和弗拉底耶( ,“无种姓者”)出身的统治者支配。甚至佛陀时代的政治状况也明显晚于奥义书中反映的政治状况。奥义书中提到迦尸是独立的王国,阿湿瓦波提、遮那迦和波罗瓦赫那·遮瓦利等国王肯定远早于公元前六世纪。而北比哈尔由跋祇人和离车人统治时,迦尸已经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奥义书中的遮那迦无论如何不可能晚于格拉罗·遮那迦,后者的垮台导致毗提诃国的君主制的解体和跋祇国的共和制的确立,这必定早于佛陀时代一个多世纪。奥义书中的阿阇世王明显属于贝拿勒斯著名的梵授王朝,其统治时期也早于佛陀时代。奥义书的语言明显晚于《梨俱吠陀》的语言,但同时早于古典梵语,其中能发现许多波你尼时代之前的较古的习惯用语。其中有大量接近梵书的散文,因此肯定能认为其早于佛陀和波你尼时代[37]。实际上,除了《弥勒奥义书》和《蛙氏奥义书》,没有哪部早期的或吠陀的奥义书能安排在吠陀之后时期[38]。罗易乔杜里(Raychaudhuri)[39]确定《摩诃婆罗多》大战年代的论点显然是错误的,而乔希为了证明奥义书晚出而加以滥用。按照这种论点,《商卡耶那森林书》中提到的古那克亚·商卡耶那间隔乌达罗迦·阿鲁尼只有两代,间隔般度族阿周那的孙子继绝七代或八代。罗易乔杜里将古那克亚·商卡耶那放在六世纪[40],设想每位族长的平均跨度为三十年,将继绝放在公元前九世纪。但是,他忘却《大森林奥义书》、《世系梵书》和《阇弥尼奥义梵书》也含有这些世系序列名单,其中的族长共有四十或四十多代。因此,如果这些名单中的乌达罗迦·阿鲁尼只早于公元前六世纪两代,那么,这些名单中的最后一代,由此这些文本的最后构成时间,必须放在一千年之后,即在笈多王朝时代。这就成了一种荒谬的主张。
,“无种姓者”)出身的统治者支配。甚至佛陀时代的政治状况也明显晚于奥义书中反映的政治状况。奥义书中提到迦尸是独立的王国,阿湿瓦波提、遮那迦和波罗瓦赫那·遮瓦利等国王肯定远早于公元前六世纪。而北比哈尔由跋祇人和离车人统治时,迦尸已经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奥义书中的遮那迦无论如何不可能晚于格拉罗·遮那迦,后者的垮台导致毗提诃国的君主制的解体和跋祇国的共和制的确立,这必定早于佛陀时代一个多世纪。奥义书中的阿阇世王明显属于贝拿勒斯著名的梵授王朝,其统治时期也早于佛陀时代。奥义书的语言明显晚于《梨俱吠陀》的语言,但同时早于古典梵语,其中能发现许多波你尼时代之前的较古的习惯用语。其中有大量接近梵书的散文,因此肯定能认为其早于佛陀和波你尼时代[37]。实际上,除了《弥勒奥义书》和《蛙氏奥义书》,没有哪部早期的或吠陀的奥义书能安排在吠陀之后时期[38]。罗易乔杜里(Raychaudhuri)[39]确定《摩诃婆罗多》大战年代的论点显然是错误的,而乔希为了证明奥义书晚出而加以滥用。按照这种论点,《商卡耶那森林书》中提到的古那克亚·商卡耶那间隔乌达罗迦·阿鲁尼只有两代,间隔般度族阿周那的孙子继绝七代或八代。罗易乔杜里将古那克亚·商卡耶那放在六世纪[40],设想每位族长的平均跨度为三十年,将继绝放在公元前九世纪。但是,他忘却《大森林奥义书》、《世系梵书》和《阇弥尼奥义梵书》也含有这些世系序列名单,其中的族长共有四十或四十多代。因此,如果这些名单中的乌达罗迦·阿鲁尼只早于公元前六世纪两代,那么,这些名单中的最后一代,由此这些文本的最后构成时间,必须放在一千年之后,即在笈多王朝时代。这就成了一种荒谬的主张。
梨俱吠陀宗教的一般特征
尽管如此,很明显《梨俱吠陀》的主要部分的产生时间早于后期本集和梵书一些世纪,虽然《梨俱吠陀》的某些部分可能出现很晚[41]。因此,《梨俱吠陀》或早期吠陀时代的宗教氛围不同于中期吠陀时代(即后期本集和梵书文本)的宗教氛围。接着,中期吠陀时代又不同于后期吠陀时代或奥义书时代的宗教氛围。
吠陀宗教(包括《梨俱吠陀》以及后期本集和梵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实用性和功利性。那些诗节虽然富有诗性,而同时意味供家庭祭司或歌手在祭祀仪式上吟诵或吟唱。祭司进行祈祷,提供祭品苏摩酒或凝乳,转而期望诸神给予祭祀者回报,诸如长寿、兴旺、牲畜和尚武的儿子等。按照布卢姆菲尔德(Bloomfield)的说法,“坦率的、无条件的交换成了公认的动机”[42]。
吠陀宗教是坦率地入世或现世的  。它给予崇拜者或家主的保证不是永生
。它给予崇拜者或家主的保证不是永生  或天国(svarga),而是长命百岁、兴旺和尚武的子孙,总之,一切现世的享乐。征服敌人、摆脱疾病和丰富的饮食似乎是吠陀雅利安人最渴望的目标。提到永生或与天神同住天国的情况是十分稀少的。
或天国(svarga),而是长命百岁、兴旺和尚武的子孙,总之,一切现世的享乐。征服敌人、摆脱疾病和丰富的饮食似乎是吠陀雅利安人最渴望的目标。提到永生或与天神同住天国的情况是十分稀少的。
吠陀宗教的另一个特征即本质上是祭司的宗教[43]。祭司在祭祀仪式中享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们是王公们和诸神之间的调解者。他们用祈祷和祭品抚慰和取悦诸神,诸神仿佛实际参与人类的战斗,使受恩宠的一方获胜。有时,双方武士祈求同样的神帮助,而诸神帮助他们恩宠的一方战胜另一方。这里似乎呈现这样的精神观念:凡受天神支持的人获得成功或胜利。
吠陀宗教是社会上层的宗教。它的前提条件是相当规模的家业、富裕的家主和大量的资财,许多祭司毫不羞于索取丰厚的酬金。它肯定不同于民间的宗教或穷人的宗教。后者采取谦卑的仪式,依靠巫师和医师,这在《阿达婆吠陀》和家庭经  中有所描述。
中有所描述。
梨俱吠陀的祭祀
吠陀宗教本质上是祭祀  的宗教。崇拜者吟唱祷词,向神供奉祭品,期望神回报恩惠,满足他们的愿望。这样,正如前面提到的,它是神和人之间互相给和取的关系。主要有两类祭祀。
的宗教。崇拜者吟唱祷词,向神供奉祭品,期望神回报恩惠,满足他们的愿望。这样,正如前面提到的,它是神和人之间互相给和取的关系。主要有两类祭祀。
(1)家庭祭  :《梨俱吠陀》中某些颂诗是在出生、结婚或其他日常生活喜庆场合、葬礼、祭祖以及求取牲畜成群和谷物丰收的仪式上用作祝福词和祷词。这些仪式称为家庭祭,属于最简易的祭祀,即向火中投放牛奶、谷物、凝乳或肉食。
:《梨俱吠陀》中某些颂诗是在出生、结婚或其他日常生活喜庆场合、葬礼、祭祖以及求取牲畜成群和谷物丰收的仪式上用作祝福词和祷词。这些仪式称为家庭祭,属于最简易的祭祀,即向火中投放牛奶、谷物、凝乳或肉食。
(2)天启祭(Srauta):这类祭祀尤其与崇拜因陀罗有关的苏摩酒祭相联系。它们只能由贵族和富人(maghavan)以及国王举行。天启祭要求比较宽广的祭祀场地,设置三个祭坛(citi),点燃三堆祭火,由四位主要的祭司带领一群祭司代表祭祀者  举行许多繁琐复杂的仪式,由此他们也接受祭祀者慷慨的酬报
举行许多繁琐复杂的仪式,由此他们也接受祭祀者慷慨的酬报 。祭祀者本人无需操劳。那些阿波利
。祭祀者本人无需操劳。那些阿波利  颂诗表明动物祭。那首原人
颂诗表明动物祭。那首原人  颂诗不是描述实际的人祭,而完全可能只是保留对人祭的记忆。
颂诗不是描述实际的人祭,而完全可能只是保留对人祭的记忆。
梨俱吠陀诸神
人性化的梨俱吠陀诸神同样具有人的弱点,明显被认为容易接受奉承和礼物。一顿丰盛的饭食就能赢得神的恩宠。《梨俱吠陀》中也提到谢恩祭品。期望回报是人们提供祷词和祭品的主要动机。然而,在《梨俱吠陀》中,祭祀仍然只是一种影响诸神恩宠祭祀者的手段。这样的观念还没有得到发展:只要崇拜者掌握正确的手段,就能控制诸神[44]。
梨俱吠陀诗人对看似神秘的、强大的自然力量的运作深感惊奇。这种运作的不可解释的神秘性几乎使这些自然力量带有一种“超自然”特性或神性。他们将这些自然力量看作是神的威力,将各种自然现象看作是人格化存在的行为[45]。因此,梨俱吠陀仙人 的宗教在初期本质上是一种多神教。其中,自然力量被神化为诸神,受到崇拜。
的宗教在初期本质上是一种多神教。其中,自然力量被神化为诸神,受到崇拜。
可能在印欧时期产生了拟人化的天神概念,如提奥(Dyaus,天空神)、密多罗(Mitra)或双马童  [46]。因此,梨俱吠陀的诸神被构想为人,具有超自然力量的人,摆脱了死亡,但仍然受缚于生,类似处在家庭关系中的人。然而,吠陀诸神缺乏希腊诸神的鲜明人格,也不像希腊男神和女神那样,通常很容易看出吠陀诸神的拟人化形态只是蒙在他们的自然成分上的一层薄纱。
[46]。因此,梨俱吠陀的诸神被构想为人,具有超自然力量的人,摆脱了死亡,但仍然受缚于生,类似处在家庭关系中的人。然而,吠陀诸神缺乏希腊诸神的鲜明人格,也不像希腊男神和女神那样,通常很容易看出吠陀诸神的拟人化形态只是蒙在他们的自然成分上的一层薄纱。
在吠陀诸神中见到的拟人化程度极其多样。在一些例举中,始终呈现实际的成分。例如,水确实是女神,也是可以饮用的。女神乌霞( ,黎明女神)被描写成美丽的少女,但也表现为自然的朝霞。太阳神苏尔耶
,黎明女神)被描写成美丽的少女,但也表现为自然的朝霞。太阳神苏尔耶  是天空的儿子,但始终保持太阳的自然形态,妨碍了它的拟人化形态的发展。火神阿耆尼(Agni)也遇到同样的情况,从未真正摆脱火的自然成分。
是天空的儿子,但始终保持太阳的自然形态,妨碍了它的拟人化形态的发展。火神阿耆尼(Agni)也遇到同样的情况,从未真正摆脱火的自然成分。
另一方面,因陀罗(Indra)是或多或少摆脱作为神的概念所由产生的自然现象的诸神之一。或许吠陀仙人已经不记得他们所象征的自然成分。伐楼那  更是失去了他的自然成分的痕迹。双马童也已经失去他们源于自然的任何迹象。
更是失去了他的自然成分的痕迹。双马童也已经失去他们源于自然的任何迹象。
在讨论诸神形态问题时  ,耶斯迦
,耶斯迦  说有三种不同观点:诸神具有人的形态,诸神不具有人的形态,诸神部分具有和部分不具有人的形态。这一事实是吠陀诸神没有获得充分人格化的又一证明。
说有三种不同观点:诸神具有人的形态,诸神不具有人的形态,诸神部分具有和部分不具有人的形态。这一事实是吠陀诸神没有获得充分人格化的又一证明。
大多数吠陀自然神被正常地构想为人形,同时也有一些神被构想为兽形。奥登伯格(Oldenberg)断言在早期宗教中,兽形神的构想比人形神更常见。但基思(Keith)认为这种理论得不到证实[47]。记载中的兽形神只有两种:独足山羊  和深水蛇(Ahi budhnya)。
和深水蛇(Ahi budhnya)。
除了那些重要的自然神的具体形象外,还有一些具有特定功能的神,虽然他们也被构想为自然力量。这类神中的典型例子是田野神  和室内神
和室内神  。这种思维态势的进一步发展,便产生诸如愤怒和语言这类没有任何直接的具体背景的神。这类神还可以提到沙维特利
。这种思维态势的进一步发展,便产生诸如愤怒和语言这类没有任何直接的具体背景的神。这类神还可以提到沙维特利  、达特利
、达特利  、德拉特利
、德拉特利  和德瓦湿特利
和德瓦湿特利  ,分别执掌推动、创造、保护和制作[48]。
,分别执掌推动、创造、保护和制作[48]。
对天上、空中和地上的自然现象的崇拜有别于对尘世对象或动物的崇敬。这些尘世对象或动物据信充满着在一定条件下适用于一定目的的神的精神。祭司崇拜他们的祭祀用具,诸如压榨石、祭柱和诸神应邀入座的圣草,被猜想在祭祀期间充满着神的精神气息。在《梨俱吠陀》中有一处,一位诗人说道:“谁出十头牛买我的这个因陀罗,等他战胜了他的仇敌,再把它还给我。”[49]按照基思的说法,这里意味某种因陀罗偶像,或者是一种粗糙的拟人画像,或者是一种更粗陋的物件。而更可能的是后者,因为直至吠陀时期结束,没有以其他方式暗示有神的塑像[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