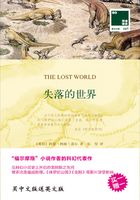
第2章 找查林杰教授去试试运气
麦卡德尔是我们报社的一名新闻编辑,上了年纪,脾气暴躁,有点儿驼背,一头红褐色的头发。我一向很喜欢他,也非常希望他能欣赏我。当然了,博蒙特才是真正的老板,但他一向高高在上,所关心的只有诸如国际危机或内阁分裂之类的大事。有时候,我们能看见他带着威严独自走进他的办公室,他目光迷离,估计思绪正盘桓在如巴尔干半岛或波斯湾这些地方发生的那些大事上。他跟我们不在同一层次,也不在同一个圈子里。但是麦卡德尔不一样,他是博蒙特的第一助理,是我们所熟悉的一个人。我走进办公室的时候,麦卡德尔朝我点了点头,把眼镜推到了光秃秃的前额上。
“嗯,马龙先生,据我了解,你最近表现不错啊。”他操着苏格兰口音说,语气里满是善意。
我对他表示了感谢。
“那次矿难中你的表现非常出色。还有在南华克区的火灾中,表现也很棒。你在这一行挺有天赋的。你找我有什么事?”
“想请您帮个忙。”
他立刻露出了警觉的神色,眼睛避开了我的目光。“啧,啧!什么事?”
“先生,您看,报社现在有没有什么任务可以派我去采访呢?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给您带些好稿子回来的。”
“你想要什么样的任务呢,马龙先生?”
“嗯,先生,只要是充满奇遇和需要冒险的任务都可以,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越是困难的任务,就越适合我。”
“你这是迫不及待地要找死啊。”
“只是为了证明自己人生的意义。”
“哇,马龙先生,这可真是太——太高尚了。恐怕像你这样有这种想法的人现在已经不多见了。所谓‘特殊任务’所要求付出的代价跟它带来的结果有时候并不成正比。在任何情况下,只有一个能够博得公众信任、阅历丰富的人才会接受这样一项任务。看看如今的地图,世界上每个角落都挤得满满当当,已经没有什么空间来容纳传奇故事了。不过,等等!”他脸上突然露出了微笑,继续说道:“说到地图,倒让我产生了一个想法。揭露一桩欺诈怎么样——那个夸夸其谈的家伙——揭露他荒谬可笑的本质。你可以将他骗子的嘴脸公之于众!呃,小伙子,这事儿不错。你看呢?”
“随便什么事,什么地方,我都无所谓。”
麦卡德尔陷入了片刻的沉思。
“我在想你能不能跟那个家伙建立友好的关系,至少得跟他顺畅地交流,”最后,他说,“你好像具有一种与人建立关系的天赋——同情心,还是天生的吸引力,或者是年轻人的活力,或是什么别的因素。我自己就能感受到这一点。”
“您人真好,先生。”
“那么你去找恩摩尔公园的查林杰教授试试运气吧。”
我当时几乎掩饰不住内心的吃惊。
“查林杰!”我大声喊出来,“查林杰教授,那个著名的动物学家!《电讯报》布伦德尔的头盖骨不就是被他打碎的吗?”
麦卡德尔笑了笑,脸上的表情有点阴森。
“你不愿意吗?你不是说想找需要冒险的任务吗?”
“是任务本身危险,先生。”我回答说。
“的确。我觉得他也不会总是那么暴力的。我想应该是布伦德尔去找他的时机不对吧,又或者是他的方式有问题。你运气可能会好一些,而且,你跟他打交道的方式也可能会更加圆滑。你有这个能力,我能肯定,况且这也是《每日公报》必须要完成的任务。”
“我对他一点儿都不了解,”我说,“这个人的名字给我留下的唯一印象就是他曾经因为袭击了布伦德尔上了法庭。”
“我这有些记录可能会对你有用,马龙先生。我关注这位教授有一段时间了。”他从一个抽屉里拿出来一张纸。“这是关于他的记录的一份总结。我简要地给你做一下介绍:
乔治·爱德华·查林杰
出生日期:一八六三年。
出生地:拉格斯。
受教育情况:拉格斯学院;爱丁堡大学。
一八九二年任大英博物馆助理;一八九三年任比较人类学系助理管理员;同年,由于书信纠纷辞职。曾因动物学研究成果获得克基斯顿奖章。是——嗯,很多组织的——外籍会员。组织数量很多,用小号字打了有两英寸长,有比利时兴业、美国科学院、拉普拉塔等;古经济瞭望,英伦协会等等。还是生物学协会前任主席。
出版物:《关于卡尔梅特人头骨研究的观察报告》,《脊椎动物进化大纲》,还有很多论文,包括《维斯曼学说的潜在谬论》,这篇文章曾经在维也纳动物学大会上引发过热烈的讨论。
休闲娱乐:散步,爬阿尔卑斯山。
家庭住址:恩摩尔公园,肯辛顿,西区。
“给!你带上吧。我能给你提供的只有这些了。”
我将这张纸装进口袋。
当我再抬起头的时候,他已经低下了头,我看到的已经不再是他那红彤彤的脸庞,而是粉红色光秃秃的头顶了。“等一下,先生。”我说,“可是我还不清楚为什么要去采访这位先生呢。他干什么了?”
他的头又重新抬起来。
“他两年前独自去南美洲进行考察了,去年才回来。他去的肯定是南美洲没错,但是他却拒绝透露具体的考察地点。开始的时候,他对这次探险描述得模模糊糊,但是后来有人开始指出他话里的漏洞,他就闭口不谈了。他一定是有什么惊人的发现——但是更多人的猜测是,他根本就是个头号大骗子。他的一些照片被毁掉了,据说是造的假。而且他也变得极其敏感,任何人提出问题都会受到他的攻击,记者们也都被他拒之门外。依我看,他也就是个暴力的夸大狂,不过刚好从事科学研究罢了。这就是你要采访的人,马龙先生。现在,出发吧,看看能从他那儿问出点儿什么。你年龄不小了,足以照顾好自己了。无论如何,你的安全都是有保证的,有《雇佣人责任法》呢,你是知道的。”
那张笑容灿烂的红彤彤的脸又低了下去,呈现在我眼前的又变成了那粉红色的光头,只有边缘处有几根细细的绒毛。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我朝野人俱乐部走过去,但是没有进去,而是靠在露台的栏杆上,长久地望着那黑黝黝、油乎乎的河水,脑子里思绪万千。在室外,我的头脑总是更加清醒,能够更加冷静地进行思考。我拿出了关于查林杰教授的那份简介,借着灯光看起来。终于,我发现了唯一让我觉得鼓舞人心的一点。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从我被告知的情况看,我深知我永远不应该希望与这位性情暴戾的教授产生什么联系。但是他的简介中提到过两次暴力冲突事件,这只能说明他是个科学狂人。难道就没有什么迹象表明他也是个平易近人的人吗?我要试一试。
我走进了俱乐部。才刚过十一点,宽敞的房间里已经聚集了不少人了,但是再等一会儿,肯定还会有大批人涌进来。我注意到火炉旁边坐着一个高高瘦瘦、棱角分明的男人。我将自己的椅子向他拉近,他朝我转过身来。从后来的情况看,我当时真是选对了人。他叫塔尔普·亨利,《自然》报社的记者,他又干又瘦,皮肤粗糙,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为人心地很善良。我开门见山地问:“你对查林杰教授了解多少?”
“查林杰?”他皱了皱眉,似乎表达了不赞赏的态度,“查林杰就是那个从南美洲带回来荒诞可笑故事的人。”
“什么故事?”
“哦,就是说他在那里发现了一种奇怪的动物,无稽之谈。我认为他就是在作出了那个发现后才回来的。不知为什么,他没有将消息公开。他接受了路透社的专访,但他不愿意这件事被大肆宣传。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有那么一两个家伙想要好好挖掘一下,但是也很快被他制止了。”
“怎么制止的?”
“呵呵,以他那令人无法容忍的粗鲁和不可思议的行为呗。其中之一就是可怜的沃德利老兄,就是动物研究所的那位。沃德利给他写了一封信:‘动物研究所所长向查林杰教授致敬,若蒙不弃,请前来参加本所下次会议,鄙人将感到无上荣幸。’结果对方的回复简直不堪入耳。”
“他怎么说?”
“嗯,原话很难听,大致意思是:‘查林杰教授向动物研究所所长致敬,如果您能去死那将是我的无上荣幸。’”
“我的天啊!”
“没错,我想沃德利老兄肯定跟你发出了一样的感慨。我还记得他在会议上的哀诉,第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在与科学界长达五十年的来往交际中——’这件事对他打击真是很大。”
“关于查林杰教授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情况?”
“嗯,你知道的,我是一名细菌学家。我就生活在九百倍的显微镜里。我很难说对自己通过裸眼看到的现象观察得多么仔细。我是在可知范围的边缘奋斗的一名拓荒者,一旦离开了自己的研究领域,跟你们这个强大、强硬、庞大的群体打交道时,我都会有格格不入的感觉。关于一些流言蜚语,我总是表现得有些漠然,然而,在一些科学界的座谈会上,我也听到过一些关于查林杰的传言,因为他属于那种不容人忽视的人。这个人极其聪明——像刚刚充满电的电池,拥有无限的力量和活力,喜欢追求新奇事物,但是又容易与人争执,脾气性情不怎么样,没有道德底线,甚至到了伪造南美任务照片的地步。”
“你说他喜欢追求新奇事物,那他是追求哪方面的新奇事物?”
“方方面面,最近的一次,他关注的是‘维斯曼与进化论’。我相信他在维也纳就是因为这个与人发生了极其激烈的争执。”
“能不能把他的观点告诉我?”
“现在不行,但是我保留了一份会议过程记录,在办公室存档了。你愿意的话可以跟我来拿。”
“这正是我想要的。我接受了采访他的任务,需要提前对他有点儿了解。你能帮我一把真是太好了。如果你不嫌太晚的话,我现在就跟你去。”
半小时后,我坐在《自然》报社的办公室里,面前放着一本大部头的书。书翻开至一篇题目为“维斯曼与达尔文”的文章,副标题是“维也纳的激烈抗议——会议现场记录”。我以前对科学知识方面的学习似乎已经荒废了,这场辩论对我来说理解起来非常困难。但是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这位英国的教授在整个辩论过程中表现得咄咄逼人,让他欧洲大陆的同事们颇为恼怒。“抗议”“哗然”“全体向主席投诉”,这是在第一部分引起我注意的三个词语。其他内容对我来说就好像是天书,根本看不懂。
“希望你能帮我翻译成英语。”我可怜巴巴地对我的帮手说。
“呵呵,这就是翻译好的。”
“那我还是看看原文试试好了。”
“对于一个门外汉来讲,确实是深奥了点。”
“哪怕我能找到一个能看懂的、发人深思的句子也好啊。啊,好,这句就行。我模模糊糊能明白一点儿它的意思,我要把它抄下来,这句话将成为我与这位可怕的教授联系的桥梁。”
“就没有什么其他我能帮忙的了吗?”
“嗯,有。我要给他写封信。我想在你这儿起草,并且用你的地址。”
“那家伙肯定会找上门来,大吵一架,砸了我们的报社。”
“不,不。你会看到这封信的,不会有任何争议,我保证。”
“好吧,那是我的办公桌,那儿有纸。写完我得先检查一遍。”
写信费了一番力气,写完之后我给自己打了打气,告诉自己写得还不错。带着些许自豪,我将自己的作品念给那位挑剔的细菌学家听。
“亲爱的查林杰教授,”我在信中写道,“鄙人是《自然》报社的一名职员,对于您关于‘维斯曼与达尔文观点的区别’深感兴趣。最近,我有幸阅读了——”
“你这个该死的骗子!”塔尔普·亨利小声嘟囔着。
“——您在维也纳精湛的演讲,让我深受启发。您陈述的观点清晰透彻、令人钦佩,一定是这个问题的最后定论了。然而,里面有一句话,就是:‘一种教条的、令人难以忍受的观点认为,每一个独立的个体都是一个微观世界,是一个需要对连续几代人的研究进行阐述的历史架构,对于这一观点我要提出强烈的抗议。’难道您不希望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对此观点进行修正吗?您不觉得这个观点有点儿过于激进了吗?如您允许,我希望能够有幸对您进行采访。我本人对这一话题很感兴趣,并有几点建议,希望能够与您当面阐述。如您允许,我将于后天(周三)上午十一点前去拜访。致以我深深的敬意,爱德华·D.马龙。”
“怎么样?”我得意洋洋地问。
“呵呵,只要你觉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行。”
“到目前为止还没什么受不了的。”
“但是你打算下一步怎么做呢?”
“先到那儿再说。只要我进了他的房间,没准儿就找到突破口了。我甚至可能会主动坦白。如果他是个爱好体育运动的人,他一定会忍俊不禁的。”
“忍俊不禁,还真是呢!他很有可能会忍俊不禁。锁子甲或是橄榄球服——那才是你想要的东西吧。好吧,再见吧。周三上午我会把他回复的情况转达你——如果他肯屈尊回信的话。他这个人性格乖戾、暴躁,比较危险,可以说是人见人恨,即便有学生敢选他作导师,也常跟他发生冲突。或许这家伙不回信对你来说是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