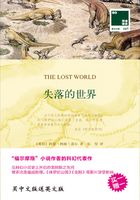
第8章 新世界偏远地区的纠察员
远在家乡的朋友们此刻应该替我们感到欢欣鼓舞了。我们达成了目标,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证明了查林杰教授的观点是可以被验证的。的确,我们还没有登上那片高地,但此刻这个地方就在我们眼前,甚至连夏莫里教授的情绪也克制了很多。虽然他还不至于现在就承认他的对手是正确的,但是至少他对自己那无休无止的反对意见已经没有那么坚持了,现在大部分的时间,他都是在安安静静地细心观察了。而此时,我也必须重新开始我的记叙,从上次结束的地方继续下去。我们招募的一个土著人受了伤,要回去养伤,因此,我将这封信托付他带回去。对于他是否能够把信带到我也没有多大把握。
我在写上一封信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土著人的村庄附近走下了艾斯梅拉达号,正准备进一步向目的地靠近。然而我这封信必须要以坏消息开始了,因为今晚团队中出现了第一个严重的个人冲突问题(两位教授之间无休无止的争吵我就略去不谈了),可能会导致很严重的后果。我曾经提到过那个英语说得很好的混血,戈麦斯——很能干,人也很好,但是经常会有一些不安的情绪,我想是由于像他这样的人经常有比较强的好奇心吧。就在昨晚,我们在对计划进行进一步讨论时,他就潜伏在我们的小屋外面偷听。而这一幕被大块头的黑人赞波看见了。赞波本身对我们就非常忠实,再加上他对混血的种族仇恨,不由分说地就将戈麦斯揪了出来,拖到了我们面前。戈麦斯恼羞成怒,抽出一把刀来,幸亏赞波力大无比、单手就把刀夺了过来,才没被戈麦斯刺伤。最后,双方被大家喝止了,被迫握手言和,大家都希望这件事情不会产生什么隔阂。至于那两位积怨已久的教授,情况也没有得到任何改善。不得不承认,查林杰挑衅能力堪称一流,而夏莫里的毒舌也不甘示弱,这对双方关系的恶化都没起什么好作用。昨天夜里,查林杰说,他从来也不愿意走到泰晤士河的堤坝上向河面上看一看,因为看到自己最终的归宿会有些伤感。当然了,他所指的是威斯敏斯特教堂。然而,夏莫里这时候却不合时宜地欢欣鼓舞起来,他脸上带着讥讽的微笑说他能理解,米尔班克监狱最近被拆掉了。以查林杰的自负当然不能容忍他这样的说话方式了。但他只是微笑着,用哄孩子的怜悯语气重复着:“真是的!真是的!”的确,这两位都像孩子一样——一个身材瘦削,不好相处;另一个傲慢自大,不好对付。但是两个人都拥有绝顶聪明的头脑,使他们自己处于时代科学领域的前沿。头脑、性格、灵魂——一个人对人生了解越多,就越能体会到每个人是多么独特。
第二天,我们正式开始了这次非凡的探险旅程。我们将需要带的物资全部装进两只独木舟,并且将人员也进行了分配,每只独木舟上六个人,出于和平方面的考虑,特意将两位教授分到了不同的独木舟上。个人来讲,我比较喜欢跟查林杰在一起。他说话比较和蔼幽默,不说话的时候也是高高兴兴地走来走去,从哪儿看都是一副善良的好人样。当然,从以前的相处我也知道,他这个人变起脸来也很快,就像六月里的万里晴空突然就会下起雷雨。如果说跟他在一起你不可能自在,那么他的陪伴同样也不可能让你觉得枯燥无味,因为你根本摸不透他那火暴脾气什么时候会突然发作。
我们在一条大河上航行了两天。那条河的河面有几百码宽,河水颜色比较深,但是很清澈,因此我们大多数时间都能看见河底。亚马逊河的支流中大概有一半都具备这种特点,另外一半的河水则是发白的颜色,而且也比较浑浊。河水的这种区别在于它们流经的国家土壤的差异。深色的河水说明这一地段有植物腐败的情况,而发白的河水则证明当地是黏性土壤。
我们遭遇了两次急流,每次都被迫登陆,在陆地上行进了大概半英里的距离以进行躲避。河岸两边都是原始森林,比次生林要好走得多,我们抬着独木舟在里面穿行并没有费多大力气。那森林的庄严与神秘我想我会毕生难忘。那参天的树木,粗壮的树干,我这个在城市里出生长大的人甚至想象不出任何东西能够与之比拟。那些粗壮的树干直冲云霄,我们只能模模糊糊地看到,在我们头上很远的地方,一些旁枝伸了出来,这些旁枝继续向上弯曲,那弧度带有典型的哥特式风格。旁枝在很高的地方互相交织在一起,最终形成了一个郁郁葱葱的顶棚。偶尔会有一丝细细的阳光穿透在那顶棚笼罩之下的一片庄严与阴森,显得无比炫目。地上铺满了腐烂的植物,像是一层厚厚的、柔软的地毯,我们从上面走过的时候几乎都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我们的灵魂也受到了这安静的洗礼,仿佛正置身于黎明的大教堂似的。此时,甚至连查林杰教授也收敛了自己的大嗓门,改成小声嘟囔了。我本来对这些巨大的树木是一无所知的,但是多亏有我们的两位科学家,他们一一指出哪些是杉木,哪些是丝绵树,哪些是红杉树……这众多的树木使得这片大陆成为大自然礼物最主要的提供者。人类的生存本来就是主要依赖于植物世界的,来自动物的产品则是处于次要地位的。鲜艳的兰花和青苔铺满了黑黝黝的树干,一束阳光照射下来,正好落在一片金色的黄蔓上,那丛生的猩红色的西番莲,还有深蓝色的牵牛花,这情景就像进入了童话世界。在这幽暗的森林中,生命都厌恶黑暗,都拼命地向上生长,追求阳光。每一株植物,甚至是很矮小的植物,也都卷曲着,盘绕着,拼命地缠绕在比自己更高更壮的同类身上,向高处那一片绿色攀去。藤蔓植物生长得体型巨大,郁郁葱葱。其他不会攀爬的植物也有自己的办法逃离昏暗的阴影,荨麻、茉莉、棕榈树都围绕着杉木生长,并且努力长得更高。在那庄严的穹顶之下,我们的走动并没有惊动任何的动物,而在我们的头顶之上则是热闹非凡,蛇、猴子、鸟、树懒,各种各样的动物都生活在高处有阳光的地方。此刻,这些动物就在好奇地看着我们几个微小的、黑乎乎的身影跌跌撞撞地走在它们下方的一片昏暗中。每到黎明和黄昏,总有成群的吼猴聚到一起尖叫,马尾鹦鹉也发出尖锐刺耳的鸣叫声,但是白天最热的时候,充斥着我们的耳朵的就只有昆虫的“嗡嗡”声了。那声音听起来像是遥远的海浪声,在寂静无声、庄严肃穆的森林中传播开,最后消失在将我们包裹起来的昏暗中。只有一次,一只动物——可能是只穿山甲或熊——迈着罗圈腿和蹒跚的步子,笨拙地匆匆从阴影中跑过。那是我在这亚马逊的原始大森林里看到的唯一一个地面动物存在的迹象。
然而,我们却发现了一些迹象,证明在这神秘的隐蔽之处,人类的活动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就在进入支流后的第三天,我们注意到了一种非常奇特的低沉的击打声,那声音听起来很庄严、很有节奏,整个早晨都在断断续续地传来。我们第一次听到这种声音的时候,两只船之间的距离不过几码远。当时我们雇佣的那两位土著人仿佛忽然变成了青铜雕像,一动不动,脸上带着恐惧的表情专心致志地倾听着。
“那是什么声音?”我问。
“鼓声,”洛德·约翰漫不经心地说,“战鼓,我以前听到过。”
“对,先生,是战鼓的声音,”那个混血戈麦斯说,“那些是野蛮的土著人,亡命徒,不是曼索人。我们每走一步都被他们盯着,随时找机会要杀了我们。”
“他们怎么盯着我们?”我望了望眼前那一片漆黑静止的空旷之地,问道。
戈麦斯耸了耸他那宽宽的肩膀。
“土著人自然知道怎么盯着。他们有自己的办法。他们监视我们,用鼓语彼此交谈,要在合适的时机杀掉我们。”
到了那天下午——根据我口袋里的日记看,那应该是八月十八日,周二——至少六七种鼓声从不同的地方传来。鼓点有时急促,有时则缓慢,有时候明显能够听出是在一问一答,远远的东方传来一阵断断续续的敲击声后,在短暂的沉默后,北方紧跟着又传来了一阵连续的低沉鼓音。这持续不断传来的鼓声让人产生了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惧,让人的神经都在颤抖,那鼓点的节奏仿佛变成了戈麦斯刚才的那句话,一遍遍重复着:“找机会杀了你们,找机会杀了你们……”在那寂静的森林里没有一个人走动的声音。在那植物形成的幽暗的幕布之下一直是大自然的安宁与平静,然而在这幕布之后,一个信息却从未间断地传来。
“找机会杀了你们。”东边的人们说。
“找机会杀了你们。”北边的人们也在说。
整整一天,鼓声有时隆隆作响,有时轻声低语,我们那几位土著人伙计的脸上则随之阴晴不定。甚至连最强悍最狂妄的混血似乎也被吓住了。但是,那天也让我了解到,夏莫里教授和查林杰教授拥有的是最高形式的勇敢,那是科学思维的勇敢,那是一种和在阿根廷人中支持南美牧人,在马来半岛的猎头中间支持华莱士的做法类似的思想。人类的大脑不能同时容忍两种不同观点的存在,所以一旦大脑对某种科学现象产生了好奇心,它一定不能容忍自己对此的理解停留在主观的个人推断层面上,这个规律是由仁慈的大自然决定的。在当天持续不断神秘的威胁中,两位教授一直在细心观察森林里每一只鸟的翅膀以及河两岸的每一株灌木,期间虽然免不了言语上的争论,比如查林杰一声低声咕哝之后,夏莫里马上就以一声咆哮作为回应,但是他们一直没有对潜在的危险和那土著人的鼓声产生什么关注,就好像他们正坐在位于圣吉姆斯街的皇家社会俱乐部的吸烟室里,而非置身于这荒蛮的南美大森林里。只有一次,两个人屈尊对这鼓声进行了一番讨论。
“米兰哈食人族或是阿马主卡食人族。”查林杰的大拇指朝那鼓声回荡的森林一指,说道。
“肯定的,先生,”夏莫里回答说,“像其他类似的部落一样,我想他们使用的也是聚合成式的语言,应该是属于蒙古人那一类型的。”
“当然是聚合成式的,”查林杰宽容地说,“我不知道这个大陆上还存在着别的类型的语言,我已经掌握了一百多个音符了。但是我对蒙古人的说法持怀疑态度。”
“我想基本的比较解剖学知识就能证明这一点。”夏莫里愤愤地说。
查林杰猛地将下巴往前一伸,我们看到的只有他的大胡子和帽檐。“当然了,先生,最基本的知识就能证实。如果一个人知识贫乏,他就只能得出不一样的结论了。”
他们都用挑战的眼神盯着对方,远方的鼓声继续从各个方向传来:“找机会杀了你们——杀了你们。”
那天夜里,我们用大石头当锚,将独木舟停泊在河中央,并为可能出现的攻击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然而,什么都没有发生。第二天一早,我们又出发了,那鼓声在我们身后消失了。大概下午三点,我们遇到了一股速度很快的急流,持续了一英里多的距离——就是这股急流使查林杰教授在第一次旅行的时候翻了船。我必须承认,看到这股急流的时候,我的内心感到了一丝安慰,因为这是我们出发以来看到的第一个证明他的故事真实性的确切证据,虽然只是个微不足道的证据。我们的土著人伙计将独木舟和物资先后扛过了那里长得格外茂密的一片矮灌木丛,而我们四个白人则肩扛来复枪,在他们周围警戒着,提防着森林里可能会出现的危险状况。傍晚时分,我们终于成功渡过了急流,又向上游行进了十英里后,抛锚准备宿营了。我大概估算了一下,我们现在所处的地点距离这条支流与主河道交汇的地方已经有一百多英里远了。
第二天清早,我们再次启程。从黎明开始,查林杰教授就表现得极为焦虑,不停地仔细检查着河两岸。突然,他满意地呼喊了一声,然后指着河边的一棵树。那棵树以一种很特别的角度从河岸边伸出。
“你说那是什么树?”他问。
“显然是棵巴西棕榈。”夏莫里说。
“没错。我就是用这棵巴西棕榈作为地标的。从河对岸再往上走半英里就是那个秘密入口了。这些树一棵挨着一棵。这就是它们的神奇与神秘之处。在这里你们看到的不再是墨绿的灌木,而将是浅绿色生长迅速的树木。通往那个神秘国度不为人知的入口就在那片高大的白杨林中。去吧,穿过这个入口,你们就都明白了。”
那的确是一个绝妙的地方。到达那一排浅绿色的树木生长的地方后,我们又将独木舟向前撑了几百码,最后进入了一条水流平缓的浅溪,溪水清澈透明,可以清楚地看见溪底的沙子。小溪的宽度大约有二十码,两岸植被茂盛,生长的不再是灌木,而是芦苇。如果不是近距离观察,没有人会猜到有这样的一条溪流存在,更不会想象得到,在这条溪流的另一边竟然有一片仙境。
所谓仙境就是指以人类的想象力所能设想的最神奇的地方。这里茂密的植被有一人多高,彼此交错,编织成了一顶天然的凉棚。穿过这条被金色晨光笼罩着的绿色隧道,就看到了静静流淌的、清澈碧绿的河水。河水本身就很美了,天空照射下来的光线仿佛经过了过滤和调和,落在河面上之后给河水增加了奇妙的色彩,看上去更是美得不可思议了。像水晶一样清澈,像玻璃一样平静,像冰山的边缘一样青翠,在那枝繁叶茂的拱门之下,那条小溪就这样在我们眼前延伸开来。我们的桨每划动一下都会在那亮光闪烁的河面上荡起千百个涟漪。这条道路通向一片神奇的土地。这里再也看不到任何土著人生活的迹象,而动物的活动却多了起来,而且从这些动物的温顺程度来看,它们应该从没遭遇过狩猎这样的事。毛茸茸的小黑狨猴露出雪白的牙齿,瞪着闪闪发光的眼睛朝我们叽叽喳喳叫着。时不时地,岸边会有一只鳄鱼跳入水中,随着沉闷的一声巨响溅起一个的水花。还有一只貘,全身漆黑、体态笨重,从灌木丛中盯了我们一会儿,然后慢吞吞地朝森林深处走去了。还有一次,一只黄色美洲狮的身影在灌木丛中盘踞着,用它那双绿色的眼睛从它黄褐色的肩膀上方投来凶恶的目光,对着我们怒目而视。这里的鸟类数量众多,尤其是涉禽,一群群的鹳、鹭、朱鹭等随处可见,蓝色、猩红、白色,从岸边伸出的每一根木头上都有。而我们船下那水晶一般清澈的河水中,各色各样的鱼也是应有尽有。
在这条仅能透过模模糊糊阳光的绿色隧道中走了三天之后,我们极目远眺,绿色的水面与拱门一样的绿色植物在远处连成一片,根本区分不开。这条奇妙的水路上是完全的平静,没有任何人类活动的迹象。
“这儿没有土著人,他们不敢来,库鲁普利。”戈麦斯说。
“库鲁普利是森林里的幽灵,”洛德·约翰解释说,“谁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样的恶魔。那些可怜的家伙认为这个方向有可怕的东西,所以他们不来。”
到了第三天,我们显然不能再依靠独木舟继续向前行进了,因为小溪突然变得很浅。我们反复地搁浅。最后,我们不得不选择将船拉到岸边,放进灌木丛中,当晚就在河岸边休息了。天亮后,我和洛德·约翰沿着小溪向森林深处步行了几英里,发现河水变得越来越浅,于是我们又回来将消息报告给大家:正如查林杰教授所料到的,这里已经是独木舟能够到达的最高点了。因此,我们将独木舟拖上岸,藏在灌木丛中,用斧头在附近的一棵树上刻上了记号,确保我们回来的时候还能找到它们。然后,我们将行李分了分——枪支、弹药、食物、帐篷、毯子等——我们把东西扛在肩上,开始了旅程更为艰难的阶段。
这个新阶段的开始则是以两个火药筒之间激烈的争吵为标志的。自从加入这个团队的那一刻起,查林杰一直指挥着大家的行动,这显然已经引起了夏莫里极大的不满。此刻,查林杰又开始给另一位教授分配任务了(其实他只是让夏莫里拿着液压气压表而已),矛盾一下子就爆发了。
“我能问问你吗,先生?”夏莫里镇定地说,但是语气里明显带着恶意,“你觉得自己有什么资格在这儿发号施令?”
查林杰立刻怒目而视。
“我是这次探险的领队,夏莫里教授,我就有资格。”
“那我不得不告诉你,先生,我不承认你有这种资格。”
“是啊!”查林杰带着讽刺的表情笨拙地鞠了一躬,“我的地位可能还得需要你来认可吧。”
“没错,先生,你的话是否真实还有待于证实,而我们这个团队来到这里正是为了这项任务。先生,现在与你同行的都是判断你是否诚实的裁判。”
“天啊!”坐在一只独木舟边上的查林杰教授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如果你不承认我是领队的话,我就没有义务为你们领路了。”
幸亏洛德·约翰和我神智还算健全,阻止了两位博学的教授因为一时的任性和愚蠢使我们无功而返。经过一番争辩、恳求和解释,我们总算是让他们平静下来了。最后,夏莫里叼着烟斗,脸上带着一丝冷笑,继续向前走去,而查林杰也嘟嘟囔囔地跟在后面。偶然之间,我们幸运地发现我们这两位专家对爱丁堡的伊林沃思博士评价都不怎么样。从此之后,我们就安全了,每当两个人剑拔弩张的时候,只要我们一提起那位苏格兰动物学家的名字,两人立刻就将矛头一起对准了那个共同的对手,甚至因为他们对他的憎恶和辱骂而结成了临时的同盟,建立了临时的友谊。
我们沿着河岸继续向前走去,不久之后,小溪变得越来越窄,最后消失在一片沼泽中,里面的水草彼此交错,像一块巨大的海绵一样,水草很高,都能没过我们的膝盖。蚊子和各种飞虫在那个地方一群一群的飞舞着,多得吓人。幸运的是,我们在沼泽旁边找到了坚实的地面,通过在树木中间绕来绕去,我们终于绕过了那片足以要人命的沼泽,将它远远地甩在了后面。而那里无以数计的昆虫还在像一把风琴一样嗡嗡作响。
弃舟登陆后的第二天,我们发现四周的景色完全不一样了。我们脚下的路开始一路向上延伸。随着我们继续向上攀登,我们发现身边的树木变得越来越稀疏,植被也不像山下那样具备典型的热带特点了。在这里,亚马逊冲积平原上常见的高大树木不多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凤凰棕榈和椰子树,一丛丛的,稀疏地分布着,而在这些树木之间,生长着茂密的灌木。潮湿的山谷里长满了绥贝棕榈,它们的大叶子优雅地低垂着。我们完全靠指南针指示着行进的方向,有那么一两次,查林杰和那两名土著人之间的意见产生了分歧,当时查林杰愤愤不平,用他的原话说,我们的整个团队“宁愿相信未开化的野蛮人那根本靠不住的直觉也不愿意相信现代欧洲文化最先进的成果”。然而,到了第三天,我们的选择就被证实是正确的了,因为查林杰也承认他看到了上次探险的时候留下来的几个记号,而且,我们还在一个地方发现了四块被火烧黑的石头,显然是有人曾经在那里宿营留下来的痕迹。
路还是一直向上的。我们又用了两天的时间,穿过了一个石子遍布的斜坡。之后,我们看到的植被又一次发生了变化。这里生长的只有象牙棕榈树和大量的兰花,而我也学会了从中辨认出稀有的旗瓣堇色兰,还有洋兰和蛇形唇瓣兰那大红大粉的花朵。偶尔会有一条小溪出现在我们面前,河底满是鹅卵石,河岸上遍布着蕨类植物,河水就在山头之间浅浅的山谷里潺潺流动着。岸边则成了我们绝佳的宿营地点。河里有成群的鱼,有着蓝色的脊背,大小形状都和英国的鳟鱼差不多。我们捉了些上来,享用了一顿美味的晚餐。
弃舟之后的第九天,根据我的估计我们已经步行了一百二十英里左右,树木变得越来越矮小,几乎跟灌木差不多了。最后连这矮小的灌木也没有了,而是出现了一大片竹林,竹子生长得很茂密,我们只能让我们的几位土著人伙计用砍刀和锚钩临时砍出了一条道路才得以通过。那天我们从早晨七点折腾到了晚上八点,中间只休息了两次,每次一小时,总算通过了这片障碍。我简直想象不出有比这更单调乏味又令人疲倦的事情了。即使是在视野最开阔的地方,你能看到的范围也超不过十到十二码。而大部分时间,我抬起头看见的只是洛德·约翰的背影,而距离我左右两边不到一英尺的地方就是黄色的竹子,像两堵密不透风的墙,将视线挡得严严实实。一道阳光从高高的天空上投射下来,细得像刀刃一样。抬起头,可以看到,在我们头顶上方十五英尺的地方,在深蓝色的天空的映衬下,竹子的顶端在随风左右摇摆着。我不知道什么样的动物能够在这样的竹林里生存,但是有几次,我们听到在距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有体型很大、很重的动物活动的声音。洛德·约翰根据声音推断可能是野牛。直到夜幕降临我们才穿过了这片竹林,然后就扎营休息了。经过这一天无休止的劳作,大家都累坏了。
第二天清早,我们又上路了。我们发现,这里的地貌又发生了变化。我们身后是密不透风的竹林,竹林的边缘清晰而整齐,就像河流的岸边一样。而我们面前是一片宽广的平原,微微有一点坡度,上面星星点点地长着一丛丛的树蕨,平原一边向远处延伸一边微微向上倾斜,边缘处是一道长长的,像鲸鱼脊背一样的山脊。我们大约中午时分到达了那个山脊,翻过去之后发现,另一边是一条浅浅的山谷,山谷另一边又是一个缓缓的斜坡,在天空上映出了一道低低的圆弧状的轮廓。当我们在爬那些连绵的小山中的第一座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我也说不好这件事的重要性有多大。
与两名土著人一起负责领路的查林杰教授突然停下了脚步,异常兴奋地指着我们的右边。我们随着他的手望去,大约在一英里之外,一只好像灰色的大鸟一样的东西从地面上缓缓起飞,从空中平缓地掠过。它飞得很低,路线很直,最后消失在树蕨丛中了。
“你看见了吗?”查林杰狂喜着大喊,“夏莫里,你看见了吗?”
夏莫里教授正死死地盯着那只动物消失的地方。“你说那是什么?”他问。
“是一只翼龙,我对此深信不疑。”
夏莫里忍不住放声大笑,笑声里满是嘲弄。“乱弹琴!”他说,“我敢肯定,那是一只鹳。”
查林杰气得说不出话来,他把背包往背上一甩,继续赶路了。然而,洛德·约翰三步两步赶上了我,手里拿着望远镜,表情比他平时还要更阴郁。
“它飞到树丛里之前我看清楚了,”他说,“我也不能断言它到底是什么,但是,我以我运动员的名誉担保,那绝对不是我在日常生活中见到的任何一种鸟。”
问题出现了。我们是否真的如我们的领队所言,已经到达了一个神秘国度的边缘,遇到了这个失落的世界里的一名成员呢?我将这件事情真实地呈现给各位读者朋友,没有一丝保留。但是就只有这么一件事,除此之外,我们再没看见一件异乎寻常的事情。
现在,我亲爱的读者朋友们,我带着你们沿着宽阔的大河一路走来,穿过了茂密的灌木丛,通过那高大的树木形成的绿色隧道,爬上长满棕榈树的长长的山坡,突破了竹林的封锁,越过长满树蕨的平原。最终,我们的目的地终于就在眼前了。爬过第二个山坡之后,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片形状不太规则,棕榈树星罗棋布的平原,平原的尽头正是我之前在素描图中看到过的高高的红色峭壁。眼前的峭壁与图画中绝无二致。峭壁离我们的宿营地点最近的一点大概在七英里以外,以这个点为基准逐渐向远处延伸,一直到我们的视线所不及之处。查林杰像只骄傲的孔雀一样昂首阔步地走在前面,夏莫里一言不发,但是脸上依然是写满了怀疑。总有一天我们的疑问会被全部解开。乔斯的胳膊被断掉的竹子扎伤了,坚持要返回,于是我将这封信交给他,希望他能将信带到。我会继续将未来的情况记录下来。我在信中还附上了一幅粗略的路线图,结合看的话会使你们更加容易理解我的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