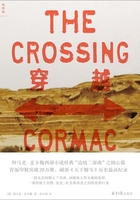
第一章
当他们离开格兰特县南迁到这里来的时候,博伊德还只是一个四五岁的小娃娃。被他们称作希格尔达的新建的县,也不过就是这个男孩的年龄。他们告别了故土,那儿是他的妹妹和外祖母的埋骨地,到新开发的边境地区来寻找新的生活。这新的县份富饶、原始。你可以骑上骏马长驱南下,狂奔至墨西哥,一路上不会碰到一道篱笆挡墙,真的如入无人之境。才刚刚到了骑马的年龄,他就喜欢把弟弟博伊德扶上马背,让他坐在自己身前,两人同乘一鞍,在原野上骑行,同时用西班牙语和英语教给博伊德这些山水鸟兽的名字,描述着自然的风光。在这所新房子里,他们兄弟二人住在连着厨房的一间卧室里。在夜里,他常常睡不着觉,心里涌动着对新生活的无限憧憬。他想倾诉,他看着熟睡的博伊德,听着他甜甜的呼吸,不禁出声对他诉说,诉说他美好的计划,他对新家乡、新生活和他们这新一代的计划。
在那年冬天的一个夜里,他被狼嗥惊醒了。这叫声是从他家房子西边的小山包里传来的。他知道这些狼是想借着新雪,乘着月光跑到平原上来猎杀羚羊。他一跃而起,从床脚竖板头上抄起裤子和衬衣,抓起他那毛毡衬里的帆布夹克,又从床底拉出靴子,走到厨房间,借着炉子散发出来的微热穿好衣裤,再把一双靴子拎到窗口,在月光下分出左右,弯腰把它们套到脚上。然后轻步走出厨房,关上了房门。
当他经过马厩时,栏中的几匹马在寒夜里对他发出低柔的嘶声。新雪在他的靴子底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他的呼吸在淡蓝色的夜光中喷出一团一团的白雾。一小时之后,他已蜷伏在一条干河床上的雪堆里。凭着留在雪上、沙上的爪印,他知道那群狼刚刚从这里走过。
它们已经下到平原上来了。他穿过了一片扇形的沙石地,干河在这里折道向南伸进了山谷,在这里,他又看见了狼的足迹。它们就在前头!他小心翼翼地趴在雪地上,肘膝并用,匍匐向前。因为冷,他把双手缩进袖筒,捏住袖口,防止冷雪涌进袖管。他爬过一片黝黑的小杜松林,从这里,看得见阿尼马斯山峰下宽阔的山谷。离狼群很近了。他迫使自己静静地蜷一会儿,稳住呼吸,然后慢慢起身,朝前方看去。
在前方的旷野上,他看到了一幅激烈的追逃景象。狼群在追杀着羚羊;而亡命中的羚羊在白皑皑的雪野上像幽灵似的急速逃窜,或长奔、或急转、或盘旋……在清冷的月光下,雪浪在它们蹄下喷飞。它们急促的气息在冷凝的寒夜中像白烟般冒出,好像体内正燃烧着烈火。这群急转着、狂跳着的狼,在这茫茫冬夜里居然保持着神秘的沉默,仿佛它们来自另外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与这里根本语言不通。一阵无声的喧闹之后,它们跑下了山谷,沿着谷底跑向了远方,很快变成了灰蒙蒙、白茫茫中的几个小点,直至消失。
他觉得很冷,但还是原地未动,他还在等。四处一片死寂。凭着自己呼出的气息,他能看出来风往哪儿偏。在这片刻的沉寂中,他所能看到的东西就是自己的呼气,两道细细的白雾,喷出、消散,再喷出、消散,反复无穷。他蹲在那里等了很长时间。终于,它们又来了。这次是跑步后的欢娱。它们大步慢跑着,8字形地交叉着跑,扭动着身躯,边跑边舞。它们时而停下来,用鼻子在雪中刨掘着什么。再慢跑几步,再停下来,立起后腿,挥动前肢,两两一组,对脸而舞。舞上一阵,又继续前跑。
一共有七只狼。它们就在离他不到二十英尺的地方跑过去了。这么近的距离,仅凭着月光他都能看清它们杏仁状的眼睛,听见它们的喘息。他甚至可以感觉到,它们知道他的存在——这种感觉一刹那如电击般令他毛骨悚然。它们聚到一堆,用鼻子互相蹭擦,用舌头彼此舔舐,好像是在传递着什么信息。但顷刻间,它们又都站住了。它们竖起耳朵站在那里,有的还把前脚提到了胸前。它们正在看着他——是一圈狼的眼睛在看着他。他屏住了呼吸,它们也屏住了呼吸。双方就这样僵持了一会儿,狼群突然转开身,疾步地但却是悄悄地跑掉了。当他回到家里的时候,博伊德已经醒了,但是他没有告诉他自己去了哪里以及看到了什么。他从来也不曾将这件事告诉过任何人。
到了这一年的冬天,博伊德已经长到了十四岁。他家附近的干河床上,树木从初冬起就早早脱去了叶子,光秃秃地立在那里。天空一天天愈加灰暗、阴沉,它笼罩下的树木更显得苍白和孱弱。一股强冷的风从北方吹来,现出了赤裸裸树身下面一派苍凉的大地,就像是岁月的一张大单据,罗列着亘古以来人类所有的债务,但所有的债权都已经过期。历史简单得不过如此。在他家房子的坡下,紧靠干河外湾的地方是一片稀疏的三角叶杨树林。此时,在萧瑟的冬天,树枝一根根惨如白骨,树干上的杂色树皮也几乎剥落殆尽。在这些杨树丛中,有几株特别粗大。其中有一棵巨树被人齐地锯掉,留下了截面宽大的树桩子。在冬天,过路的牧人利用它做木板地面,可以在上面搭起四英尺乘六英尺的帆布帐篷来防冷、避风、安度寒夜。他驾着马拉橇,带着博伊德外出拾捡木柴,一路上看着冬阳下自己的影子、马和木橇的影子,一棵一棵地穿过树桩。博伊德坐在木橇上,手里握着斧子,就像在守护着自家收集的木柴。他斜过眼睛,注视着西边的天空。荒野的山峦下,一轮血色的太阳满环光焰,正在缓缓沉入被它照得通红的干湖之中。在西天的晚红下,几只羚羊摇摆着脑袋,轻踏着步子,正巡游在牛群当中。在那方小平原上,宛如一幅灿烂、生动的剪影画。
他们踏着一路上的干树叶堆,驾橇来到了干河床里一个蓄着水的池塘旁。他在这里下了马,给它饮水,而博伊德却绕着水塘查找小老鼠的踪迹。博伊德无意间擦身经过了一个印第安人。这个人正弯着腰、全神贯注地蹲在那里,连眼皮都没有抬一下。当博伊德发觉了他并转过身来时,这个印第安人只是把眼光投向博伊德腰间的皮带,仍然没有抬眼。直到博伊德完全停在身边,他才抬起眼睛。博伊德几乎要碰到这个人了。这个人蹲在一丛细秆的芦苇草下,并没有特意隐藏,但博伊德却没能早一点发现他。他横膝握着一杆老式的0.32英寸口径单发来复枪。在这黄昏时分,他在守候着射猎前来池塘饮水的鸟兽。此时,他仍然蹲在那里。他看着孩子的眼睛,孩子也看着他的。他的眼睛那么黑,好像满眼都是黑色的瞳仁。在这双漆黑的眸子里,太阳正在西沉。在这双漆黑的眼睛里,是这个孩子站在太阳旁边。
过去,博伊德从不知道他能够在别人的眼睛里看见自己,也不知道他能在别人眼里看见像太阳这样的东西。现在,他看见自己成双配对地站在这两眼黑色的深井里,连细弱的头发都能看见,只是样子有点古怪。但这是一个和他一模一样的孩子。就像是他走失了的双胞胎兄弟,此刻正站立在另一个世界的窗口。但那是一个黑洞洞的世界。在那里,太阳是永沉不升的。这景象又像是一个险象环生的迷津。在那里,这两个令人怜爱、同情的孤儿在生活的旅途中迷失良久,最后终于找到了回来的路,但却被横挡在一堵古旧黑暗的警戒墙之后,似乎永远也无法逾越。
博伊德站在那里,一时间看不见他的哥哥以及他们的马。但越过这丛芦苇,他能看到那边水中不断扩出的一圈圈波纹。那应当是马儿饮水激起的波纹。他还注意到这个印第安人干瘦无毛的颌下,颈部细密的线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