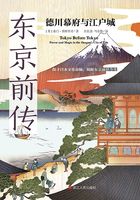
引言
本书所讲述的,是东京成为现代日本首都之前的故事。在1868年之前,它还不叫东京,彼时这座城市一直被称为江户。
一直以来,江户城的地位与历史更悠久的古都——京都不相上下。事实上,“京都”这个词原本就是“首都”的意思。古老的京都是神秘的宗教兼文化人物“内裏”的居所,“内裏”的字面意思是“皇宫”。古时候,“内裏”曾以“天皇”这一头衔统治日本。但在12世纪,武士阶级崛起,天皇便大权旁落了。因此,内裏只能算是现代日本天皇的祖先。1868年,日本天皇重掌朝政,确立了相当于欧洲君主立宪制的国家政体。自此,日本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内裏”迁往江户,江户因而成了日本的首都。由于江户位于日本东部,于是就被命名为东京(东方之都),而京都则成为一个专有地名。此后的种种过程将在后记中讨论。本书主要讲述的是江户的故事,也可以将其命名为《东京前传》。
江户自古以来就有人生活,这一地区曾发现了许多史前文物。但直到1590年德川家族控制江户,江户才成为一个重镇。在此之前的几十年时间里,德川这个伟大的武士家族渐渐崛起。他们在1600年取得了一场重大战役的胜利,并在1603年说服内裏封德川家康为征夷大将军,也称幕府将军,即国家的军事首领。幕府将军必须由内裏任命,内裏不掌握实权,只有名义上的最高统治权,实际控制并管理国家的是幕府将军。内裏只不过是傀儡,而幕府将军一旦获得头衔则可以世袭。日本历史上有三大幕府时代,德川幕府是最后一个。
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们将对江户做一个评估,考察它的城市规划、文化以及生活。但这并不是一本编年体通史,也并非要对江户包罗万象的城市风貌和超过250年的历史进行系统的概述。我们只选取其中的一些片段,着重讲述这座城市当年的运行机制及其往事经历。其中一部分是关于江户相较于首都的角色定位(这里的首都是指现代的京都城)。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这两座大都市在东西轴线上恰好相距500公里。如今,日本的旅游指南上将京都称为“日本的皇城古都”,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确实如此。但在我们所说的那个时期,即1590—1868年,首都和江户一样,都处于幕府的控制之下。请注意,彼时的内裏并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真正意义上的“天皇”。作为统治中心和政令中心,这对双子城实际上都是德川氏的领地。
日本是一个群岛,而且地形极其狭长。日本本土从北纬31度一直延伸到北纬45度,东西横跨经度约有20度。如果把日本群岛置于地中海地区地图之上,从东北到西南的范围大约相当于从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一直延伸至撒哈拉沙漠中部;如果将其标绘在美国地图上,则大约是从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到得克萨斯州东南角的范围。日本同时也是多山国家,其地形与瑞士相似。放眼欧洲和北美,没有哪一个地方在拥有如此密集的山峰的同时,还能有较多的供人类居住的平地。在日本历史的进程中,为数不多的平地都被开发利用了,但江户周围的地区一直是片处女地。江户位于广阔的武藏野上,有人居住的地方也只是若干零星散落的小村庄。又由于地处海湾,其地理位置能庇护人们不受风暴的侵袭,这里成了渔民的家园。江户的意思就是“海湾门户”。尽管如此,江户并没有得到发展。它不是什么重要的地方,与日本早期的大城市相比简直微不足道——不要说首都,就是与奈良和大阪也没有什么可比性。1590年之前的江户闭塞落后,就像一潭死水。
那时的江户之所以落后,是有原因的。日本大部分地区都有火山,许多地方属于地震多发区域。其中江户尤其严重,算得上是全球范围内地震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今天的东京也依旧如此。地震时摇晃的地面会导致建筑物倾斜倒塌,更为糟糕的是,打翻的火盆和炉子会引发火灾。此外,地震还会引发海啸,而江户这个“门户”却无法完全防御海啸。因此,没人会在这里建造重要的建筑。
除了自然条件严酷外,日本还多次遭受内战的摧残。和日本许多地方一样,江户曾修建过一座城堡,但时间较晚,准确地说是在1457年。江户的海滨位置赋予了它潜在的战略意义,至少是一个瞭望站。在海湾附近的大片沼泽地中有一块突出地面的岩石,城堡就建于此处。这座城堡并不算坚固,1524年被北条氏纲围困时,很快就被攻陷了。城墙下,渔民们依旧继续着他们靠海吃海的劳作。
宽阔的隅田川沿着武藏野的边缘蜿蜒流淌,在江户流入海湾,所以江户也有淡水。碰巧的是,江户上游有一座佛教寺庙,由于建在隆起的土地上而免受洪水侵袭,寺旁还有一个叫作浅草的村庄。该寺的僧众声称他们供奉的佛像很灵验,能够创造奇迹。浅草寺曾是当地人的祈愿圣地,但“浅草寺”的寺名也说明它的身份比较卑微。在日本,有名望的寺庙一般很少会简单地使用地名来命名,大多数都会取一些源于神学概念的高雅名称。然而,在江户崛起的过程中,浅草寺将发挥关键的作用。
1603年,德川幕府(或称江户幕府)建立后,江户得到了巨大的发展。17世纪,当地的营房、宅邸、宗教建筑以及普通民居和道路建造速度迅速提升。到1720年左右,江户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都市之一,居住人口足有100万之多。在这里,维持秩序、供应食品、清理污水和维持卫生条件等事务纷乱庞杂,(维持城市运作)需要付出旷日持久的努力。或许,当今日本社会仍然存在这些情况,但江户时期的原本面貌几乎完全消失了。目前,东京城里幸存下来的江户时期建筑屈指可数。城堡的护城河壕沟大都被填埋,填海工程也彻底改变了海岸线。反倒是江户城天守的石础历经磨难,连同一两座城门和几座寺庙的大殿部分得以保存下来,但俗世的建筑没有一座能够幸存。20世纪经历的战争灾难无须重提,在此之前就有接二连三的火灾一次又一次地焚毁了江户的城市肌理。不过,由于房子都是木制的,早晚也都要更换木材的。因而,江户的建筑风格始终处于一种变迁状态。一直以来,江户就像“祖父的斧子”[1],不断除旧更新。但在21世纪的今天,除了零星的街道布局外,江户已经荡然无存。一些历史学家称东京为“一座只有故事的城市”。确实,它只有记忆,很少有实物。本书并不会强调这一点。我们要做的,是将故事与故事之间的空间填充起来,即使没有太多的有形建筑物,那至少还有普通人的现实生活和经历可以借鉴。我们将挖掘(有时确实是字面上的意思)塑造这座幕府城市并支配其空间逻辑的力量。这种力量由两部分组成:权力,即武力的统治;魔力,即天地间的无形力量对江户的掌控。自上而下,由高到低,江户的百姓都生活在这两种力量的控制之下。而1603年的幕府绝不会想到,这种状态将持续250年以上。
也许我们缺少构建这段历史的建筑材料,但我们并不缺乏其他的资料证据。江户流动的文化在绘画、版画、照片以及印制书籍中保存得相当完好(见图2)。这些描绘城市风光的资料可能对我们非常有用。另外,相关文字记录亦有流传,这些文本是本书写作过程中主要的参考资源。例如日记和随笔,还有被称为“川柳”的俳谐诗,后者常以诙谐幽默或讽刺的方式调侃市民生活。图片可能更有价值,但是必须审慎地看待,因为它们属于艺术构建,而不是对城市的真实描绘。

图2:《江户地图》,高井兰山1849年绘制(1861年修订),117厘米×131厘米。当时制作最完整的江户印刷地图之一。这类作品当年随处可见,但由于要对城堡以及其他权力场所进行保密管理,故在图中对这些区域作留白处理。此处将地图的方向进行了旋转,角度与图1大致相同,上方为西南

图3:《洛中洛外图》,佚名作,1660年。六曲一双屏风,纸本金底彩绘,尺寸均为227厘米×152厘米。此类描绘京都壮丽风光的成对屏风在16世纪风靡一时,至江户时代依然盛行。上图中,位于右侧的高大建筑是大佛殿,左侧与之对称的是幕府城堡二条城。上图为右围,下图为左围
在日本,贯穿整个16世纪的漫长内战时期,艺术家们发展出一种全景演绎的形式,再现京都这座屡次被烧毁的兵家必争之地。为最大程度展现城市英姿,京都全景被绘制在大幅折叠式屏风上。屏风通常是成对制作,左右两围各有六扇,每扇的尺寸大约有一人大小。屏风画面气势磅礴,由于在绘画之前经常贴上金箔,所以显得金碧辉煌。据记载,第一件描绘都城的屏风出现在1506年,当时一个朝臣兴奋地记录下了这一消息1。现存最早的实物屏风可追溯到的时间则稍晚于此(见图3)。从1630年左右,也就是德川统治的第三代开始,描绘江户的类似屏风开始问世。其中有两件屏风对我们重新了解江户特别有帮助。它们都以目前所保存的地方而闻名,一件收藏在出光美术馆,另一件收藏在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也即众所周知的历博(见图4和图5)。出光美术馆收藏的屏风特别长,高度也出奇地低,比常见的屏风都要低矮许多。屏风底部描绘的是流经江户的大河——隅田川。全景图从右至左展开(这是欣赏东亚艺术的正确打开方式),右上角是位于江户东北部的浅草寺,左下角是南部的江户湾。这样的布局意味着江户城恰如其分地坐落在画面的正中间,正如其作为江户的统治中心一样。作为权威的标志,城堡绘制在左围屏风的首位,而非右围屏风的末位。出光美术馆屏风所要展现的真正主题是和平、富足,以及全体百姓在幕府政权的庇护下安居乐业、各享其乐。定制屏风的人一定享有很高的地位,因为幕府重地非普通人可描绘,也非普通人所能收藏。
出光美术馆收藏屏风的制作年代,迄今尚无定论。有人认为最早在1630年左右,即在德川幕府建立之后不久,这一时期的江户社会安定,城市规模和繁华程度开始能与京都一争高下。藏于历博的屏风,其制作年代同样存在争议,但普遍认为制作年代更晚。这一点显而易见,因为画面中出现了死于1651年的第三代幕府将军德川家光的形象。当然,这件屏风也是为地位极高的人制作的,否则绝对不会出现幕府将军的形象。大多数学者认为,这件屏风是在德川家光去世后制作的,用以追忆这位幕府将军。1657年,一场可怕的大火烧毁了江户大部分地区,这可能是这座火灾频发城市在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一次大火。这件屏风很可能是在那之后制作的,用来纪念这位强权统治者治下的江户过往。德川家光的儿子们继承了他的头衔,并把幕府统治一直延续到下个世纪,但历史上对他们的总体评价并不高。历博的屏风则沿袭了出光美术馆藏品的全景布局,从浅草到海湾,但尺寸更大更高,画面更雅致,总体上更技高一筹。此外,该屏风使用的绘画视角更高,给人以向下俯瞰的感觉。同时,屏风也用了更多的画面空间来展现城堡英姿。虽然德川家光现身于画中,但总是遮遮掩掩的,表现为或戴着帽子、或打着伞盖等诸如此类的样子。

图4:《江户风光》,佚名作,17世纪初。八曲一双折叠式屏风,纸本金底设色,尺寸均为107.5厘米×49厘米。描绘江户风光的屏风制作得很少,因为不宜如此公开地展示幕府所在地。这组屏风可能是现存最早的江户屏风,它比大多数屏风都长,也更低矮,画面布局仿效描绘京都风景的屏风,寺庙绘于右侧,城堡绘于左侧

图5:《江户图》,佚名作,17世纪。六曲一双折叠屏风,纸本金底彩绘。尺寸各为366厘米×162.5厘米。这组华丽的屏风当为一位地位非常显赫的高官专门定制。画中有几处描绘了幕府将军德川家光,但是每一处都遮挡了他的脸部。该屏风可能是德川家光死后所制,以纪念1657年在大火中焚毁的江户。上图为右围,下图为左围
一个世纪之后,也就是18世纪60年代,出现了另一种视觉史料,来自权力天平的另一端:那就是为普通消费者生产的廉价风俗版画。在此之前,江户的版画文化很繁荣,著名的题材是歌舞伎演员和性工作者,她们是表现“浮世”花街柳巷享乐环境的两大支柱。但在18世纪60年代,突然出现了一种表现普通城市风景的版画。这些版画便于携带,目标客户很可能是外来务工人员或游客,他们可以拿给无法亲眼参观幕府所在地的同乡人欣赏。另一些受众可能是江户的本地居民,他们由于身份或性别的原因出行受到限制,无法在街上自由行走,这些版画的出现,正好弥补了他们出行受限的遗憾。这些版画确实能给人带来一种新鲜感,证明江户在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在这些画中,江户的对照物不再是京都,而是更远的地方。有趣的是,这些城市风景画的出现与欧洲城市风景画的兴起时间恰好相吻合。欧洲城市风景画起源于欧洲富家子弟的游学旅行,并逐渐盛行于欧洲各国。富人购买当场完成的罗马或巴黎风景画,而不太富裕的人或无法出门的人则靠欣赏版画游历欧洲,这些画大多出自奥格斯堡、伦敦和巴黎。欧洲人可能把这些作品带到了日本。17世纪40年代,幕府与激进的基督教传教士之间出现矛盾,伊比利亚人最终被驱逐出日本。此后,唯一与日本进行贸易的欧洲人是荷兰东印度公司,他们的相关记录也将有助于我们了解江户。欧洲的版画在本国很便宜,用来当作礼品非常合适,于是东印度公司带来了很多这类东西。这些画也可能是由中国船只经由第三方港口运抵日本的。
有一幅版画的流传经历值得在此详细介绍一下。虽然它的艺术水平远不及出光美术馆或历博收藏的屏风,但很能说明问题。画中所描绘的是游客最多的欧洲城市威尼斯,是乔瓦尼·安东尼奥·卡纳尔(Giovanni Antonio Canal),即卡纳莱托(Canaletto)的作品。1735年,英国领事将他的部分作品以黑白图集的形式印刷出版。由于这套图集的价格只是卡纳莱托单张作品售价的零头,因此传播范围很广。但在当时,它们的价格仍然很贵,于是在大概18世纪60年代的德国出现了盗版画,不仅手工添加了颜色,售价也要低得多。其中至少有一幅画又被人带到了江户。很显然,这套再版图集中的某张卡纳莱托画作是江户艺术家歌川丰春仿制的。歌川派是公认的最著名的“浮世绘”画派,但歌川丰春通过借用一些外来特色开拓了画风。欧洲的版画是铜版蚀刻,而日本采用的是木刻印版技术,可以进行彩色印刷。歌川丰春的版画可能制作于1770年左右——也就是说,它完成于日本城市风光画出现的初期(见图6和图7)。自此,脱离戏院和妓院主题的江户风景画开始进入大众视野。

图6:《从圣十字教堂望向赤足的圣父的风景(拿撒勒圣玛利亚堂)》,安东尼奥·维森蒂尼(Antonio Visentini)作,仿自安东尼奥·卡纳尔,即卡纳莱托,1735年,铜版蚀刻。这幅作品没有标题,只标有阿拉伯数字(编号2)。它肯定与1735年英国驻威尼斯领事约瑟夫·史密斯出版的那套著名的图集有关。那套图集由12幅画组成,名为《威尼斯运河的壮丽景色》,且每一幅都标有罗马数字。这12幅图都出自卡纳莱托的手笔。后来出现了许多史密斯版图集的盗版复件,有些是手工上色的,歌川丰春肯定见过其中的某一幅

图7:《荷兰法兰克港敲响万里起航之钟》,歌川丰春作,1770年,套色木刻版画。由于歌川丰春不能确定图中建筑物的地点,所以他自造了一个华丽的标题,还在前面加上了“浮绘”一词,即透视图。原作的左边部分被裁切掉了
* * *
起初,江户只是一个小村庄,后来演变为一个城下町,再之后逐渐壮大繁荣,但从来都没有做过首都。本书的第一章将探讨江户独特城市概念的形成过程。我们将通过其城市布局来了解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江户的发展遵循了某些大城市的先例,但也规避了某些方面,尤其显著的一点是它拒绝采用四四方方的棋盘格布局。如今的东京经常被诟病城市建设毫无规划,并将其归咎于江户发展初期的漫不经心。这种观点其实是不对的。本书第一章主要对江户看似四仰八叉、杂乱无序布局背后的模型和反模型进行研究与调查。
与日本或东北亚其他地方的早期城市相比,江户在布局中最大的一个不同点就是,拥有一座大桥。这是第二章的主题。这座桥不仅格外宏伟壮观,而且被确定为城市中心。在此之前,日本没有哪一个城市有市中心。而树立一个纪念碑式的焦点来代表一个政权对子民的统治,此前的日本也没有这样的概念。这座中央大桥建于1603年,也就是德川幕府建立的那年,虽然缺乏文献记载,但它肯定是作为德川家族统治的象征而建造的。欧洲城市理所当然地有市中心,这个传统起源于罗马广场。从这个意义上说,江户首开日本城市之先河。
第三章将从具体的城市转向抽象的事物,重点探讨魔力的护佑。随着城市的发展,江户虽然不再作为一个要塞而存在,但是它与京都相比还是略逊一筹。在其蜕变过程中,有一个因素极大地影响了城市各要素的布局,那就是“大地的魔力”——堪舆术,即汉语中的“风水”,日语称其为“fūsui”。在江户看风水的阴阳师称他们的法术为“onmyō-dō”,即“阴阳道”2。风水的字面意思为“风和水”,它指的是人类极其需要但又无法驯服的两大力量。风和水必须通过神秘的推算并加以诱导,才能变得对人有利。阴阳道也是这个意思,不过是一种更概念化的说法。阴指一切雌性的因素,而阳则代表雄性。阴阳包含了所有的二元性和矛盾性,比如潮湿与干燥、黑暗与明亮、凹与凸等。阴阳涉及一切力量,无论是看得见的还是看不见的。阴阳道是一门平衡矛盾与对立的学问,矛盾生万物,保持均衡则受益良多,处置不当则乱象丛生。江户城的建造,其根本依据就是阴阳风水学。
获取魔力护佑还有第二种途径,即神的庇佑,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佛教的庇佑,这也是第三章要探讨的主题。江户原本有一座古老的寺庙,但很快又增建了更多。幕府还下令从全国各地借鉴多处圣地,主要是参考了京都,在江户进行仿造、重现。于是,佛教历史映射到了江户的近代史中,与其产生了紧密联系。由此,江户被推上神坛,成为日本宗教信仰历史的守护者和继承人。
第四章将讲述江户独一无二、最宏伟、最令人瞩目的建筑——江户城。当年的普通人无法进入其中,如今它也已消失无踪(除了前面提到的主堡基础),但它曾经确是一个宏大的建筑群,有城楼、城墙,还有住宅和接见大殿,建筑绵延铺陈,形成错落有致的天际线。德川氏的政令就发自这里。江户城的形状和内部布局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进行重现,包括其中一间又一间装饰华丽的房间。我们将对江户城的特点进行解读,由内到外,以便深入理解它想要传达的信息。要做到这一点,对比一下位于京都的同类建筑二条城或许会有帮助,二条城有一部分有幸保存了下来。同样能帮助我们理解江户城的,还有19世纪初为再现江户城壁画而创作的一批筹备画,以及同一批艺术家创作的其他一些没有直接画在墙上的绘画作品,这些绘画得到了保存。
日本的城市若想变得高贵脱俗,还需要另外一种元素。这是一种极其难以捉摸的文化内在,也是第五章的主题。内裏的一个主要职责是传承古代文学经典,尤其是一种叫作“和歌”的宫廷诗。和歌经过精心编选和研究,在宫廷圈子中传播推广,备受推崇。和歌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以真实的地点为背景进行创作。由于朝臣很少冒险行走远处,因此大多数激发文学创作灵感的地点都不可避免地选在京都附近。很少有作家去过江户所在的东部荒原。因此,从文化史上来讲,江户给人一种单薄而贫瘠的感觉。然而,有一篇古代文本是个例外。这是一部采用虚构叙事手法的和歌集,创作于公元900年之前,作者不详,但诗中确实提到了一位远行至江户的朝臣。这部名为《伊势物语》的和歌故事集记叙了一个无名主人公,因为厌倦了宫廷生活,和几个同伴一起流浪。他们从京都出发,一路跋山涉水,经过现今我们也熟悉的地方:先是经过富士山,然后来到一条大河,文中写明这条河就是隅田川。当时这里还是一片不毛之地,但在700年后,这里变成了德川幕府城,成了日本的权力中心。纵观古典文学经典,《伊势物语》不仅是唯一一部提到江户地区的作品,还是一部影响力巨大的作品。长期以来,《伊势物语》因其创作年代久远和引人入胜的诗句而备受赞誉。其中的一些诗歌也被收录在其他作品集中,这些诗歌据称为歌人在原业平创作。在原业平于880年去世,但是目前尚不清楚《伊势物语》讲述的到底是不是某个人的真实旅程——这一点在当时并不像今天这样引起较多关注。以往许多经典著作都比较晦涩难懂,除了学者之外,普通人难以理解;《伊势物语》却不同,相当通俗易懂。书里的故事各成一体,互不相干。书中有一段是说主人公(也许就是在原业平)在行路的过程中创作了一首《东下》。对于江户人来说,这篇故事对他们的城市和幕府统治做出了惊人预言,证实了江户地区的悠久历史。更重要的是,主人公因厌倦京都的舒适享受而选择东行,在江户的所见所闻深深地打动了他。于是,“东下”便成为江户时代文学和绘画艺术中的一个重要主题。
在第六章,我们将去见识一些不一样的事情。相较于江户所有的正统特质,江户也有它的“浮世”,或称娱乐区。今天,与“将军”一词同样知名的就是“艺伎”。许多日本城市都设有所谓的“游郭”,这是一个官方许可的供饮酒、娱乐和狎妓的场所。江户逐渐发展出行业首屈一指的游郭,并以其所在地吉原闻名于世。这个地名原本的意思是“芦苇之原”,但很快就被改为更悦耳动听的同音异义词“吉原”。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在日语中频繁使用的双关语,根本就不是(约翰逊博士说的)什么“最低级的智慧”。早在欧洲的城市风景画开始流行之前,浮世绘创作就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浮世绘作品题材丰富,既有表现江户餐馆的,也有描绘女子闺房的。红灯区作为性剥削场所有很多值得谴责的地方,吉原尤甚,但是它们同时也催发了令人赞叹的多层次文化表达。因此,第六章将着力讲述吉原,特别是它在江户世俗文化中的位置。吉原被建于江户城外,是为了维护幕府城市的法纪和尊严,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为了避开一切“正统”。我们将在这一章讨论从江户到吉原的旅行经历,看看“正统”是如何让步于“浮世”的。
最后,我们将在后记中看到江户在1868年变身为东京。随着幕府倒台,江山易手,江户城变成了首都。为了满足新政府的需要,武士的宅邸被没收改造,为新政府所用。城内修建起了旅馆、法院和火车站;木质建筑用砖瓦进行了加固;江户人赖以乘坐的轿子和渡船等城市交通工具让位于人力车和马车。当幕府之城转变为日本的现代首都时,江户便渐渐成为传说。
* * *
江户这个名字的知名度可能不及京都或东京,因为今天的日本文化是由后两个城市所定义的。但实际上,我们在“日本文化”这个标签下所能想到的大部分内容都是江户文化,而不是整个日本列岛的文化。富士山是江户的象征,只是到了后来才成为日本的象征;同时,也只有江户人才吃寿司;套色木刻版画几乎是江户的独家制作;樱花也是江户独享的美丽标志;追求整洁漂亮也是彻头彻尾的江户特征之一。在现代之前,日本其他地方无一如此。
大约在1800年,幕府的首席老中[2]松平定信在回顾他所在城市200多年的历史时,就提到了这一点。松平定信在他的摘抄本里抄录了一些他所见闻的与江户有关的特殊文化现象及其原因:
有人说,如果江户没有频繁的火灾,那么人们会更花哨奢侈。京都人或大阪人做事讲究华贵优雅:家家悬挂绘画,户户摆放插花。但在江户,即使是在富裕的地区,一切也都是从简的。人们只在竹筒或朴素的花盆里插上一枝花。富人家有精美的棋具,但棋盒盖子里面会固定一张纸(绘有棋盘格),可以兼作棋盘。江户的简洁意识源于持续不断的火灾。3
为了避免让读者认为本书对江户的理解主要来自精英阶层,我们对江户的普通人也给予了应有的重视。普通居民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可以在自下而上的发声中看到。在松平定信编写摘抄本的同一时间,市民作家式亭三马也写了一部滑稽小说,由浮世绘艺术家歌川丰国为其绘制插图(见图8)。滑稽本的首页描绘了一个江户人的诞生,或者如他们自称的那样,一个“江户子”的诞生。一个男孩降生在一个充满爱心、谦逊朴素的家庭。当家人给新生儿洗浴的时候,他突然跳起来挠了挠腋窝,似乎准备好了迎接未来的战斗,抑或是准备出拳迎接他人生的第一场拳赛。江户人把自己看作是“未经打磨的钻石”,“比较硬朗”,这与京都居民的弱不禁风形成了鲜明对比。同大阪一样,江户也是商业城市,但江户的市民和幕府将军的随从们住得很近,武士精神感染了下层的人。现代日本人礼貌勤奋又充满强烈的自豪感,其中也许就有江户遗风。对出身低微的江户居民来说,他们的城市里有三样东西最多,即稻荷神社[3]、吵架和狗屎。首先,江户的街坊四邻都受到狐狸这种卑微神灵的庇护。尽管身份低微,狐狸却来去无踪并常以智斗威猛的大型动物而闻名。其次,纠纷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生活在一个拥挤不堪而又平淡无趣的大城市里。实际上,尽管在现代日语中“kenka”一词的意思是“争执”,但是在江户时代,它指的是一种可管控的纠纷,并不会随便诉诸暴力,当时的人们只要发生“争执”就可以选择报官。最后,犬类的排泄物可能令人不快。但它也表明江户人善待并喂养流浪狗,而不是虐杀它们。总体来说,江户人很谦虚,善良坦诚而又大智若愚。歌川丰国的画中所描绘的就是这样的江户人,画中窗外浮现的是江户城堡的尖顶,顶上的鱼形兽“金鯱”[4]是祈愿城堡免遭火灾之虞的特色标识。

图8:式亭三马所著单色印刷本《人间一心 替操》的插图,歌川丰国作,江户,1794年。这是一本通俗印刷故事书,这一页描绘了一个结实、健壮的江户平民的诞生,他看上去跃跃欲试,仿佛想要跟人打上一架。窗外是幕府城(被得体地遮挡住)
替操》的插图,歌川丰国作,江户,1794年。这是一本通俗印刷故事书,这一页描绘了一个结实、健壮的江户平民的诞生,他看上去跃跃欲试,仿佛想要跟人打上一架。窗外是幕府城(被得体地遮挡住)
[1]英语俗语,意为祖辈一代代传下来的东西,每一代都更换其中一部分,最终所有的零件都被替换。——译者注
[2]即江户幕府最高官职。——编者注
[3]稻荷神是日本神话中的谷物和食物神,主管丰收。日本将狐狸视为稻荷神的使者。——译者注
[4]鯱(hǔ),日本汉字,指的是一种日本海兽,在日语中也会用来称呼逆戟鲸。它作为保护神,常被置于屋脊两端,传说有防火之效。——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