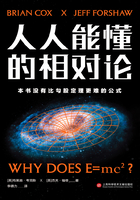
第一章 空间和时间
想想看,什么是“空间”?“时间”又是什么?你或许会把空间描述成,寒冷冬季,当你凝视夜空时,星星背后的黑暗区域。又或许,你会指着月亮和地面间的大块空白说,那就是空间。看!那闪闪发光、点缀着星条图案的飞船在里面航行,它载着一个叫巴兹的光头探险家驶向洪荒之地。而提到时间,你也许听到了手表的嘀嗒声,或是想到随着太阳第五十亿次向北纬倾斜中,渐渐变黄的叶子。这些都是我们对空间和时间的直观感觉,与生活密不可分。我们立足于这蓝色星球的表面,随时光的流逝穿行在宇宙之中。
19世纪末,科学在不同领域取得突破,迫使物理学家重新审视空间和时间的直观图景。等到20世纪初,基于直觉的时空观落下帷幕,它已不再扮演承载星球伟大旅程的舞台。对此,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导师兼同事赫尔曼·闵可夫斯基(Hermann Minkowski)深有体会,他激动地写道:“从今往后,作为空间的空间和作为时间的时间都销声匿迹了,一个时空的结合体已取而代之。”这是一则著名的讣告,古老时空观被宣判死亡。
闵可夫斯基所说的时空结合体是什么呢?想要明白这听起来近乎神秘的说法,就需要理解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这个理论带来了世界上最著名的一个方程:E=mc2。同样也因为这个理论,符号c(也就是光速)成为解释宇宙造化时占据中心位置的符号。
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是关于空间和时间的理论。其核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速度。宇宙中任何东西,无论多么强大,无论如何加速,都无法超过它。这个特别的速度也就是光速,299792458米/秒是它在真空中的数值。地球发出的光以这个速度飞行,8分钟到达太阳,10万年穿过银河系,200万年抵达它最近的邻居仙女座。与此同时,地面上最大的望远镜正在凝视夜空,捕获着来自遥远恒星的微光。这些微光在100亿年前就出发了,它们从可观测到的宇宙边缘开始了旅程,出发时,比地球的诞生还要早几十亿年,那时地球还是一团星际尘埃,而现在那些恒星早已灭迹。光速很快,但这也不是绝对的。相对于恒星间遥远的路程和星系间巨大的间隙,光速可是慢得令人心急;并且,在瑞士日内瓦欧洲核子研究中心,27千米长的大型强子对撞机可以把足够小的物体加速到光速的百分之一[2]。
这个特别的速度也叫作宇宙上限速度,这是一个非常古怪的概念。尽管光在爱因斯坦的宇宙中扮演着深刻的角色,它有充分的理由能以宇宙上限速度传播,但随着阅读的深入,你会发现将这个特别的速度和光速相关联,就是一个障眼法。关于爱因斯坦的宇宙我们稍后再谈。现在只需要知道当物体接近这一特殊速度时,奇怪的事情就会纷至沓来。是什么限制了物体的加速超过上限速度呢?这就好比有一个普遍的物理定律限制着汽车,使它永远不能超过70英里[3]每小时的速度行驶,无论引擎有多强大。这和高速公路的限速不同,不需要警察来强制执行。这是时空在建构自己时所遵循的规律,从来没被打破过。我们应该为此感到庆幸,否则就会灾难不断。若假定光速可被超越,我们便能制造时间机器,穿越历史,回到过去的某一时刻。比如,抵达我们出生前的某一刻,巧做安排,使得父母永远不能相见[4]。命运悖论是科幻小说里常见的精彩情节,可是宇宙并不是这样构建的,爱因斯坦的发现也证实了这一点。真实的时间和空间巧妙交织在一起,防止着悖论的出现。要进入爱因斯坦的宇宙,唯一让我们付出的代价便是抛弃根深蒂固的时空观念。在爱因斯坦的宇宙中,运动的时钟缓慢地嘀嗒作响,运动的物体尺寸收缩变小,人们可以穿越数十亿年进入未来;人的一生几乎可以无限期地延长,直到太阳死亡,海洋沸腾,太阳系陷入永恒的黑夜;我们可以观察到恒星从旋转的尘埃云中诞生,行星的形成,还有创世之初生命的蠢蠢欲动。总的来说,在爱因斯坦的宇宙中,遥远的未来大门敞开,过往却被牢牢地锁死。
爱因斯坦描绘的宇宙光怪陆离,他是如何“被迫”构建这样的宇宙观的呢?在本书的结尾,你会一探究竟。你还将了解到这些概念在科学实验和技术应用中是如何一遍遍地被印证的。例如,车上的卫星导航系统就证实了卫星轨道上时间的律动与地面上的不同。爱因斯坦的观点是激进的:空间和时间并不像它们看起来的样子。
我们进行得有点快。我们必须回到相对论的核心,也就是空间和时间这两个概念上来,只有对它们仔细琢磨,才能理解和欣赏爱因斯坦的重大发现。
设想你正在航行中的飞机上看书,12点钟,你放下书,离开座位,沿着过道去找前面10排处的朋友聊天。在12点15分,你回到座位重新拿起了书。直觉告诉你,你回到了同一个地方。因为返回时你走过了同样10排的距离,而书本仍然静静地躺在那里。现在,让我们深入地思考一下“同一个地方”这个概念。这可能看起来迂腐可笑,当我们这样形容一个地方时,指向岂不是显而易见的事情?打电话给朋友想碰头喝一杯时,我们可以约在酒吧里,酒吧会一直在那,就在前一晚我们离开的同一个地方,一动不动地等着我们。乍一看,本章开头的许多内容都显得可笑。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坚持下去。这样,我们才能跟上亚里士多德、伽利略、牛顿和爱因斯坦的步伐,对这些显而易见的概念进行思索。如何准确地定义“同一个地方”呢?我们已经知道如何在地球表面做到这一点:地球仪表面画有一组网格线,即纬线和经线。地球上任何一地方都能用两个数字标示出在网格上对应的位置。例如,英国的曼彻斯特市位于北纬53度30分,西经2度30分。有了这两个数字,沿着赤道和格林尼治子午线,我们就可以轻易地找到曼彻斯特。接着,通过类比,还可以建立一个巨大的三维网格,来确定任意一点的位置。想象一下,网格可以从地球表面向上,往空中延伸;向下,穿过地心到达地球的另一边。基于这张网,空中飞禽、地面建筑和地下岩石都可被准确定位。假如网格从我们生活的世界继续向外延伸,掠过月球,经过木星、海王星和冥王星,再穿越银河系,达到宇宙最遥远的地方,它便可以包罗万物,为万物标定位置。用伍迪·艾伦的话来说,如果你是那种永远记不起东西放哪的人,这非常管用。总之,这张大网是万物运行的舞台,是装着宇宙的巨大盒子,我们不妨叫它“空间”。
让我们回到飞机上,继续探讨“同一个地方”是什么意思。在飞机上,你可以说12点和12点15分你在同一地方。可对于一个坐在地上看飞机的人,情况并非如此。当飞机以600英里每小时的速度飞过头顶,他会说在12点到12点15分之间你已经移动了150英里。也就是说,12点和12点15分,你处在不同地方。谁是对的?谁是运动的,谁又是静止不动的?
如果你答不出来这个看似平常的问题,别担心,很多人有同样的苦恼。古希腊圣哲之一亚里士多德都完全搞错了。他会毫不含糊地说,是你——飞机上的乘客——在运动。亚里士多德认为地球是静止的,它的外面是55个同心的水晶球面,像俄罗斯套娃一样层层套在一起。太阳、月亮、行星和恒星附着在这些水晶球面上围绕着地球旋转。他展示了一个顺应直觉的空间,装着地球和水晶球壳的盒子或舞台。这幅宇宙图像只由地球和一组旋转球壳组成,让现代人听起来很可笑。但是稍做思考,你会得到什么宇宙图像呢?前提是你尚未被告知地球绕着太阳转,也不知道恒星是远处类似太阳的星体,其中一些甚至比太阳亮几千倍,只是相距太远,有数十亿英里。你肯定也难以想象地球是在一个巨大的宇宙中流浪的星体。现代宇宙图像是通过几千年的实验和思考形成的,来之不易,而且常常违反直觉。若非如此,像亚里士多德这样的旧时代伟人早就自己解开谜团了。因此,如果你觉得本书中的每一个概念都很难理解,那么请记住: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也有同样的感受。
现在让我们暂时接受亚里士多德的解答,看它会得出什么结果,从而找出其中的漏洞。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们可以用以地球为中心的虚拟网格线来填充空间,借此来确定万物的位置和运动状态。如果空间是一个盒子,装满物体,地球被固定在它的中心,那么飞机上的你很明显已改变了位置,而看着你飞过的人静止地站在地球表面,在空间中一动不动。也就是说,这个假设中绝对运动是存在的,相对应的绝对空间也因此存在。如果一个物体随着时间的流逝改变了它在空间中的位置(以地球为中心的假想网格就可以把运动测出来),它就被认为处于绝对运动的状态。
问题来了,地球并不是静止的,也不是宇宙中心,它是一个围绕太阳公转的球体。地球正以67000英里每小时的速度相对太阳运动。从上床睡觉到早晨起床,8个小时内,你已经走了不止50万英里了。你可能会说,当地球用大约365天时间完成绕太阳一周的轨道运动时,你的卧室就回到了空间中完全相同的地点。因此你决定把网格的中心放在太阳所在的位置,这样稍做修改就保持了亚里士多德观点的精髓。这个想法很简单,但还是错了,因为太阳在以银河系为中心的轨道上。我们身处的银河系是一个拥有超过2000亿个太阳的岛屿,大得超乎你的想象,转上一圈可需要不少时间。而太阳距离银河系中心156000万亿英里,以48.6万英里/小时的速度绕其运行,完成一周需要2.26亿年。因此不得不进一步移动网格的中心,来尝试拯救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把网格的中心放到银河中心呢?你可以想到:上次地球经过你在床上所躺的这个位置时,一只恐龙正在清晨的阴影里吃史前的叶子。事实上,星系正在彼此飞离,距离我们越远的星系,飞离的速度越快。所以把银河系作为中心的空间也难以描述。总之,在包含无数星系的宇宙中,想要精准地锚定我们的运动状态确实非常困难。
物体“静止不动”的这种状态无法被准确定义,这正是亚里士多德体系的问题。也就是说无法给他的网格系统找到一个中心,以此为原点确定物体的位置和它们的运动状态。亚里士多德本人却从未受到这个问题的困扰。因为在之后的2000年中,他所倡导的地心说[5]也从未受到过严重的挑战。或许早该有人提出疑问,但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即使对于最伟大的思想家,看透本质也绝非易事。公元2世纪,在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工作的克劳迪斯·托勒密斯(Claudius Ptolemaeus),也称托勒密(Ptolemy),他是一个细心的夜空观察者,五颗在空中运动相当奇怪的星星让他感到忧心忡忡,这五颗星星又叫“游荡的星”,而“行星”一词就起源于此。通过数月的观察,他发现行星并不沿一条平滑路径穿行于星空,反而会迂回前行。这种奇怪的运动被称为“行星逆行”,事实上,这早已为人所知,比托勒密早了几千年的古埃及人将火星描述为“向后移动的行星”。托勒密深信亚里士多德的地心说。但是为了解释行星逆行,他不得不将行星安置到不以地球为中心而旋转的更小轮轴上,再把这些轮轴安置在绕地球旋转的球壳上。这个模型能够解释行星在夜空中的运动,却相当复杂,更谈不上优美。直到16世纪中叶,尼古拉斯·哥白尼(Nicholas Copernicus)才提出了更为正确而美妙的解释,即地球并非静止在宇宙中心,而是与其他行星一起绕太阳运行。哥白尼的作品饱受批评,直到1835年才从天主教会的禁书名单中移除。通过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的精确测量和约翰内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伽利略(Galileo)和牛顿(Newton)的大量工作,才终于证明了哥白尼的理论是正确的。这些工作还促进建立了以牛顿力学定律和万有引力为基础的行星运动理论。在1915年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问世之前,这些规律很好地解释了从炮弹到行星,再到旋转星系在内的所有重力作用下的物体运动。
人们对地球和行星的位置以及它们在天空中运动状态的观点不断改变,这为所有对自己的认知深信不疑的人上了一课。乍一看,许多事情似乎不言而喻,例如,当我们不动时,就认为自己是静止的。而未来某天的观察总能让我们大吃一惊。或许不应该太惊讶大自然有时会违反我们的直觉,毕竟我们只是类人猿后代中比较善于观察的一支,拖着碳水构成的血肉之躯漫游在一个岩石堆积的行星表面。而这颗行星所围绕着的一个恒星又是银河系边缘最普通的一颗中年恒星。事实上,本书中所给出的时空理论也仅仅是为更加深奥的理论提供近似的初步探讨。科学是一门拥抱不确定性的学科,认识到这一点是取得科学成功的关键。
在哥白尼提出日心说宇宙模型后的第二十年,伽利略·伽利雷(Galileo Galilei)出生了。他对运动的定义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尽管他的直觉很有可能和我们一样:地球在脚下静止不动。然而,行星在天空中运动的有力证据表明事实并非如此。伽利略伟大的洞察力让他从这个看似矛盾的现象中得出一个深远的结论。感觉上,我们是静止不动的,内心却知道我们在绕太阳运动。不可能有办法提出一个准则决定什么是静止的,什么是运动的。也就是说,只有相对于其他物体时,谈论运动才有意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想法,又似乎是明摆着的事情,但要充分理解它的内涵需要做些思考。很明显,当你在飞机机舱里读书时,书就在你手里,你把它放在桌子上,书就会和你保持固定的距离,书相对于你并没运动。对于地面上某个人,这本书却是随着飞机在空中运动的。伽利略真知灼见的真正意义在于,这是唯一可以成立的解释。当你描述书本是如何运动时,只能描述为它是如何相对于你运动的,是如何相对于大地、太阳、银河系运动的,总是需要相对于其他某个物体运动的,那么绝对运动便是一个多余的概念。
这听起来像算命先生的禅语。然而,结果表明这是伟大的洞见,伽利略绝非徒有虚名。为说明伽利略工作的重要意义,我们首先建立一套能判断物体是否处于绝对运动状态的亚里士多德网格系统,进一步看它是不是一套有效的科学理论。有效的科学理论可以预测可观察的结果,能够通过实验测量得到验证。在这里,“实验”指的是对事物的测量,如,测量钟摆的摆动,测量燃烧的蜡烛火焰发出的光的颜色,或者测量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大型强子对撞机中的亚原子粒子的碰撞(我们稍后再讨论这个实验)。如果从一个科学观点不能得出可观察的结果,那么无论它多么迷人,都不是理解宇宙运作的必要理论。
在一个充斥着各种各样想法和观点的世界里,这种方法行之有效,它可以把正确的观点选出来,就像把小麦从麦壳里拣出来一样。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曾用中国茶壶打比方来说明,坚持那些没有可观测效果的概念是徒劳的。罗素声称,他相信在地球和火星之间有一个中国茶壶在运行,它太小了,无法被现有最强大的望远镜发现。如果人们建造了一个更大的望远镜,并对整个天空进行了长时间的仔细观察,仍没有发现茶壶存在的证据,罗素会说茶壶比预想的要小一些,但仍然存在。这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移动的球门门柱(moving the goalposts)”[6]。但罗素接着说道:“尽管茶壶可能永远不会被观察到,对于怀疑它存在的人来说,‘存在一个茶壶’仍然是一个‘无法容忍的假设’。”事实上,无论多么荒谬,其他人应该尊重罗素的立场。罗素并不是主张他有权独自妄想,而是说,一个无法通过观察来证明或反驳的理论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无论你对它多么的深信不疑,它却什么也教不了你。为了理解宇宙,你可以发明任何自己喜欢的理论,但如果这些理论无法被观测或者导致可以被观测的结果,那么它们就是非科学的。依据这样的逻辑,如果能够设计出一个实验来验证绝对运动的观念,那么绝对运动的概念将具有科学意义。例如,我们可以在一架飞机上建立物理实验室,通过对所能想到的物理现象进行高精度的测量,进而再一次挑战有关运动的问题。架设一个钟摆,测量它摆动的时间,利用电池、发电机和电动机进行电学实验,或者观察核反应并对核辐射进行测量。如果空间足够大,我们可以在飞机上进行人类历史上所有的实验。本书的一个核心观点是如果飞机没有加速或减速,无论在上面做任何实验,结果都不能告知我们的运动状态。即使往窗外看也没有用,因为可以这样说,我们站在窗前静止不动,而地面却从身边以600英里每小时的速度飞过。能得到的结论是“相对于飞机我们是静止的”,或者“相对于地面我们是运动的”。绝对运动并不存在,因为它不能被实验测量。这就是伽利略的相对性原理,现代物理学基石之一。对我们来说,这事并不为奇,因为我们已有了相对运动的直观经验,例如,如果你坐在静止的火车上,旁边站台的火车缓缓驶出车站,也许一瞬间,你会感觉到好像自己在移动。我们很难检测到绝对运动,因为它并不存在。
这种相当哲学的思考得出了一个有关空间性质的深刻结论,我们向爱因斯坦相对论迈出了第一步。从伽利略的论证可以得出关于空间的什么结论呢?这个结论是:如果不能检测到绝对运动,那么用来定义“静止”的特殊网格就没有价值,因此,绝对空间也没有意义。
让我们更进一步研究这一重要认识。我们已经确定,如果可以定义一个覆盖整个宇宙的亚里士多德特殊网格,那么相对于该网格的运动即是绝对运动。我们认识到,特殊网格的想法应该被抛弃,因为不可能设计出一个实验能来确定我们是否在运动,也无法确定网格应该被固定在什么位置。如果没有亚里士多德的特殊网格,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定义一个物体的绝对位置?我们在宇宙中的什么地方?这些问题就毫无科学意义。唯一能确定的是物体的相对位置。也就是说,无法在空间中确定物体的绝对位置,促使我们认定绝对空间没有意义。把宇宙想象成一个包含运动物体的巨大盒子,是无法被实验所证实的。以上分析非常重要,值得一再强调。伟大的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曾经说过,无论你的理论多么美丽,你多么聪明,还有你是谁,只要它们与实验不符,那就是错误的。这是科学的关键。反过来说,如果一个概念不能通过实验来检验,那么它的对错就无从判断,也没有意义。当然,我们仍然可以假设这个不可测试的想法是正确的。这样做带有偏见,具有阻碍未来进步的风险。所以,既然没有办法来确定亚里士多德网格,我们不如从绝对空间和绝对运动中解放出来。那又会怎样?接下来我们会在第二章中发现,从绝对空间的重担中解放出来对下一个世界的爱因斯坦发展他的空间和时间理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在,我们已经从绝对空间中获得自由,但我们还没行动起来。为了激起读者的兴趣,这里提前透露一下,如果没有绝对空间,两个观察者就没有依据就一个物体的大小达成一致。如果我说随着绝对空间的消失,“一个球的直径是4厘米”这么板上钉钉的事情,也变得不确定了,你一定会惊掉下巴。
至此,我们已经详细讨论了空间和运动的联系。那么,时间呢?事实上,时间已经进入我们的思维。用来描述运动的速度可以用英里每小时来衡量,或者用在特定的时间间隔内运动的距离来定义。那么有什么关于时间的说法吗?我们是否可以做实验来证明时间是绝对的,或者是否应该抛弃时间这个更加根深蒂固的概念?伽利略摒弃了绝对空间的概念,但他的理论根本没有触及绝对时间的观念。他仍认为时间是绝对的,绝对时间是指完美的时钟可以在宇宙的任意角落嘀嗒嘀嗒地同步运作。飞机上的时钟、地面上的时钟、太阳表面上的时钟(需要足够坚固),还有一遥远星系的轨道上的时钟,若能正常计时,它们将永远显示相同的时间。令人惊讶的是,这个看似显而易见的假设与伽利略所说的——没有任何实验可以告诉我们是否处于绝对运动状态的说法,是直接矛盾的。更难以置信的是最终摧毁绝对时间的证据,竟然来自中学物理课上,与电池、电线、电机和发电机有关的实验。为了摈弃绝对时间这一概念,我们必须要进入19世纪——发现电和磁的黄金时代。
[2]光速并非快不可及。
[3]1英里约等于1.6千米。
[4]类似于祖父悖论。
[5]多个球体环绕静止的地球进行旋转。
[6]“moving the goalposts”,表达此行为有失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