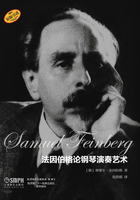
改编曲
原作曲者想参与自己构思的音响体现过程,是可以理解、合乎情理的。补充乐谱所写的演奏提示有时会很详细,说明作曲家对未来演绎的方法和完美非常关心。
另一方面,优秀的演奏家一生为了完美体现不同作曲家的构思,花费了无数小时练习和掌握乐器的技巧,以掌握特殊的、他独有的体现音响的秘密,未必能够对有时甚至最伟大的作曲家都会有的表述上的失误和缺点漠不关心。在任何情况下,下面的这种看法都是错误的:认为演奏家作个别修改和订正,只是由于不谦虚和无论如何也要越过屈居配角的界限。
音乐史上有一些出于伟大的友谊以自我牺牲精神,从事改编工作颇有成效的例子,如: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在创作上帮助过穆索尔斯基;李斯特的改编曲是为了提挈他喜爱的、甚至还未世界闻名的原作曲者。此外,还有钢琴大师布索尼、陶西格等人的巴赫管风琴改编曲(在苏联,首先可以举盖吉凯的巴赫改编曲,尤其是他的交响改编曲《帕萨卡利亚》)。
现在必须事先说明,钢琴或其他乐器的改编,与编辑只作表述上的校订不同。前者在改编时做比较大的修正,有点不完全按照原谱。而这种改变,当然是由于另一种乐器的性能或另一种配器体系引起的。
总之,在改编时更改一些原谱是不可避免的,但很难找出演奏家插手作曲家的乐谱成功的例子。
音乐会演出的实践和著名钢琴家常常作的修正表明,即使偏离原谱不大,仅在和弦里加进一个多余的音符,改变音型或一些细节,通常也会歪曲作曲者原本的构思。这样的“改善”常常证明演奏家不完全理解原作曲者的风格。
让人惋惜的是许多优秀的音乐家和杰出的演奏家有时没有分寸感和缺乏艺术感,这不仅表现在音乐会舞台上,这还可以说是一时心血来潮的即兴作怪,还表现在已经深思慎审研究过的古典作品的版本上——放纵自己随意篡改原谱。即便是最伟大的演奏家有时也会犯太随心所欲的毛病,例如布索尼在肖邦练习曲的末尾加了两小节基音和五度音位置的琶音,这绝对是个败笔。
修订古典作曲家乐曲版本的失败例子,可以举从比洛和车尔尼到克林德沃得特、阿尔伯特、里蒙德等人修订的古典音乐的版本。属于这类情况的还有济洛季改编柴科夫斯基的几首作品,如《F大调变奏曲》。
当没有任何根据就怀疑原本风格无懈可击的原作曲者的表述不完美时,编辑自作聪明的插手特别令人讨厌。所以许多有经验的演奏家宁愿研究未经出版社编辑之手的作品原稿。
许多编辑不是专心仔细阅读作曲家的原稿,体会他的构思和意图,细心保持具有作曲家本人特征的乐谱原貌,而是全凭自己的想象修改一切细节,添加重叠,把声部移换八度或者几乎更改了所有的连线和演奏提示。编辑抱着宽容的心情原谅作曲家,把他看成灵机一动的疯子或娇生惯养的孩子,没有时间清楚地记下自己的构思或不愿从崇高的创作任务屈身从事细写谱子这样平凡的活。
一些编辑的校订自认为改善了乐器的演奏技法。例如,常常增添音符或把声音移高或移低到另一个音区,理由是在创作作品的那个年代,作曲者没有大音域的键盘。不错,贝多芬在许多奏鸣曲或《第四协奏曲》第一乐章中,由于这种原因不得不变动再现部。但是,如果我们恢复同呈示部相符的再现部,就会失去在创造上丰富了作品创造性的宝贵变体。作曲者的独出心裁是由于受当时钢琴的八度数量的限制。超出作曲家所用音列范围之外的音符会使声音显得与作品的风格大相径庭,就像在深思熟虑合理安排的总谱中偶然出现了其他乐器。因此柴科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第一乐章在过渡到副部时,用低音单簧管演奏4个音符的办法,应该认为是不完全合理的。
实践证明,即使原则上有经验的天才钢琴演奏家能够帮助作曲家校订其原谱,他所能找到的修正和增补的方法也未必能提高原作的品质。如果有人吃力不讨好地写一部校订经典作品的历史的话,那大概是一部被或多或少地歪曲和几乎被通篇无理篡改的历史。贝多芬作品的天才演绎家李斯特于临终前,也后悔他在音乐会演出中曾偏离了原作。
总之,钢琴家唯一有权力创造性地修正原作者风格的领域是改编曲。可是即使在这里也应该避免不必要地脱离原谱、画蛇添足地加进捏造的经过句和装饰音,从而破坏了作曲者的风格。改编曲的任务是尽可能地保持作品的风格,用其他手段表达原作音响的特性,还不能机械地履行这个任务。这就需要精通自己的乐器,还需要创造性地寻找相应的表述形式和揭示作曲家乐思的新的表现手法。正是为了保持而不是破坏作品的本意,才需要新的陈述和新的表现手法。
李斯特在改编的《纺车旁的玛格丽特》中更改了节拍和旋律的轮廓,由此使钢琴曲获得了近似声乐的表现力。相反地,在《魔王》的降B大调段落中,改编曲只用左手保持伴奏的进行,获得紧张的技艺性跳跃,代替了舒伯特原曲的轻巧。当然,常出现用演奏者的技巧掩饰改编的困难,但这对改编曲是不利的。
不仅陈述具有显著特征的钢琴改编曲中有主题成分的改动,在交响乐作品中,从一种乐器转到另一种乐器通常在记谱上也有修改。贝多芬在《第九交响曲》中,由大提琴和低音提琴奏出的末乐章主题常用一个二分音符代替两个四分音符。不由得想起文学翻译中类似的情况:同义词不是永远只有一个涵义,诗人、翻译家常常改变原作的格律和音节数,力求准确地表达出诗本来的神韵。
不论对另外一种乐器的改编或写成改编曲有怎样的看法,不容否认的是,这个体裁的许多杰作值得存在,是一种创造性的演绎。然而同样毋庸置疑的是,改编版分割了原作版的演出范围,在一定程度上侵占了原作曲家的创作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