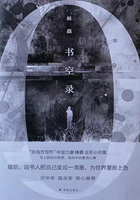
上辑 虚构之敌
书空录
我不会说出我的名字,不然有人会按图索骥,把套子给我准备好,挖好一个深坑,又在旁边竖起一块引人走近的指示牌——即使于己毫无好处,他们也要把一个个无关之人送进水深火热和狼狈不堪之中。我见多了这样的人。我多次看到这些人,在别人背后,刺出锋利冰冷的尖刀。当然,即使我说出我的名字,也不会有人注意到我。我是一个有名字的无名者,我所供职的杂志社,不会在扉页打上我的名字,那些索引狂魔和好奇怪叔,绝不可能从中国文学杂志的海洋里,把我打捞出来。我不过是一个编务,一个负责打打草稿、排排版的小人物,不会有人认识。我不是扉页上的社长、主编、副主编或者编辑部主任,不会有人在投来稿件的时候,附上一封信,抬头写上“尊敬的……”——当然,我一点都没有妒忌的意思,恰恰相反,我乐于这种被遗忘,热衷于当一个不存在的人、当一个无、当一团空荡荡。我不愿说出我的名字,那样,我吐出的这些疯言妄语,就不会有人嘲笑,不会有人投来不怀好意或充满同情的目光。
事实上,从很多年前,杂志社的老社长把我招进来当编务开始,我就一直怀疑自己干不好这件事——虽然这事并非多难。那是一个热火朝天的年代,当时我是一家文化单位看门的保安,但我很快连保安也当不了了。一场车祸夺走了我的妻子和刚刚开始摇摇晃晃走路的女儿,我则折了一条腿——关键是,肇事司机是个孤家寡人,也在车祸中把命丢了。他是潇洒走一回,我就很惨了,天降大祸,索赔无门。拎着一瘸一拐的腿,我连看门的保安也没法当了——小偷们都轻便得很,他们就是大摇大摆在我面前走过去我也追不上,何况他们都神出鬼没。那时候我天天恨不得去死,也曾好几回走到城市里的河边,望着水里浑浊的旋涡和泡沫,觉得底下便是鲜花盛开的龙宫或光耀明亮的天堂。我还没跳进去,当时的老社长就叫了一个与我倒班的保安盯紧我,把我从旋涡和泡沫的诱惑中拉上岸好几回。老社长找我聊过几次,他说,既然当不了保安,就到他的杂志社来,脚动不了,手还是可以的。他安排我去培训,学习电脑打字,后来我成了杂志社的编务,用敲打的手指,养着我那无底洞般的嘴。我的残疾证,也是老社长帮忙办下的。老社长后来升迁到上级部门去了,他跟继任者强调,无论如何都不能把我裁掉。我于是成了在这个杂志社工作最久的一个人,人们一个个地到这里,有的升有的迁,只有我,不断地在电脑上打印出一份份草稿,经过编辑们的编校之后,我排好版,出菲林,给印刷厂寄去。到后来,就不再寄菲林,而是直接在网上给印刷厂传压缩包,厂里刻版就开印。
这本杂志自当年的老社长主持改版之后,在国内外都有了一些名气,编辑部人来人往,不少著名的人物都曾来拜访,甚至有讲着不知道哪国语言的卷毛老外。我敢说,全国对这杂志的内容最了解的人,肯定是我。那些流水的编辑、有一搭没一搭的订户,肯定没有像我一样的,笨拙地把一期期杂志啃下去。能读得懂的少,读不懂的多,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感觉能读懂的内容变多了——当然,这可能是我的幻觉。我是一个时常有幻觉的人,比如说,我会从那条河的旋涡和泡沫上,发现妻子和女儿的脸;会从一篇来稿的题目中,听到妻子和女儿的笑声。这些幻觉我不敢跟人说,也没法说。
当年老社长主政之时,为了提高我们的知识水平,让编务把稿子打印出来后做第一遍校对,我也因此笨拙地翻着词典,把那些稿子看了,起先,我改掉的“错别字”和“标点”,常常被后几道校对的编辑在旁边打上三角形——也就是“恢复原样”的意思。编辑们投来愤怒的目光,我只假假地当作不知,当然,为了不让编辑们移恨老社长,我翻看词典更加勤奋了。我把编辑们处理过的稿子拿过来仔细查看,一天天过去,编辑们打上三角形的地方,越来越少。后来有了校对软件,社长也不是当年的老社长了,新的编辑只让我们根据校对软件的提示,标出可能有误的地方给他们斟酌,我还是忍不住把一篇稿子从头到尾读一遍,改掉我觉得需要修改的地方。若有一篇稿子中我改的地方没有被编辑们改回来,我就会窃喜好久。当那些文章被印刷出来,翻开整齐、崭新的书页,在一行行文字和标点的队伍中,我可以找出我的声音和动作。我的幻觉又出现了,手拿红笔在纸张上滑动的画面不断出现;我甚至看到,某个读者捧着杂志,目光在我修改过的地方失焦、出神,魂不守舍或者发出一声长叹。我觉得自己是一个躲在暗处的人,透过文字和标点的缝隙,看到读者们无法隐藏的表情。对了,不是因为老社长在我最绝望的时候帮过我我就说他的好话,他确实是一个想法超前的人。很早的时候,他就在单位里鼓励我们学英语、背单词,谁背得多,年货就多一些。我也因此死记硬背过英语单词,虽然那些单词都随着老社长的升迁还回去了,可我们的脑袋就像房间,那些单词短暂入住之后,即使很快搬迁,房间里也永远留下了它们生活过的痕迹。
我没有发稿权,我甚至不是普通的编辑,可若说我一个人编过很多期杂志,你们会不会觉得又是我的幻想症发作了?但这是真的,在我那一个人的房间里,有一个书柜,专门摆着这些杂志。那个书柜是编辑部淘汰的,我给捡回来了。那是老社长用过的书柜,我把我编的杂志摆在里面,就像看到当年我恨不得跳进旋涡和泡沫时,那个保安伸出的带着温度的手。这些当然不是正式的出版物,可若是你看到了,一定会很惊奇。它们是打印稿,一本本处于未完成的样子,可在我眼中,那就是完整的,就是杂志最终的样子。我甚至按照杂志封面的风格,给它们设计了封面,用同样的纸张打印出来,精心裁切,一眼看上去,你肯定认为那就是杂志的某一期。可这是属于我一个人的杂志,我是这杂志唯一的编辑,我有着至高无上的发稿权;我也是这杂志的唯一读者,我独享它的所有页码、文字、标点和空白。
你知道的……可能,你也未必知道——无论哪家杂志,都有很多稿子是没法刊登的,甚至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九的稿子,没法转化为最终刊登出来的成品。写得好不好只是一个缘由,还有各种原因,让那些稿子永远无法面世:风格不符、题材禁忌、趣味怪异……还有很多理由甚至是没法理解也不能说出来的。那么多年里,我曾听编辑们无数次私下的牢骚,听过杂志社举行笔会时作家们的抱怨,他们在吐槽之后,却在一个无法描述的地方停歇、嘴巴微张,留下一阵阵寂静的空茫。一篇稿子投到编辑部,若是纸质稿,我会登记、编号,交给编辑;若是电子稿,则在打印出来、登记编号后,也交给编辑。很多被淘汰掉的废稿,最终又由我来处理,我也因此看了很多无用之稿。慢慢地,我竟然培养起自己的看稿“喜好”——我不知道能不能用“喜好”这个词——就是说,我会对某种风格的稿子特别喜欢,会在幻觉里看到那个作者写下文章时的画面,看到他是嘴角带笑还是眼睑遭遇洪灾。这些稿子被我单独挑出,仿照着杂志的栏目设定,给那些稿子写稿签决定是否留用,然后校对、排版、设计封面。我会在家里的旧电脑上,把版式调整到我最满意的程度,再到杂志社的编务室打印一份。我用最原始的手工装订,努力把它做得像是一本真杂志——真的,只要你不细看,只要你不是对印刷的纸张很了解,你一定以为那就是一本印刷出来的正式刊物。当然,这些杂志都是没有刊期、刊号的,在该标明刊期、刊号的地方永远是空白,永远是虚无。这本一个人的杂志,就像一个在杂志社里隐匿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无名瘸子,在某些人眼里永远不存在。我通常每年编两本,这五十本刊物就写着我的四分之一个世纪。我不是说我老有幻觉吗?是的,在某些幻觉里,我是一个时光收藏者,用老社长用过的旧书架,装下了我的四分之一个世纪——可那仍旧是一期又一期的空荡荡。
有一年,编辑部来了一个新编辑,还处于适应工作的状态。一次,他接待了一个缩着腰前来编辑部拜访的中年人。老实讲,这样的人我见多了,基本上不打招呼就自己跑来编辑部的作者,百分之八十都不太正常——若结合他颤颤巍巍的身形,这个可能性就要上升到百分之百了。那编辑毕竟太嫩,毕恭毕敬地接待他,接下来他递过来的稿子,听他唠叨了一个小时之后,才终于把他送走。他的稿子是所谓“诗词”,编辑很快按照他留的电话,回复他说杂志没有相应栏目,可另行处理。在电话里,这个投稿者回答得挺正常,挂电话之后,却立即给编辑发来了短信:“你有什么权力封杀我?这么优秀的稿子,你却不用,我要去买一把斧头,我要当顾城,你就是谢烨。”还没等编辑回话,他的连续轰炸又来了:“你要把我的稿子转给×××看,由他来裁决,你没资格审判我的稿子。”他说的×××,就是当年的老社长,编辑苦笑着给他回短信:“这位老师已经离开我们杂志社十多年了,你有渠道,你可以把稿子转给他看看,我没义务代转。”这句话更惹怒了“顾城”,各种威胁继续飞来,把编辑吓得掏出他的诺基亚手机,给我们看那些短信:“这些我都存着,若有一天我真出什么事了,你们报警时,记得从这里找线索。”
大概两个月后的一天,我在单位附近的超市,认出了那个投稿者——我当然能认出他来了,他一遍遍给小编辑发威胁短信,还继续往编辑部投来打印的“诗词”,每封信都附上他的艺术照:一个中年男人,在高光的掩盖下,无比怪异。他正在超市门口推一辆购物车,腰身弯折,头几乎要贴到车上。我拄着拐杖过去,拍拍他的肩膀,他斜着眼看我,满脸疑惑。我说:“你不要再那样做了。”他眉头紧锁,显然,他不理解我指的是什么。我说:“你以为你做的事没人知道,好像别人拿你没办法……看到我这只脚了吗?被人砍的,你再那么过分,哪怕我另一只脚没了,也要把你废了。”他紧张起来:“……你……你……你说、说什么?”我把拐杖抬起,砸到他的购物车上:“不管你懂不懂,反正给我小心点,要不然,我把你写进黑名单……”他的腰更弯了,购物车也不推了,惊慌地钻入超市的人流。
这样的作者写的东西,有一点点审美的杂志自然都是看不上的。就连我编给自己看的那本杂志,也瞧不上他的稿子。可那人颤颤巍巍的身形,一直倔强地在我脑子里摇晃,没法擦除。某种恶趣味忽然涌上我心头:我是不是可以编一本专门刊载差稿、烂稿的刊物呢?在这本刊物里,一切标准都是颠倒的:言辞不通、标点混用、错漏百出,所有的表达都饱含着硬邦邦的粗俗和低劣的煽情。这本该是一闪而过的念头,在冒出来后,却再也驱赶不去。很多次,我在自己的窝里,翻看那些我依照自己的趣味编成的世界上唯一一本的杂志,觉得里头所有的表达都太“准确”了,经过我一遍遍校对、排版才最终打印出来的“定稿”,呈现出某种“权威”——虽然这“权威”只属于我。是的,这个世界太正确了,连我从来稿废渣里淘洗出来的东西,也被固有的秩序改正了,闪着理性的光辉。恶趣味不断成长、变大,形成一种滚动的力量,驱使着我。
首先,得选一个刊名。既然是恶趣味,那就彻底一点,叫作“0”吧。《0》的办刊宗旨可以是:”这些胡思乱想让我特别兴奋,我甚至立即开始制作创刊号的封面,我用设计软件所能调出的最黑的颜色,涂了一个圈——那个圆圈太黑了,俨然一个黑洞,能把一切都吸进去,能把一切都化为乌有。至于内容,就简单多了,威胁我们新编辑的那个家伙既然执念深重,那就把他的平仄不通、格律全无的诗词发头条吧。当然不能办成他一个人的专刊,还得有:一个退休老干部逢年过节创作的诗情洋溢的散文诗;一个自称一天可以写两百首诗、至今已经写了八万多首诗的神秘诗人曾寄来一堆诗稿和自荐信,我不发他的诗,只发他的信;一个抱着半麻袋手写稿的阿姨,曾不断跟我们编辑说,她这稿子一发,诺贝尔奖后年就该给她了——至于为什么不是明年,是因为出版、翻译以及诺贝尔奖那帮评委老头读到她的作品还需要一点时间,她的这部巨著《啊!岁月》篇幅太长发不了,三万字的前言是可以发的……我甚至都不用输入,只需把这些稿子挑出,手头有订书机就用订书机、有夹子就用夹子,把它们凑到一起后,把封面一贴,就成了敷衍潦草的一期《0》。封面上那个黑压压的洞,好像就算我把冰箱丢过去也能吞下。翻看这么一本“杂志”的时候,也能挖出某种乐趣来,一字一句惹人笑,所有的错误和不通皆成微言大义。
不知道是碰巧还是我定下的办刊宗旨起了作用,那个年轻编辑再也没有收到“顾城”的骚扰短信。有一次吃饭闲聊时,那年轻编辑还很疑惑:“有这个人?”当时我一愣,心想:不会因为《0》的刊发,那人就从除我之外的人的记忆中删除了吧?这个想法让我有了犯罪的忐忑,可转念一想,就算我拿着那本乱糟糟的《0》去公安局报案,向他们坦白封面上那个黑洞可以吸走内文刊发的作者,他们恐怕也只会建议我去安宁医院,或者根本不搭理我吧。我再细看那编辑的手机,早已不是那款诺基亚了,而是一款翻盖手机——也就是说,编辑曾收到的各种威胁短信,不会存在于这款新手机上。
自从编了一期《0》后,投到杂志社的所有稿子都成了宝贝:可用之稿,被编发到那个有着全国知名度的文学杂志上;正式刊物不能用的,被我分为两类,符合我审美的,被我编到那每年两期的正规刊物的“分身”上;那些让我讨厌甚至恶心的,则是《0》的菜,被我不定期归类,用一个封面捆绑、吸纳、消融于无形。我就像坐在键盘面前删除掉一个个不喜欢的文字一般,在幻想中删除掉那些写出“奇葩”文字的人。有时我想,若是《0》的宗旨真的起了效用,那些作者是多么倒霉啊,悄无声息地成为虚无,与除了我之外的所有人的记忆告别。
我所住的房子是老社长早些年把杂志办得风生水起的时候购下的。那时,文学还是社会上的焦点。在杂志发行的高峰期,为避免拖延刊物面世时间,老社长在三个省的五家印刷厂同时开印,以保证刊物准时发往全国。当年杂志社赚下的钱,老社长用一部分购买了一些房子,后来在各种改革中,有三四套被低价处理给一些老弱病残的员工,我也得以用几年的收入买了一套。这个小区修建较早,已破旧不堪,车位不够不说,位置也不好。我的房子有窗户对着一条河,算是某种程度上的河景房,我曾看过绿草在河边摇曳生姿。可你知道的,流经市内的河水,无论原来有多清澈,最后都会成为臭水沟。在城市改造的过程中,这条河不断变化,记不起从哪年开始,西面窗户正对的河边就安装了一个排污口,每天凌晨四点半排污口准时发出轰响,连玻璃窗和墙壁也隔绝不了。很多个夜里,我被冲出排污口的水吵醒,只好编着那一本本独属于我的杂志。后来,多了一本《0》,乐趣就更多了些。我不好意思说——其实,我也写点文字的,这几乎是每一个跟文字打交道的人都抵制不住的诱惑。这些文字没有人看过,怎么好意思给人看呢?我曾想化名投到我们杂志,然后从编辑的审稿意见上,了解自己写得怎么样,可还是不敢。留着一个人翻翻吧,哪天自己动不了了,就一把火烧掉,干净。
这些妄语怎么能见人呢?我甚至从来没有把它编入我那每年两期的杂志里——人真是蠢笨,写不出自己喜欢的文字,甚至,蠢笨到写下的每一个字都面目可憎。这样的文字只能属于火,火把纸张烧成灰,微风掠过,纸灰化为粉尘。对我来讲,文字的神圣仍然存在,有时看到一篇绝妙的文字,我只能叹息:真是老天爷赏饭吃,是老天爷握着作者的手指,敲下了那一行行文字。可这样的文字,从来不属于我。
有一段时间,我担任编务的杂志陷入了某种说不清的麻烦,无论我们的编辑多么如履薄冰,总还是有“读者”给上级部门写信,说我们杂志出现了各种问题:内容低俗,格调不高……给我们扣上一顶顶大帽子。那些信反馈回来,上级部门让编辑部写自检报告。编辑们头发变白的速度在加剧,他们看稿、校稿的精细程度提升了好几倍,仍没能阻止那些雪花般的举报信。编辑们同情主编,说他的任务就三个:道歉;回答“是是是”“我们一定更加小心”;装孙子。我们也很快知道,所有的举报都来自一人:一个胖乎乎的老人。他退休之后,精力过于旺盛,“想拯救一下破败的文学事业”,就把他关于“养三只小鸡”的八百字“散文”投来了。稿子没被留用,于是老人立志把杂志整垮。他细读杂志上的每一个字,从标点符号里挖掘出作者和编辑十恶不赦的可怕用心——按照他的说法,我们这里不但是卖国大本营,也是反人类的大本营,得装到火箭里射到太空去。他的信不但出现在省里相关部门的案头上,还漂洋过海摆在了更大的领导的办公桌上。他在信里把我们写得如此罪大恶极,让相关部门如临大敌,组织人把杂志一遍遍通读,只读出两吨疑惑与万米不解,没挖出可疑之处。
我们的主编说:“你看,你看,专家们不也跟我们编辑想法一致?”一个领导支招:“天天被折腾也不是办法,你就把他文章发一发,认怂算了。”主编苦笑道:“要是发了就能解决问题,就不会这样了……”其实,主编托人传过话,让那个老人再赐稿三则,好一并刊发之类。据传话的人描述,老人用鼻孔冷冷哼了几声:“杂志版面,是他们用来谈条件的?能发就发,不能发就不能发,我岂是接受招安的人?没我同意发表我的文章,我告死他!”——他还理直气壮了。领导一拍桌子,指着我们主编的鼻子吼:“不管用什么方法,你把这事解决好,再这么闹,一堆人给你们陪葬,那还不如你们早点关门好了……”主编只能点头:“是是是。”
编辑们想了很多法子,甚至有人喊出一句:“要不,我豁出去,把他装麻袋、推海里?”一阵哄笑。这话我倒听进去了,我想到了之前那个“顾城”被我在超市制服的情形——要不,我拎着拐杖,去找那老人谈谈?住所倒是好打听,要见到这人,有机会跟落单的他说上两句,倒也不容易。他从小区出来,拎着一张报纸刚走进旁边小公园的时候,我走了上去:“你认得我吗?”他盯了我好半天,说:“你……是……我不认得。”我说:“不认得就好。我认得你,这些年,你举报信写得挺多的吧?”他说:“举报信,你在说什么?”我说:“有人因为你的举报信被关起来了,托人找到我,让你给个说法……”他说:“听不懂!”我呆了一会,抬出“必杀技”:“那就讲你听得懂的,我看上你的脚了,想让你摘下来……给我安上去。”他喘着粗气:“……你……你……你……”我说:“如果还到处寄信,下次你就得把腿取下,等我来。”我把脸凑过去,几乎要贴到他圆乎乎的脸上,我吹了一口气,他脸色煞白,瘫软在地。
这事之后,杂志的麻烦并没有断——我能想象,那张圆脸上两点绿豆大的眼珠,在放大镜后面不肯眨,深挖着我们杂志上的罪恶。我当然不会真要去把他的腿给卸了——万一扭打起来,我能不能顶住他肥胖的身躯都不好说。我最后的“办法”,是把他的稿子编到《0》里头,想利用办刊宗旨的“诅咒”力量,把他吸入封面上的“0”。可关键是,要找他的稿子,并不容易。我也是花了快一周时间,才翻出他那篇“养三只小鸡”的奇文,幸好,这篇文章还在杂志仓库的废稿堆里。我立即编发,并把那些被转了几道终于抵达编辑部的举报信复印件再次复印,附在后头,编了一本《0》的专刊——这是老人一个人的专号。
好像真的有用。之后的半年里,转过来的举报信变少了,终趋于无。我暗暗惊喜,不再觉得这是巧合,《0》,确实有着抹除的魔力。大约一年之后,无意中打听起这人,有人说他好像生了一场病,在重症监护室里待了一个多月,活是活过来了,却已经不大认识人,对着妻子喊妈妈,对着儿子喊书记。这些传言让我很失望,因为,在最初的设计里,《0》要抹除的不仅是这个人,还有别人对他的记忆;此刻,他人还在,大家都还记得他,这无疑说明,一切都跟《0》毫无关系。我只好安慰自己:会不会这一次没有抹掉别人对他的记忆,而是把他自己的记忆抹除了呢?不然,他何以对着妻子喊妈妈,对着儿子喊书记?
——这难以验证真假莫辨的猜测,让我陷入悲伤。
看到老社长的近况,编辑部的人情绪都不大对。大家回来之后,就开始默默翻看他当年编过的旧刊,虽有一行行印刷文字的确证,虽然这杂志栖身于全国各地图书馆和个人的书架,它却总给人摇摇欲坠烟消云散之感。编辑们还找出老社长当年留下的砚台、笔筒之类,睹物怅然。这一趟拜访老社长之行,编辑部的人都去了,我也跟去了。此前,有时想起老社长,我也会打个车,拎点水果去看看他。但无论我如何推辞,走的时候我还是发觉自己从他家拎走了更多的水果,甚至会提着油腻腻的半只鸡。退休多年,他过着隐姓埋名的日子,每有他当年推出来的作家打听到编辑部,希望去拜访他,他一概拒绝。老社长是一位纯粹的编辑,能抵制书写的诱惑,不论在不在编辑之位,都不搞创作——可即便如此,他早年在一些会议上的发言,还是被整理出来,都是一字不可移的好文章。一些作家在文章中写道,老社长往往敏锐地指出某位作家有什么缺陷,又可以把哪个优势发挥到极致,作家心悦诚服。有作家在文章中写道:“这么一个目光如钉子、开口即金句的人,竟全没写作的欲望,这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害怕写下的句子被归类为小说、散文、诗歌或评论,他不屑和那些打内心鄙视的写作者同写某种文体。”退休之后,他甚至没在家里摆放什么书,该打麻将打麻将,该喝茶喝茶,从来不认为多读几本书是多么了不得的事。
我们前去探望的时候,他已经从一场急病里出院一个月。他的身体倒没啥,就是记性特别差,当我眼前迷蒙嘴角泛酸站在他面前,他指着我的腿问:“你……是……来卖拐的?”他是在说赵本山的小品?编辑们跟他谈起当下的杂志状况、话语空间和文学潮流,他听倒是听得仔细,末了却说:“文学?杂志?什么?”面前的四五个编辑,他也对不上号,他老伴在一旁一遍遍重复介绍。到了此时,就不得不跟他告别了,不得不跟与此相关的记忆告别了。他老伴在后面挥手:“走好,走好,感谢大家……”
回到编辑部,编辑们嘴唇发抖,老社长怎么能忘了呢?他当年是这杂志的奠基人、开山者,是国内文学期刊界的一位大佬……怎么就……连他都这样了,我们一期又一期编着这“废纸”,可曾改变了一丁点世道人心?我没加入编辑们的七嘴八舌,我说不出“虚无”之类的词,可想到老社长认不出我,我就觉得腿脚发痛——仿佛当年被压断的位置重被撕裂,一回又一回。最痛的,当然不是身体之伤,而是看到身子不完整的妻子女儿,她们的头脚分离,某个角落还溅射着她们的一摊血、小块肉。她们定格于最好的年龄,而我已老残如斯,若她们隔了这么多年后,再见到此时的我,定然只能喊出:“阿公。”别说她们,我盯着镜子,也很想对着镜子里的人伸手问:“您是?”身心之痛越来越清晰,却又连自己的长相都忘了——我的记性是更好了还是更坏了?
我终于要给自己编一本《0》了,这是属于我的专刊,当然得郑重其事地写几句编前语。当收集工作开始,我才发现,曾在我脑子和手指下诞生又被我遗忘的文字在一点点冒涌,残缺、陈旧的纸张从某个角落里飘来,被遗忘的片段从电脑文档中浮现,它们争相报名,排队向《0》走来。这简直是一项永远没有尽头的工作,可我乐在其中。我给自己定下了一个规矩:“如果有七天没有再翻找出一行文字,那就定稿。”刚开始时,我几乎每天都要接待这些来访的文字,它们呼朋引伴,希望我认出它们,希望我想起写下它们时的表情。勤快的文字来过后,剩下的就是羞怯的文字,它们扭扭捏捏,在我的视线之外徘徊,但总会在七日之内出现。当我七天内没再发现任何文字时,已经过了大半年。望着那些文档和纸张,这就是我的“全集”了吧?
既然是我的专刊,当然不能像那些被我“抹掉”记忆的人那样潦草对待,这些文字得全部录入、排版,给它们一间舒适的居所。这又是一项不小的工程,可我时间那么多,兴趣那么少,它们总有完成的时候。封面纸张也要郑重其事,我专门去与我们杂志社长期合作的印刷厂,找老板要来几十种纸,终于选中一种据说原料极其复杂的特种纸——我倒不是喜欢那种纹理——选它的原因在于,看着这种纸的时候,你没法想象它的原料是什么。也就是说,这是一种丢失了来路和记忆的纸。我还在网上买了我所能买到的最黑的材料,剪了一个圆形——它太黑了,以至于剪刀剪过它,像光刺破深夜。光射上近乎绝对的黑,几乎没有任何反射。
内文装订好之后,我在家里狭小的空间走了好几遍,把摆在书架上的所有“书刊”都取下,手指在书的边缘划过,我得确认,自己仍旧记得它们的每一个细节。我当然没有忘记。好好洗了一个热水澡,水珠在腿上的伤疤流淌,当年的痛仍未减弱。我给自己二十分钟冥想,还有什么事情是遗忘了的?确定记忆清晰、诸事就位,我终于要给这本属于我的《0》装上封面了。我太熟悉这个工序了,固体胶涂抹到哪个位置、什么程度,不需要眼睛来看,只凭手感即可。这么一个重要的时刻,我竟然没有一点激动,太奇怪了。画龙之后,最后的点睛,会让龙飞升——给《0》装上封面,我慢慢摩挲,封面终于完美无缺了,真正的印刷品也没这么完美的品相。我的手掌在封面上轻轻一拍,完工。
我期待那个时刻的到来:《0》编好的瞬间,到底是我的记忆被抹除,还是别人会遗忘我?我会痴痴地回想“我是谁”,还是曾经的熟人投来茫然的目光:“你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