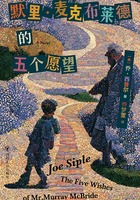
第4章
默里·麦克布莱德
伊利诺伊州,柠檬林
二十年前
又是麦片。我都已经记不清吃了多少天麦片了。大概自珍妮去世后,我每天的早餐都是难以下咽、令人作呕的麦片。但我也不是那挑剔得顿顿都要吃最顶级鱼子酱的人,一直都不是。
我盯着那盒麦片如临大敌。我试着咀嚼、吞咽,而麦片却想凭着索然无味置我于死地。但愿我能战胜它。
今天是我的生日——一百岁大寿。这个日子除了能提醒现在的我孤苦伶仃之外,没什么意义。我没有家人,除了那个很少来看我的白眼狼孙子。我没有朋友,除了便利店那个打了鼻环的收银员——她的鼻环真的很亮,我总是忍不住盯着看。虽然没什么可吹嘘的,但我还是想把我的内科医生,也就是基顿医生,分到朋友这组来。如果我们不是朋友,他没必要坚持给我做生日体检。瞥了一眼表,我可能要迟到了。但这有什么好担心的呢?到了我这把岁数,大家不会抱有很高期望的。
我碾碎药片——只吃一颗就好,不像那些老家伙们每天要吃二十来片药。我把药末和麦片搅拌均匀,慢慢地把它们吞下去。这个过程不太光彩,但我还是在这场战斗中获胜了,所以我大概又得多活一天。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但至少基顿医生会对此感到开心吧。
凌晨四点我就开始梳洗穿戴。人一旦上了岁数,觉就不像以前那么多了。是不是觉得我好像说反了?我这个岁数的老人,只要愿意,应该就能睡上一整天。但我发现我可能是个特例。现在的这些小孩,正处于最绚丽多彩的人生阶段,但却像婴儿一样贪睡。有一次,我亲眼看见一个看起来十二岁左右的小伙子,睡过了整个复活节弥撒。我实在是没忍住,低声骂了几句。那天晚些时候,我去向詹姆斯牧师忏悔,可牧师只顾着哈哈大笑。我不想质疑牧师,但实话实说,我对他这个反应有点不爽。
我家和基顿医生的诊所只隔了两个街区,所以我大概半个小时就能走到那里。他们把我安排在了一个单独的房间。过了几分钟,基顿医生风风火火地进来了,他似乎很高兴见到我。他问我怎么来的,在得知我是步行过来之后,他吓得差点儿蹦起来。“只是走路而已,”我对他说,“要是有一天我连路都走不了了,那我就去见耶稣了。”
我的腿在检查台边上晃来晃去,就像我八岁、三十八岁和八十八岁时在医生办公室里那样。一切仿佛都是老样子。
“非常健康,”基顿医生重复了好几遍,“心脏就像五十五岁的人一样强壮。”
他很善良地略过了我胸腔内这对还在吃力工作的肺。要不是每天早上都就着麦片吃下碾碎的保命药片,它们早就不行了。为了满足我时不时萌生的冒险精神,我有时会准备一些吐司片和果酱。但我最近几乎没这么干过,因为工作实在多得要死。
“二十二号吧。”我不用解释,他知道我在说药的事情。其实,一年半以前我就想停药了,但我不想让基顿医生难过。我不敢去想如果当时真的停药,他会有多难受,甚至可能会把责任揽到他自己身上,怨恨自己。但我是真的想停药了。我早就知道自己活不到新世纪了。如果现在停药,也只不过是活不到1998年而已,没什么差别。
“别拿这种事情开玩笑,默里。”基顿医生说道,“你还记得吗?我们之前谈过这件事。一旦停药,液体很快就会浸满整个肺部,你会在几个小时内窒息而死。你确定这是你想要的吗?”
我真的很想给出一个让他满意的答案,可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发出呼噜噜的气声,可能还偷偷放了个屁。
“工作如何?布兰登打电话来了吗?最近有没有新的拍摄任务?”基顿医生问道。
“相当多,”我说,“几周前有家灯泡公司,还有几个不同品牌的燕麦广告。还有一个,但我想不起来了。哦,洗发水。你敢相信他们居然让我去拍洗发水的广告吗?”
基顿医生正了正领带,忍住了笑意。依我看,医生在工作期间还是应该穿白大褂,这样显得正式得体一些。他盯着我脑袋侧面剩下的几缕头发,问:“他们让你干什么?”
“他们想让我盯着一个头发乌黑茂密的年轻小伙看,拍了一千多张我盯着那小伙看的照片,还让我演得更‘渴望’一些,就好像我多稀罕那个男人的头发似的!然后他们给了我两百美元,告诉我可以走了。要是有人想说服我去死,只用这件糟心事差不多就能让他达到目的了。”
基顿医生举起手投降了。“好了默里,别再拍洗发水广告了。但是听我说,我们给你安排了一些社交活动。你现在的身体状况非常非常好,但是……”他看我的眼神和其他人这些天看我的眼神一模一样,充满了怜悯。
“但是什么,医生?”我略带挑衅地追问他。
“已经过了多长时间了?十八个月?”
我使劲盯着地面,但眼睛还是不经意间透过双焦眼镜瞥到了那面布告栏。基顿医生在上面贴满了圣诞贺卡、婴儿照片,还有人们和自己孙子孙女的合影。这面布告栏就像一片人间圣地。在这里,病人们会和基顿医生分享生活。钉在最上面的照片,是我在世上最美丽的女人的脸颊上留下深深一吻的画面。我和我的妻子珍妮的照片就在这个标题——“当地八十年婚龄夫妇”的正下方。我用力咽了下口水,肯定是早上吃的麦片太干了。“到下周二就整整十八个月了。”
“珍妮肯定想让你开心快乐地活着,想让你有朋友陪伴。她走后,你是不是一个新朋友都没有认识?”
我走到角落里挖了挖鼻孔。我老了,根本没人在意我挖鼻孔这种事。“便利店有个收银员,”我一边说,一边研究手指上的老年斑,“我会盯着她的鼻环看。身后排着长队时,我还会慢吞吞地清点找回来的零钱,但她还是朝我笑。现在大家怎么都不用现金了呢?”
基顿医生忽视了我提出的问题,也忽视了我这番回答。“你知道有专门给退休人员设立的组织吧?或许你可以加入他们,他们每天早晨都在麦当劳喝免费咖啡。你起床很早,七点肯定能到那儿,对吧,默里?”
七点?谁要是能让我一觉睡到七点,找我要什么都行。我不知道怎么措辞才能不顺带把自己也骂了,所以干脆实话实说:“那群人实在太老了。”
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可笑的,但基顿医生一直笑个不停。“那你是想和年轻人在一起?”他说,“一些心理年龄和你一样年轻的人,而非身体年龄。我理解得对吗?”
“最近我心理上也不再年轻了。”我意识到,青春真是……大脑真的不如以前灵光了。振奋,对,就是这个词,青春真是令人振奋。
基顿医生从桌子下面拿出了一个纸杯蛋糕,上面插着一根蜡烛。他点燃了蜡烛,手比我的稳多了。“这根蜡烛,献给我最喜欢的百岁老人。”
真贴心。他其实没必要为我做这些,他可以只花十五分钟给我做一个例行检查,然后去照顾排在我后面的老太婆。但我不一样,我对他来说很重要。可我还是没法使劲挤出一个微笑。
我尽可能地深吸一口气,再一鼓作气把它呼出去,但没能吹灭蜡烛。幸运的是,有几滴唾沫从我嘴里飞出去,正好落到火苗上。“青春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我的声音盖住了蜡烛熄灭的“咝咝”声。
话音飘到窗外,消融在夏日潮湿的空气中。空气潮湿,但也清新,因为柠檬林离芝加哥还很远,足足有二十五英里[1]。
“有个消息要告诉你,”基顿医生终于忍不住说了出来,“布兰登说,自从拍洗发水广告之后,你就再也没给他回过一个电话,不理经纪人是不礼貌的。而且当初是我给你俩牵的线,你现在这样让我很难做。”基顿医生看着我,就像看着一个要被罚站的小孩子:“我不想当你的秘书,但他还是让我转告你,他给你找了一些别的工作,是在一个社区教育中心的美术课上做模特。这可能正是你需要的,默里,就在今天下午晚些时候。”
他递给我一张纸,上面写着大楼地址和房间号。我接过来,塞进了我衬衫前面的口袋。“我会考虑的。”
看到我这个反应,他有些不悦,身体凑过来,两个胳膊肘杵在膝盖上。“好吧,我和你直说了,默里。如果你现在还不做任何改变,那你就会这样可悲又可怜地孤独终老。”
他可真是直言不讳。我更希望他说“你这一生非常圆满”,而不是“你可悲、可怜又孤独”。这些词听着着实刺耳,但也确实激起了我的些许斗志——我很擅长解决问题。但这次的问题有点棘手:像我这样又老又没用的人,怎么可能找得到活下去的理由呢?
注释
[1]1英里=1609.3米=1.6093千米。——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