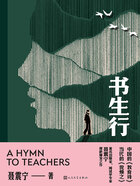
第一章
在荒原上长时间奔跑的夜行列车,最像孤独的奔跑者。
在夜行列车上长时间面朝窗外暗夜的旅客,最像孤独的思想者。
卧铺车厢灯光转暗,旅客已经匆匆就寝。秦子岩却一直独自坐在边凳上,长时间面朝窗外暗夜。
这样的夜晚,这样的时候,他在窗外还能看到什么呢?
他什么也看不见。可是,这时候他只能看往窗外。他想起家乡人常常把一个人独坐无语而久久看向远方的状态称为“狗望大水”——家乡的龙水河夏天涨大水,时常能见到有大狗端坐在河岸边的悬崖上,一动不动,面朝大河,若有所思——这时候觉得自己真有点像“狗望大水”,心中不禁自嘲地一乐。
一九六三年的特快列车,车厢降温设备是藏在车厢顶棚上的电风扇,客车停靠车站时风扇才会开启,列车行驶中车厢的降温只能靠打开车窗,让自然风吹进车厢来帮助降温消暑。
秦子岩坐在面朝列车行进方向的边凳上,让猛烈的夜风吹。九月广西的夜风还带着明显的暖意。尽管如此,一般旅客坐在秦子岩这个位置,还是会把车窗放下来一些,避免脑袋伤风。可他却任凭车窗半开,让暖风吹拂,觉得如此这般才淋漓痛快。车疾风大,浓密的长发被吹得全都后倒,那情状像是一个骑士驱马狂奔。很快就有列车员前来干预,说是这么大的风会影响到入睡的旅客,一边说一边把车窗降到进风很小的高度。
秦子岩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助教——严格地说,两天前他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助教,现在,他只能是原助教。再过不到半个小时,列车就要停靠在他的家乡沂山县,明天,最迟不过后天,他将成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沂山县第一中学的教师。此刻,他不敢再睡。不敢再睡并不是因为近乡情怯,而是马上就要下车。其实,他也算是睡够了的。从北京站出发后的四十个小时里,除了吃饭喝水上厕所,其余大多数时间他都在上铺安静躺平,似睡似醒,时睡时醒,东想西想,真睡假寐。只是在汉口站和武昌站两次停车,他两次下到月台上散步,说散步其实也只是徘徊几步,停在月台边上,朝车站外面无目的地眺望。他想,武汉这个城市真好,特快列车可以两次停车。
四年前,在武汉大学珞珈山下樱花开放的时节,他初见一个让他怦然心动的女学生,后来那女学生成了他的妻子。而已经成为他妻子的那个女学生此时正在距此千里之外的沂山等候他。武汉大学在武昌,可是车停汉口站,他就迫不及待地下到月台上徘徊,觉得毕竟已经到了武汉的地面。车行片刻,又停武昌,他更是立刻下到月台远眺,仿佛如此这般才算是贴近了一点自己的妻子,重温当年初见的激情和几年来守盼的念想。
要不了多久,秦子岩此行的目的地沂山站就要到了。特快列车在县级车站只能停靠五分钟,下车的旅客必须提早做好准备。他的铺位是上铺,上下不便,尤其是行李架上堆着一只超大的被褥包袱和两只皮箱,在北京上车时全靠两个学生送站,眼下却是独自一人孤军奋战,他盘算好了,停车前他必须分两次把行李移动到车厢门口。
列车奔跑在广西西北山区。傍晚车过桂林,从车窗里望出去,暮色苍茫中,山峰远远近近,典型的喀斯特地貌,险峻、秀丽、奇崛,造型奇奇怪怪,像是各种动物卖萌。车厢里就有来自北方的旅客啧啧赞叹,赞叹中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桂林山水甲天下”,有时尚的人即兴哼唱起在全国各地电影院热映的电影《刘三姐》里的插曲《山歌好比春江水》。车上的广播很是配合,及时播放这首插曲。一时间,车厢里熙熙攘攘,说说唱唱。然后人们各自吃上两角钱一份的盒饭,然后喝水闲聊,然后熄灯上床,然后渐渐静默。
车厢静默,能够听到车轮与铁轨发出强有力而单调的摩擦声。车窗外的山野已被夜色遮蔽。一弯新月挂在远处山顶,连片的参差山峰一片黢黑,肃穆矗立。
夜行列车,孤独地奔跑,不倦地奔跑,偶尔发出几声孤独的汽笛声。
这是公元一九六三年九月中旬的一个夜晚。
秦子岩知道,列车应该已经驶入沂山县境内,通过三个小站就是沂山站,他依序默念三个小站的站名:三合站、岭东站、岭西站。作为道地的沂山人,这些小站名他很是熟悉,是那种亲切的熟悉。他终于回到故乡并且从今往后将长久地在这里生活了。秦子岩上小学时,父亲患大肚子病(血吸虫病)去世,那时他还懵懵懂懂,就成了村上老人们哀叹的“孤寒仔”。母亲身强体健,是村里的砍柴高手,靠着砍柴和种地,含辛茹苦供他读书,一直上到北京的大学。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母亲被派往公社的钢铁工地劳动,因为她身强体健,因为她是刚刚成立的生产队妇女队长,因为妇女能顶半边天,她被派去跟几个男子汉一起做炉前工,结果,土法上马的小高炉坍塌,几个炉前工全部遇难,秦子岩就从“孤寒仔”成了孤儿。等到秦子岩接到这个噩耗赶回沂山县,已经是半个多月后,母亲已经成了他父亲坟旁的一座新坟。一九五八年,北师大教育系二年级劳动委员秦子岩,先是系里学生中“除四害运动”的标兵——所谓“四害”,指的就是老鼠、麻雀、苍蝇、蚊子,全国各地齐动手,不除四害不罢休。作为最擅长打老鼠的广西农家子弟,秦子岩轻而易举地在灭鼠斗争中大显身手,头一个月他就灭鼠八十八只,夺得全北京市高校“除四害”第一名;后来他又作为北师大大炼钢铁的主力,日夜奋战在一百公里外的密云山区的钢铁工地上,接到公社发来的加急电报时,距离母亲遇难已经整整过了两个星期。
人们通常将一个人回往故乡生活称作“叶落归根”,可秦子岩却不是。这里已经没有了他的亲人,也就没了根的感觉。何况,他还很年轻,距离老之将至而念想故旧的岁月还差得很远。北师大毕业后他留校任助教刚满三年,正是枝繁叶茂的青春季节。他之所以叶没落却也归根,放弃了在一家全国著名高校的美好前程,完全是为了信守承诺回到自己妻子的身旁。
近一个月来,秦子岩要调回广西老家的消息,在北师大教育系差不多成了一个热门话题,几乎所有听到这消息的人都会问“为什么”。调回广西老家,为什么?调回广西的一个县城中学,为什么?在北京许多人的印象里,广西已经足够偏远,而足够偏远的广西一个以前听都没听说过的沂山县,又是一个多么遥远、多么荒凉、多么让人难以想象的地方!而且,他可是全国著名大学的一个老师,当时说是天之骄子一点都不过分。可是,就因为妻子调不来北京,他就放弃了眼下的一切,太可惜了,太应当给予巨大的同情了。
其实,秦子岩不需要同情,或者说他从来就不习惯被人同情,更不要说什么巨大的同情。大一刚开学时,他申请的人民助学金还没有发放,身上剩下的钱不到两块,他一点都舍不得花,在食堂吃饭也只敢买几分钱一份的大白菜。一次,来自广州的一位舍友跟他在一张餐桌上吃饭,动了同情心,佯称“今天食堂师傅肉给多了,来,帮帮忙”,说着就拨给他两块鸡肉。“不用!”他的反应十分激烈,而且猛一下抽开饭盒,刚刚拨过来的一只油汪汪的鸡腿掉到地上,弄得周围的同学很是惊讶,觉得挺可惜。广州舍友一脸尴尬,只好苦笑摇头。可秦子岩并不觉得可惜,迅即起身走开了。这就是秦子岩!这就是不习惯接受别人同情的秦子岩,这就是大学一些高班同学开玩笑称他“小广西”的秦子岩,这就是当学校人事处处长张军第三次告诉他妻子调京无望后断然做出调回家乡广西决定的秦子岩!
人事处处长张军是位转业军人,据说官至团级,四十岁上下的年纪,生就一副端端正正的面孔,一张国字脸很像当时国产电影战斗故事片里的我军指挥员,让秦子岩觉得很像标准的领导干部。他永远穿一身褪色的军装,风纪扣永远扣着,胸膛永远挺着,举止永远孔武有力,说话永远有板有眼:“总而言之,言而总之,秦老师,您的困难我们完全理解,可是国家的政策您也要理解。当前国民经济正在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调整’摆在首位,机关单位都还在精简机构,继续动员城市人口下放到农村去,怎么可能外地农村的人还返回城市呢?而且是首都北京呢?对对,我知道,您爱人在县城,不是农村,可是对于调入首都北京,其中差距也就差不多啦。这么说吧,您妻子要调进北京来,不要说是从广西的一个县调来北京,就是从广西的南宁、桂林调来,只要不是国家工作的直接需要,目前的情况还是毫无可能的。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只要政策允许,我们一定给您办,连夜都要给您办;政策不允许,我们也毫无办法、爱莫能助呵。”
其实秦子岩心里挺喜欢张处长的国字脸,也喜欢他永远挺着的胸膛。子岩自己也永远穿着褪色的蓝色中山装,不过他永远不喜欢扣风纪扣,也不喜欢言行举止太过于有板有眼。他叹了口气,说:“张处长,谢谢您跟我把情况说明白了。看来不要耽误大家的时间了,既然我爱人不能来,那我调过去,政策总归是允许的吧?本来大学毕业时我也给系里打报告要求分配回家乡,我的志趣至今没变。好吧,我请调去广西!”张军处长没想到这位青年教师竟然如此迅速做出人生重大决定,一时愕然语塞。他一面同情地打量因为绝望而面庞涨红的秦子岩,一面冷峻地不置可否地轻轻摇头,以为年轻的秦老师说的是气话。他们教育系这一届二十多名毕业生,差不多都留在了北京,但大多数去了中小学任教,留在大学的很少,而留校做助教的更少,怎么可能说不做就不做了呢!作为人事处处长,当然也作为曾经的团政委,这时他要做的不是火上浇油,而是劝其冷静:“冷静冷静,秦老师,您不要急着做决定。在重大事情面前要冷静,一定要冷静!秦老师,您各方面都表现很优秀,北师大教育系也是很需要您的。”
其实,秦子岩日思夜想的是早日跟新婚不久的妻子团聚。毕业时他可是态度坚决地要求回到边远的少数民族家乡去,回去建设落后的家乡,“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当时别人并不知道他的未婚妻在那儿。他曾经海誓山盟地承诺毕业了一定回去,回去跟她结婚。结果秦子岩还是被留校了。留校的同学大都欢天喜地,可他却悄悄跟系主任说了他需要回去跟未婚妻结婚。系主任大不以为然,说:“没问题呀,毕业了你就回去结婚,我让系办公室给你开证明,然后,把她调到北京来,做什么工作就不用你操心了,我说话算话!”秦子岩觉得系主任倒也是指了一条光明大道,倘若妻子能进北京,妻子所钟爱的图书馆事业一定会有大的发展。总而言之,只要夫妻两人能在一起,只要不把妻子一个人留在那遥远的沂山,怎么办都行,何况是调来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
系主任的安排当然很好,可系主任也只是囿于大学校园里的一个迂夫子,基本上不懂行政人事管理那一套。后来还是秦子岩在学校人事处处长那里才明白此事“毫无可能性”。对秦子岩来说,尽管留在北师大将有远大前途,可是如果失去了妻子的信任,特别是失去了爱妻的爱,那么,再远大的前途对他来说都没有意义——尽管妻子对于自己独守空房从无怨言,来信说的全是学校图书馆工作的点点滴滴。他来来回回冷静地想过,直到有板有眼的人事处处长明确告诉他“毫无可能性”后,他才有板有眼地表达了出来。这些天,他脑子里时时浮现出“天涯何处无芳草”一类带有无奈情绪的诗句,时时又想起“青山处处埋忠骨”一类悲壮的诗句,最后让他心情平复下来、决绝下来的还是“一种相思,两处闲愁”的缠绵悱恻和“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的旷达心情。他喜欢文学,尤其迷恋古典诗词,上大学他之所以进教育系而没有进中文系,只是因为高考总分不够,只好退而求其次的缘故。因为喜欢文学,也就导致他的思维容易偏向感性。“诗人气质!”广州舍友这样说他。比如,那次广州舍友匀给他一只鸡腿,当时,他一面下意识地拒绝,一面也想起了“廉者不受嗟来之食”的古训。
从人事处回来,秦子岩当即分别给妻子和沂山一中老校长写信,而且寄的是航空信——尽管那时航空信最快四天才能从北京到达沂山,可毕竟要比平信快上一天——可见他性子急、意志坚定。
很快,秦子岩也收到了两人及时的回应——也是航空信——看来两边都是急性子、意志坚定。妻子的回信只抄了两首诗词,一首是南唐后主李煜的:“一重山,两重山。山远天高烟水寒,相思枫叶丹。 鞠花开,鞠花残。塞雁高飞人未还,一帘风月闲。”一首是唐人李商隐的:“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末了加了一句陶渊明的名句:“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秦子岩展信一看,止不住心头一阵发热,想两个人不约而同想到了陶渊明的句子,觉得有趣,勾起了夫妻情爱的回味,不禁微笑。老校长的热情当然也在秦子岩的预料之中。老校长在信里写道:“子岩同志:沂山需要你,一中需要你!我相信,你调回沂山一中,必将成为我校发展史上一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大事。”秦子岩想,如此这般,于公于私,夫复何求!当即铺纸写下请调报告,请求调回他的母校广西沂山县第一中学。“这样既可以解决夫妻两地分居的困难,不再给组织上添麻烦,也能为少数民族地区同时又是边远山区党的教育事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他在报告里写道。既实实在在,又体现理想抱负,相当符合一个党员青年教师应有的思想觉悟,无可挑剔。
后来的两个多月里,自然是少不了的各种谈话、各种惋惜、各种挽留。张军处长还特意到秦子岩的宿舍看望他,一再叮嘱他今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可以跟学校联系,跟他联系。“秦老师,您是北师大的优秀毕业生,也是优秀教师。北师大就是您的家!记得常回家看看!”接着又补充了一句,“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可以请家里帮助!”
一个正正板板的领导说了这一番暖情暖意的话,感动得秦子岩差点落泪。
又是两声孤独的汽笛声。在大山之间,火车的汽笛声显得突兀而空洞。
一直对着窗外暗夜愣神的秦子岩,忽然想到和妻子分别大半年了,想到她那柔软的身躯和那柔到骨子里的说话腔调,尤其是那一双时时供他抚摸欣赏的纤纤玉手,不由得心头顿时一热,继而,觉得浑身上下都温热起来,隐隐觉察到一个青春男人的欲望又在涌动。
长期的单身生活,已经让秦子岩练就了一些冲淡欲望的办法。他马上用两只手掌贴在冰冷的车窗玻璃上,用冰冷的玻璃降低身体的热感,这是他自嘲的“物理干预法”;或者转念去想别的事情,背诵几句古诗词,或者去想一些需要理性思考的事情,这是他自己命名的“心理转移法”。
这样,他就努力去回想起离开北师大前的点滴事情。
几天前,准确地说,就是四天前,秦子岩终于在北京站排队购得火车卧铺票,兴冲冲回到新街口外的北师大东门,迎面看到系里的讲师郭远明低着头走来。郭老师一副踽踽独行的样子。
子岩知道郭老师近来心情不好,因为前不久整个教育界忽然开始了严厉批判母爱教育的运动,差一点儿要殃及他。批判的起因是一九六三年五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斯霞和孩子》一文,介绍南京师范大学附小著名教师斯霞以“爱心”爱“童心”,文章认为儿童不但需要老师的爱,还需要母爱;教师要像一个辛勤的园丁,给我们的幼苗带来温暖的阳光,甘甜的雨露。可是几个月后,北京的教育界忽然掀起了一场关于母爱教育的讨论和批判。斯霞的名字忽然变成了舆论的焦点,批判的声势比较大。国内各大报刊如《人民教育》等同时刊发了一系列文章,提出必须和资产阶级教育划清界限,认为所谓母爱教育,就是资产阶级教育家早就提倡过的“爱的教育”,这涉及教育有没有阶级性,要不要无产阶级方向,要不要对孩子进行教育,教育要不要在孩子思想上打下阶级烙印这些重大问题。有意思的是,郭老师早前在附中参加教育实践时曾经提出过“没有爱就没有教育”的观点,主张对个别缺少母爱的同学要给予更多爱、更多温暖,而且也取得了一些明显的教育效果。主管附属中小学的师大副校长知道了,认为很好,还特别建议郭远明把教育实践中的体会写成文章发表。郭老师素来爱教课爱行动,却不太勤于写作,还没来得及写成文字,忽然就爆发了声势很大的母爱批判运动,不太勤于写作的习惯却帮助他逃过一劫,没有撞到枪口上。可是,没承想,系办公室一位中年女干事却在餐厅吃饭时大声跟人议论,说郭远明老师就曾经主张母爱教育,这回恐怕也要受到批评了。秦子岩刚好跟她是邻座,立刻打断道:“您这可是犯了一个逻辑错误哦!”女干事一愣,不晓得自己犯了什么逻辑错误,有点骇然,说:“哦哦,秦老师我晓得你是逻辑大王咧,你说我犯了什么逻辑错误?”秦子岩道:“您犯了一个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报纸上批判的是资产阶级的母爱,咱们郭远明老师讲的是无产阶级的母爱,并不是一个概念呀,难道您要批判无产阶级的母爱?”同桌吃饭的几个老师也都微微点头表示有道理。不用说,秦子岩在逻辑上是弄了一点手脚,玩了一把偷换概念的游戏,当时报刊上依据的理论认为所谓母爱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概念,这种理论并不承认无产阶级有母爱。可是女干事反应不及,准确说来,她对所谓母爱教育本来就不曾有过认真的学习了解,身为母亲的她却要跟着批判母爱教育,其盲目程度实在匪夷所思。要扭转因无知而造成的盲目跟风行为,比较有效的办法是尽快树立起知识的大旗——秦子岩如此一说,女干事便不再往下说,反而朝秦子岩竖了一下大拇指,红着脸表示佩服。
秦子岩从心底里并不认同报刊上把母爱这个概念送给资产阶级的做法,他认为无产阶级一定有母爱(最有力的依据就是新中国很多读者当时非常崇拜的苏联作家的名著《母亲》,作品中就有相当深厚的无产阶级母爱),同时他也明白在当时这不是可以公开讨论的问题,为此他赶紧找到系总支书记,建议系领导要注意保护郭老师,特别是要警惕某些人因为无知跟风或者为了私利而加害于郭老师。书记是一位来自延安陕北公学的老革命,经历过延安整风运动,在政治上经验十足,对颇富正义感的秦子岩点头赞赏,明确表示决不会被个别人的议论所左右,同时也叮嘱秦子岩此时此地无须再谈母爱。事情过去后,不晓得郭老师如何知晓此事,他私底下向秦子岩表示过感谢,同时也无可奈何地叹息。
批判母爱教育,北师大教育系虽然有惊无险,却也让非常信奉母爱教育的郭远明老师心情压抑。五十年后,已经是全国著名教育家的郭远明先生在一部回忆录里回忆道:“好在我那时人微言轻,说过母爱教育这样的话,系领导表示没有产生不良影响,不加追究,算是逃过一劫。”其实,也好在有一个同样人微言轻却敢于仗义执言的秦子岩,还有,好在系领导稳妥把握,否则,郭远明能不能逃过那一劫还不好说。
在校门口,郭远明猛然抬头见到秦子岩,很是意外,一面与他握手,一面操着明显的江苏常州口音关切地问道:“秦老师,笃定是要调回广西老家了?”神情和口气里满是遗憾和不舍。
我们知道,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前,我国大多数地区的交通条件都相当落后,以至于亲朋好友一旦分别去远方,不说是犹如生离死别,也往往有“西出阳关无故人”的离别之苦和悲怆慨叹。那年月,在火车站,我们常常会看到有人挥泪告别的场面。尤其是在站台上,有时车上车下的人都挥泪不止,甚至列车启动时车下送行的人还不由自主地哭着追送列车。而现如今,许多大城市之间都有“夕发朝至”和“朝发夕至”的列车,更不要说神速一般的高铁动车,坐飞机也是家常便饭,倒退回去五六十年,真可以称得上是“匪夷所思”。知道秦子岩即将离去,极富爱心的郭老师,免不了离愁别绪;何况不久前两人还有过一番道义之交,郭老师自然遗憾,表示同情。
可是秦子岩并不习惯接受别人的同情,而更喜欢表示自己一切都好。于是他做出洒脱的样子,用俄语回答道:
“Да, да.Вы правы, все верно.(是的,您说得对。)”
郭远明曾经在苏联国立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教育系留学五年,一口纯正的莫斯科口音,秦子岩和一些羡慕留苏的青年教师有事没事总喜欢跟郭老师念叨几句俄语。秦子岩这时故意用俄语来婉拒郭老师的同情,其实也就是躲在俄语后面回避对方的同情。
郭远明当即用俄语很是动感情地回应:
“Как жаль!(太遗憾了!)”
“Не беспокойтесь, все будет хорошо.(别担心,一切都会好的。)”上学时秦子岩俄语经常得满分五分,跟郭老师来一点寒暄没有问题。
郭老师加重了握手的力度,双眼涌出惜别的情绪,郑重道:
“Огромное спасибо вам за все, что вы для меня сделали!(非常感谢您为我所做的一切!)”
虽说是寒暄,郭老师发自内心的感谢秦子岩当然感觉到了,忽然想到就此要跟值得尊敬的郭老师分别,心里难过,轻声回道:
“Пожалуйста, не за что.(没什么,不用谢。)”
郭远明用一种“尽在不言中”的表情回应:
“Всего хорошего!(珍重,一切都好!)Счастливого пути!(一路顺风!)”郭老师用力握着子岩的手,动情说道,“Mой драгоценный друг, всего доброго!(我亲爱的朋友,再见!)”这个回应不仅有再见的意思,还含有“一切顺利,一切都好,慢走,走好”的意思。
车头传来一声长鸣,打断了秦子岩的思绪。
秦子岩在车窗玻璃的映照下发现身后站着一位绿衣少女的身影。这是那位在桂林站上车、睡在中铺的姑娘。姑娘身着淡绿色长袖运动衫,胸前印有“广西师范学院”几个红色大字。她身材丰满,很容易让人误以为她身上的运动衫尺寸小了一点,当然,也很容易让人觉得姑娘青春活力四射。绿衣少女的同伴是一位比较瘦弱的小伙子,看样子两人关系是同学或者同事。小伙子穿的是褪了色的蓝布上衣,面容清癯,神情腼腆,看上去像是有点儿营养不良——在那个年头,到处都能看到营养不良的人,只是这个小伙子在身材丰满的姑娘身边越发显得瘦弱罢了。秦子岩在一旁观察,觉得这绿衣少女娇憨活泼,开朗豪爽,跟她的同伴大声说话,跟秦子岩他们几位旅客随意寒暄,言行举止有点儿不拘小节,颇为有趣。不一会儿,秦子岩就弄明白了,绿衣少女来自金丹县教育局教研室,那瘦弱的小伙子则来自天湖县,都是去桂林参加教育会议的。两人都是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的,去年刚毕业。“所以,”绿衣少女说道,“一回到师院,就觉得还在上学,上了火车还以为是放暑假,有点像做梦。”她咧嘴笑了笑,露出保护得很好的一口细米白牙。有意思的是,绿衣少女竟能很快套问出周围几个旅客的来历,一个是昆明卷烟厂的采购员,两个是贵阳钢铁厂的技术员,都是从北京出差回来,这是此前几位旅客互相之间都不曾打听过的信息,全让她一阵风似的搜罗了出来。秦子岩也未能幸免,姑娘不仅弄清楚他来自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而且还知道他是教育系的助教。
“啊,北师大!大教授!”她像有了巨大发现一般地惊叫道。
“哎呀哎呀,我只是一个助教。”秦子岩惊慌失措地解释道,仿佛是自己刚才无耻地撒谎吹牛了一样。
“没有助教哪来的教授?提前叫你大教授!”绿衣少女不管不顾地径自强调道。
秦子岩赶紧说:“您可犯了逻辑错误!”
“噫,什么逻辑错误?”娇憨活泼的女孩听说是逻辑错误,先就吃了一惊。
“以偏概全呀。你不能因为大学里有教授就把大学里所有老师都当作教授,还有副教授、讲师、助教,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助教。”
绿衣少女在逻辑面前哈哈一笑:“这个我当然晓得,我们广西师院也有教授的呀!”言下之意算是承认称他为教授不过是调侃而已。
“大教授,快到你们沂山县了啵!”绿衣少女一面说着,一面坐到秦子岩对面的边凳。
“是的。”秦子岩晓得人家是决心把调侃进行到底的了,不如由她去,笑了笑,说,“您怎么不睡了?”
“您您您,我就喜欢听北京话里的您!”
秦子岩作古正经道:“您还早吧?还要三个多小时才到你们金丹县吧?”
“你不是要下车吗?送你呀。”
“哦,不用不用,不用送!”
“你们沂山县好哦,沂山的风景好,都说是小桂林。我们金丹县,都到云贵高原了,真正称得上是云雾山中呢。”绿衣少女叹了口气回答道,忽然有点儿自嘲地说,“告诉你一个笑话。说到沂山县、金丹县、天湖县、青城县这些地方,经常有外省大学生闹笑话。有的大学生分配到广西教育厅,听说要派去你们沂山县工作,都不高兴,他们认为地名有山的地方肯定就是山区,说到要去金丹县、天湖县、青城县就觉得好,地名有诗意呀,像是城市,都高兴。结果,在柳州上火车,才发现是先到沂山县,去青城县还要从沂山县坐两个小时的汽车,坐火车过了沂山还要三个多小时才到金丹县,一下就泄气了。更不要说分到天湖县工作的人了,到金丹站下火车,还要坐班车在大山里跑一天,都气晕过去了。”
秦子岩觉得有趣,微微笑了笑,揶揄道:“您去那里工作,也是奔着金丹那个富有诗意的地名去的吧?”
绿衣少女噘了噘丰润的嘴唇,说:“我爸就在金丹县工作,是他把我要回去的——不过,你说对了一点,当年我爸从部队转业到广西,沂山和金丹这两个县,他一眼就看中了金丹县,莽莽撞撞就提出要去金丹县,后来我们全家都埋怨他,一去五六年,现在才有机会调出来,成了我们家笑话的保留节目。”
“准备调去哪里?”
“沂山呀。可笑不可笑?”绿衣少女回道。她忽然想起了什么,赶紧问道:“大教授这次是回沂山探亲?”
秦子岩微微点头,不置可否地笑笑,无言以对。他当然是不会做交浅言深的事情。
就在这时,车厢灯光突然大亮,车厢里的电风扇顿时开启。列车员慵懒地哼哼着招呼:“沂山站就要到了,下车的旅客请提前做好下车准备哦!”然后又补充最重要的一句,“不要拿错别人的行李啊!”沂山站是个县级站,卧铺车厢上下车的旅客不过一二,列车员喊得有气无力的。
秦子岩赶紧起身去行李架上取自己的行李。绿衣少女立刻起身过来帮忙,说“我送你下车”,一副侠肝义胆的样子。秦子岩吓了一跳,一面连声称谢,一面赶紧阻拦绿衣少女碰自己的行李:“谢谢谢谢!怎么能要您女同志帮忙呢?”
场面有点乱。
那瘦弱的小伙子也相跟着从卧铺上下来,一旁幽幽地打趣道:“没事,帮这点忙算什么!她就是爱两肋插刀。你不晓得,她是我们师院有名的玛格丽特!”
秦子岩知道小伙子说的是绿衣少女的绰号,可是一个中国女孩的绰号怎么会是玛格丽特这么一个欧洲女人的名字呢?说的是哪部小说里的玛格丽特呢?是《红与黑》还是《茶花女》?
秦子岩原本打算自己夜间悄悄下车,不惊动别的旅客,没想到竟然被玛格丽特折腾了这么一通。他气息刚刚喘定,列车进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