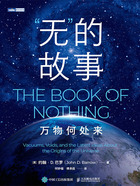
序言
决定一本书的开头,犹如确定宇宙的起源一样复杂。
——麦克拉姆(Robert McCrum)
“因为它不存在”——这也许是撰写一本“无”(nothing)之书的充足理由,如果作者已经撰写了一本“万物”(everything)之书,那么尤其如此。然而,幸运的是,有比这更好的理由。如果我们察看一下那些特殊问题(它们曾是人类沿着最古老和最执着的探究之路前进的主要动力),就会发现“无”,它恰当地伪装成某种东西,从不远离事物的核心。
“无”有着各种各样的伪装,几千年来它一直是一个魅力经久不衰的论题。哲学家争取理解它,而神秘主义者梦想他们能想象它;科学家力求创造它;天文学家徒劳地寻求确定它的位置;逻辑学家对它望而生畏,神学家却渴望由它召唤出一切;数学家则达到了目的。与此同时,作家和爱开玩笑的人乐于竭其所能,激起对“无”的无谓的纷扰。沿着所有这些通向真理的小径,“无”作为某种意料不到的关键性事物而出现。基于它,许许多多的中心问题得到了仔细考虑。
在此,我们将集中描绘我们关于“无”的认识是如何影响知识增长的。我们将看到,古代西方人对逻辑学和分析哲学的沉溺,如何阻碍了他们发展到一个很有成效的图景:“无”作为某种事物,可以是我们对所见事物所作解释的一部分。与此相反,东方哲学家则具有这样一些思维习惯:“‘无’是某种事物”的观念很容易把握,而且它在其衍生物中不仅仅是消极的。从这简单的第一步开始,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对人类来说的巨大跃进:通用计数系统(counting system)得到发展,它可以向前和向上演进为现代数学的各个深奥领域。
科学上,在对实际真空(vacuum)的可能性、必要性和地位进行曲折争论的一千年当中,我们会看到对制造一个实际真空的某些追求。这些想法塑造了物理学和工程学中许多领域的未来发展方向,同时也使得哲学和神学上对真空——物质上的“无”——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争论发生了改变。对神学家来说,这些争论在某种程度上是“宇宙必须从一个既是物质上的也是精神上的‘无’之中被创生出来”这一关键论点的继续。可是,对于大哲学家们来说,这些争论只不过是关于事物最终本质所提出的考虑欠周的问题的特例,它们正在逐渐声名扫地。
一开始,诸如“无”的意义这样的问题看上去很难,它们显得无法回答;其后,它们又显得毫无意义:关于“无”的问题并不是关于“任何事物”(anything)的问题。然而,对于科学家来说,真空的制造看起来具有物理上的可能性。人们可用真空做实验,并可将其用于制造机器:这是对它的实在性的一个严峻考验。不久,这种真空似乎不可接受了。出现了这样一幅图像:宇宙充满着一种无处不在的以太流体。不存在“空空间”(empty space)。万物通过以太运动,万物受到以太的作用。以太是万物漂游其中的海洋,这保证了宇宙的每一角落或缝隙都不是空的。
这种幽灵般的以太是持久不变的,需要一个爱因斯坦把它从宇宙中清除掉。但是,当一切可清除的东西都被清除掉以后,所剩下的仍超过他所意料。相对论和量子论相结合产生的洞察力揭示了惊人的新可能性,它们把现代天文学中最重大的未解决问题呈现在我们面前。最近几十年来,人们逐渐明白,原来真空甚至比爱因斯坦所能想象的更为不同寻常、流动性更大、空虚程度更低、不可捉摸程度更小。在各种自然力作用于其上的那些最小和最大的空间范围内,它的存在也同时被感知。仅当发现了真空微妙的量子效应时,我们才能理解,各种不同的自然力在由物质的最基本组成部分聚居着的沸腾的微观世界里是怎样统一起来的。
天文世界同样屈从于真空的性质。现代宇宙学依据真空的特殊性质构建了关于宇宙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主要图像。唯有时间将告诉我们这种构建是否建筑在散沙之上。然而,我们也许不必等待很久。现今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天文观测,似乎正在通过宇宙真空对宇宙膨胀的影响揭示宇宙真空。我们还指望其他实验能告诉我们,真空是否如我们所猜测的,在近 150 亿年前完成了某些有力的动作,把宇宙安置在一个特殊的过程之中,正是此过程导致宇宙成为现在的样子,并变成它最终将变成的那个样子。
我希望这个故事使你坚信,存在着远比所见到的多得多的“无”。如果我们要了解我们是怎样来到这里,怎样像现在这样思考的,那么对“无”的本质、特征,以及它既能突然变化又能缓慢变化的倾向有一个正确的理解是很重要的。
全书各章首页章数旁边的头像,是玛雅人美妙的头像变形数字的复制品。它们代表了一系列著名的男女神灵,曾在 1500 多年前被玛雅人广泛应用于记录日期和时间间隔。
我要感谢比恩(Rachel Bean)、博舍尔(Malcolm Boshier)、达布罗夫斯基(Mariusz Dąbrowski)、金格里奇(Owen Gingerich)、亨斯根(Jörg Hensgen)、海因兹(Ed Hinds)、卡克(Subhash Kak)、林德(Andrei Linde)、洛根(Robert Logan)、马盖若(João Magueijo)、里斯(Martin Rees)、萨穆特(Paul Samet)、谢拉德(Paul Shellard)、苏尔金(Will Sulkin)、泰格马克(Max Tegmark)和维连金(Alex Vilenkin)在不同时期所给予的帮助和讨论。谨以本书纪念西阿玛(Dennis Sciama),假如没有他的早期指导,无论是本书还是我几十年间的一切其他著作,都不可能面世。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经历了一次搬家和三次办公室搬迁。在面对所有这些真空状态的变化时,我要感谢我的妻子伊丽莎白,她向我保证:有一点终究比无强。我也要感谢我的儿女戴维、罗杰和路易丝对整个写作计划所提出的无数疑问。
约翰·D. 巴罗
2000 年 5 月于剑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