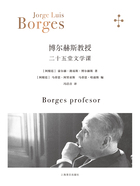
第一课
盎格鲁——撒克逊人 日耳曼国王的谱系 诗与隐喻语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四日,星期五
英国文学始于七世纪末或八世纪初,我们现有的最早期作品就出自那个时代,时间早于任何其他欧洲文学作品。在最初的两个课程单元中,我们要讨论这种文学:盎格鲁——撒克逊诗歌和散文。为了学习这些课程的资料,你们最好参考我同巴斯克斯女士合著的《日耳曼中世纪文学》1,由法尔博书人出版社出版。在继续讲课之前,我要先说清楚这门课的出发点是文学,只有为了理解课文需要时才会参考经济、政治和社会背景。
现在我们就开始第一课。我们将讨论史诗和盎格鲁——撒克逊人,他们是在罗马军团离开不列颠群岛之后到来的。我们谈的是五世纪,大约为公元四四九年。不列颠群岛是罗马最遥远的殖民地,位于最北边,一直到加勒多尼亚,也就是今日苏格兰的一部分,都被征服了,当时这里居住着皮克特族,他们是起源于凯尔特的民族,哈德良长城将其与不列颠其他部分分开。南边住着凯尔特人,他们皈依了基督教,还有罗马人。在城市,受过教育的人说拉丁语;低阶层人说各种凯尔特方言。凯尔特人是居住在伊比利亚、瑞士、蒂罗尔、比利时、法国以及不列颠的一个民族。他们的神话毁于罗马人以及野蛮人的入侵,除了在威尔士和爱尔兰之外,那里还保留着一些残余。
四四九年,罗马崩溃,军团撤离不列颠,这是非常重要的事件,因为这个国家失去了赖以生存的保护,很容易受到北部皮克特人和东部撒克逊人的攻击。撒克逊人被视为强盗部落联盟,因为塔西佗在他的著作《日耳曼尼亚志》中并没有称其为“民族”。他们属于“北海日耳曼语系”,与后来的维京人有关系。他们居住在下莱茵河流域和低地国家。盎格鲁人居住在丹麦南部。朱特人(the Jutes),如他们的名字所表明,居住在日德兰(Jutland)。恰好有一位凯尔特酋长,一位不列颠人,看见南部和西部都受到强盗的威胁,意识到可以让他们互斗。因此他召唤朱特人帮助他抵抗皮克特人。两位日耳曼酋长就是这时候出现的:亨吉斯特(Hengest),他的名字意为“雄马”;霍萨(Horsa),他的名字意为“牝马”。2
“日耳曼”则是一组部落的通用名称,这些部落各自有不同的统治者,说着相似的方言,而现代丹麦语、德语、英语等就源自这些方言。他们共有一些神话,但只有古代北欧神话流传至今,而且也只是在欧洲最遥远的地方:冰岛。我们根据《埃达》中保存的神话知道它们之间有某些联系:例如北欧神奥丁(Odin)是日耳曼神沃丁(Wotan)和英格兰神沃登(Woden)。3诸神的名字保留在一周日子的名称里,从拉丁文译成古英语:周一(Monday)是月亮(moon)日。战神(Mars)日,周二,是日耳曼战争和光荣之神的日子。信使墨丘利的日子则是沃登日,周三(Wednesday)。主神朱庇特(Jove)日是周四(Thursday),雷神托尔(Thor)日,这是他的北欧名字。周五(Friday)是美神维纳斯日;在日耳曼语中是弗丽嘉(Frija),在英格兰则是Frig。周六(Saturday)是农神萨杜恩(Saturn)日。主的日子——西班牙语是domingo,意大利语是domenica——则是太阳(sun)的日子,周日(Sunday)。
盎格鲁——撒克逊神话保留下来的很少。古代北欧人信奉瓦尔基里——女武神,能够飞翔,并且将死去武士的灵魂带往天堂;我们还知道英格兰也信奉她们,因为九世纪曾经有次审判,一位老妇人被指控信奉瓦尔基里。换句话说,基督教把这些用飞翔的马匹将死者带往天堂的女武士变成了女巫。旧时的诸神通常被诠释为魔鬼。
虽然日耳曼人并没有在政治上统一,但的确认可另一种统一:民族统一。因此异族被称为wealh,这在英语里变成了“Welsh”,意为“来自威尔士(Wales)的人”。Welsh在西班牙语里是galeses,这个词还保留在“加利西亚”(Galicia)或西班牙语galo中。也就是说,这个名称曾被用于指代任何不属于日耳曼民族的人……所以凯尔特人酋长沃蒂根呼唤皮克特族人来帮助他,但是等他们划动船桨——他们没有船帆——抵达肯特郡时,凯尔特人立刻发动战争,轻而易举地打败了他们。实际上胜利来得如此轻而易举,以至于他们决定侵略整个国家。这不能真的被称为武装侵略,因为征服几乎是和平地进行的。随即建立了英格兰第一个日耳曼王国,亨吉斯特为其统治者。接下来建立了许多小王国。同时,日耳曼人放弃了整个丹麦和日德兰南部地区,建立诺森布里亚(1)、韦塞克斯、伯尼西亚。因为罗马和爱尔兰修道士们的努力和召唤,所有这些小王国一个世纪之后全都皈依了基督教。起初这些努力是互补的,但很快就变成这两个地域的修道士们的对立竞争。这种精神征服有几个有趣的方面,第一是异教徒接受基督的方式。尊者比德讲述过一位国王有两个圣坛的事情:一个奉献给基督,另一个给魔鬼。4这些魔鬼无疑就是日耳曼人的神了。
现在我们来谈另一个问题。日耳曼国王是诸神的直接后代,不可能禁止一位酋长尊崇自己的祖先。因此,基督教教士的职责是记录国王的宗谱——有些流传至今——发现自己处于两难的境地:他们不想冒犯国王,同时也不想违背《圣经》。他们找到的解决办法的确很新奇。我们必须意识到,对于古人来说,“过去”并不会超过十五或二十代人:他们构想的过去不像我们构想的那么长。因此,追溯数代人,就与诸神有了亲缘关系,而诸神与希伯来族长有关系。因此,例如,奥丁的曾祖父是某族长的一位侄儿,由此就有了与亚当的直接关系。他们对过去的概念至多延至十五代,或者稍微多一点。
这些民族的文学跨越许多世纪,大部分都已遗失。因为尊者比德的缘故,我们将其开始的日子定于大约五世纪中期。从四四九年直到一〇六六年,即黑斯廷斯战役那年,这整个阶段只有四部主要手抄本和几种小作品留存下来。5第一部是《韦尔切利抄本》,二十世纪在意大利北部同名修道院里发现,是以盎格鲁——撒克逊语言写成,被认为是英国朝圣者在从罗马归国途中带到这里的,对我们来说幸运的是,他们把手稿忘在修道院里了。还有其他手抄本:《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一部波爱修斯作品译本,奥罗修斯的一部作品,法典,《所罗门与萨图恩对话录》。6就这些了。然后是史诗,著名的《贝奥武甫》,作品包含近三千两百行,表明也许曾经还有其他湮没的史诗。但这全都是假设。何况,考虑到史诗出现在短篇诗章激增之后且从中而来,如果认为这一史诗独一无二,那也是合乎情理的。
在所有情况下,诗歌都先于散文。似乎人们在开口说话前先唱歌,但这也有其他非常重要的原因。一行诗一旦拟就,就成为范例,被一再重复,然后我们就有了一首诗。另一方面,散文就要复杂得多,要求更多的努力。而且,我们还不应该忘记诗行有助于记忆的价值,因此在印度,法典都是以诗行的形式写成的。7我猜它们肯定都有些诗的价值;当然这并非以诗行来写的理由,而是因为以这种形式,就更容易记住。
我们必须仔细看看所谓“诗行”是什么意思。这个词的意思非常有弹性,对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而言,并非总是同一个意思。例如,我们想到了押韵或者等音节的诗行;希腊人想到了吟唱出来的诗行,特点是平行的结构,彼此平衡的词组。日耳曼诗行完全不是这样。很难找到决定这些诗行是如何组成结构的规律,因为在法典中,那些诗并非——不像我们的诗行——上下一行行写出来,而是连续书写的,而且也没有标点符号。但最后还是发现每行前三个单词的首音节是重音,并且押头韵。也发现了韵,但这只是偶然的:那些听这些诗歌的人很可能听不出来。我说那些听的人,因为这些诗歌旨在朗读或者吟唱,由竖琴伴奏。有一位日耳曼学家说,头韵诗行的好处是能形成一个单元。但是我们也必须提到它的缺点,那就是不允许诗节。的确,如果我们听见西班牙语中的韵,我们会因此期待有结尾;即,如果一个四行诗节的第一行结尾是-ía,然后有两个结尾是-aba的诗行,我们就会期待第四行诗结尾也是-ía。但是押头韵的情况下就不是这样。例如,在几行诗之后,第一行诗的声音从我们心中消失了,因此诗节的感觉也消失了。是韵将诗行聚集在一起。
后来,日耳曼诗人发现了叠句,有时也会用到。但是诗歌发展出了另外一种诗的分层手段,那就是隐喻语(kennings)——描述性、具体的比喻。8因为诗人总是谈着同样的事情,总是应对同样的主题——即,长矛、国王、剑、地球、太阳——因为这些词并非以同样的字母开始,他们必须要找出一个解决办法。如前所述,当时唯一的诗歌是史诗。(没有艳情诗。情诗要很久以后才会出现,在九世纪,随盎格鲁——撒克逊哀歌一起出现。)为这种诗歌——仅仅是史诗——他们组成了复合词来指代一些其名称不是以所要求的字母开头的事物。在日耳曼语言中,这种结构形成是很有可能的,很正常。他们意识到这些复合词能够很好地被用作比喻。以这种方式,他们开始称呼大海为“鲸鱼——路”、“船帆——路”,或者“鱼——澡盆”;他们称呼船只为“海——马”或者“海——鹿”或者“海——猪”,总是采用动物的名称;总的来说,他们将船只视为活物。国王被称为“民众的牧羊人”,而且——这肯定是因为吟游诗人的缘故,为了他们自己的好处——“赐予指环的人”。这些比喻,有些很美,被用成了套话。每个人都用,每个人都懂其含义。
但是,英格兰的诗人最后意识到这些比喻——我再重复一次,有些很美,例如称鸟为“夏日守卫”——会牵制诗歌,因此就逐渐放弃了。另一方面,在斯堪的纳维亚,他们将其用到了最后阶段:他们从比喻中创造了比喻,使用一连串的组合。因此,如果船只是“海——马”,海是“海鸟地”,那么船只就成了“海鸟地之马”。这能够被称为一级比喻。因为盾牌是“海盗之月亮”——盾牌是圆形的,木头制作——长矛是“盾牌之蛇”,因为长矛可以摧毁盾牌,因此那个长矛就是“海盗月亮之蛇”。
这就是诗歌如何进化得非常复杂和隐晦的例子。当然,这是发生在博学的诗歌界的事情,处于社会最高阶层。鉴于这些诗歌是朗诵或吟唱的,那就必须认定主要的比喻,那些作为基础的,是已经为受众所熟悉的。熟悉,甚至非常熟悉,以至于几乎与词本身同义。尽管如此,诗歌还是变得非常隐晦,以至于找出真实意思就好像猜谜,以至于接下来数世纪的抄写者表明——根据我们现有的同一些诗歌的抄写复本来看——他们并不明白其意义。这里有一个比较简单的隐喻:“死神啤酒的天鹅”,我们第一次见到时,不知道该如何解释。所以,如果将其拆分,就会看到“死神的啤酒”意为血,而“血的天鹅”意为死神之鸟,即“乌鸦”。在斯堪的纳维亚,整首诗都是这样写就的,越来越复杂。但是这种情形并没有在英格兰发生,比喻只停留在第一个层面,没有继续下去。
至于头韵的用处,有趣的是一行诗即使包含了以不同元音开始的重音词,也被视为押头韵。如果一个诗行包含具有元音a的词,另一个词具有e,还有另一个具有i,它们就是押了头韵。实际上,我们并不确切知道在盎格鲁——撒克逊语言里,元音是如何发音的。毫无疑问,古英语比今天的英语有着更加开放的声音,更强的发音。如今在英语里,辅音成为音节的重点,相反,盎格鲁——撒克逊语或古英语——这两个词同义——是非常元音化的。9
另外,盎格鲁——撒克逊词汇是完全日耳曼的。在诺曼征服之前,唯一另一个重要的影响是从拉丁文引进了约五百个词,这些词大多是宗教用词,或者如果不是宗教用词,那就是用来指称此前在这些民族中不曾存在的概念。
至于日耳曼民族的宗教皈依,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因为信奉多神教,接受另外一个神不存在问题:再多一个也没什么。对于我们来说,要让我们接受多神异教是很困难的,但是对于日耳曼民族而言,并非如此;起初基督只不过是一个新的神而已。而且,皈依也没有什么问题。皈依当时并不像现在是个人的行为,事实上,如果国王皈依了,整个民族就皈依了。
有些词在盎格鲁——撒克逊语言中找到一席之地,因为它们代表了新的概念,例如,“皇帝”这样的词,这是他们从前没有的概念。即使现在,同一含义的德语词Kaiser,也出自拉丁词caesar。日耳曼民族实际上非常熟悉罗马,他们认可其为更高级的文化,推崇它。这就是为何皈依基督教意味着皈依更高级的文明;无疑它有着无可争议的魅力。
下一堂课我们要来看看《贝奥武甫》,一首出自七世纪的诗,最早的史诗,早于九或十世纪的《熙德之歌》以及比《熙德之歌》与《尼伯龙根之歌》早一个世纪写成的《罗兰之歌》。10这是全欧洲最早的史诗。然后接下来我们会谈到《芬斯堡之战》片段。
(1) Northumbria,位于今英格兰北部和苏格兰东南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