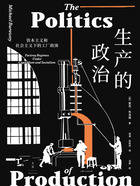
中文版序1
能得到邀请给35年前出版的《生产的政治》一书的中文版写序言,这让我感到十分荣幸。这样一本年代久远的著作还有什么价值?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它变得不过时?书中的思想是否能被延展到当下的现实中?
让我们首先回到1985年。那时,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社会科学中正迎来一次复兴。我坚定地支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议程——今天依然如此,但却不是以一种机械或教条的方式,将马克思或其他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著述看作是永恒的真理。我认为,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不断地重构马克思主义,使其能够解释持续变动世界中那些原先不能被解释的异例。如果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的变化会导致观念的变化,那么马克思主义自身也要不断发展。如果马克思主义试图为世界的变迁提供某种指导,那么随着世界的改变,马克思主义自身也要改变。一个跨院系、跨学校、跨国界的马克思主义者群体应当发展起来,这个群体的使命便是不断重构马克思主义,使其能够回应时代提出的挑战。在不同的地方,这个群体关心的议题不同,依靠的马克思传统源流也不同。在有些地方它更偏向理论,在另一些地方它更看重实践。
在美国,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更多地限于学术界之内,尤其在社会学中积累起不小的能量。在马克思主义者试图解答的问题中,有两个问题尤其吸引了大量关注和精力。第一个是关于工作的组织,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劳动过程。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的《劳动与垄断资本》(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一书尤其激发了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兴趣,并带我们重新回到了《资本论》第一卷(Capital, Volume 1)。布雷弗曼考察了劳动过程在一个世纪以来的变迁,认为工作形态变迁的轨迹体现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概念和执行的分离,这使资本家获得了更多控制力和利润。通过工作的去技能化,资本能更为有效地规制工作过程,同时降低劳动成本。第二个问题聚焦于国家及其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对这一问题的兴趣,是被拉尔夫·米利班德(Ralph Miliband,他将国家看作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和尼科斯·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他将国家看作是具有相对自主性的一种结构,是保护资本主义既不被资本家破坏也不被工人破坏的必要条件)之间的辩论推动起来的。
《生产的政治》一书试图将这两方面的问题连接起来。我试图同时向劳动过程理论和国家理论提出挑战。对于劳动过程理论而言,我的贡献在于指出生产场域除了工作本身之外同样也是政治场域,其自有一套规制模式,形塑了生产环节与其他环节的斗争。对于国家理论而言,我的贡献在于指出国家并不是唯一的政治场域,生产场域的支配关系恰恰是国家有效运作的必要条件。换句话说,生产领域的政治是塑造国家与劳动过程之间关系的重要环节。我进一步指出,这一生产的政治有其自身的“内部国家”,或者说“生产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机构”,它既是阶级斗争所形塑的对象,也在规训和限制着阶级斗争。
概念创新始于理论与实践的交汇处。在芝加哥大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训练之后,当时还是博士研究生的我在南芝加哥的阿利斯-查默斯工厂(Allis-Chalmers)找到一份机械操作工的工作。这个工厂是美国三大农业和建筑设备制造商之一。这既是我博士论文研究的对象,也是我生计的来源。在那个年代,有工会组织的蓝领工人拿的薪水不亚于一名大学助理教授。如果算上加班工资,我比我的一些老师们挣得还多。
在工厂中,我惊讶于工友们在工作时是多么努力,并感到很纳闷:为什么他们如此努力地为资本家的利润卖命?虽然布雷弗曼描绘了工作的组织结构在客观层面发生的变迁,但他并没有分析工人在主观层面对此有何反应。既然去技能化的工作如此没有意义,工人们为什么还工作得那么努力?我所看到的情况似乎和马克思在19世纪描绘的情况不同:驱使工人努力工作的动力,似乎并不是经济层面的市场强制力量或是对失去工作的恐惧。这一动力也不像经济学家们说的那样来自奖金等物质刺激。我在1979年出版的《制造同意》(Manufacturing Consent: Changes in the Labor Process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一书中所讲的故事要更加复杂。工作场域中的客观限制并不像布雷弗曼预设的那样令人窒息,而是为工人们留出了自己为工作赋予意义的空间。为了减轻工作时的辛苦感和无聊感,工人们将工作建构为一种游戏,这种游戏有自己的规则,被工人们共同认可和执行。
但生产场域包含的不只是工作本身。一系列规制机构为赶工游戏确立了条件。三种规制机构对确保工人努力工作而言尤其重要。首先是内部劳动力市场,其允许工人竞争空余岗位,一般是资历最老、相关经验最丰富的工人胜出。这样一来,工人们在工厂中待的年头越久,在厂内的位置也越高,工资也就越高。其次,工人们被建构为拥有权利和义务的个人主体,这些权利和义务靠申诉机制执行。如果管理方违反了集体谈判合同中的条款,工人们可以通过工会层层向上发起申诉。最后,工会代表工人和资方进行集体谈判,视工厂的盈利情况而争取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福利待遇。不管是在个人层面还是集体层面,工人们都有充分的理由努力工作,而无需强制的持续干预。
我借鉴了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用来分析宏观政治的“霸权”这一概念,将我所看到的景象称作霸权式的生产政体,这一政体将工人对资方的认同组织起来。我指出,这一生产政体是区分发达资本主义和早期竞争资本主义的主要因素。高薪、高福利、工作稳定性这几个条件加在一起,使得管理者不可能再用强制手段逼迫工人努力工作,他们必须说服工人努力工作。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事情很快就会发生重大转变:在国家的引领下,资本家向工人阶级展开进攻,使得工人与工会屈服于市场,一种新的生产政体即“霸权专制主义”出现了。我在《生产的政治》中提出了这一预想。
我的批评者们笑了起来:你只不过是研究了一家工厂,如何将结论推广到整个发达资本主义?这个问题使我开始对不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政体做比较研究。瑞典、日本、英国的生产政体都是霸权政体的变种,其具体类型取决于国家对生产的规制及其在生产场域之外提供的福利。为了确认各种霸权政体的共同特征,我将其与马克思笔下的19世纪专制生产政体比较。我的研究显示,在马克思所描绘的专制政体之外,还有其他类型的专制生产政体。专制生产政体的具体类型,一方面取决于劳动过程,另一方面取决于19世纪的国家形态。从历史文献中,我发掘出一系列存在于美国、英国、俄国早期纺织业中的市场专制生产政体:企业国家、父权制、家长制等政体,并试图理解这些生产政体得以存在的条件及其对形塑阶级斗争的后果。
我的批评者们再次笑了起来:这与资本主义无关,不过是工业化导致的结果罢了。我因而重新审视了自己早先(1968—1972年)对赞比亚铜矿行业所做的研究,并指出这一行业中存在另外一种专制生产政体,即一直持续到后殖民时期的殖民专制政体,或者说殖民主义在后殖民时代的再生产。可我的批评者们还是不满意:非洲的工业化进程本来就落后。这样一来,我非常清楚自己必须要做什么: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工厂,并揭示其中的生产政治与资本主义社会有本质不同。我一直很想去中国做研究,但我知道这超出我的能力范围。另外,我对1980—1981年的波兰团结工会运动十分着迷,这个运动就像突然冒出来一样,尝试去重构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我收拾好行装打算去波兰,但还是晚了一步——雅鲁泽尔斯基将军(Wojciech Jaruzelski)行动得比我更早,他在1981年12月13日宣布戒严。团结工会转入了地下,直到1980年代末以一种完全不同的面目重新出现,参与到有关资本主义转型的谈判中。
在我不得不向团结工会说再见之后,我的朋友、也是我未来的同事塞勒尼(Iván Szelényi)邀请我陪他于1982年夏天去匈牙利,这帮了我大忙。这也是塞勒尼自1976年开始政治流亡之后第一次返回匈牙利。在此之前,米克洛什·哈拉兹蒂(Miklós Haraszti)对匈牙利一家机械工厂中种种磨难的动情记录早已激起了我的好奇心[1]。在他的笔下,机械操作工完成的工作对我而言看起来根本不可能:同时操作两台机器。这是为什么?我之前一直以为,如果说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争取到了什么权利的话,那就是不用辛苦工作的权利!和塞勒尼同去匈牙利的十天震撼了我的世界。在此之后,我决定在匈牙利开启我的下一段研究旅程。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在社会主义工厂中找到工作——那是工人国家中的神圣领地,即使对本国的研究者也是严防死守,更别提来自外国的持批判态度的马克思主义者了。但当时正值匈牙利的改革年代,我还是无所畏惧地在1983年的夏秋之季前往匈牙利做研究。靠着朋友们的帮助,我在一家香槟工厂和一家合作社的纺织工厂找到工作。接着,我在1984年进入一家机械工厂,那家工厂与南芝加哥的阿利斯-查默斯厂以及哈拉兹蒂笔下那家布达佩斯的工厂都颇为相似。我之后又从那家机械工厂跳槽到了米什科尔茨(Miskolc)的列宁钢铁厂(Lenin Steel Works),这家工厂堪称匈牙利工人阶级的心脏。在1985—1988年间,我有三段时间在这家工厂当熔炉工。
所以我是这样回应我的批评者的:国家社会主义造就了一种独特的生产政治——官僚化的生产政治,资方、工会、党组织作为国家的延伸部分在其中相互合作。这种官僚化生产政体处于一种独特的生产过程和一种独特的国家形态之间,带来了非常真实的后果。与资本主义经济体时常陷于系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不同,国家社会主义经济体面对的危机来自于短缺:劳动力、原材料、机械设备等等的短缺。为了应对具体生产过程中短缺造成的困难,就需要一种灵活的工作组织形式,需要工人对生产过程至少有某种程度的集体控制权,虽然时常会遭到武断的官僚管理的阻挠。
在生产过程之外,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形态又是怎样的呢?与惯于将剥削过程神秘化(模糊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同,国家社会主义之下的剥削过程是非常透明可见的,因此需要被正当化(合法化)。所以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国家比在资本主义国家要重要得多。与其他国家一样,社会主义国家也宣布,国家代表所有人的共同利益,社会主义是高效和平等的,但在一些国家,工人们实际看到的是遍地的低效和不平等。工人所做的其实不外乎是呼吁国家兑现其做出的承诺。通过揭露国家的言行不一,工人拥抱了一种社会主义的批判立场。合法性的失败导致集体抗争行动时常爆发,并在一些情况下导致国家公开使用暴力。在国家社会主义之下,强制与同意在历史中不断交替;而在资本主义社会的霸权生产政体中,强制与同意共存,强制保证同意的实现并且自身也是同意的对象。
我原以为这一动态中孕育着民主社会主义的未来可能性,那种可能性是我在团结工会所发起的革命中直观感受到的,虽然团结工会运动自己给自己施加了许多限制。但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匈牙利工人对社会主义话语的运用只是表面现象,他们对任何社会主义未来的犬儒心态要根深蒂固得多。他们对社会主义现实的批判将他们引向了资本主义,而非民主社会主义。当国家社会主义在1989年崩溃时,有工人试图重建1956年匈牙利革命时曾出现的那种工人委员会,也有工人试图掌管工厂,但这些毕竟是工人中的少数。大多数工人都愿意在资本主义中找找机会,并没有意识到这其实意味着工厂的关闭、福利保障与社会安全网的泯灭、免费教育的消失和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的终结。我的匈牙利工友们当时并未意识到共产主义正在成为“辉煌的过去”——这正是1992年我与亚诺什·卢卡奇(János Lukács)合作出版著作的标题(1)——也没有意识到他们在共产主义的生活要比在资本主义好许多。
到了1990年,匈牙利明显在全力奔向资本主义,所以我去了苏联,当时正是苏联改革年代的黄昏时刻。要想进入苏联那隐蔽的生产场域并不容易,但我最终和亨德利(Kathryn Hendley)一起进入了雷齐纳工厂(Kauchuk i Rezina),那是一家位于莫斯科的著名橡胶厂。[2]苏联的生产政治和匈牙利又是不同的。我们目睹了工厂中正在进行的内战:总工程师和总经理支持苏维埃计划体制和苏联的完整性,而年轻的工程技术人员支持市场经济和俄罗斯独立,叶利钦是他们的英雄。双方阵营的领袖都试图说服基层工人,获取工人的支持,其间上演着各种戏码。这是1991年的年初,凄冷的冬天和整个国家的经济混乱正在制造前所未有的短缺。与匈牙利一样,苏联的企业管理者也用各种方式给自己找后路:剥离仍在盈利的合作社,免费拿走企业的资源,或是通过搞副业牟利。
在这至关重要的一年,我在4月去了北极地区,到了我的朋友克罗托夫(Pavel Krotov)的家乡——科米共和国(Komi Republic)的首府瑟克特夫卡尔(Syktyvkar)。我们一起潜入了北方家具厂,这是一家生产壁橱的年轻企业。我成为一名机械操作工,而克罗托夫主要负责和管理者接触。与雷齐纳工厂不同,北方家具厂得益于对产品和原材料的垄断以及靠近消费者的优势,因此境况很不错。他们通过以物易物,用生产的壁橱换取肉、酒(当时正处于严格的配给制中)、糖以及子女在南方参加夏令营的名额。[3]我在6月离开了那里,而到了年底,苏联就不复存在了。当我下一年回到这家工厂时,这里境况惨淡。
似乎我每到一个地方,就给那里带去了灾难。1968年,当我开始在赞比亚的铜矿工作时,铜价保持高位,整个产业十分繁荣。但在我1972年离开之后,铜价马上就开始下跌,一直跌了20年。经历了国有化的铜矿产业陷入困境,赞比亚被迫进行结构性调整,最终不得不将铜矿重新私有化,而不幸的是,在这之后铜价马上开始回升。1973—1974年,当我在阿利斯-查默斯厂做工时,厂子情况很不错,堪称模范工厂。但当我离开之后,衰败就开始了。1986年,厂子倒闭,成为了南芝加哥城市衰败的一部分。那片区域成为贫民窟,聚集着大量因公共住房被拆毁而流离失所的非裔美国人。列宁钢铁厂以及俄罗斯的整个工业图景最终都落入了同样的命运。我觉得自己最好还是不要去任何还没有去过的国家了。在接下来的十年,我一直在瑟克特夫卡尔做研究,见证了苏维埃经济的毁灭和工人的苦难——这是在和平年代从未出现过的大衰退。我对生产政治的研究转向关注家庭,因为在当时,家庭、尤其是家庭与国家之间的联系,成为人们赖以维系经济生存的关键。[4]
当我开始研究国家社会主义时,我试图寻找一种独特的生产政治。但当我找到这种社会主义的生产政治之后,它马上就解体了。我的批评者们对我说:我所找到的例外恰恰证明了他们的法则。一切都会朝着资本主义趋同,国家社会主义无法持续。但他们显然忘记了中国!中国的崛起和苏联的衰退一样迅猛。通过我的学生们的研究工作,我见证着中国的经济发展。沈原教授时常邀请我去中国,但他严禁我接近任何工厂。虽然工业生产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转型后的苏东国家不断消失,但在中国却不断扩张,这让《生产的政治》焕发了新的生命。中国善于吸引外资,并积累起自己的工业资本,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着在移民工人的基础上建立起新型的官僚化专权生产体制而实现的。
我关于中国的知识,局限于一些考察中国生产体制的英文著作和博士论文,而不是我自己的一手观察。在这些研究中,潘毅对这一生产体制之下工人生存状况的描写尤其动人,[5]而李静君则通过比较华南地区的生产体制与香港的生产体制来阐明前者的性质,并犀利地批评我忽略了生产政体的性别维度。[6]在李静君2007年出版的下一本著作中,她比较了中国的沿海工业区和内陆老工业区,将前者的性别权威生产体制与后者的企业权威生产体制进行对比,并分析了与两类生产体制对应的斗争类型。[7]而正如程秀英所指出的那样,生产政治也会被导向法律场域,抗议者在这个高度官僚化的迷宫中晕头转向——这塑造了一种转移注意力的生产制度(diversionary production regime)。[8]
中国政府明白的事情恰恰是俄罗斯的高级干部们不明白的:成功的市场转型需要一系列法律、社会与政治层面的支持结构。党和国家体制不应被摧毁,而应被重新构建,以监管和控制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9]与中国的演进道路不同,俄罗斯的精英们梦想以一种布尔什维克的方式迈向资本主义:用一种革命的方式将一切与共产主义有关的事物破坏殆尽。他们觉得,只有在七十年的共产主义遗产全被破坏的时候,市场经济才能焕发生命力,就像浴火重生的凤凰一样。但事实上,以纯粹的市场化道路通向市场经济谈何容易。
当我在俄罗斯北部时,见证了沃尔库塔(Vorkuta)的矿工正和西伯利亚、乌克兰的矿工一道发起罢工,将体制逼入崩溃边缘。在撕毁了党章并建立了他们自己的自治生产政体之后,工人们发觉资本主义对他们生产的昂贵煤炭并不怎么感兴趣。煤矿一个接一个地倒闭,这可是全世界煤炭储量最丰富的煤田之一,如今却开始陷入衰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问那些留下的人们。他们答道:“这说明你不能在七十年的共产主义基础上建设资本主义。”不论大家名义上怎么说,俄罗斯的资本主义转型事实上不是革命性的,而是内卷性的。交换没有刺激经济扩张,而是阻碍了生产,形成一个“去原始积累”的过程——关厂、资产剥离、人们倒退回自给农业中。这不是波兰尼(Karl Polanyi)所说的大转型,而是一场大内卷。[10]俄罗斯花了很长时间才止住急速衰落并开始复苏,大大落后于经济扩张中的中国。
随着中国的增长机器势头强劲,它也为自身的转型埋下了种子。通过将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丢到以家庭自给农业为主的农村地区,整个劳工迁徙系统使廉价劳动力成为可能。[11]在中国,户口制度使移民工人家庭无法在城市定居,而是鼓励单身男女工人迁徙并在建筑业与制造业寻找工作。这一生产政体使得工人无法脱离与农村地区之间的联系。在农村地区,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的农村改革负担了照护老人与儿童的主要成本,而地方政府则负责养老与教育。随着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超出了沿海工业所依赖的劳工迁徙系统。随着农村地区发展出一种新的积累模式,许多农村居民被迫离开农村、迁入拥挤的巨型城市,这也给户口制度带来了重重压力。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负担对财政的压力过大,使得农村基层政府开始寻找新的财源。获取新财源的一种做法是创建新的产业集群式工业区。胡丽娜考察了河北省的一个工业区。在那里,以家庭为单位的“工厂”生产着行销全球的箱包。[12]茱莉亚·庄(Julia Chuang)2020年出版的著作则研究了四川省以建设新城为目的的农村土地征收和交易。[13]这一基于土地商品化的新积累模式正在逐步取代基于移民劳工的旧模式。
随着中国内部的工业发展不断推动消费品与资本品的出口,中国也开始到境外寻找原材料供应渠道。李静君跟随着中国资本来到赞比亚的铜矿[14]——巧合的是,那些铜矿恰恰就是我四十年前研究过的。中国试图将其独特的生产政体移植到非洲,激起了赞比亚矿工的斗争。在赞比亚矿工眼中,这一生产政体看起来就是殖民专制主义的重演。但赞比亚政府很快意识到,与那些流动性更高、在铜价下跌后马上开始外逃的跨国私人资本相比,还是中国资本更能使他们获益。中国资本之所以没有外逃,是因为它不仅对利润有需求,而且对铜本身有大量需求,因此它和赞比亚政府之间建立了一种合作关系,以规制生产政体,保证铜产量的稳定,虽然这种合作关系既不顺利也不平等。
在跨国比较中,我强调了国家如何创造、破坏、维护以及不断规制生产政治。但在劳动过程一边,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我们如何分析零工经济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种新的工人类别——那些使用自有的生产资料来为消费者提供服务的独立承包工人?奇怪的是,关于游戏的观念越发根深蒂固了。[15]在隐藏于平台之后的管理者所提供的激励背景下,零工经济的工人组织起他们自己的游戏。实际上,软件工程师成了游戏化的专家。和原来一样,游戏诱使工人展开竞争,但这不是相互之间的竞争,而是自己和自己的竞争,生产力就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提高。[16]这些游戏瞬息万变,不断变化的算法随时召唤着新的策略。在不稳定用工的时代,这种工作吸引着那些寻找额外薪水、希望按照自己的时间安排来灵活决定上工时间的兼职工人。这是生产政治的原子化:不可见的管理者,不可见的工友,以及一系列匿名的顾客。[17]
但维系着零工经济的,其实是一种我们更加熟悉的劳动过程。正如舍斯塔科夫斯基(Shestakofsky)在2017年发表的研究所揭示的那样,创造激励系统、招募工人、吸引顾客,这一系列过程不仅需要软件工程师,也需要大量劳动力提供计算劳动和情感劳动,这些劳动过程是在全球层面被组织起来的。[18]自动化的神话再一次被刺破。这些劳动过程服务于大企业的总部,而大企业则服务于风投资本的逻辑。风投资本首先希望看到的,是企业能够存活并且将来能够盈利的证据。在企业发展和扩张的每个新阶段,软件工程师都需要重新设计那些决定劳动服务关系的算法。
零工经济的核心是手机。手机已经变成了我们这个时代具有象征性的生产工具,成了我们自己的一部分,对我们的存在而言越发重要。它不仅在我们的生活中不可或缺,而且记录着我们的每一次移动、每一次消费、每一次通讯和我们点击的每一个“赞”和“踩”。正如祖博夫(Shoshana Zuboff)所描述的那样,我们自身与劳动过程融为一体,自发地、充满激情地生产着数据。这些数据被整合、分配,反过来用以监控我们的生活,政府或企业也通过挖掘和利用这些数据来获利,不论是靠监视我们还是靠精准投放广告。[19]布雷弗曼所说的概念与执行的分离达到了顶点,从而创造出一种新的生产政治。在这种生产政治中,生产过程变成自我诱导或者由企业诱导的游戏,生产过程与其规制手段融为一体,像福柯所说的全景监狱一样无缝运转。这种原子化的生产政治与政治狂热高度适应。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特朗普主义,在这种政治生态中,推文就是无法被证伪的真理。这一逻辑在社会运动的组织当中同样重要,不论社会运动有何种政治色彩。
我和我的手机为谷歌、亚马逊、阿里巴巴、微软和苹果创造利润,同时为一种新的经济提供基础。然而这里依然存在着一种劳动过程背后的劳动过程,一种生产政治背后的生产政治:典型的例子便是苹果在中国的准军事化工厂,成千上万的工人在学徒制度的规训下生产着苹果手机。
但任何革命都是有局限的,数字革命也不例外。这一点在应对新冠疫情的过程中变得尤其明显。关键部门的工人——护士、医生、百货店的店员、学校教师、司机、农业工人、家政工人、肉类包装工等等——需要将自身的生命置于险境,以保证我们其他人能够活下去。这些工人无法居家工作,而是必须到他们原来的工作场所中,与客户、消费者、病人面对面接触,不论他们是否获得了足够的防护设备。他们组成了一个下层阶级,往往被他们的种族、性别与公民身份标识出来。他们本就是最不稳定的工人,无法承受不去上班的后果,所以在病毒面前他们所承受的风险最大。具体的劳动过程也许还和原来一样,但其规制模式已经发生改变,变得更具有强制性,不管是以潜在还是外显的方式。
一种新的阶级结构正在形成当中:通过远程通讯工具居家办公的职业群体与那些必须出现在危险的工作场所中的一线工人之间正在形成区隔。布雷弗曼所说的概念与执行的分离正在固化为阶级区隔,或者说一种潜在的阶级对立。在美国,这一阶级区隔开始和党派政治交叠。数字化正在为一场新的阶级战争打下基础,这一阶级战争正在不时地爆发出来:教师的抗争、平台工人的抗争、租户的抗争、巴士司机的抗争以及反对警权的抗争。劳动和生活已经变得不可分割。
但数字化也使我们得以想象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一个工人集体自我管理的未来世界。在这一图景中,必要的工作在社会全部成员中通过平等合作实现均匀分配,以此缩短工作时间。这种集体自我管理正是在瘟疫时代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必要条件,也是我们的唯一出路。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只要资本主义还在,它就永远激励着人们去探索社会主义的理念。
2020年12月
1 本书方括号“【】”内数字为原书页码,以下同。
[1] Miklós Haraszti, A Worker in a Worker’s State, Harmondsworth, England: Penguin Books, 1977.
(1) 此处指《辉煌的过去》(The Radiant Past: Ideology and Reality in Hungary’s Road to Capitalism)。——编者注
[2] Burawoy and Hendley, “Between Perestroika and Privatization: Divided Strategies and Political Crisis in a Soviet Enterprise”, Soviet Studies, 1992, 44(3), pp. 371-402.
[3] Michael Burawoy and Pavel Krotov, “The Soviet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 to Capitalism: Worker Control and Economic Bargaining in the Wood Lndustr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2, 57(1), pp. 16-38.
[4] Michael Burawoy, Pavel Krotov and Tatyana Lytkina, “Involution and Destitution in Capitalist Russia”, Ethnography, 2000, 1(1), pp. 43-65.
[5] Pun Ngai, Made in China: Women Factory Worker in a Global Worplace, Durb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6] Ching Kwan Lee, Gender and the South China Miracl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7] Ching Kwan Lee, Against the Law: Labor Protests in China’s Rustbelt and Sunbel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8] Xiuying Cheng, “The Circular State-Symbolic Labor Politcs in Transitional China”,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2010.
[9] Michael Burawoy, “The State and Economic Involution: Russia through a Chinese Lens”, World Development, 1996, 24(6), pp. 1105-1117.
[10] Michael Burawoy, “Transition Without Transformation: Russia’s Involutionary Road to Capitalism”,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2001, 15(2), pp. 269-290.
[11] Michael Burawoy, “The Functions and Reproduction of Migrant Labor: Comparative Material from Southern Afric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6, 82(5), pp. 1050-1087.
[12] Lina Hu, “Familial Politics of Production: Household Production in China”,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2013.
[13] Julia Chuang, Beneath the China Boom: Labor, Citizenship and the Making of a Rural Land Market,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20.
[14] Ching Kwan Lee, The Specter of Global China: Politics, Labor, and Foreign Investment in Af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7.
[15] Tongyu Wu, “Brogrammers, Tech Hobbyists, and Coding Peasants: Surveillance, Fun, and Productivity in High Tech”,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Oregon, 2018.
[16] Griesbach, Kathleen, Adem Reich, Luke Elliott-Negri, and Ruth Milkman,“Algorithmic Control in Platform Food Delivery Work”, Socius, 2019, 5(1), pp. 1-15.
[17] Milkman, Ruth, Luke Elliott-Negri, Kathleen Griesbach and Adem Reich,“Gender, Class, and the Gig Econmy: The Case of Platform-Based Food Delivery”, Critical Sociology, 2020, 47(3), pp. 357-372.
[18] Benjamin Shestakofsky, “Working Algorithms: Software Automation and the Future of Work”, Work and Occupations, 2017, 44(4), pp. 376-423.
[19] Shoshana Zuboff, 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The Fight for a Human Future at the New Frontier of Power,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19.